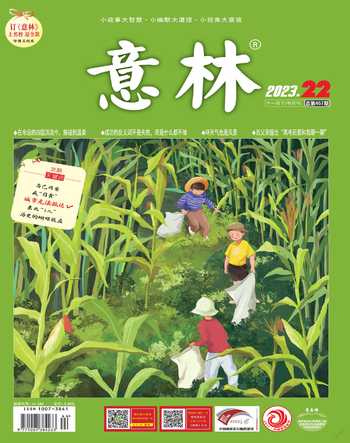當父親提出“高考后要和我聊一聊”
周冀

前不久,作家王欣在微博上發(fā)文感嘆,母親竟能熟練運用各種互聯(lián)網(wǎng)工具獨自規(guī)劃出游。這條微博的評論區(qū)內(nèi),網(wǎng)友紛紛曬出自己的“驚喜父母”。我仔細回憶與父親的過往,好像沒法兒在他身上找出這樣的驚喜,但相似的“反轉(zhuǎn)”有跡可循。
小時候,父親永遠是拒絕遷就我的一方,在某些方面有自己“頑固”的原則。舉例來說,高三以前,除非身體抱恙,他每周必須拉著我打一次羽毛球,我屢次抗議未果。后來,我習慣了在小事上默認他的決定,避免爭執(zhí)。但整個中學時期,因為自己的未來規(guī)劃與父親期待的并不一致,還是下意識把父親當成“假想敵”,認定高考之后必有一場“惡戰(zhàn)”。所以,當父親提出“高考后要和我聊一聊”,我如臨大敵,在腦海里預演了無數(shù)次“劍拔弩張”的場面。
那天,父親拿上他裹著棕色皮套的筆記本,喊我去陽臺的藤椅上坐坐,還罕見地泡了兩杯茶。他習慣直來直去,不看重所謂的“儀式感”,與人協(xié)商決議常是隨處一坐,高效解決,這一系列“興師動眾”的籌備工作讓我隱約感到了這場談話的特殊性。
4個小時的長談由高中以來貫穿于我們所有交談的問題開啟:“還是想學寫作相關的專業(yè)嗎?”我再次給出肯定的答案,父親卻一反常態(tài)地不再強調(diào)如此的風險,反而對我說:“這問題我反復問你,是不希望你將來為自己草率地作選擇后悔。但寫作你喜歡了十幾年,這已證明你足夠堅定。”這一輕描淡寫又重于千金的應允讓我預先籌劃的“反擊”霎時失去了意義。我正愣神兒,父親利落地從筆記本中撕下三頁,遞到我手里,上面密密麻麻地寫著后來談話涉及的種種話題,和我生活中與之對應的細節(jié)。
在“堅持鍛煉”的話題旁,父親完整列下了我18年來嘗試過的所有運動和每項運動的堅持時間,我瞥到時心中暗暗吃驚。
那次長談讓我在父親身上看見了此前從未發(fā)覺的包容與細膩。這種反差像偶然漏出的光,借由它,我開始重塑父親的身影。過去,成見讓我將他困在“監(jiān)護人”“獨裁者”的形象中,認定他只想按照自己的心意編織子女的人生。可仔細回憶,高二我提出獨自外出旅行,常嬌慣我的母親猶豫不決,反倒是父親,選擇信任我的自理能力,坦然放手。
前段日子聽的播客中提到,被困在時間中的“留守父母”,面臨著跟不上時代思潮的困境,而子女需要成為他們的一座橋梁。可某種程度上,回到小家的生態(tài)里,我們很多人又何嘗不是“留守子女”?當我們走進更大的世界,對小家的關心愈來愈少,本應隨時間更迭的記憶出現(xiàn)一個個斷口;又或者,因為始終“留守”在自己的偏見里,盲視父母與偏見不符的行為,在心里為他們搭建片面的形象。
發(fā)現(xiàn)“驚喜父母”的時刻,斷口被光呈現(xiàn)、填補,偏見被擊碎。但這種反轉(zhuǎn)、頓悟式的體驗也帶給我們省思,伴隨它們而來的可能是驚喜,也可能是遺憾。正如電影《曬后假日》中,已為人母的蘇菲回憶起童年與父親的那次土耳其之旅,終于明白父親當年復雜苦澀的心境,卻為時已晚。
無論父母還是孩子,在對方身上看到出乎意料的一面時,若感到的是驚喜,便是幸運的。我們也不應只讓這驚喜成為剎那的火花,而應以此為契機,思考我們過往在親子關系中是否有怠惰疏忽,以此重建或促進親子間的親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