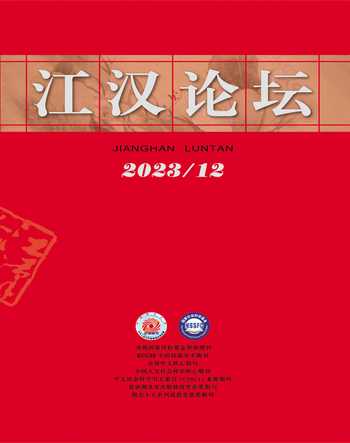論馬克思對印度與中國的跨文化研究
摘要:在東方各國中,馬克思最關注的是印度與中國。馬克思曾經以研究印度社會而得出的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特征,置于“古代的、封建的”之前,作為比較原始的社會形態。我們既不能像斯大林的“五形態說”那樣完全忽略亞細亞生產方式,又要看到以亞細亞生產方式套用中國古代社會所造成的缺憾:馬克思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從對于印度社會的分析得來的,鑒于中國社會與印度社會的巨大差異,很多關于印度社會的特征是不能套在中國社會之上的;然而,我們又不能忽略其中精辟深刻的理論論述。同時,我們還要提防有些西方學者借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研究對中國的歷史與現實進行惡意的攻擊。馬克思對于印度社會的歷史與文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因而我們認為賽義德在《東方學》中將馬克思關于印度研究的東方學視野看成是歌德等文化先輩建構出來的結果,是一種對馬克思的誤讀,而對于馬克思的準確解讀,需要了解馬克思在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之間的張力。即馬克思在歷史主義的層面上充分肯定英國侵略者摧毀印度的充滿田園牧歌情調的愚昧專制的歷史進步性;而從倫理主義的角度看,馬克思是永遠站在被壓迫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立場上說話的,因而賽義德站在被壓迫的東方立場反抗西方建構出來的學術暴力,反而與馬克思主義的倫理選擇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值得注意的是,與馬克思對印度社會的歷史與文化分析相比,馬克思對于中國的社會現實更感興趣,而且馬克思更同情中國。在英國侵略者與中國之間,馬克思激烈地抨擊侵略者,同情中國人民。而且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前夜,馬克思就意識到了中國將發生均貧富的革命,認為中國具有濃厚的社會主義土壤。這也許就是后來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基因。
關鍵詞: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印度;中國;跨文化研究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恩格斯與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16BZW014)
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854X(2023)12-0005-10
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努力方向。重讀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是實現“兩個結合”的題中應有之義。翻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們會發現在繁多的東方國家中,馬克思論述印度與中國者最多,表明經典馬克思主義對東方國家的關注。耐人尋味的是,日本人向來自我感覺良好,加上近代以來是東方開國較早的國家——日本明治維新之時,正是馬克思出版《資本論》的時代,然而馬克思卻很少論及日本。馬克思普泛地使用“東方”或“亞細亞”的概念時,主要是指印度和中國,然而,仔細研讀馬克思關于印度與中國的論述,就會發現這樣一個悖論:印度文化不重視歷史,然而馬克思卻更多研究印度的歷史文化;中國文化特別重視歷史,但是馬克思卻更關注中國被列強凌辱的現實。馬克思對于東方的關注先是印度后是中國,然而,他對中國比對印度更有感情,他對于中國的預言后來也都成為現實。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馬克思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從對于印度社會的分析得來的,鑒于中國社會與印度社會的巨大差異,很多關于印度社會的特征是不能套在中國社會之上的。過去我們的理論界忽視了這一點,仿佛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既適合解釋印度社會,也適合解釋中國社會。既然“亞細亞生產方式”是馬克思研究東方社會的重要成果,那么我們的研究就先從“亞細亞生產方式”切入。
一、馬克思對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跨文化研究
馬克思跨文化研究的重大成果是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研究。因為這個問題不單純是東方個別國家的問題,而是東方社會的普遍問題,甚至是人類社會發展鏈條的問題。不過,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共產黨宣言》等著作中,馬克思還沒有注意到東方社會。1853年6月馬克思寫作《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同年7月寫作《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開始關注東方社會在經濟與社會上的獨特性。
馬克思于1857年10月到1858年5月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在《資本章》第二篇《資本的流通過程》第二節《資本主義生產以前的各種形式》中有《亞細亞的所有制形式》等小節,將“亞細亞的所有制形式”放在“古代的所有制形式”之前,認為“亞細亞形式”的特征是:第一,以鄉村公社為基本單位,“單個人對公社來說不是獨立的,生產的范圍僅限于自給自足,農業和手工業結合在一起”(1)。而且城市是鄉村化的:“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鄉村無差別的統一(真正的大城市在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營壘,看作真正的經濟結構上的贅疣)”。(2) 第二,財產以公有為主與政治上的專制主義是結合在一起的。“在東方專制制度下以及那里從法律上看似乎并不存在財產的情況下,這種部落的或公社的財產事實上是作為基礎而存在的,這種財產大部分是在一個小公社范圍內通過手工業和農業相結合而創造出來的,因此,這種公社完全能夠獨立存在,而且在自身中包含著再生產和擴大生產的一切條件”(3)。第三,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東方各國社會發展呈現停滯狀態。馬克思后來在《資本論》中對這一點說得更清楚:“亞洲各國不斷瓦解、不斷重建和經常改朝換代,與此截然相反,亞洲的社會卻沒有變化。”(4) 1859年1月馬克思寫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將亞細亞生產方式作為人類社會的一個發展階段:“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5) 而馬克思晚年通過對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等著作的研究,發現了比亞細亞生產方式更為原始的氏族社會形態。
馬克思發現了人類社會歷史不同于生物界的演進與發展,然而卻像達爾文一樣將不同地域橫向出現的社會形態進行了縱向的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進化排列。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介紹的研究方法之一,是從歷史上最發達的和最復雜的社會來剖析較為原始的社會,“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資產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6)。所以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與《資本論》中剖析亞細亞生產方式,并將其置于人類初始的社會形態。于是,在馬克思寫作《政治經濟學》的前后到研究摩爾根《古代社會》之前,亞細亞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就成為馬克思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之前的社會發展階段。然而在中國,明末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已經盎然勃發,并產生了李卓吾、公安派個性解放的文藝主張與黃宗羲的民主政治思想(7),而《牡丹亭》與《金瓶梅》從縱情與縱欲兩個方向演繹著薄伽丘式的文藝復興。可是,馬克思為什么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細亞的”看成是人類最古老最原始的社會形態呢?我們認為這與黑格爾的影響有關:黑格爾將不同地域橫向出現的文化進行了縱向的發展排列,認為世界歷史從低級到高級的上升是以東方為起點的,東方是世界歷史的幼年,希臘是青年,羅馬是壯年,日耳曼是成熟的老年。但在多年之后,中國文化學者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也是以這種將不同地域橫向出現的文化進行縱向的發展排列的方法,雄辯滔滔地論證西方文化(包括日耳曼與黑格爾)是向前追求的青少年文化,中國文化是意欲調和持中的成年人文化,印度文化是反身向后的老年人文化。當然,梁漱溟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較早對“亞細亞生產方式”進行獨特的理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俄羅斯的普列漢諾夫,他認為俄羅斯及東方專制社會的演進與西方社會并不完全相同,在原始的氏族社會崩潰之后,東方社會并沒有像西方那樣出現形態完備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而是出現了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形態,然后直接面對資本主義。1938年斯大林完全忽略亞細亞生產方式而提出了社會發展的“五形態說”:“歷史上有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系: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8) 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在對中國社會進行定位時,大多數都是沿用斯大林的“五形態說”,忽視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將中國從周秦到晚清的社會定性為封建社會,此前的社會則依次為原始社會與奴隸社會。(9) 有的學者論及亞細亞生產方式,然而也是有意無意地忽視了馬克思的原意,譬如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呂振羽在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中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屬于封建制生產方式;然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明明將“亞細亞的”置于“古代的”之前——古代之前即原始的,而在《資本論》中又明明將亞細亞的與原始的畫等號。(10)
那么,我們應該怎么看待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跨文化研究的成果呢?首先,馬克思本人后來在研究摩爾根的《古代社會》等成果之后,觀點也在發生變化;而從斯大林到中國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沒有重視這一研究成果。可以說,這一觀點確實有著自身的缺憾,除了前面我們說到的明末的反證,關于鄉村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可能對于印度與俄國切中要害而對于中國則不然,中國從兩千六百年前春秋時期的魯宣公十五年就開始了土地私有化。而且中國從古就沒有印度那樣的種姓制度,兩千多年前的陳勝就喊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元代汪洙的《神童詩》將此詩化:“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一介布衣看上皇帝的女兒并無不妥,關鍵是這介布衣能不能中狀元。因而將宗教色彩濃重的印度與世俗化的中國納入一個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模式,難免會忽視差異。其次,我們應該以史為鑒,不能以馬克思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述對中國古代與現代的社會制度進行惡意的攻擊。20世紀20至30年代,日本學者以亞細亞生產方式對中國進行攻擊,平野義太郎認為日本已擺脫亞細亞階段,中國仍然是亞細亞生產方式而無法進入現代;秋澤修二則批判中國的亞細亞停滯狀態的奴隸制,甚至為日本軍國主義張目。20世紀50年代美國德裔學者魏特夫出版了《東方專制主義——對于極權力量的比較研究》,該書從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切入,認為東方社會作為治水社會,對大型水利工程的組織導致了東方的極權專制,使人民在恐怖統治下屈從,并對蘇聯與中國的現代社會進行了攻擊。事實上,馬克思在對東方社會的具體論述尤其是在對鄉村公社的分析中,幾乎沒有提及中國,而更多分析的是印度與俄國,馬克思提及中國的多是現實問題。如果中國僅僅是在亞洲就屬于亞細亞生產方式,那么,日本又為什么不是亞細亞?不可否認,日本的萬世一表與中國的改朝換代不同,日本的幕府制度與中國的大一統不同,然而中國古代的社會制度與印度的種姓制度差異也是巨大的!并且除了受黑格爾影響從而對中國的社會形態評價較低外,馬克思對中國人還是非常友好的,當中英發生戰爭的時候,馬克思對英國侵略者進行了譴責,同情全在中國人民這邊。因此,將亞細亞生產方式作為攻擊、貶低其他文化的武器,既非學術研究的態度,又離政治正確相當遙遠。
從斯大林到中國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都覺察到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問題,我們也分析了這一概念的缺憾,那么,我們是否應該像斯大林與中國大多數的馬克思主義者那樣,忽視甚至無視這一概念呢?我們認為這種做法也不妥當。馬克思是觀點精辟犀利的思想大師,我們應該對圍繞著這個問題的觀點加以具體分析。馬克思對于東方社會的經濟自給自足,農業與手工業結合在一起的分析,就一針見血地切入了中國社會的特征;并且中國古代城市確實是皇帝與王公大臣居住的地方,如果與西方中世紀封建貴族在鄉下而城市為工商業者居住以至于孕育出資本主義進行比較的話,那么“亞細亞的歷史是城市和鄉村無差別的統一”又是切中要害的至論。
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對于東方社會停滯的分析,與魯迅基于改造國民性的立場對中國文化的分析,幾乎完全一致。馬克思前文認為亞洲社會不斷瓦解和不斷改朝換代,然而社會卻沒有發生變化。魯迅將馬克思所說的“不斷瓦解”說成是沒有建設的“奴才式的破壞”與“寇盜式的破壞”,結果就是“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11);而所謂“改朝換代”,在魯迅看來就是修補老例的一治一亂(“暫時做穩了奴隸”與“想做奴隸而不得”)的循環(12),結論是與馬克思完全一致的:社會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當然馬克思主義是從社會形態的角度進行分析的,魯迅則更多是從文化價值的角度加以論述的,然而二人卻得出了相同的結論。
因此,我們下面將從馬克思的具體論述出發,以觀其對印度與中國的跨文化研究的異同。
二、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馬克思對印度的跨文化研究
馬克思對印度的研究是從與歐洲的意大利的比較切入的:“印度斯坦——這是亞洲規模的意大利。”(13) 從文化上說印度與歐美都是宗教文化,而中國從古就是以倫理主導的世俗文化。馬克思從社會學出發將印度與歐洲進行比較:“從社會方面來看,印度斯坦卻不是東方的意大利,而是東方的愛爾蘭。意大利和愛爾蘭——一個淫樂世界和一個悲苦世界——這樣奇怪地結合在一起的現象,在印度斯坦的宗教的古老傳統里早就顯示出來了。這個宗教既是縱欲享樂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義的宗教。”(14)
馬克思不相信印度古代有過黃金時代,而是揭示了印度歷史上的災難,并論及印度的現實災難,而英國的侵略顯然加深了這種災難:“內戰、外侮、政變、被征服、鬧饑荒——所有這一切接連不斷的災難,不管它們對印度斯坦的影響顯得多么復雜、猛烈和帶有毀滅性,只不過觸動它的表面,而英國則破壞了印度社會的整個結構,而且至今還沒有任何重新改建印度社會的意思”,可以說,“不列顛人給印度斯坦帶來的災難,與印度斯坦過去的一切災難比較起來,毫無疑問在本質上屬于另一種,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馬克思接著就引證了萊佛爾斯爵士的話來說明英國在印度的殘酷,認為一心賺錢的英國人“對待自己的臣民還不如過去的西印度種植場主人對待他們的奴隸”,種植場主人對奴隸還付錢,而英國人一文錢都沒有花過,“這樣,它就加重了任意妄為的半野蠻政府所造成的禍害”(15)。
馬克思從亞洲社會的一般特征來切入對印度社會的分析:“在亞洲,從很古的時候起一般說來只有三個政府部門:財政部門,或對內進行掠奪的部門;軍事部門,或對外進行掠奪的部門;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門。氣候和土地條件,特別是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區直至最高的亞洲高原的一片廣大的沙漠地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設施成了東方農業的基礎。無論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以及其他國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濫來肥田,利用河流的漲水來充注灌溉渠。”(16) 魏特夫的亞細亞治水社會導致極權主義的論調,應該是從這里闡發出來的,然而很明顯,馬克思在這里論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區”,卻并沒有提及中國。而馬克思在這里分析的地域范圍以及國家的三部門制度,并非自己考察與研究的結果,而是來源于恩格斯的通信:“東方各民族為什么沒有達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沒有達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認為,這主要是由于氣候和土壤的性質,特別是由于大沙漠地帶,這個地帶從撒哈拉經過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韃靼直到亞洲高原的最高地區。在這里,農業的第一個條件是人工灌溉,而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在東方,政府總共只有三個部門:財政(掠奪本國)、軍事(掠奪本國和外國)和公共工程(管理再生產)。”(17) 恩格斯的信也沒有包含中國,而且有些字句與馬克思的文章完全是一樣的。留心一下就會發現: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是1853年6月6日,而馬克思寫作《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是同年同月的10日。魏特夫們凸顯了馬克思對于亞細亞治水社會研究的貢獻,完全沒有注意到關于亞細亞的治水社會的思想原來是來自恩格斯給馬克思的信!而中國政府卻遠不止三個部門,西方剛進入中世紀不久,中國的三省六部就已經全面推開,而三省絕非馬克思所說的財政省、軍事省與公共工程省,而是負責決策的中書省、負責執行的尚書省、負責審核的門下省。根據官職重要性,六部依次是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六部中涵蓋了財政部門的是戶部,涵蓋了軍事部門的是兵部,涵蓋了公共工程部門的是工部。漏掉了最重要的吏部(相當于中央組織部加國家人事部)、禮部(中國是推崇禮教的國家,禮部非常重要,在職能上相當于外交部、教育部與文化部的相加)以及刑部(因有大理寺與都察院是以不很重要)。如果中國是魏特夫所說的治水社會,那么,工部應該在第一位,事實是工部是六部中最不重要的部門。
馬克思在論述英國侵略者的到來使印度的三個部門所發生的變化上,仍然借鑒了恩格斯信件的內容。恩格斯認為:“在印度的英政府成立了第一和第二兩個部門(指的是財政與軍事兩個部門——引者),使兩者具有了更加庸俗的形態,而把第三個部門(指的是公共工程部門——引者)完全拋開不管,結果是印度的農業完全衰落了。”(18) 而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中也是這樣認為:“現在,不列顛人在東印度從他們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財政部門和軍事部門,但是卻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門。因此,……農業便衰落下來了。”馬克思進而分析印度社會的停滯:“從遙遠的古代直到十九世紀最初十年,無論印度的政治變化多么大,可是它的社會狀況卻始終沒有改變。”(19) 馬克思繼續深入分析說:“從很古的時候起,在印度便產生了一種特殊的社會制度,即所謂村社制度,這種制度使每一個這樣的小單位都成為獨立的組織,過著閉關自守的生活。”(20) 后來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的注釋中,從跨文化比較的角度認為羅馬和日耳曼所有制原型可以從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中推出來。(21) 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中,馬克思在論述印度的村社制度之后指出英國人的到來所造成的解體:“不列顛的蒸汽和不列顛的科學在印度斯坦全境把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徹底摧毀了。”(22)
英國侵略者的目的是很卑劣的,然而,他們又摧毀了印度落后的制度。馬克思說:“英國在印度斯坦造成社會革命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鈍。但是問題不在這里。問題在于,如果亞洲的社會狀況沒有一個根本的革命,人類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國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這個革命的時候畢竟是充當了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于是馬克思指出了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的背反,并且在印度社會之愚昧背后也存在著野蠻的殘酷:“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勤勞的宗法制的和平的社會組織崩潰、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悲傷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初看起來怎樣無害于人,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范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任何歷史首創精神。我們不應該忘記那種不開化的人的利己性,他們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塊小得可憐的土地上,靜靜地看著整個帝國的崩潰、各種難以形容的殘暴行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殺,就像觀看自然現象那樣無動于衷;至于他們自己,只要某個侵略者肯來照顧他們一下,他們就成為這個侵略者的無可奈何的俘虜。我們不應該忘記:這種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茍安的生活,這種消極的生活方式,在另一方面反而產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縱的破壞力量,甚至使慘殺在印度斯坦成了宗教儀式。”(23)
薩義德在《東方學》中,在引證了馬克思的這段話之后說:“馬克思的經濟分析與標準的東方學行為完全吻合,盡管從馬克思的分析中顯然可以看出他的博愛、他對人類不幸的同情。然而當馬克思的社會經濟理論淹沒在下面這一標準的古典形象中的時候,最終占據上風的卻仍然是浪漫主義的東方學視野。”薩義德將馬克思的東方學視野看成是歌德等文化先輩的結果,認為被西方學者建構出來的東方學傳統是如此強大,以致連馬克思也難以挑戰。(24)我們認為這是薩義德對馬克思的誤讀,而對于馬克思的準確解讀,需要了解馬克思在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之間的張力,即馬克思主義從歷史進步的角度,敢于直面歷史的殘酷,充分肯定英國殖民主義者摧毀印度的落后愚昧專制的歷史進步性,無論這種專制主義充滿了多么濃厚的田園牧歌情調,戴著多么美麗的脈脈溫情面紗;然而從倫理主義的角度看,馬克思是永遠站在被壓迫階級與被壓迫民族的立場上說話的,是反抗壓迫階級、顛覆世界霸權的革命導師。這一點毛澤東理解得非常準確,他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25) 就此而言,薩義德站在被壓迫的東方立場,反抗西方建構出來的學術文化暴力,反而與馬克思主義的倫理選擇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在跨文化研究中,人們會發現,野蠻族人即使占領文明國家的領土,很快也會被文明國家同化;中國版圖的擴大就與同化了許多北方占領中原的蠻族有關,印度也是如此。馬克思說:“相繼征服過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和莫臥兒人,不久就被當地居民同化了。野蠻的征服者總是被那些他們所征服的民族的較高文明所征服,這是一條永恒的歷史規律。”(26) 馬克思指出,英國人正是在印度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侵入的:“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大莫臥兒的無限權力被他的總督們打倒,總督們的權力被馬拉提人打倒,馬拉提人的權力被阿富汗人打倒;而在大家這樣混戰的時候,不列顛人闖了進來,把所有的人都征服了。……印度本來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運,而且它的全部歷史,如果要算作它的歷史的話,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歷史。印度社會根本沒有歷史,至少是沒有為人所知的歷史。我們通常所說的它的歷史,不過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征服者的歷史,這些征服者就在這個一無抵抗、二無變化的社會的消極基礎上建立了他們的帝國。因此,問題并不在于英國是否有權利來征服印度,而在于印度被不列顛人征服是否要比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國人征服好些。”(27)在這里,馬克思又分析出印度文化的一個特征,就是不關注歷史甚至沒有歷史,相比之下,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都非常關注歷史,只不過中國人更將歷史看成興亡盛衰的“資治通鑒”,而西方人更將歷史看成是一個發展過程。
馬克思認為:在多個侵入印度的民族中,“不列顛人是第一批發展程度高于印度的征服者,因此印度的文明就影響不了他們。他們破壞了本地的公社,摧毀了本地的工業,夷平了本地社會中偉大和突出的一切,從而消滅了印度的文明。”馬克思說:“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個是破壞性的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當然建設性是逐漸展開的。“蒸汽使印度能夠同歐洲經常地、迅速地來往,把印度的主要海港同東南海洋上的港口聯系了起來,使印度擺脫了孤立狀態,而孤立狀態是它過去處于停滯狀態的主要原因。在不遠的將來,鐵路加上輪船,將使英國和印度之間的距離以時間計算縮短成八天,而這個一度是神話中的國度就將同西方世界實際地聯結在一起了。”有時候利己的考慮也會在無意中有利于印度的建設:“工業巨頭們發現,使印度變成一個生產國對他們有很大的好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就要供給印度水利設備和內地的交通工具。現在他們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個鐵路網。”昔日的文化阻礙社會進步,蒸汽機則在推動印度社會的發展。
最后,馬克思對于西方文化所受印度文化的影響進行了回顧,并對印度的復興寄予了厚望:“在大不列顛本國現在的統治階級還沒有被工業無產階級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民是不會收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在多少是遙遠的未來,這個巨大而誘人的國家將復興起來。這個國家里的人民文雅……這個國家里的人民的沉靜的高貴品格甚至抵消了他們所表現的馴服性;他們看來好像天生疲沓,但他們的勇敢卻使英國的軍官們大為吃驚;他們的國家是我們的語言、我們的宗教的發源地,從他們的札提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從他們的婆羅門身上我們可以看到古代希臘人的原型。”(28)
三、同情與希望:馬克思對中國的跨文化研究
與馬克思對印度的歷史、社會與文化的全面分析研究相比,馬克思對于中國是時事評論居多,而且大都與西方列強的入侵聯系在一起。與在分析印度社會與歷史時無情的冷靜分析態度相比,在評述中國文化時馬克思則顯得充滿溫情,他還將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相提并論,而馬克思就深受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尤其是在評述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時候,馬克思站在被壓迫民族的立場上,對中國人民充滿真切的同情,并精準地預見了中國的發展前途,而對西方列強則加以憤怒的控訴與譴責!馬克思一家人幾乎都有綽號,而馬克思的長女燕妮的綽號是“中國皇帝奎奎”,簡稱“中國皇帝”。中國在走向現代的道路上最終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并且在蘇聯解體、蘇聯與東歐的紅旗落地之后仍然高揚馬克思主義的旗幟,這是一種跨時空的文化認同吧!
我們先看馬克思在哲學文化方面對于中國的評述與分析。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黑格爾認為“中國占主導地位的規定性是‘有,印度占主導地位的規定性是‘無”(29)。不過更準確地說,儒家哲學是“有”,道家哲學則傾向于“無”,而中國最早對于佛經的翻譯正是以道家的語言進行的。馬克思恩格斯又說:“雖然中國的社會主義跟歐洲的社會主義像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具有共同之點,但是,有一點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8年來在英國資產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響之下已經處于社會變革的前夕,而這次變革必將給這個國家的文明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30)在這里馬克思點出了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具有共同之處,不久馬克思又指出黑格爾的“對立統一”“可以從中國革命對文明世界很可能發生的影響中得到明顯的例證”(31)。黑格爾哲學與西方傳統片面分化的哲學不同,而是推崇辯證法,雖然辯證法的二元對立及其否定性與中國的中庸之道的二元中和及其肯定性有所差別,然而畢竟都是講求整體性,所以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哲學與黑格爾哲學的共同之處。
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前夜,馬克思恩格斯就意識到了中國將發生均貧富的革命:“有名的德國傳教士居茨拉夫從中國回來后宣傳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事情。”人口眾多的中國在英國的沖擊下瀕于破產,“在造反的平民當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貧窮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現象,要求重新分配財產,過去和現在一直要求完全消滅私有制。當居茨拉夫先生離開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歐洲人中間來的時候,他聽到人們在談論社會主義,于是問道:這是什么意思?別人向他解釋以后,他便驚叫起來:‘這么說來,我豈不到哪兒也躲不開這個害人的學說了嗎?這正是中國許多庶民近來所宣傳的那一套啊!”馬克思恩格斯又發現中國處于革命的前夜,一個新中國已經呼之欲出:
世界上最古老最鞏固的帝國8年來在英國資產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響之下已經處于社會變革的前夕,而這次變革必將給這個國家的文明帶來極其重要的結果。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后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末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
REPUBLIQUE CHINOISE
LIBERTE,EGALITE,FRATERNITE
中華共和國
自由,平等,博愛 (32)
就是馬克思恩格斯的敵人,也不能不佩服他們敏銳而準確的預言。這篇文章寫作后還不滿一年金田起義就爆發了,太平天國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所主張的“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正滿足了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中國人民“要求重新分配財產”的訴求。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自由,平等,博愛”的“中華共和國”,到60年后的辛亥革命得以實現,那是整個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而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理想,是在文章寫作的近百年后才得以實現。雖然時間有先后,但這篇文章的所有訴求與理想都在中國的現實中開花結果,不能不說馬克思恩格斯具有不同凡俗的前瞻性。
馬克思為太平天國革命所吸引,認為閉關自守的大門被打開后革命也接踵而來,而且中國革命對世界至關重要,在馬克思看來甚至超過俄國:“歐洲各國人民下一次的起義,他們下一階段爭取共和自由和爭取比較廉潔的政體的斗爭,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決于天朝帝國(歐洲的直接的對立面)目前所發生的事件,而不是取決于現時的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取決于俄國的威脅及其后果——可能發生的全歐洲的戰爭。……中國的連綿不斷的起義已延續了10年之久,現在已經匯合成一個強大的革命,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么,也不管這些原因是通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推動了這次大爆炸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33) 馬克思充滿激情地說:“可以大膽預言,中國革命將把火星拋到現代工業體系的即將爆炸的地雷上,使醞釀已久的普遍危機爆發,這個普遍危機一旦擴展到國外,直接隨之而來的將是歐洲大陸的政治革命。將來會有這樣一個奇怪的場面:中國在西方世界中引起動亂,但西方列強則借助于英法美等國的軍艦在上海、南京和運河口建立‘秩序。”(34) 西方列強之所以不顧基督教的文化認同,從觀望轉變到敵視、扼殺太平軍,除了他們到天京的宗教使團發現太平軍表面上信奉基督教實則是異教徒以及太平軍抵制鴉片并且不同意與列強瓜分中國等其他原因外,擔心馬克思所說的革命火種燃燒到歐洲無疑也是一個原因,而且是過去被我們的學術界忽視的原因。
鴉片戰爭爆發時馬克思還在大學學習而沒有登上學壇;而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之后馬克思已是著名學者與革命家,在評述中英戰爭時旗幟鮮明站在中國一邊指責英國:“我們認為,每一個公正無私的人在仔細地研究了香港英國當局同廣州中國當局之間往來的公函以后,一定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在全部事件過程中,錯誤是在英國人方面。”(35) 馬克思在辨析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人的廣州屠殺后說:“英國輿論界另一家著名的報刊卻用比較合乎人情和恰當的語氣表達了意見。‘每日新聞(英國自由派報紙——引者)寫道:‘真是奇怪,為了替一位英國官員的被激怒了的驕橫氣焰報仇,為了懲罰一個亞洲總督的愚蠢,我們竟濫用自己的武力去干罪惡的勾當,到安分守己的和平住戶去殺人放火,使他們家破人亡,我們原來是像不速之客那樣闖入他們的海岸的。且不說這次轟擊廣州的后果如何,無所顧忌地和毫無意義地把人命送上虛偽禮節和錯誤政策的祭壇,這一行為本身就是丑惡和卑鄙的。”(36)在《議會關于對華軍事行動的辯論》中馬克思還稱英國軍隊轟擊廣州的第二次鴉片戰爭為“廣州屠殺”,并認為“政府方面唯一的法學權威——大法官說過:‘如果英國在‘亞羅號事件上沒有充分的根據,那末英國的一切行動自始至終都是錯誤的。”(37) 馬克思在《英國即將來臨的選舉》一文中又改稱“廣州大屠殺”。在《帕麥斯頓內閣的失敗》一文中馬克思將“屠殺無辜者”的罪行追到帕麥斯頓勛爵頭上:“帕麥斯頓勛爵在1849年8月18日,即在他退出羅素內閣之前不久,給駐在香港的英國公使發出了如下的訓令:‘不要讓廣州的高級官員或北京政府自我陶醉。英國政府迄今表現寬容,并不是由于它感到軟弱,而是由于它意識到自己具有優勢力量。英國政府很清楚,只要形勢需要,英國的軍事力量能夠毀滅廣州城,叫它片瓦不留,從而使該城居民受到最厲害的懲罰。由此可知,屠殺中國人的事情是由帕麥斯頓勛爵親自策劃的,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38) 馬克思甚至在寫印度起義的文章中都不忘控訴英國人在華的暴行:“強奸婦女,槍挑兒童,焚燒整個整個的村莊,這些并非由中國官吏而是由英國軍官親筆記載下來的暴行,完全是恣意的胡作非為。”(39)
馬克思認為在“廣州大屠殺”后,英美報刊反而向中國人潑臟水:“英國政府報紙和一部分美國報刊就不斷地誣蔑中國人——不分青紅皂白地非難中國人違背條約的義務、侮辱英國國旗、羞辱旅居中國的外國人,等等。”(40) 馬克思進一步揭露英國人的虛偽與殘暴:“廣州城的無辜居民和安居樂業的商人慘遭屠殺,他們的住宅被炮火夷為平地,人權橫遭侵犯,這一切都是在‘中國人的挑釁行為危及英國人的生命和財產這種荒唐的借口下發生的!”馬克思滿懷同情地為被壓迫的中國人民辯護,指出英國的暴行必將換來中國人憤怒的火焰:“英國報紙對于旅居中國的外國人在英國庇護下每天所干的破壞條約的可惡行為是多么沉默啊!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充實英國國庫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外國人經常賄賂下級官吏而使中國政府失去在商品進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對那些被賣到秘魯沿岸去充當連奴隸都不如的牛馬以及在古巴被賣為奴的受騙的契約華工橫施暴行‘以至殺害的情形,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外國人常常無恥地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國人的情形以及這些外國人在各通商口岸干出的傷風敗俗的事情,我們一點也聽不到。……同時,本來已趨于平息的、在鴉片戰爭時期燃起的仇英火焰,在中國爆發成了憤怒的烈火,一切關于和平和友好的聲明都未必能撲滅這股烈火。”(41)
恩格斯具體描繪了中國人的這種“仇英火焰”:“現在,中國人的情緒與1840—1842年戰爭時的情緒已顯然不同。當時人民靜觀事變,讓皇帝的軍隊去與侵略者作戰……現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現在軍事行動只限于這些省份之內),民眾積極地而且是狂熱地參加反對外國人的斗爭。中國人極其鎮靜地按照預謀給香港歐洲人居住區的大量面包里放了毒藥(有些面包已送交李比希化驗。他發現大量的砒霜毒液浸透了面包,這證明在和面時就已摻入砒霜。但是藥量過大,竟使面包成了嘔吐劑,因而失去了毒藥的效力)。中國人暗帶武器搭乘商船,而在中途殺死船員和歐洲乘客,奪取船只。中國人綁架和殺死他們所能遇到的每一個外國人。連乘輪船到外國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約定好了,在每個放洋的輪船上起來騷動毆斗,奪取輪船,他們寧愿與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燒死,也不愿投降。”(42) 恩格斯指出,在中華民族保衛家園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里,“英國人陷入了窘境”(43)。并且恩格斯還從這種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看到了亞洲的曙光:“中國的南方人在反對外國人的斗爭中所表現的那種狂熱態度本身,顯然表明他們已覺悟到古老的中國遇到極大的危險;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國作垂死的掙扎,同時我們也會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44)
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進一步揭露了英國侵略者自私自利的嘴臉:“如果中國政府使鴉片貿易合法化,同時允許在中國栽種罌粟,這意味著英印國庫會遭到嚴重的損失。英國政府公開宣傳自由買賣毒品,暗中卻保持自己對于毒品生產的壟斷權。”(45) 英國人明明知道中國政府查禁鴉片貿易,卻以腐蝕朝廷官員的方式打通海關,馬克思說:“中國人在道義上抵制的直接后果是英國人腐蝕中國當局、海關職員和一般的官員。浸透了天朝的整個官僚體系和破壞了宗法制度支柱的營私舞弊行為,同鴉片煙箱一起從停泊在黃埔的英國躉船上偷偷運進了天朝。”(46) 馬克思認為鴉片貿易甚至比奴隸貿易還不道德:“英國人蒙哥馬利·馬丁都這樣寫道:‘可不是嗎,同鴉片貿易比較起來,奴隸貿易是仁慈的;我們沒有摧殘非洲人的肉體,因為我們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們的生命;我們沒有敗壞他們的品格,沒有腐蝕他們的思想,沒有扼殺他們的靈魂。可是鴉片販子在腐蝕、敗壞和毀滅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還折磨他們的肉體;貪得無厭的摩洛赫時時刻刻都要求給自己貢獻更多的犧牲品,而充當兇手的英國人和吸毒自殺的中國人彼此競爭著向摩洛赫的祭臺上貢獻犧牲品。”(47)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稱為半野蠻人的中國人在禁止毒品維護道德,被稱為文明人的英國人卻在放毒破壞道德。(48)
馬克思還對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一個插曲進行了描述:1859年“6月25日,英國人企圖強行進入白河時,約有兩萬蒙古軍隊做后盾的大沽炮臺除去偽裝,向英國艦隊進行猛烈的轟擊。陸戰水戰,同時并進,結果進攻者完全失敗”(49)。盡管馬克思認為責任在英方,然而第二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火燒圓明園加以報復,使得在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的基礎上又加訂了“北京條約”。馬克思對于英國逼迫清政府簽訂賠款條約進行了跨文化的反諷:“慣于吹噓自己道德高尚的約翰牛,卻寧愿用海盜式的借口經常向中國勒索軍事賠款,來彌補自己的貿易逆差。”(50) 馬克思還指出,在這次戰爭中真正撈到好處的是俄國。(51) 恩格斯完全贊同馬克思關于俄國撈取最大利益的觀點,進而指出清政府已經搖搖欲墜:“這個帝國是如此衰弱,如此搖搖欲墜,它甚至沒有力量來度過人民革命的危機,因為連激烈爆發的起義也會在這個帝國內變成慢性的而且顯然是不治的病癥;這個帝國是如此腐化,它已經既不能夠駕馭自己的人民,也不能夠抵抗外國的侵略。”(52)
第二次世界大戰侵略法國、波蘭與蘇聯等國的是希特勒,這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兩次鴉片戰爭侵略中國的罪魁禍首是誰呢?恐怕很少有人知道。馬克思指出此人是帕麥斯頓:“他的一次對華戰爭曾經遭到議會的譴責,他不顧議會又進行了另一次對華戰爭。”(53) 馬克思還指出,盡管“發生過炮擊廣州、白河慘敗以及英法遠征等事件”,但是卻根本沒有宣戰,“在對中國的關系上,帕麥斯頓違背了有關交戰的所有國際法準則”。(54) 馬克思多次著文抨擊、嘲諷這位侵華的罪魁禍首:“厚顏無恥使他對任何突如其來的攻擊都能處之泰然;利己的心腸和圓滑的手腕使他不致有任何真情的流露;極端的輕佻,十分的冷淡,以及貴族的傲慢態度,使他永遠不致激動。他善于說十分巧妙的俏皮話,因此能博得一切人的歡心。他從來不發脾氣,因此能戲弄暴跳如雷的敵手。”(55) 馬克思因為經常批評帕麥斯頓,后來覺察到此人已經在注意他。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之后,馬克思已逝世十年多,恩格斯對于這場戰爭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進行了評論:“中日戰爭意味著古老中國的終結,意味著它的整個經濟基礎全盤的但卻是逐漸的革命化。”(56)恩格斯在稍后的一封信中也表達了大致相同的意見:“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了;即使是為了軍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須敷設鐵路,使用蒸汽機和電力以及創辦大工業。這樣一來,舊有的小農經濟的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農戶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業品),以及可以容納比較稠密的人口的整個陳舊的社會制度也都在逐漸瓦解。”(57) 恩格斯對甲午戰爭促成古老中國的解體與走向西化,精辟至極!可以說,鴉片戰爭僅僅是將一個東方老大帝國不情愿地拖入現代世界,鑒于古代中國經常被蠻族打敗而又能夠同化蠻族,因而英國人的大炮并沒有警醒中國人,他們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文化選擇方案下,在船堅炮利方面西化的同時,卻在文化與文學上更加保守,致使1840到1894年的文學還不如明代中葉的李卓吾、公安派與清代中葉的《儒林外史》《紅樓夢》更具有現代性,這是因為中國人在“用”上西化的同時,而以“體”上的更加以尊崇傳統來掩蓋受傷的自尊心。然而,甲午戰爭使得中體西用的文化選擇方案徹底破產——過去中國文化的學生日本僅僅因為全面西化的明治維新,就快速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以至于在中國的家門口打敗了北洋水師。因而邏輯的結論就是:中國要想不落后挨打,就要毫不猶豫地走上西化的道路,不但在船堅炮利與科技工藝上,而且還要在文學與文化上。嚴復全面介紹西方文化與林紓譯介西方文學,就發生在甲午戰爭之后。問題是,恩格斯的前兩封信僅僅是在甲午戰爭后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寫的,完全是一種精準的預言!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對于中國文化及社會現實的比較分析,與對于印度歷史文化與社會變遷的論述是極為不同的。可以說,馬克思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論述主要是基于對印度社會的分析,而對于鄉村公社的研究則在研究印度社會的同時參照了俄羅斯社會,基本上是與中國社會無關的。印度的歷史文化與社會同中國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是差異巨大甚至是南轅北轍的:印度從古以來是以宗教社會為主導的,而中國從古以來則是以世俗社會為主導的;印度文化中沒有歷史意識也不看重歷史,而中國文化則講六經皆史并且特別注重歷史;印度的鄉村公社是土地公有,而中國從春秋開始就在進行土地私有化……從這個意義上說,完全套用馬克思以印度社會為分析對象而得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社會理論模式來分析中國社會與文化,在理論方法上是有問題的。然而,馬克思又在某些地方是對亞細亞社會的普遍分析,如《資本論》等論著中出現的“亞洲各國”的論述,往往就適合于對中國社會的分析,有些分析還是非常精辟與深刻的,并且與魯迅透視中國歷史文化的一些觀點非常相似。因此,我們對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方式是否適合分析中國社會采用了一分為二的方法,就是一種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
馬克思對于印度與中國的跨文化研究,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盡管印度文化與西方文化在某種意義上具有同源的性質,但是馬克思更認同中國文化,這與馬克思主義與黑格爾哲學的親緣關系有關,而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哲學與中國文化又有相似性。這樣,就可以在馬克思主義、黑格爾哲學、中國文化之間建立起一種精神聯系。因此,與馬克思以歷史主義的冷靜態度無情地分析英國侵略者摧毀印度社會的進步性相比,馬克思對于遭受英國侵略的中國人民卻是滿懷同情,并且總是站在中國人民的立場譴責英國侵略者。馬克思從文化前瞻的視野出發,對于中國社會普遍存在著的均貧富的訴求的看重、對于中華共和國的展望以及在中國現實中醞釀的社會主義理想,在后來的中國社會發展中一一得以實現。就此而言,馬克思不但是分析精辟、見解獨到的偉大理論家,而且是中國革命的偉大預言家。在西學東漸的文化語境中,中國拋棄了形形色色的各種西方學說與主義,最終實現的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革命,并且在蘇聯與東歐的社會主義垮臺之后,還是高舉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我認為這并不是一種巧合,而是具有歷史與文化發展的必然性。
注釋:
(1)(2)(3)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4、480、473頁。
(4)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7頁。
(5)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頁。
(6)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頁。
(7) 林紓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指責西化的新文化運動是拾了李卓吾之余唾,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認為西化的新文學源自公安派。
(8) 斯大林:《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斯大林文選(1934—1952)》上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9頁。
(9) 由于中國社會不具有希臘羅馬到中世紀那樣明顯的社會轉換,所以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有的認為封建社會從西周始,有的認為封建社會從東周始,有的認為封建社會從秦代始,有的認為封建社會從魏晉始……
(10) 馬克思:《資本論》第4卷《剩余價值論》第3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6卷第3冊, 人民出版社 1973年版,第465—466頁。
(11) 魯迅:《墳·再論雷峰塔的倒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頁。
(12) 魯迅:《墳·燈下漫筆》,《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13頁。
(13)(14)(15)(16)(19)(20)(22)(23)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3、143—144、144—145、145—146、146、147、148、148—149。
(17)(18) 恩格斯:《致馬克思(1853年6月6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0—263、263頁。
(21)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資本的生產過程》,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4—95頁。
(24) 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98—202頁。
(25) 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1949年12月20日。
(26)(27)(28) 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7、246—247、250—251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第六章《絕對的批判的批判或布魯諾先生所體現的批判的批判》(1)《絕對批判的第一次征討(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4頁。
(30)(32) 馬克思、恩格斯:《國際述評(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264—265頁。
(31)(33)(34) 馬克思:《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9、109—110、114頁。
(35)(36) 馬克思:《英中沖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12、117頁。
(37) 馬克思:《議會關于對華軍事行動的辯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8頁。
(38) 馬克思:《帕麥斯頓內閣的失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8—159頁。
(39) 馬克思:《印度起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09頁。
(40)(41) 馬克思:《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6、177—178頁。
(42)(43)(44) 恩格斯:《波斯和中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1、232、234頁。
(45)(46)(47)(48) 馬克思:《鴉片貿易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1、588、584—585、587頁。
(49)(51) 馬克思:《新的對華戰爭——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69、568頁。
(50) 馬克思:《英中條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05頁。
(52) 恩格斯:《俄國在遠東的成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62頁。
(53)(54) 馬克思:《英國的政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0、13頁。
(55) 馬克思:《帕麥斯頓勛爵——第一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90頁。
(56)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94年9月23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88頁。
(57) 恩格斯:《致弗·阿·左爾格(1894年11月10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7頁。
作者簡介:高旭東,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上海,200240;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100872。
(責任編輯 劉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