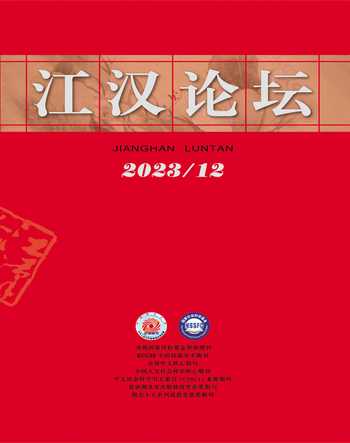國際體系視角下的近代中國變遷
摘要:近代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封建王朝向現代國家的轉型,同時也從一個相對封閉的狀態最終走向世界。如果將近代中國的這一變化放到國際體系的層面來審視,我們會看到一些不同的畫面,對一些歷史事件的解讀也會有所不同。實際上,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也體現出了國際體系的轉換過程:以中國為中心的宗藩體系在西方維也納體系的沖擊下開始瓦解,中國逐漸接受了西方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開始建立起來的國際關系原則,并逐漸進入到正在形成的新的國際體系之中。從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到雅爾塔體系,中國不僅對國際格局有了越來越清晰的認知,還能與之進行互動,積極開展外交。然而由于近代中國的政府都只是仰賴于西方國家的同情心,不敢、不能、也無法突破本身存在嚴重問題的國際體系,因此也不可能真正改變近代中國的命運。
關鍵詞:國際體系演變;近代中國變遷;宗藩體系;世界體系
中圖分類號:K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854X(2023)12-0100-08
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過程中,近代是一段風云變幻的時期,整個國家經歷了從封建王朝向現代國家的轉型,中國社會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改變。而這些變化之所以發生,除了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邏輯之外,對外關系也在其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和影響。近代以后,中國從一個相對封閉的狀態最終走向世界,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當然,中國的這種變化并不是孤立進行的,與此同步發生的是整個世界范圍內國際關系的變化。地理大發現拓展了人們對于“世界”概念的認知,工業革命帶來了新的交通與通訊手段,各個文明之間的聯系日趨頻繁,彼此的交流與互動、相互的影響與制約都在加強,國際社會的體系也由此開始形成。而中國作為這一時期國際社會的一個成員,也逐漸進入到這個正在形成與變動之中的全球性國際體系里,并與之產生互動。
通常我們對近代中國的解讀主要聚焦于中國自身的變化,對于這一時期對外關系的關注,也多立足于中國,以中國為主體來看待我們與世界各國關系的展開,如不平等條約的簽訂與國家主權的喪失、從洋務運動開始的國家外交體制的改變、20世紀20年代的修約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等等。這些都是近代中國的重要課題,在學界也有大量研究成果,但如果我們調整一下角度,從全球史觀和國際體系演變的視角來看待近代中國的變遷,就能夠在一個更加宏觀的層面上,獲得一些不同的畫面和思考,對于一些歷史事件也會有新的解讀。由于近代中國對外交往不斷加深,在這段歷史的發展脈絡中,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國際體系演變所投射下的畫面。而對于國際體系的每一次演變,中國也都會與之進行某種形式的互動。
當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被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中國正在以一種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到國際體系的建設與全球治理當中。在新時代的背景之下回顧歷史,能讓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國際社會的演變,感受到今天中國的發展與成就。
一、馬嘎爾尼使團來華:各執己見的東西大國
當我們回顧國際體系的發展歷程的時候,不難看到,雖然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具有現代意義的國際關系體系,確定了國家主權和平等交往的基本原則,也因此被視為近現代國際關系的奠基石。但從地理范圍來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還只是一個區域性的國際體系。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結束了歐洲的三十年戰爭,因此主要是在歐洲大陸暫時建立起了一個均勢格局。而在此時的東亞地區,維系各國關系的則是以明朝為中心的宗藩體系。這兩個國際體系分別位于歐亞大陸兩端,相對獨立地存在,但并非完全沒有聯系。隨著近代以降全球聯系的加強、西方近代殖民的推進,這兩個體系開始出現碰撞。
(一)東西國際體系的第一次交鋒
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來華,其背后最重要的推動力當然是英國方面希望解決中英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愿望。乾隆皇帝對使團所提出的貿易要求的斷然拒絕,也被視為封建王朝下中國以天朝大國自居、不了解外部世界的表現。但同時,這次訪問也被視為東西方兩種國際體系的第一次交鋒。英國試圖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的國際交往原則來進入中國,然而中國此時正處于封建王朝的鼎盛時期,仍以宗藩思想指導對外關系。
英王喬治三世在給馬嘎爾尼的私人指示中明確指出:“在中國經商的英國臣民很久以來多于任何其他歐洲各國。……英國商人……在這個遙遠的國度里,每每被人誤解而得不到尊重。在這等情形下,雖然英國本身的經濟繁榮絕不依靠在華英商的成敗和得失,我對于自己的遠方臣民不能不予以應有的關懷,并以一個大國君主身份有力地要求中國皇帝對于他們的利益予以應有的保護。……自不待言,除了人類的幸福,兩國的互利和中國政府對英國商業的應有的保護而外,我們沒有任何其他的目的。”在給中國皇帝乾隆的信中,喬治三世也表達了同樣的意思。(1)可以看到,喬治三世并不完全了解中國當時的對外關系模式,只是單方面從自己的想法出發,認為英國所提的要求非常合理,沒有什么不合適的地方。
但很顯然,中國的乾隆皇帝并不這樣認為,因此在那兩封著名的回信中,對于英國的各種要求都表示了拒絕:“爾使臣以爾國貿易之事稟請大臣等轉奏,皆系更張定例,不便準行。”乾隆對此給出的原因則是:“天朝統馭萬國,一視同仁,即廣東貿易者,亦不僅爾英吉利一國,若俱紛紛效尤,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循所請?念爾國僻居荒遠,間隔重瀛,于天朝體制原未諳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詳加開導,遣令回國。”(2)隨后乾隆對英國所提出的要求又逐條進行了駁斥。
可以看到,此時的中英雙方,作為各自所處國際體系內的大國,都缺乏對對方的了解,只是單方面用自己的思維模式來同對方打交道,并希望對方能夠接受自己的交往模式與規則,這樣的溝通必然難以取得成效。
(二)以宗藩模式解讀英使來華
在馬嘎爾尼的這次訪華過程中,更有意思的一點是中國方面對相關文件的界定與翻譯。喬治三世的信被定為“表文”,乾隆的回信被定為“敕諭”,這顯然是套用了宗藩體系下的往來模式。也正因為這樣的界定,英王的信在譯成中文之后,加入了大量表達恭順的文字。如英王信中講道:“英國現在正與世界各國和平共處,因此英王陛下認為現在適逢其時來謀求中英兩大文明帝國之間的友好往來。”(3)這句話在呈遞給乾隆皇帝的版本中,表述為:“如今本國與各處全都平安了,所以趁此時候得與中國大皇帝進獻表貢,盼望得些好處。”(4)個中差異一目了然。
此外,最經常被提到的跪拜禮問題,顯然也是中國方面希望以宗藩模式來處理馬嘎爾尼使團訪華的一個突出表現。
如果從外交體制的角度來看,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常駐外交代表機關的派駐,然而這樣的機關在宗藩體系內沒有存在的空間。在清代早期,具體負責處理與屬國之間各項事務的主要機構是禮部和理藩院,而這兩個機構本身并不是專門的對外機構,其主要職責仍然在于處理清政府的內部事務,對外事務對于它們來說,只是兼管而已。因此,在鴉片戰爭之前,在中國統治者的觀念當中,對外事務并不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也就不需要就對外交往設立專門性的職能部門。再加上華夷觀念的影響,當英國依照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中的慣例,提出要在中國常駐使節時,自然遭到了堅決的拒絕。“至爾國王表內懇請派一爾國之人,住居天朝,照管爾國買賣一節。此則與天朝體制不合,斷不可行。”(5)乾隆在此并不完全是出于自大或者無知,而是無論從思想層面還是操作層面來看,英國所提要求難以在中國既有的對外關系體系內實現。
二、鴉片戰爭之后:宗藩體系走向瓦解
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之后,以強權政治為重要特點的維也納體系取代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雖然維也納體系所討論的問題主要是歐洲事務,但它已經開始將世界其他地區作為歐洲國家的擴張對象納入進來。正是維也納體系下西方列強愈演愈烈的對外擴張行為,使得東亞地區的宗藩體系遭到了毀滅性打擊,以中國為中心的這一體系最終瓦解,并徹底退出歷史舞臺。
(一)從宗藩體系到條約體系
1840年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歷史的起點,中國開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國家主權喪失,國際地位下降。從國際體系演變的角度來看,鴉片戰爭則是誕生不久的維也納體系在世界范圍內瘋狂擴張的過程中,開始以暴力沖擊東亞地區的宗藩體系,這一進程從19世紀中葉開始,最終在19世紀末期基本告一段落。
縱觀這一時期國際體系的變遷,首先當然是宗藩體系的瓦解。維也納體系下的西方列強繼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殖民擴張,在這一過程中,不僅作為宗主國的中國遭受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中國自明清時期以來的屬國也紛紛淪為列強的殖民地,與中國之間的傳統關系自然也就不復存在,宗藩體系開始解體,直至甲午戰爭后徹底消失于歷史之中。
但比較耐人尋味的是,開啟和結束宗藩關系消亡進程的卻并非歐美國家,而是向歐美國家學習的日本。19世紀70年代,日本占領琉球,并最終將之吞并,這成為中國“所有朝貢的屬國一個一個地相繼地被割去的一個序幕”(6)。此后不久,中法戰爭爆發,法國奪取了中國對越南的宗主權。隨后,中國又陸續喪失了對南部的暹羅、南掌、緬甸三國以及西南部的錫金的宗主權。暹羅在中法戰爭爆發不久就宣布停止向中國朝貢,南掌也于1893年被法國兼并,成為法屬印度支那的一部。緬甸則在1886年完全落入英國的控制之下。1890年,中英簽訂《藏印條約》,同意“哲孟雄由英國一國保護督理”。(7)
宗藩體系最終解體的標志則是中國對朝鮮宗主權的喪失。朝鮮與中國的藩屬關系最為穩固,也是中國屬國中最重要的一個。但同時,朝鮮又一直是日本侵略擴張野心的對象。近代之后,日本不斷向朝鮮滲透,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此役中國慘敗,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喪失了對朝鮮的宗主權。至此,在東亞地區維持了數百年的宗藩關系完全消亡。
其次,條約體系被引入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在清代中國所熟悉的認知范圍內,朝貢與冊封是對外關系的主要內容,其規則由中國方面依“禮”而定。盡管清政府也簽訂過諸如《尼布楚條約》之類的條約,但它并非清代對外關系的日常內容。然而鴉片戰爭卻給中國帶來了遠超過朝貢與冊封的對外交往,通商口岸、關稅、領事裁判權等新事物與傳統的宗藩體系格格不入,其運行依賴中外條約而展開。因此,在鴉片戰爭之后的中國,條約體系與宗藩體系共存,中國依照兩套不同的規則分別與兩個不同的國家群體開展往來。當然,隨著宗藩體系的解體,條約體系在當時中國對外交往中所占的比重日漸擴大。
而在1900年《辛丑條約》的談判過程中,各國由于彼此意見大相徑庭,難以達成一致,在經過長時間的爭吵之后,它們最終接受了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方案。“門戶開放”由此成為列強在處理對華關系時共同遵守的一個原則。這樣,各國將由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開啟、維也納體系進一步確認的“均勢”原則強加在中國頭上。
(二)洋務派眼中的國際格局
眾所周知,19世紀60、70年代的洋務運動是晚清時期外交近代化的重要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國際法觀念開始進入中國,其中一個重要渠道便是丁韙良所翻譯的《萬國公法》。與丁韙良交往密切的張斯桂為此書所作的序文中,他對當時的國際格局進行了這樣一番介紹:
間嘗觀天下大局,中華為首善之區,四海會同,萬國來王,遐哉勿可及已。此外諸國,一春秋時大列國也。若英吉利,若法蘭西,若俄羅斯,若美利堅之四國者,強則強矣,要非生而強也。
……
在昔春秋之世,秦并岐豐之地,守關中之險,東面而臨諸侯,俄羅斯似之。楚國方城漢水,雖眾無用,晉則表里山河,亦必無害,英、法兩國似之。齊表東海,富強甲天下,美利堅似之。至若奧地利、普魯斯,亦歐羅巴洲中兩大國,猶魯、衛之政,兄弟也。土耳其、意大利,猶宋與鄭,介與大國之間也。瑞士、比利時,國小而固,足以自守。丹尼、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國,昔為大國,后漸陵夷,然于會盟、征伐諸事,亦能有恃無恐,而不至疲于奔命。其間蕞爾國,不過如江、黃、州、蓼,降為附庸,夷于邱縣,或割地而請和,或要盟以結信,不祀忽諸,可勝道哉?可知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鮮虞不警邊,舒、庸不設備,千古有同慨焉。(8)
這段介紹非常有趣,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首先,盡管當時的洋務派已經開始去了解西方世界,但還是習慣性地用中國歷史來進行解讀,將當時的西方國際格局比附春秋戰國的形勢。而這恰恰體現了洋務運動時期一種新舊混雜的過渡狀態。
其次,盡管認識不完全正確,但此時的洋務派已經看到了維也納體系的重要特點:國家因實力不同而在體系中有著不同的地位,大國相互維持均勢,中等國家基本可以自保,其他小國則在其間艱難生存。
第三,除了在此引文中所提到的“昔為大國,后漸陵夷”的幾個國家之外,在這篇序文中還分別對英、法、俄、美“非生而強”的發展過程進行了簡要介紹。由此可見,當時的洋務派也已經認識到了,國際格局是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的。
(三)晚清外交機制的形成
這一時期中國對國際體系的認知與接受是比較被動的。從1842年8月29日的中英《南京條約》開始,到清朝于1911年被辛亥革命推翻為止,清政府一共與18個國家簽訂了不平等條約,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不斷遭受侵害,國際地位日漸下降。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不得不接受列強所要求的交往模式,西方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之后所形成的各種國際關系原則逐漸滲透到中國和東方世界。
鴉片戰爭以后,隨著中外交往逐漸增多,清政府開始感覺到,僅靠原來的禮部和理藩院,已經難以應對越來越復雜的對外事務,現實要求清政府建立新的外交體制。洋務運動期間,除了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外,還有南洋通商大臣與北洋通商大臣共同管理洋務。但總理衙門和南北洋大臣均是臨時設置,由其他官員兼任,因此在權力上有諸多限制,而且政出多門,也帶來很多問題。1901年,清政府又依照《辛丑條約》談判過程中列強的要求,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改為外務部,中國的外交機構完成了近代轉型。
此外,作為西方外交原則的一個重要內容,清政府也被迫接受了互派公使一事。1858年《天津條約》對此作出了規定,盡管其間經歷了一些波折,但1861年以后,英、法、美等國的公使相繼來京,建立使館。清政府向外派駐使節一事則因為各種原因拖延了相當一段時間,也因此導致了西方國家的一些不滿。1865年11月,赫德向清政府遞交了《局外旁觀論》,直指“派委大臣駐扎外國,于中國有大益處。在京所住之大臣,若請辦有理之事,中國自應照辦;若請辦無理之事,中國若無大臣駐其本國,難以不照辦。”次年3月,英國參贊威妥瑪也在其《新議略論》中批評:“此中華全取其益者,即如派委代國大臣駐扎各國京都一節。”“如今中國獨立,不與鄰邦相交,各國未免心寒。”(9)
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之下,1875年馬嘉理事件之后,清政府任命郭嵩燾為駐英公使,隨后又任命陳蘭彬為駐美公使。從此之后,清政府陸續任命駐外使節,到20世紀初,共向14個國家派出了常駐使節。
總之,晚清時期,到19世紀末,中國逐漸接受了西方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后所形成的一些基本準則和觀念。
三、日俄戰爭:過渡時期的東亞角逐
日俄戰爭通常被視為參戰雙方對于中國東北地區的一場爭奪和瓜分,清政府在此次戰爭中所采取的“局外中立”立場也成為它在覆滅前的一個重要注腳。但如果從國際體系演變的角度來看,日俄戰爭則有著不太一樣的重要意義,它實際上是東亞地區在宗藩體系解體之后、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確立之前的一次大國角逐,其結果則為后來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在遠東地區奠定了基本的格局。
(一)全球對抗中的遠東霸權
在東亞地區的宗藩體系解體之后,這一區域的國際秩序開始進入過渡狀態。日本與俄國這兩個之前位于體系之外的國家開始了較量。日本此前一直游離于以中國為核心的宗藩體系之外,并且按下了中國喪失屬國的開啟鍵和結束鍵。但日本并不否認華夷思想,并且在“華夷之辨”的基礎上發展出了“華夷變態”思想,尋求在東亞地區建立一個以日本為中心的新華夷秩序。俄國作為一個地跨歐亞大陸的大國,其政策重心一直以歐洲為主,對于與其政治中心相距甚遠的遠東地區,則多少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西伯利亞鐵路的修建開始為俄國進入遠東創造條件。
甲午戰爭后,三國干涉還遼將日俄矛盾推向一個新的階段。俄國因此獲得了中國的信任,得以在中國東北修建鐵路,即著名的中東鐵路。中東鐵路與西伯利亞鐵路相連,大大方便了俄國直接深入中國東北地區和插手遠東事務。日本國內則因此致其反俄情緒日趨高漲。“此時郁積在他們心中的不平不滿也一時爆發出來。生出昨日過于驕傲、今日卻蒙受奇恥大辱之感。”(10)此外,隨著中國中斷與朝鮮的宗藩關系,俄國力量進入朝鮮與日本對抗。由此,在朝鮮與中國東北,日俄兩國開始了正面沖突。
這種沖突最終以日俄戰爭中日本的勝利而告終,俄國的影響大大收縮。這一結局也就意味著,在即將形成的新的國際秩序中,日本將成為遠東地區的主導國家。
同時,日俄兩國的爭奪也不僅僅只發生于日俄之間。日本在戰前即與英國結成同盟,英國與俄國在全球擴張中一直存在矛盾,此次借助日本的力量成功遏制了俄國。然而與英國的間接介入相比,更有意味的是美國的直接介入,美國一直關注日俄兩國的爭奪,在戰爭后期積極調停,促成了《樸茨茅斯和約》的達成。戰爭結束后,面對日本在中國東北地區不斷擴張權益的做法,清政府希望引入美資遏制日本。美國方面也很有興趣,但這一構想最終未能達成。相反,美國與日本以換文的形式達成《羅脫—高平協定》,“兩國政府的政策不被任何侵略意向所左右,其目的在于維持上述地區目前的現狀,以及維護在中國通商和開辦工業的機會均等原則。”(11)美日兩國暫時達成了平衡,但它們之間在遠東地區的爭奪其實已經悄悄拉開了帷幕。英美等國的介入,恰恰意味著此時的遠東地區已經是未來世界秩序中的重要部分。
(二)并非“局外”的“局外人”
在1904年的日俄戰爭中,中國采取了所謂“局外中立”的立場,這也導致在戰后的談判中,無論是談判的日俄雙方,還是作為調停者的美國,都沒有把中國放在眼里。中國被排除在整個談判過程之外,其國土完全由其他國家來任意宰割。
但中國顯然不是此次戰爭的“局外人”,盡管行將就木的清政府無力采取任何行動,但中國社會各階層對于此次戰爭則極為關注,當時的報刊更是隨時報道戰況、發表大量評論。從一些報刊文章能看到,除了對中國自身命運的擔心,時人中部分有見識者,已經對于這場戰爭的國際意義有了一定的認識。
1904年6月的《東方雜志》轉載了香港《華字日報》的文章《論旅順關系》,其中就清楚地指出:“旅順者,為俄人所必守,為日人所必奪,為中國所必失。而戰事之結局、亞洲之霸權,亦以此為關鍵。”(12)在這里,中國的知識分子已經認識到,此役關系“亞洲之霸權”。
不僅如此,1904年9月的《東方雜志》所刊登時評《日俄交戰之關系》中更是講道:“不意日俄之沖突,反于歐洲得均勢之良果。英皇愛德華善乘其機,故親歷各國,與列國君主,先后歡會,莫不締結盟約,以固歐洲均勢之力。”(13)雖然這里對這場戰爭的解讀未必完全準確,但時人顯然已經明了,這場發生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戰爭,是與歐洲的局勢緊密相連的。
此外,當時身在海外,尤其是美國的一些留學生,還感受到了日美之間矛盾的開啟。當時在美國留學的顧維鈞就回憶道,“本來日本人在美國還是受歡迎的。小小的日本顯示了它戰勝北方巨熊的決心和能力,這正符合美國人民的想象。但是由于日本公眾輿論開始譴責美國堅持不涉及戰爭賠款的和談,反美情緒也就出現。這種情緒隨著它的發展,導致了兩國人民之間友好關系的不斷削弱。……我認為到日本進攻滿洲時,關系沒有好轉。”(14)
四、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參與全球體系
維也納體系并不能真的維持歐洲大國之間的均勢,各國在殖民擴張的過程中爭斗不斷,最終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戰爭結束后的巴黎和會與華盛頓會議建立起了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中國雖然以戰勝國的身份參與到這一體系當中,但由于中國自身國家實力有限、國際地位較低,因此在體系建立之初,還是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然而,中國也開始利用這一體系所建立起來的各項規則,嘗試收回國家主權、提高中國國際地位。
(一)在戰后秩序中獲得一席之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無疑是近代國際關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維也納體系的均勢無法解決西方各國在世界擴張中的重重矛盾,這場規模空前的大戰也讓各國始料未及,戰后各國認為需要建立新的國際秩序以維持和平,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由此誕生。
一戰爆發之初,中國宣布中立;但自1917年美國態度發生改變之后,中國國內關于參戰與否的爭論熱烈起來。孫中山等人認為中國不應參戰,“加入之結果,于國中有紛亂之虞,無改善之效,則頭等國之想象,恐未可幾。……且歐戰本為利害之爭,我國事與彼殊,不必以人道為由,自驅笠入。”(15)但也有相當多的政治家,尤其是外交界人士,力主參戰。這些主張參戰的人當然無法直接預測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的出現,但他們非常清楚的一點是,只有參戰,中國才有可能參與戰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才有可能在戰后獲得發言權,才有可能解決讓當時中國人痛心疾首的“二十一條”以及山東問題。顧維鈞就表示:“當時的局勢在我看來,不難理解,為使山東問題獲得妥善解決,為在戰爭結束時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中國必須參加協約國。”(16)
事實證明,盡管巴黎和會上中國的要求被拒絕,中國的國家地位并沒有因為戰勝國身份而得到明顯改變,中國的利益仍然得不到西方強國的重視,仍然只是西方國家之間討價還價的籌碼,但中國確實在戰后國際秩序中獲得了一席之地,成為國際聯盟的創始國。中國“藉由參加歐戰,成為協約國一員,以戰勝國身份參與歐戰后世界新秩序的規劃,對‘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積極參與,并對這個體系主要條約基礎的《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都參與其制訂過程,加入了中國的意見。”(17)也就是說,中國的參戰與參會,其實正是參與到了新生的全球性國際體系的建構當中。
此外,在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作為《九國公約》的簽字國,也承認了“門戶開放”原則,這進一步體現出了中國對于新的國際體系的接納與融入。
(二)在新的體系內開展積極外交
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遭遇重大挫折,這讓當時的中華民國開始意識到需要著手解決晚清遺留下來的不平等條約問題。在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建立起來之后,中國開始改變外交政策,在新的國際體系框架之內,運用其規則嘗試進行修約和廢約,以收回主權、提高國家地位。
實際上,在華盛頓會議上,中國就借這個多邊場合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希望取消列強在華特權。如關稅問題、領事裁判權問題、勢力范圍和租借地問題、外國駐華軍警問題、中日“二十一條”問題,以及電臺和郵局問題等。對于中國所提出的大多數要求,華盛頓會議都未給予明確答復,但也未明確拒絕,而是表示今后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考慮。例如中國最為關心的關稅問題,會議通過了《關于中國關稅稅則之條約》,表示可以“由特別會議立即設法,以便從速籌備廢除厘金,……以期征收各該條款內所規定之附加稅”,“該會議應于本條約實行后三個月內在中國會集”。但同時條約反復強調厘金問題,其實是以此作為向中國施壓的一個首要條件。(18)又如領事裁判權問題,會議通過了《關于在中國之領事裁判權議決案》,表示“允助中國政府,以便實行其所表示改良司法制度期等于泰西各國之志愿,并宣言一俟中國法律地位及施行該項法律之辦法并他項事宜皆能滿意時,即預備放棄其領事裁判權”,同樣將“改良司法制度”設置為門檻。(19)只有電臺和郵局問題,列強做出了一點讓步。會議形成了《關于在中國之外國郵局議決案》和《關于在中國無線電臺議決案并附聲明書》,規定“關于中國政府表示在中國境內之外國郵局除在租借地或為約章特別規定者外期得撤消之志愿,認為公平”;“如有外國政府或其人民在中國境內未得中國政府之允許而存留之電臺,……由中國交通部接管。”(20)可以看到,盡管廢除和修改不平等條約的過程十分曲折和漫長,但這一步伐確實已經邁出。
而中華民國政府此時能開展積極外交,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便是新一代外交人才的出現。這一時期的外交官,基本都有過留學經歷,而且大都學習法律、政治、外交等專業,他們熟悉西方社會,了解國際規則,同時對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命運都深感痛切,希望能用自己所學推動祖國的進步與發展。如顧維鈞就回憶,當他在美國要選擇未來學習的專業時,盡管同學孫嘉祿“極力主張我干工程這一行”,但他自己還是想學政治學和外交學,原因正是“我想為改善國家的狀況做一些事情……我的目的是為國效力,以實行改革,特別是在處理外交關系方面。”(21)而顧維鈞后來博士論文的題目則是《外國對中國政府的權利要求》,盡管最后只是以原計劃的引言部分作為論文進行了答辯,但顧維鈞對此問題的關注是顯而易見的。他在論文中就指出:“外人在中國所享各種權利特權,為在他國所未有者,固彰彰甚明也。”(22)也正是在國外的學習經歷與對國際社會的了解,促成了他后來在巴黎和會上引人注目的表現。
五、第二次世界大戰:雅爾塔體系的確立
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內部存在嚴重的矛盾,它所帶來的戰后和平極其脆弱。很快,隨著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危機的爆發,兩次大戰間的各種矛盾最終導致了新的世界大戰,世界各國的力量對比也徹底被改寫,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誕生出來的雅爾塔體系將戰后世界帶入了美蘇冷戰的態勢之下。而中國在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后又面臨著國內政局的轉換,在新的國際體系中的位置也相應進行了調整。
(一)美蘇最終犧牲中國權益
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改變了國際格局。在這場戰爭中,作為對抗法西斯的重要力量,中華民族艱苦卓絕的戰斗極大地打擊了日本法西斯力量,使其侵略野心最終破產。中國人民的流血犧牲使得中國在戰爭后期開始獲得大國地位,與美、英、蘇各國展開合作。盡管出于戰爭的需要,逐漸形成了美、英、中、蘇四強格局,但事實上,主宰世界的主要是美蘇兩國,這一點在雅爾塔會議上已經完全凸顯出來,戰后的雅爾塔體系也由此確立。
雅爾塔會議的一個重要議題是對日作戰問題。為鼓勵蘇聯對日作戰,會議給予蘇聯一系列權益,而這些權益分別是來自于作為敵人的日本,以及作為盟友的中國。雅爾塔體系的本質在這一紙協定中也暴露無遺。
1944年10月,顧維鈞向蔣介石報告,在與美國參謀總長會晤時,對方談及蘇聯對日作戰問題時,“料蘇俄愿在遠東取得旅順不凍港,英必贊成,美亦無反對之意。”蔣介石復電詢問:“彼特于此時忽提及旅順事,以兄當時察其辭色與推想此語之所由,其用意何在?請詳告。”(23)可以看到,蔣介石對此十分意外,甚至有些慌張。隨著雅爾塔協定的出爐,美蘇也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國透露了其內容。蔣介石指示駐美大使魏道明、駐英公使顧維鈞,以及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等人多方交涉,他本人也與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分別會談,希望能改變局面。然而在戰爭局勢日益明朗的情況下,再加上自身反共的需要,蔣介石政權無法對抗美蘇強權,只能被迫接受協定中的安排,于1945年8月14日與蘇聯正式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滿足了蘇聯的要求。
然而,盡管蔣介石政權出于各種考慮接受了雅爾塔協定,但中國人民這次卻再度奮起反抗,繼續進行救國道路的探索。1949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以展開,中國共產黨將帶領中國人民在雅爾塔體系之下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
(二)隨戰爭局勢調整對外政策
從中國在抗戰中的外交政策與活動來看,在抗戰開始后,南京國民政府在外交上主要依靠的對象,除了國際聯盟之外,便是美國與蘇聯。但由于戰爭局勢的變化,這些政策也有一些調整。
首先,抗戰爆發之初,國民政府在現有的國際框架之下,援引一系列國際條約,控訴日本的行為已嚴重違反國際法,要求以國際聯盟為首的國際社會對日本采取行動。“九一八事變”之后,國民政府“特種外交委員會”發布“現在處理時局之根本方針”,列舉出了七條具體的外交決策,其政策對象除日本之外,就是國聯與美國,具體的考慮則包括:“判斷此時仍須盡力表示中國政府完全信任國聯之意思。如此,第一、對于國內可減少人民責備政府之心理。第二,不致傷各國之感情。第三,將來運用九國公約,而對美國做工夫時較易說話。”(24)1932年9月15日,日本宣布承認所謂“偽滿洲國”。第二天,國民政府即發布抗議書,列舉日本的行為已違反國際公法之基本原則、違反法律之初步原則與人道觀念、違反《國際聯合會盟約》、違反《非戰公約》、違反《九國公約》、違反其自為之誓約、違反國際聯合會歷史訓誡。(25)可以看到,此時國民政府主要還是依靠國聯與美國,蘇聯并未正式進入其視野之內。
其次,在全面抗戰開始之后,國民政府一方面繼續在國聯活動,同時加強了與美國的關系,另一方面,蘇聯也開始成為其外交工作的重點。1937年10月,面對即將召開的布魯塞爾會議,國民政府雖然認識到“依照目前形勢,會議無成功希望”,但仍然向中國參會代表顧維鈞等表示:“我方對各國態度須極度和緩,即對義德兩國亦須和緩周旋,勿令難堪,并須表示會議成功之愿意。我方求在九國公約規定之精神下,謀現狀之解決,此系我方應負之原則。”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國民政府還提出,“我方同時應竭力設法促使英美贊成并鼓勵蘇聯以武力對日。”(26)與此同時,中國駐蘇聯大使蔣廷黻也在竭盡全力地進行游說,在與蘇聯外交次長斯多蒙涅哥夫的一次談話中,他明確表示:“現在各大國之中惟獨蘇美兩國能對日本多出力,吾人深望貴國能多助我一份。”(27)最終,國民政府爭取到了蘇聯的一些貸款和軍事援助,這也是抗戰開始以來中國獲得的首批外援。
最后,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后,蘇、英、美日益成為國民政府外交布局中的重中之重。珍珠港事件發生當天,蔣介石即向三國提出建議,表示“中國現決心不避任何犧牲,竭其全力與美、英、蘇聯及其他諸友邦共同作戰”“中國建議美國對于德義兩國與蘇聯對于日本,皆請同時宣戰”“中國政府建議各友邦(中、英、美、澳、荷、加拿大、紐絲綸),應成立軍事同盟”。(28)此外,中國還利用抗戰的機會,與美國和英國交涉,廢除不平等條約,訂立新約,收回了大多數的國家主權,使得中國“強國”的稱呼更加名實相符。
應當說,國民政府基本上還是把握住了日本侵華戰爭所帶來的有利于中國的局勢變化,并能相應作出外交政策上的調整,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弱國無外交”的鐵律最終導致《雅爾塔協定》給了蔣介石一個響亮的巴掌,在雅爾塔體系所確立的美蘇主宰世界的格局中,中國依然難以擺脫被犧牲和出賣的命運。
六、結語
可以看到,近代以來,隨著各國交往日益頻繁,隨著中國對外關系不斷擴展,國際體系的演變與近代中國的發展一直在進行著各種形式的互動。在國際體系的視角下看待近代中國的變遷,能清楚地看到以下兩個特點。
首先,在國際體系的演變中,中國的態度越來越趨于主動。晚清時的中國在未做好準備的情況下被敲開國門,在相對被動的狀態中接觸到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確立和維也納體系中得到進一步確認的西方國際交往規則,在西方的壓力之下建立了近代外交機制。中華民國成立之后,中國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身份參與到凡爾賽—華盛頓體系當中,中國也開始學會利用國際規則、嘗試收回國家權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于中國人民在反抗日本法西斯戰爭中的浴血奮戰和巨大犧牲,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有所擴大,中國也得以以更加主動的態度參與國際事務。
其次,盡管中國的態度越來越主動,但無論是清政府還是中華民國政府,一個最根本、也是最致命的問題在于,它們都將自身獲得獨立自主的希望寄托于西方國家。它們接受和參與了新的國際體系,也用這些體系來約束自己,卻并沒能認識到,這些體系本身就是建立在忽視和犧牲諸如中國等弱小國家的利益這一基礎之上的。在這樣的體系內部,不可能真正實現中國的強大。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中國以“四強”之一的身份參與反法西斯同盟,卻在戰爭即將結束時被美蘇無情地出賣,就最為明顯地體現了這一點。而對這一問題的突破,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堅定地從中國自身國家利益出發,實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因,也是這一外交政策能真正取得成果的關鍵所在。
注釋:
(1)(3) 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葉篤義譯,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27—28、29頁。
(2)(5) 梁廷枏等纂:《粵海關志》,臺灣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1679—1680、1674頁。
(4) 故宮博物院編:《掌故叢編》,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722頁。
(6) 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2卷,張匯文等譯,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290—291頁。
(7)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1冊,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552頁。
(8) 張斯桂:《萬國公法序》,惠頓:《萬國公法》,丁韙良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頁。
(9) 寶鋆:《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臺灣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3783—3784、3801、3803頁。
(10) 陸奧宗光:《蹇蹇錄》,伊舍石譯,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88頁。
(11) 《國際條約集》(1872—1916),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年版,第436頁。
(12) 《東方雜志》1904年第1卷第4期。
(13) 《東方雜志》1904年第1卷第7期。
(14)(16)(21) 《顧維鈞回憶錄》第1分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2—33、152、26—27頁。
(15) 孫中山:《致北京參議院眾議院電》,《孫中山全集》第4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8頁。
(17) 唐啟華:《北洋外交與“凡爾賽—華盛頓體系”》,金光耀、王建朗主編:《北洋時期的中國外交》,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頁。
(18)(19)(20) 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第3冊,三聯書店1962年版,第222、199、200—201,206頁。
(22) 顧維鈞:《外人在華之地位》,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年版,第209頁。
(23)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二)》,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第539—540頁。
(24) 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綜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6—87頁。
(25) 張篷舟主編:《近五十年中國與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1—303頁。
(26)(27)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2編《外交》,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02頁。
(28)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3編《戰時外交(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第41頁。
作者簡介:陳濤,外交學院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副教授,北京,100037。
(責任編輯 張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