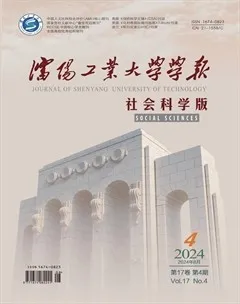侵害品種權合法來源抗辯:理論證成、適用界限與法律后果
摘" 要: 合法來源抗辯是知識產權侵權訴訟中常見的抗辯事由之一,信賴保護原則、善意第三人理論和過錯責任原則為其理論基礎。合法來源抗辯是對品種權人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的限制,為平衡品種權人與善意侵權人的利益,應從行為類型、主觀要件、客觀要件等方面明確其適用界限。構成合法來源抗辯的,侵權人應停止侵害和支付合理開支。應限制停止侵權的適用,可根據具體案件采取支付合理費用、事后許可及取得侵權物等代替救濟方式,按照合理性、真實性、關聯性確定合理開支的數額。善意侵權人所獲利益的返還,應以現存利益為限。我國應借鑒其他知識產權領域立法、他國相關立法以及司法實踐,完善侵害品種權合法來源抗辯制度。
關" 鍵" 詞: 品種權; 合法來源抗辯; 善意侵權; 停止侵害; 合理開支
中圖分類號: D923.4"""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674-0823(2024)04-0430-10
*如無特殊說明,本文所涉法律名稱均按慣例省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字樣。
①TRIPs協定第45條:“對于故意或有充分理由應知道自己從事侵權活動的侵權人,司法機關有權責令侵權人向權力持有人支付足以補償其因知識產權侵權所受損害的賠償。”
②品種權通常又稱為“育種者權利”(Plant Breeders′ Rights,PBR)或“植物品種權”(Plant Variety Rights,PVR),兩種稱謂不同,不過是“一體兩面”問題:前者側重于權利的主體——育種者,后者側重于權利的客體——植物新品種。澳大利亞、加拿大、瑞典、日本、肯尼亞、南非等國的立法采育種者權利的稱謂;歐盟、美國、新西蘭、韓國、越南、泰國、菲律賓等國家或地區的立法采植物品種權的稱謂。我國現行立法采取的是植物品種權的稱謂,簡稱“品種權”。
③參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修正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
④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的統計,共有18件侵害品種權案件涉及合法來源抗辯,其中有12件參照其他知識產權的規定予以判定。
收稿日期: 2023-11-27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23BFX078)。
作者簡介: 萬志前(1974—),男,湖北仙桃人,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農業知識產權等方面的研究。
【法律理論與實務】
DOI:10.7688/j.issn.1674-0823.2024.04.11
一、問題的提出
合法來源抗辯作為知識產權侵權訴訟的抗辯事由之一,最初源于《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以下簡稱TRIPs協定)的規定,即善意侵害知識產權者免于承擔賠償責任①。為與國際知識產權保護規則接軌,我國2000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以下簡稱《專利法》)、2001年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以下簡稱《商標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中分別規定了侵害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的合法來源抗辯事由。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以下簡稱《種子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均無關于侵害植物新品種權(以下簡稱品種權②)合法來源抗辯的規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次會議于2021年8月17日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修正草案)》第72條中原本增加了“合法來源抗辯”條款,即“不知道是未經植物新品種權所有人許可的授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或者收獲材料,能證明該繁殖材料或者收獲材料具有合法來源的,不承擔賠償責任。”然而,該條款在最終審議通過的《種子法》中被刪除,主要原因是侵害品種權行為的認定技術性較強,比較復雜,可由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中具體處理③;且合法來源抗辯會減輕相關當事人的侵權責任,增加了品種權人的維權成本,削弱了品種權保護力度,加之《國際植物新品種保護公約》(以下簡稱UPOV)亦未規定此項抗辯事由[1]。司法實踐中,若被告提出合法來源抗辯,法院往往參照適用其他知識產權制度中的合法來源抗辯制度④。《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二)》(以下簡稱《品種權司法解釋(二)》)第13條認可了這一制度該解釋第13條第1款規定:“銷售不知道也不應當知道是未經品種權人許可而售出的被訴侵權品種繁殖材料,且舉證證明具有合法來源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判令銷售者承擔賠償責任,但應當判令其停止銷售并承擔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但尚有不足。2022年11月24日,農業農村部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修訂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修訂征求意見稿》)第47條從行政執法層面增加了侵權人合法來源抗辯條款該《修訂征求意見稿》第47條規定:“當事人不知道也不應當知道是侵權品種的繁殖材料、收獲材料,并且能夠證明有合法來源的,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農業農村、林業草原主管部門應當責令停止侵權,可以依法免除或者減輕處罰。”,以與《品種權司法解釋(二)》的規定相銜接。
合法來源抗辯是重要的侵權抗辯事由,在《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均有規定的情況下,侵害品種權合法來源抗辯制度的缺失會影響知識產權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和協調性;同時,合法來源抗辯通過對侵權責任的合理分配,能降低銷售者市場活動風險,保障正常的市場經營活動,督促商品銷售者加強進貨渠道管理,在訴訟中披露上游供貨者,以便權利人找到侵權源頭,從根本上打擊侵權行為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終728號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終631號民事判決書。。因此,在立法上設置合法來源抗辯制度實有必要。現有關于合理來源抗辯制度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領域,對侵害品種權合法來源抗辯的研究不多參見郭杰,植物新品種侵權中“合法來源抗辯”適用分析,種子,2022年第6期,第142-148頁;周波,植物新品種案件中的獨占實施許可與合法來源抗辯,人民司法,2021年第5期,第86-89頁。,有待深化。基于此,本文擬以現有研究為基礎,結合種子生產經營的特殊性,參照各知識產權部門法、我國司法實踐等,從理論證成、適用界限、法律后果三方面分析侵害品種權合法來源抗辯制度,并提出完善建議。
二、侵害品種權合法來源抗辯的理論證成
品種權作為知識產權的一種,如同用專利保護工業領域的發明創造一樣,是用專門法律制度保護農業領域的育種創新成果,是維護品種權人合法權益、促進育種創新的根本保障[2]。合法來源抗辯作為侵害品種權的限制,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了品種權保護力度,因此需要從理論上證成其合理性。
1. 信賴保護原則是理論淵源
信賴保護原則又稱“保護合理期待原則”[3],其具體內涵是在交易中行為人對他人的身份資質等信息已盡形式審查義務,依此形式表象產生信賴,并實施相應的民事行為,形成相應的法律后果,即使該法律后果具有一定的違法性,但為了保障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法律應當保護這種信賴利益。正如拉倫茨所言:“只有當必不可少的信賴被保護時,人類才有可能在保障每個人各得其應得者的法律之下和平共處……故促成信賴并保護正當的信賴屬于法秩序必須滿足的最根本要求之一。”[4]合法來源抗辯制度通過免除善意侵權人的損害賠償責任,保護已盡合理注意義務行為人的信賴利益,從而達到保護私法秩序的目的,符合信賴權利外觀保護制度的原理。基于信賴保護原則的合法來源抗辯制度既能將種業企業的知識產權風險控制在合理范圍內,保障其正常運營,免除其顧慮,促進品種權交易,也有助于促使品種權人溯源維權,打擊源頭侵權。
2. 善意第三人理論是法理基礎
善意第三人理論是民法上的一項重要理論,其作為法律上的概念起源于羅馬法取得時效制度中的善意占有,即從非所有人手中取得物品而認為該人是物品的所有人,自己根據正當原因取得占有,因而獲得了整個權利[5]。按照這一理論,如果行為人在實施民事行為時主觀上出于善意且支付了合理對價,則應當根據公平原則保護該善意行為人的權利。知識產權與物權的制度設計以及制度框架下無權處分人的侵權行為具有同構性或同質性,故知識產權侵權中合法來源抗辯制度可類推適用于物權上的善意取得制度[6],以保護善意第三人。在市場交易中,除了保護“靜的安全”(權利不受他人隨意侵害)外,“動的安全”(交易相對人對合法獲得權利的使用過程)同樣需要法律保護[7]。保護善意第三人能引導市場主體規范經營,鼓勵其積極參與市場交易,進而實現“動的安全”,維護交易秩序,提高交易效率,在激勵育種創新與交易安全、保護品種權人與善意第三人權益之間實現適當平衡,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
3. 過錯責任原則是責任基礎
過錯責任原則是指以過錯作為行為人承擔侵權責任的倫理和正義性基礎,行為人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是因為其主觀上具有可以歸責的事由(故意或者過失)[8]。該原則以過錯作為侵權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唯一歸責事由,從積極方面而言,就是“有過錯,或有(賠償)責任”,從消極方面而言,就是“無過錯,必無(賠償)責任”[9]。我國侵權損害賠償以過錯責任為歸責原則,以無過錯責任(又稱嚴格責任)為例外。《民法典》侵權責任編中的責任形式以損害賠償為中心,并以此為基礎區分了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與絕對權請求權,規定了適用于損害賠償責任的過錯責任原則[10]。停止侵害等主張屬于消極防御性絕對權請求權的范疇,此類請求權不以過錯為前提[11],但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則以侵權人過錯為前提。品種權屬于私權,侵害品種權作為一般侵權行為,其侵權責任應與我國《民法典》中一般侵權歸責原則保持一致《民法典》第1165條第1款規定:“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即侵權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需以過錯為前提,而侵權人承擔停止侵害等民事責任則無需考慮過錯。因此,能證明授權品種繁殖材料或者收獲材料合法來源的無過錯者不承擔賠償責任,是遵循損害賠償過錯責任原則的必然結果。如韓國《種子產業法》第86條規定所體現的就是損害賠償過錯責任原則,即品種權持有人或獨占許可被許可人可以向故意或過失侵犯其品種權或獨占許可權的人員請求損害賠償[12]。根據該規定,若侵權人無“故意或過失”(過錯),則不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日本《植物品種保護與種苗法》第34條第1款也有類似規定日本《植物品種保護與種苗法》第34條第1款規定:“育種者權利持有人或排他使用權人,對故意或因過失侵害了自己育種者權利或排他使用權的侵權人請求賠償損失時……”。。此外,我國《專利法》第77條《專利法》第77條規定:“為生產經營目的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售不知道是未經專利權人許可而制造并售出的專利侵權產品,能證明該產品合法來源的,不承擔賠償責任。”、《商標法》第64條《商標法》第64條第2款規定:“銷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冊商標專用權的商品,能證明該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說明提供者的,不承擔賠償責任。”以及《著作權法》第59條《著作權法》第59條第1款規定:“復制品的出版者、制作者不能證明其出版、制作有合法授權的,復制品的發行者或者視聽作品、計算機軟件、錄音錄像制品的復制品的出租者不能證明其發行、出租的復制品有合法來源的,應當承擔法律責任。”均規定了無過錯者不承擔賠償責任,這些都是過錯責任原則的體現。因此,合法來源抗辯免除無過錯者的損害賠償責任,符合一般民事侵權損害賠償的歸責原則。品種權作為一種私權,同樣要遵循一般民事侵權損害賠償的歸責原則,不應予以區別對待,否則會破壞整個私法以及知識產權領域立法的統一性。
綜上,信賴保護原則、善意第三人理論、過錯責任原則三者分別構成了合法來源抗辯的理論淵源、法理基礎和責任基礎,共同證成了合法來源抗辯的正當性。信賴保護原則是理論基礎,善意第三人理論和過錯責任原則是信賴保護原則的具體運用。善意行為人在其主觀不知道且能提供合法來源的情況下免除損害賠償責任,是保護善意第三人信賴利益的具體體現。善意侵權人不承擔賠償責任,也符合侵權損害賠償的過錯歸責原則。
三、侵害品種權合法來源抗辯的適用界限
與其他民事權利相比,知識產權的權利范圍更為模糊[13],品種權亦如此。這種模糊性往往使市場主體因擔心侵權賠償對其敬而遠之。合法來源抗辯作為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的抗辯事由,是對品種權人請求權范圍的限制,能消除市場主體的顧慮,促進品種權交易與利用。同時,這種限制也可能削弱品種權的保護力度,影響育種創新,因此,需要從行為類型、主觀要件、合法來源等方面明確其適用界限,以實現品種權人與善意侵權人之間的利益平衡。
1. 行為類型
對于哪些行為類型可以主張合法來源抗辯,各知識產權部門法以及各國法律有不同規定。一是對所有善意侵權行為均可主張。如韓國《種子產業法》第86條、日本《植物品種保護與種苗法》第34條均規定,不區分行為的類型,只有故意或過失侵權者才承擔賠償損失責任,亦即所有善意侵權行為不承擔賠償責任。我國《修訂征求意見稿》第47條的規定也未限制行為的類型。二是對使用行為、許諾銷售行為、銷售行為可以主張。如《專利法》第77條規定,“為生產經營目的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售”適用合法來源抗辯。三是僅對銷售行為可以主張。如《商標法》第64條第2款、《品種權司法解釋(二)》第13條的規定即是如此。在我國侵害品種權糾紛處理的司法實踐中,法院也僅認可銷售行為適用合法來源抗辯,其他行為則不適用。如在重慶奔象果業公司與九蓮生態農業開發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中參見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21)渝01民初809號民事判決書。,九蓮生態農業開發公司的侵權行為是種植和繁育,法院認定其不符合合法來源抗辯中的“銷售”,故不支持其合法來源抗辯。在侵害品種權糾紛中,銷售行為固然可適用合法來源抗辯,但生產行為、繁殖行為以及進出口行為是否適用,仍需討論。
生產或繁殖行為是否適用合法來源抗辯?可以借助《專利法》中合法來源抗辯的規定加以分析。2000年《專利法》第63條第2款規定,使用或銷售具有合法來源的專利產品構成侵權,但不承擔賠償責任。該規定作為第63條(不視為侵犯專利權)的第2款,邏輯上存在問題。因此,2008年《專利法》第70條將“合法來源抗辯”作為獨立條款加以規定,同時增加了“許諾銷售行為”的類型,但沒有規定制造行為。2020年修改的《專利法》仍然沒有將制造行為納入合法來源抗辯的范圍,其原因在于,制造專利侵權產品的行為是其他侵權形態的基礎行為,專利法對專利產品的制造提供的是一種“絕對保護”[14]96-97,因此不論制造者是否具有主觀故意,只要是為生產經營目的、未經授權且無法律規定的例外,則制造專利產品構成侵權行為,應承擔包括損害賠償在內的侵權責任。品種權所控制的生產或繁殖行為類似專利權所控制的制造行為,故為從源頭上加強品種權保護,生產或繁殖行為不適用合法來源抗辯。
若生產行為涉及的是農民根據農業農村部辦公廳《關于種子法有關條款適用的意見》(2019年1月4日)的規定,農民是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形式簽訂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的農民個人,不包括合作社、種糧大戶、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種植行為,則這種行為類似專利法中的使用行為。此種情況下農民是否可以主張合法來源抗辯,需要分兩種情況討論。一是農民種植自己所留種子,若符合農民留種豁免條件,則其留種種植行為不構成侵權,無需適用合法來源抗辯;若農民留種不符合豁免條件,如留種的數量或種植的面積超過法律規定的邊界,則構成侵權,農民不能以不知道法律規定為由,主張其為善意而構成合法來源抗辯。若農民無意留種(如基因漂移),根據2002年Monsanto Canada Inc.v.Schmeiser案的判決,農民的主觀意圖應當作為其是否承擔侵權責任的考慮因素,以避免農民的善意誤植被視為專利侵權[15]。但這種情況多為自然因素引起,不屬于合法來源抗辯的情形。二是農民所種植的授權品種繁殖材料來源合法,但所購買的繁殖材料侵權。此種情況下有兩種制度安排:其一,農民主張合法來源抗辯,可免除侵權賠償責任,但要停止侵權,即銷毀繁殖材料或不得繼續種植;其二,農民的種植行為不構成侵權,如依據印度《2001年植物品種和農民權利保護法》第42條規定印度《2001年植物品種和農民權利保護法》第42條規定:“依據本法確立的權利受到農民侵犯,但該農民當時并未意識到該權利存在的,不應當視為侵權。”參見朱建國,鄒萍:《亞洲部分國家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文獻匯編》,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05頁。,農民的無意侵權行為不構成侵權,不承擔侵權責任。對此本文認為,若農民符合法律規定的特定身份,且能證明被訴侵權的授權品種繁殖材料具有合法來源,則不構成侵權;若為不符合法律規定的農民身份(如種糧大戶、家庭農場等),則構成侵權,但可以主張合法來源抗辯,免除侵權賠償責任。
進口或出口行為是否適用合法來源抗辯?此種情況可以借鑒其他知識產權領域的判例加以分析。在丹納赫西特傳感工業控制(天津)有限公司訴趙元鴻等侵害商標權糾紛案參見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4)滬一中民五(知)終字第78號民事判決書。中,進口商(侵權人)提出了合法來源抗辯。法院認為,外國公司在中國境外生產制造被控侵權產品,該行為本身并不侵犯在中國的注冊商標專用權,但進口至我國境內并銷售被控侵權產品將直接導致該產品在涉案商標受保護的法域內從無到有。進口商對侵權產品的銷售構成該產品在商標注冊國市場上的最初流通,其行為與生產或制造行為性質相似,因此應承擔與生產商相同的侵權責任,包括賠償責任。此外,進口商對進口商品是否侵犯他人商標權應負有較高的注意義務,不能以“不知道”為由免除賠償責任。因此,進口或出口行為不適用合法來源抗辯。
《品種權司法解釋(二)》第13條僅規定了銷售行為的合法來源抗辯,2021年修改的《種子法》則增加了品種權對許諾銷售行為的控制。由此推斷,許諾銷售行為也應當適用合法來源抗辯。既然實際銷售行為都可以主張合法來源抗辯,舉重以明輕,發生在實際銷售行為之前的許諾銷售行為更有主張合法來源抗辯的理由。綜上,品種權類似專利權,合法來源抗辯的適用行為類型應借鑒《專利法》相關規定,即使用行為(種植行為)、銷售行為、許諾銷售行為均可適用合法來源抗辯。
2. 主觀要件
關于合法來源抗辯主觀要件的規定,國內各知識產權部門法以及各國立法有所不同。有的從正面規定,即“不知道”(實際不知道且不應當知道)為適用合法來源抗辯的主觀要件,如《專利法》第70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25條該解釋第25條第1款規定,“為生產經營目的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售不知道是未經專利權人許可而制造并售出的專利侵權產品……”;第2款將“不知道”解釋為“實際不知道且不應當知道”。的規定即是如此。有的從反面規定,即“故意或過失”不適用合法來源抗辯,品種權人可以向故意或過失侵害品種權的侵權人請求損害賠償,如韓國《種子產業法》第86條、日本《植物品種保護與種苗法》第34條、印度尼西亞《植物品種保護法》第67條第1款印度尼西亞《植物品種保護法》第67條第1款規定:“植物品種保護權所有人或者被許可人或者強制許可獲得人有權通過國家法院對無權行使本法第6條規定的行為卻故意為之的任何人提出損害賠償。”的規定即是如此。《品種權司法解釋(二)》將合法來源抗辯的主觀要件表述為“不知道也不應當知道”,屬于從正面規定。
關于知識產權法中“不知道”的內涵,學術界和實踐中有不同理解。一種觀點認為,“不知道”應當被理解為“實際得知”的反義詞,包括不可能知道和應當知道而實際并不知道[14]645。另一種觀點認為,不知道不包括“應當知道而實際不知道”的情形[16]。兩者的分歧在于,“不知道”是否包含“應當知道而實際不知道”。合法來源抗辯旨在免除無過錯方的賠償責任,而“應當知道而實際不知道”是一種主觀上的過失,如果將此種情形包含在“不知道”范圍內,那么侵權人很容易以此為由規避侵權損害賠償責任。為平衡品種權人與侵權人之間的利益,“不知道”中應當排除“應當知道而實際不知道”的情形。品種權是一種絕對權,任何人不得以不知曉他人的品種權為由而主張“不知道”。因此,“不知道”作為“實際得知”的反義詞,解釋為客觀上的不知道更為妥當[17],即侵權人在實施侵權行為時,并未意識到其行為構成侵權,強調的是一種客觀事實狀態。
“不應當知道”的反面是“應當知道”。“應當知道”一詞被用來指稱下述事實:具有正常理智與智力或超常智力的人在履行對他人的義務時,應當以審慎的態度確定有關事實是否存在,或者根據該事實存在的假設控制其自身的行為[18]。“應當”引導的法律規范屬于弱強行性規范[19],“應當”作為規范性概念,可以引導涉及價值判斷的規則,并為主體創設實體性義務[20]。故盡管侵權人可能確實不知道侵權事實存在,但法律不允許其因不知道該事實而主張不構成侵權。《品種權司法解釋(二)》將侵害品種權合法來源抗辯的主觀要件規定為“不知道也不應當知道”,對善意侵權人設置了較高的注意義務,可以督促其在交易前深入了解相關信息,謹慎交易,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品種權人的傾斜保護,這也是種子交易市場的嚴格監管要求使然。
法院在認定合法來源抗辯者是否符合主觀要件時,往往將“知道或應當知道”之義務轉化為合理的注意義務。注意義務是指行為人在特定情形下所必須遵循的行為準則以及依該準則而采取的合理防免措施[21]。在河南鑫民種業公司、中種聯豐種業公司等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終2485號民事判決書。等案件中,因銷售者未盡到合理的注意義務,合法來源抗辯理由未獲法院支持。在鄭州市二七區百領水果種植園與中國農業科學院鄭州果樹研究所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終592號民事判決書。中,法院認為百領水果種植園作為專業種植樹苗的經營者,對經營行為的合法性應負有較高的注意義務。將“知道或應當知道”轉化為合理的注意義務,其實是將主觀問題客觀化,即通過可衡量的外在客觀因素判斷抗辯者的主觀狀態。法院對是否盡到合理注意義務的判斷,應綜合考慮權利客體的可識別性、抗辯者的審查能力、第三方的信賴程度、抗辯者與第三方責任能力的對比以及產品的表面合法性等因素[22]。同時,法院應遵循合理限定原則,將注意義務限定在一定范圍內,既要加強行為人對他人、對社會的責任心,又不能無限擴大注意義務,使人因所要求的注意程度太高而“無法注意”,從而影響其正常業務和行為[23]。由于種子生產、經營的特殊性,生產經營者對其經營的植物新品種來源有較嚴格的注意義務,但對此也要把握適當的度,如果太過嚴苛,將會影響種子交易市場的活力。
關于主觀要件的舉證責任分擔,大致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即抗辯人證明說和權利人證明說。抗辯人證明說主張依據“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由抗辯者舉證證明“不知道也不應當知道”[24]。此種舉證責任分擔對品種權人或被許可人有利,對于侵權人所列證據,品種權人或被許可人有權舉出相反證據予以駁斥。權利人證明說認為,“不知道也不應當知道”應由原告承擔舉證責任,即由品種權人或被許可人證明侵權人知道或應當知道在廣東雅潔五金有限公司訴楊建忠、盧炳仙侵害外觀設計專利權糾紛再審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87號民事判決書指出:“對于主觀善意的成立要件,需要侵權產品使用者、銷售者證明其不知道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售的是侵權產品,這是一種消極事實,根據消極事實的證明規則,一般應由權利人來證明侵權者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所使用、許諾銷售或者銷售的是侵權產品,從而否定合法來源抗辯的成立。”。有觀點認為:“根據舉證責任分配的一般規則,作為消極事實的‘不知道’,通常不由提出該主張者承擔舉證責任;而主張積極事實(知道或應當知道)的一方應當對其主張承擔舉證責任。”[25]據此,“不知道”作為消極事實,侵權人難以直接舉出證據予以證明,舉證責任應轉移至權利人,即由權利人舉證證明侵權人“知道或應當知道”。其實,消極事實與積極事實并非相互沖突[26],二者通常難以完全區分,僅是語言文字上的轉化。“不知道也不應當知道侵權”的消極事實,當其被表述為“善意侵權”時,就是一種積極事實。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往往采取抗辯人證明說,同時,將侵權人“不知道也不應當知道”的主觀心理狀態轉化為客觀的合理注意義務,由侵權人舉證證明其是否已盡合理的注意義務。在安徽皖墾種業公司訴安徽省壽縣向東汽車電器修理部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參見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皖01民初749號民事判決書。中,法院認為,銷售者應當在查清繁殖材料來源的基礎上,進一步審查該繁殖材料的提供者是否依法取得了相應生產經營許可證或者是否屬于法定無需辦理生產經營許可證的情形,但銷售者未盡到此種注意義務,因此存在主觀過錯。
3. 客觀要件
合法來源抗辯的客觀要件是侵權產品有合法來源,包括來源明確與來源合法。來源明確是一個客觀事實判斷,而來源合法則兼具事實認定與法律評價色彩[27]。來源明確的具體含義是侵權人應當提供前手供貨方的具體信息,以明確侵權產品來源者身份。抗辯者僅提供侵權產品來源線索而無法確定來源主體身份信息的,不滿足來源明確的要求,否則,通過合法來源抗辯制度披露被訴侵權產品、溯源追蹤侵權人、打擊源頭侵權和維護種業市場秩序的目標難以實現。在山東登海先鋒種業公司訴新絳縣華豐種業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知民終796號民事判決書。中,因華豐種業公司未提供河南太谷農業科技有限公司民事主體資格和向其銷售侵權種子的相關證據,法院未支持侵權人的合法來源抗辯。《品種權司法解釋(二)》第13條第2款規定,銷售者一般應當舉證證明“存在實際的具體供貨方”,實際上是對來源明確的要求。對實際供貨方信息的證明要求可以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關于被告具體信息的要求,如自然人的身份證明及其他個人信息、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的工商登記資料等信息。
對來源合法的證明往往需要提供完整的證據鏈,以證明侵權產品的獲得過程,該過程應當圍繞侵權產品從前手到后手的交易展開,通常情況下可以通過買賣合同、轉賬記錄或憑證體現。如在江蘇保豐集團公司訴新沂市禾源種業有限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09)蘇民三終字第0069號民事判決書。中,禾源公司為證明其銷售的小麥品種來源合法,提供了購種協議、收款單、留村農場的種子生產許可證、種子經營許可證以及加蓋留村農場印章的購種協議等證據,以證明禾源公司系從留村農場購得被控侵權小麥品種。因此,法院支持了禾源公司的合法來源抗辯。但在種業經營領域,因經營者的證據意識較弱以及交易習慣影響,抗辯者往往不能提供體現侵權產品交易全過程的證據,難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對此,應針對不同規模的抗辯主體區分證明標準。若經營主體經營規模較大、財務制度較規范,應當提供完整、規范的交易過程憑據;若經營主體為規模較小、財務制度不健全的個體工商戶或個人,則不應苛求其證據的完備性。此外,來源合法不僅要求購貨渠道合法,而且包含銷售者或許諾銷售者自身的銷售資質合法,即要求銷售者提供相關種子生產經營許可、授權書以及營業執照等證明材料。《品種權司法解釋(二)》第13條第2款規定,銷售者一般應當舉證證明“購貨渠道、價格、生產經營許可證等”,實際上是對來源合法的證明要求。當然,還應當根據證據本身與被控侵權行為及被控侵權產品之間內容和時間上的關聯性判斷來源是否合法[28]。
四、侵害品種權合法來源抗辯成立的法律后果
侵害品種權合法來源抗辯成立,抗辯者仍構成侵權,可以免除損害賠償責任,但應當停止侵害并支付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
1. 停止侵害
停止侵害是指權利人要求侵權人停止正在進行(而非已經停止或尚未實施)的侵害絕對權的行為[29]。侵害絕對權的救濟應以停止侵害為主[30],以制止侵權行為,防止侵害進一步擴大。但在知識產權領域,一旦侵害事實發生便施以停止侵害責任過于絕對。絕對化的停止侵害救濟模式源于對知識產權的物權化理解和對知識產權排他性的錯誤認識[31]。不加限制地行使停止侵害請求權,會對自由市場競爭、技術創新等造成負面影響,有悖知識產權保護的宗旨[32]。知識產權侵權救濟在保護權利人權利、實現社會經濟秩序安定的同時,還要使個體效率與個體成本、社會效率與社會成本達到最佳配置[33]。因此,不應絕對化地適用停止侵害,可考慮適用替代性措施。然而,盡管法院可以在認定某一行為構成侵權的同時不判令行為人停止侵害,但侵權行為的存在意味著對權利人市場份額和預期收益的繼續侵占,因此,判令“不停止侵權”并不能成為法律責任承擔的終點[34]。正如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當前經濟形勢下知識產權審判服務大局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當不宜適用停止侵害時,可以采取更為合適的替代性措施。司法實踐中,對替代性措施也多有采用在南京現代雕塑中心著作權糾紛案中,法院認為銷毀被訴侵權產品會使個體利益失衡,因此不支持停止侵害。在2006年廣州新白云機場幕墻專利侵權糾紛案中,法院認為,考慮到機場的特殊性,停止使用不符合社會公眾利益,因此準許其使用被控侵權產品,但應支付使用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植物新品種權糾紛案件具體應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一)》(以下簡稱《品種權司法解釋(一)》)第7條第2款規定,侵權物正處于生長期或者銷毀侵權物將導致重大不利后果的,可以不采取責令銷毀侵權物的方法,但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相較而言,《農業植物新品種權侵權案件處理規定》第10條所規定的“銷毀生產中的植物材料,已獲得繁殖材料的,不得銷售”,《品種權司法解釋(二)》第14條所規定的“責令采取消滅活性等阻止被訴侵權物擴散、繁殖的措施”等停止侵害的簡單處理方式值得商榷。因為此類處理方式對權利人不具有任何效用,權利人無法從該滅活處理行為中獲得損害補償,且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因此,處理有價值的侵權產品不能簡單地“一毀了之”或“一禁了之”,而應當考慮其他替代性措施。
根據《品種權司法解釋(一)》的規定,侵權物正處于生長期或者銷毀侵權物會導致重大不利后果的,可以采取替代性措施。此外,適用停止侵害影響社會公共利益、導致當事人之間利益失衡或停止侵害難以實際履行、無益于彌補權利人損失等時,也可以考慮采取替代性措施。停止侵害的替代性措施可以是支付合理費用、事后許可以及由權利人獲得侵權產品或收獲物等。支付合理費用由品種權人或被許可人與侵權人協商確定,協商不成的,由法院參照品種權的許可費確定。事后許可是指由侵權人與權利人達成許可協議,支付許可費,變侵權實施為合法實施。如果在不違反法律法規的情況下采取事后許可方式,可避免造成破壞交易秩序、浪費資源等消極后果,產生侵權方與權利人各得其所的“雙贏”積極效果。事后許可與支付合理費用有一定相似性,兩者的不同之處在于是否具有時間上的延續性:支付合理費用屬于一次性行為,侵權人將其當前持有的被訴侵權植物新品種進行銷售或使用等處理后,應當停止后續侵權行為;而事后許可意味著侵權人對當前持有侵權物進行處理后,仍可基于權利人的事后許可繼續銷售或使用。此外,還可以由品種權人或被許可人與侵權人協商取得侵權產品或被訴侵權繁殖材料的收獲物,以彌補因合法來源抗辯成立而不能請求損害賠償的損失。此種情況下,權利人應支付給善意侵權人必要費用。
2. 支付合理開支
合理開支是指因知識產權遭受不法侵害,權利人為查明侵權事實、收集證據、制止侵權行為或進行訴訟所支出的、能夠得到法律認可的各種費用,主要包括侵權行為調查、取證的合理費用以及律師費。訴訟維權的合理開支體現為當事人獲取(接近)正義的成本[35]。當合法來源抗辯成立時,權利人主張的損害賠償雖然得不到支持,但為維權而支出的合理費用應當得到補償。
品種權人或被許可人在訴訟過程中涉及查明事實、搜集材料等工作。在此過程中,權利人首先需要購買涉嫌侵權的授權品種繁殖材料,并對購買的繁殖材料是否與其受保護品種的繁殖材料一致進行公證和鑒定,由此產生的購買費、公證費、鑒定費以及交通費、差旅費等都屬于調查取證費用,應當由侵權人支付。但并非全部調查取證費用都應由侵權人承擔,必須對費用用途進行真實性、關聯性、合理性審查。真實性是指權利人主張的費用必須真實存在,而不能借合理支出之名獲得不義財產。權利人應對自己所主張的合理支出進行舉證,出示收據或發票等能夠證明交易真實存在的證據。關聯性是指該支出是否與調查事實、收集證據以及制止侵權行為存在相關性。合理性又可理解為必要性,即權利人主張的合理開支是否為調查取證所必要。若來源提供者被列為案件的共同被告或第三人,則在侵權行為成立時合理支出應當由其承擔,除非合法來源抗辯者自己愿意承擔合理支出。因為合法來源抗辯者無主觀過錯,而侵權產品來源提供者具有主觀過錯,兩者作為共同被告,若由無過錯的合法來源抗辯者支付合理開支,明顯不公[36]。
在侵害品種權訴訟中,權利人往往會委托律師,由此產生的律師費應計入為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律師費一般由當事人和律師事務所約定,基于地域差異,律師費收費標準可能存在較大差異。對此,法院同樣需要進行合理性、真實性、關聯性審查,以確定律師費用的具體數額。對律師費的合理性審查主要包括委托合同所約定律師費是否明顯高于正常行業收費慣例,服務費用究竟包括哪些內容,以免對合理開支的重復賠償。真實性審查同調查取證費用一致,合理的律師代理費必須以執業律師已實際收取費用的正規票據為證據[37]。關聯性審查主要涉及委托合同的內容,以查證該委托是否針對所涉植物新品種侵權糾紛,避免侵權人對品種權人的其他委托支出進行賠償。
3. 返還所獲利益
對于善意侵害品種權所獲利益是否應當返還,大部分國家法律并未明確規定,我國司法解釋對此亦未提及。判斷是否應當返還,首先需要明確善意侵權所獲收益的性質。有觀點認為,善意侵權所獲收益符合不當得利的構成要件,性質上屬于不當得利[38]。按此觀點,善意侵權所獲收益應當返還,因為不當得利規范的目的乃在去除“受益人”無法律上原因而得到的利益,而非在于賠償“受損人”所受的損害,故受益人是故意或過失,其行為是否具有可資非難的違法性,均所不問[39]。另有觀點認為,適用不當得利實際上是變相地要求善意侵權人承擔賠償責任,不能將侵權收益認定為不當得利[40]。本文認為,侵權人因其善意侵權客觀上獲得了無法律依據的利益,權利人因侵權行為而受到損失,且權利人所受的損失與善意侵權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故構成不當得利,應當予以返還。行為人侵害他人權益縱無過失(善意),也不應當保護其所獲得的利益,這是公平原則的基本要求[41]。善意侵權所獲利益應當返還在有關規范中也得到了體現。如TRIPs協議第45條第2款后半句規定:在適當情況下,各成員可授權司法機關責令其退還利潤和/或預先確定賠償金(pre-established damages),即使侵權人不是故意或沒有充分理由知道自己從事侵權活動。
考慮到侵權人的主觀善意,不當得利的返還范圍應限定于現存利益。“利得人為善意者,僅負返還其現存利益之責任;所謂現存利益,系指利得人所受利益中于受返還請求時尚存在者而言;于為計算時,利得人茍因該利益而生具因果關系之損失時,如利得人信賴該利益為應得權益而發生之損失者,于返還時亦得扣除之,蓋善意之利得人只須于受益之限度內還盡該利益,不能因此更受損害。”[42]“善意之利得人,惟于現存利益之限度內負返還之義務……現存利益,謂利得人所受利益中于受返還請求時尚存在者而言。現已消滅者,不問消滅原因如何,利得人不負其責。”[43]根據我國《民法典》第986條規定,主觀善意的不當得利人僅返還現存利益,取得利益不存在的,不承擔返還利益的義務。返還現存利益時,應當扣除必要的費用。善意侵權人在實施侵權行為時會產生一些費用,如購入侵權植物品種的成本費用、經營場所的租金、運輸費用等,在返還不當得利時此類費用應當扣除。
五、結" 論
侵害品種權合法來源抗辯制度作為平衡權利人和善意侵權人利益的一種重要制度安排,以信賴保護原則、善意第三人理論以及過錯責任原則為其理論基礎。基于植物新品種保護的特殊性,目前我國尚未在立法層面規定合法來源抗辯,僅通過司法解釋加以規定且表述較為簡單。基于上文分析,我國《種子法》和《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應在現有司法解釋基礎上,參照《專利法》《商標法》和有關立法的規定,設置合法來源抗辯制度。就合法來源抗辯的適用行為而言,應在現有司法解釋所規定的“銷售行為”基礎上,擴展至使用行為(種植行為)、銷售行為和許諾銷售行為;在主觀方面,可保留現有表述方式,即“不知道也不應當知道”,以嚴格界定合法來源抗辯的適用條件;在客觀方面,應明確“合法來源”的具體內涵;鑒于《種子法》已將品種權保護延伸至收獲材料,故應將侵權對象由“被訴侵權品種繁殖材料”擴展至“被訴侵權品種繁殖材料或收獲材料”;明確善意侵害品種權所獲利益應當返還,但應以現存利益為限。
法院應根據具體案情靈活適用侵害品種權合法來源抗辯制度。在司法實踐中,品種權侵權人主張合法來源抗辯鮮有成功之例,其主要原因在于對合法來源抗辯的證明標準缺乏明確具體規定,加之通過提高植物新品種保護水平以實現種業振興的戰略要求,法院在認定合法來源抗辯時,往往會對相關證據進行嚴格審查,從而大大增加了證明難度,難以實現合法來源抗辯的制度功能。因此,法院應當結合個案對不同類型的侵權人課以不同的證明責任,對證明能力較強的侵權人課以較重的舉證責任,對證明能力較弱的侵權人適當降低證明標準。在適用停止侵害時,法院應根據個案情況采取支付合理費用、事后許可等替代性方式,以平衡各方利益,并在審查合理性、真實性與關聯性的基礎上確定合理開支數額。
總之,我國植物新品種保護制度在體現加大種業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政策要求如2021年,國務院印發《“十四五”國家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規劃》要求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要求強化種業知識產權保護;2022年,《關于保護種業知識產權打擊假冒偽劣套牌侵權營造種業振興良好環境的指導意見》要求嚴厲打擊侵害種業知識產權行為;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加強知識產權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專門提出“深入實施種業振興行動”。以及考慮侵害品種權特殊性的同時,立法上應設置合法來源抗辯制度,至于侵害品種權合法來源抗辯的適用難點,可通過不斷豐富的司法實踐加以解決。
參考文獻:
[1]劉振偉.努力提高種業知識產權保護法治化水平——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種子法》修改 [J].中國種業,2022(2):1-4.
[2]劉振偉,張桃林.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制度 [M].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22:23.
[3]宋承恩.信賴保護原則的實質面向——英國法之啟發 [J].月旦法學雜志,2002(4):272-286.
[4]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 [M].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351.
[5]優士丁尼.法學階梯 [M].徐國棟,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147.
[6]黃建文.合法來源抗辯適用善意取得制度審查的合理性分析 [J].知識產權,2016,26(10):32-38.
[7]戴秋燕,寧立志.專利善意侵權的法理分析與制度完善 [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48(2):61-72.
[8]張新寶.侵權責任法 [M].5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16.
[9]程嘯.侵權責任法 [M].3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112-113.
[10]王利明.我國《民法典》侵權責任編損害賠償制度的亮點——以損害賠償為中心的侵權責任形式 [J].政法論叢,2021(5):15-24.
[11]吳香香.中國法上侵權請求權基礎的規范體系 [J].政法論壇,2020,38(6):172-181.
[12]朱建國,鄒萍.亞洲部分國家植物新品種保護法律文獻匯編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23.
[13]張振鋒.論知識產權濫用的界定 [J].沈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14(1):73-80.
[14]尹新天.新專利法詳解 [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2.
[15]吳亮.農民留種行為與品種權的沖突及其解決——立足于美國“農民留種免責”規則的考察 [J].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5(6):73-80.
[16]馮曉青.商標侵權專題判解與學理研究 [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0:99.
[17]歐修平.知識產權法中“不知道”的含義 [J].人民司法,2012(5):91-94.
[18]許傳璽,石宏,和育東.侵權法重述第二版:條文部分 [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7.
[19]謝暉.“應當參照”否議 [J].現代法學,2014,36(2):54-66.
[20]麻昌華,陳明芳.《民法典》中“應當知道”的規范本質與認定標準 [J].政法論叢,2021(4):127-138.
[21]廖煥國.注意義務與大陸法系侵權法的嬗變——以注意義務功能為視點 [J].法學,2006(6):28-33.
[22]李潔.知識產權審判中合法來源抗辯之審查 [C]//最高人民法院.探索社會主義司法規律與完善民商事法律制度研究——全國法院第23屆學術討論會獲獎論文集(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460-468.
[23]晏宗武.論民法上的注意義務 [J].法學雜志,2006,27(4):144-146.
[24]徐卓斌.專利侵權糾紛中合法來源抗辯的主觀要件 [J].法律適用,2022(12):96-106.
[25]呂娜.知識產權侵權訴訟中的合法來源抗辯——以專利侵權訴訟為例 [J].人民司法,2007(19):83-88.
[26]李秀芬.從訴訟證明的角度看消極事實的特征 [J].法學論壇,2006,21(4):90-93.
[27]陳中山.合法來源抗辯的審查認定 [J].人民司法,2019(28):36-40.
[28]王儲.知識產權侵權訴訟中“合法來源抗辯”的認定 [J].社會科學戰線,2020(8):267-271.
[29]程嘯.侵權責任法教程 [M].4版.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375.
[30]黃金菊,陶恩萍.不可量物民事侵權救濟制度比較研究 [J].沈陽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6(1):92-96.
[31]陳武.權利不確定性與知識產權停止侵害請求權之限制 [J].中外法學,2011,23(2):357-368.
[32]張云鵬,張嘯天,王娜,等.論涉罪企業合規的刑行銜接 [J].遼寧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24(2):58-64.
[33]楊濤.知識產權法中的停止侵害救濟制度 [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7,35(5):101-114.
[34]王國柱.知識產權侵權責任承擔方式的特殊法理 [J].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22,40(4):114-125.
[35]陳志興.專利侵權訴訟中法定賠償的適用 [J].知識產權,2017,27(4):29-34.
[36]朱文彬.論合法來源抗辯成立時合理費用承擔的認定——汪文旭訴誠立公司侵害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評析 [J].科技與法律,2013(3):85-91.
[37]竇玉梅.因制止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費用之確定 [J].人民司法,2008(11):42-44.
[38]張玉敏.侵害知識產權民事責任歸責原則研究 [J].法學論壇,2003,18(3):20-28.
[39]王澤鑒.不當得利 [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3.
[40]樂耀.論專利善意侵權案件中不當得利制度的不可適用性——兼評《專利法》第70條 [J].金陵法律評論,2017,26(1):197-221.
[41]鄒海林.侵害他人權益之不當得利及其相關問題 [J].法學研究,1996,18(5):153-161.
[42]王澤鑒.債法原理·不當得利 [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216-217.
[43]史尚寬.債法總論 [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92.
Legitimate source defense for infringement of variety right: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application boundary and legal consequences
WAN Zhiqiana,b, WANG Zijiea,b
(a.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b. Agricultural and Rural Rule of Law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Legitimate source defense is one of the common defense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which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eliance protection, the bona fide third-party theory, and the principle of fault liability. The legitimate source defense is a restriction on the right to claim damages for infringement.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variety right holder and the bona fide infringers, its application boundaries should be clarified in terms of the types of acts, subjective elements and objective elements. If the legitimate source defense is established, the infringer shall cease infringement and pay reasonable expenses. The application of cessation of infringement should be replaced by such remedial means as payment of reasonable expenses, post-facto licenses, and obtaining infringing objects, and the amount of reasonable expenses should be determi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reasonableness, truthfulness and relevance. The return of benefits obtained by bona fide infringers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existing benefits. China should draw on the legislation in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fields, relevant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in other countries, so as to improve the defense system of legitimate source of infringement of variety rights.
Key words: variety right; legitimate source defense; bona fide infringement; cessation of infringement; reasonable expense
(責任編輯:郭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