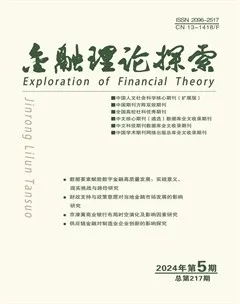京津冀商業銀行布局時空演化及影響因素研究


















摘" "要:基于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登記的商業銀行微觀統計數據,綜合利用空間熱點聚類、最鄰近指數(NNI)、Ripley's K函數、復合年增長率(CAGR)和標準差橢圓等研究方法,對京津冀商業銀行分布時空格局演化、集聚特征和熱點區分布特性進行研究,并進一步研究了其影響因素。研究結果表明: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分布不均勻,京津冀整體和三地局部尺度上均表現出顯著的空間集聚特征;空間集聚程度隨著觀測距離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熱點區主要分布在以北京市、天津市、邢臺市和廊坊市為核心的集聚區內,呈現“主次型”單一結構;工業化水平和政府行為是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集聚的核心影響因素,城市環境、經濟發展水平對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集聚的影響程度逐年增強。
關" 鍵" 詞: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演化;金融地理學;泊松回歸
中圖分類號:F832;F205" " " 文獻標識碼:A" " " "文章編號:2096-2517(2024)05-0047-12
DOI:10.16620/j.cnki.jrjy.2024.05.005
一、引言
2024年是京津冀協同發展重大國家戰略實施十周年, 十年間京津冀三地在區域產業結構升級、交通一體化水平提升、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但仍面臨著京津冀區域內部GDP差距擴大、區域空間結構有待優化等新問題[1]。其中,京津冀三地金融體系建設被視為推動京津冀區域經濟融合發展和空間結構優化的關鍵因素。作為金融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商業銀行承擔著資金存儲、信貸支持、支付結算等基礎金融服務功能,在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塑造發展形態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深入研究京津冀商業銀行網點分布的時空演化及影響因素,有助于優化金融資源配置、 提高金融服務覆蓋度,對于實現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加快京津冀協同發展步伐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空間分布綜合反映了所在地區金融生態的發展狀況, 正逐漸成為金融地理學領域的研究熱點。金融機構空間布局是金融地理學領域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作為一門交叉學科,金融地理學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20世紀80年代迅速興起,2008年金融危機后金融地理學的學科范式逐漸成熟,以地理學視角研究金融領域問題進入繁榮發展階段[2-4]。對于金融機構時空演化問題,已有學者以中原城市群為例研究了欠發達地區金融機構的空間格局、集聚特征、熱點分區以及空間集聚的影響因素[5],分析了基于銀行、保險和證券三個主流細分行業的中國城市群金融網絡演化問題[6]。也有學者關注金融機構之間的網絡特征及演化分析,利用鏈鎖網絡模型就中國城市間金融網絡的空間演化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揭示了關鍵資源、空間距離、區位條件和歷史基礎因素對空間演化的顯著影響[7]。雖然也有文獻的研究區域涉及京津冀地區[8-11],但專門針對京津冀地區金融機構空間演化問題展開的研究仍較少。
金融機構空間布局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已有研究主要從居民收入[5]、對外交通[5]、金融關聯度、區位條件、政府治理、產業布局[12]、經營成本[13]等角度展開分析,發現城鄉居民儲蓄、對外交通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區位優勢、第一產業發展水平等因素對商業銀行空間布局的集聚水平具有正向促進作用[5],而移動互聯網發展、勞動力成本和市場競爭加速了線下銀行網點的退出[13]。
金融機構空間布局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對于優化金融資源配置和促進區域發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然而,目前針對京津冀地區這一重要城市群的相關研究較為匱乏,為了全面系統地了解該區域的金融服務布局發展狀況,迫切需要基于商業銀行微觀數據的實證研究以及長時間尺度下的空間布局演化分析。因此,本文以京津冀地區的13個城市作為研究對象,并參照相關研究[14-15],利用1990—2023年京津冀商業銀行數據,借助空間熱點聚類展現京津冀商業銀行各階熱點區的動態變化過程[16]。同時,通過最鄰近指數探究1990—2023年京津冀全局和三地局部集聚的單尺度特征[17],并運用Ripley’s K函數進一步分析京津冀商業銀行分布的多尺度集聚特征[18],最后進行集聚程度演化模式分析。此外,本文還繪制標準差橢圓[19]以探究集聚重心的動態演化過程。 由于2022年和2023年社會經濟統計數據缺失, 本文選取了1990—2021年京津冀商業銀行集聚水平數據(平均最鄰近距離),使用泊松回歸模型實證檢驗了各類宏觀和微觀因素對商業銀行集聚水平的實際影響,包括工業化水平、經濟發展水平、政府行為、對外交通、區域面積、城市環境、人力資源、科技投入、城鎮化率和人口密度等十個具體指標。本文的研究旨在推動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布局優化,為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參考。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1.空間熱點聚類
本文采用最近距離層次聚類分析方法對京津冀商業銀行分布的熱點區域進行識別,在CrimeStat-IV軟件中設定每個聚類級別的最小點數閾值為10。為了確保模擬結果的精確性,將Monte-Carlo模擬的次數設定為2000。
2.最鄰近指數
最鄰近指數(Nearest Neighbor Index,NNI)主要用來衡量一個區域內點要素的實際最鄰近距離(DN)與在隨機分布假設下的理論平均距離(DR)的比值,從而描繪點集合的空間分布形態[20]。
式(1)中,NNI表示最鄰近指數;di代表商業銀行i與其最鄰近商業銀行之間的地理距離;A代表京津冀的地理面積;n代表京津冀商業銀行數目。當NNI=1時, 表明商業銀行在京津冀呈現隨機的空間分布;當NNIlt;1時,表明商業銀行在京津冀呈現集聚的空間分布;當NNIgt;1時,表示商業銀行在京津冀呈現均勻的空間分布。
3.集聚性演化模式分析
CAGR,即復合年增長率(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衡量在特定時間段內京津冀各市域或區域內商業銀行集聚程度年均增長率。
式(2)中,CAGR表示復合年增長率,將閾值設定為2%;SVi代表時間段開始時的商業銀行i與其最鄰近商業銀行之間的地理距離;EVi代表時間段結束時的商業銀行i與其最鄰近商業銀行之間的地理距離;n代表時間段年數,時間段分隔為1990—2000年、2000—2010年、2010—2020年、2020—2023年。當|CAGR|lt;2%時,表明該區域商業銀行在設定的時間段內呈聚集程度穩定型;當CAGRlt;-2%時,表明該區域商業銀行在設定的時間段內呈聚集程度增長型;當CAGRgt;2%時,表明該區域商業銀行在設定的時間段內呈聚集程度下降型。
4.多距離空間聚類分析(Ripley's K函數)
多距離空間聚類分析通過比較觀察到的點集與隨機分布模型下的期望點集之間的距離函數來判斷點集的空間分布特征,能夠準確分析中國行業集聚的點格局。
式(3)中,K(d)為Ripley's K函數;A為京津冀的總面積;n為該地區商業銀行的總數;wij(d)表示在距離d內的商業銀行i、j的間距。若L(d)gt;0,表明京津冀商業銀行屬于集聚分布;相反地,L(d)lt;0意味著京津冀商業銀行呈分散分布。
5.標準差橢圓(SDE)
標準差橢圓是多元統計分析中常用的一種可視化工具,用于表示空間點數據的分布情況,解釋數據的地理特征,它能夠描述京津冀商業銀行布局的方位、中心性、展布性、密集性等特征。標準差橢圓相關參數計算公式如下:
加權平均中心點坐標:
坐標轉換到平均中心的偏離:
x'=xi-xwmc,y'=yi-ywmc (5)
方位角函數:
沿x軸的標準差:
沿y軸的標準差:
(二)數據來源與處理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北京現存商業銀行4282家,中途退出共657家;天津現存商業銀行2858家,中途退出共718家;河北現存商業銀行9028家,中途退出共888家。通過收集和整理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登記的商業銀行金融許可證信息,建立京津冀商業銀行數據庫。借助百度地圖API,將機構住所轉換為精確經緯度坐標。為使本文研究具有更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將數據分析年份限定為1990年之后。 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集聚程度影響因素各指標均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對于部分缺失數據均采用了線性插值法進行補全。為使京津冀商業銀行分支機構數據與社會經濟統計數據相匹配, 實證部分本文抽取了1990—2021年的數據進行檢驗。
三、 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分布及演化
(一)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分布
對1990、2000、2010和2023年京津冀商業銀行數量分布進行分析,將北京和天津按區域邊界劃分, 河北省11個城市按照縣域邊界劃分。1990年,京津冀商業銀行主要分布在北京朝陽區, 邯鄲、石家莊、唐山、秦皇島等地市轄區,均超過100家;北京海淀、西城、豐臺等區以及天津濱海新區、河西區, 張家口市轄區商業銀行數量較多, 均超過50家;商業銀行數量由城市群中心向四周遞減的態勢明顯, 京津冀的商業銀行目前仍處于起步階段, 尚未顯現出明顯的空間集聚趨勢。2000年,北京和天津的中心城區,唐山、石家莊、邯鄲等地市轄區商業銀行發展仍迅猛,廊坊市轄區商業銀行數量迅速崛起,達到101家,總體來看,以北京、天津、唐山、廊坊為核心的京津冀交界地區商業銀行數量較多,已初步顯現空間集聚現象。2010年,京津冀金融機構數量迅速增加,京津冀商業銀行“多中心”分布格局已初步形成,北京市朝陽區、海淀區、石家莊市轄區三地的商業銀行數量分別達到771、558和530家。除承德市外,河北省各地級市市轄區商業銀行數量也均超過100家。另外,石家莊市正定縣成為第一個河北省內商業銀行數量超過50家的縣級區域。總體來看,京津冀商業銀行數量仍呈現“中心多四周少”的態勢,未形成次一級的集聚中心。
(二)京津冀商業銀行熱點區
最近距離層次聚類分析能夠將數據劃分為更緊密的集群來逐步形成聚類,找到數據中的多層次結構。 對京津冀商業銀行熱點區的分析發現,1990年,京津冀銀行業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形成了1個一階熱點區域、6個二階熱點區域和66個三階熱點區域。 一階熱點區處于廊坊和天津交界處,二階熱點區僅分布在河北省, 三階熱點區零散分布。2000年,一階熱點區轉移到了京津冀交界處,二階熱點區分布在北京、天津、邢臺、邯鄲、張家口、秦皇島, 三階熱點區則分布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北京、天津、唐山、石家莊、邢臺等地。2010年,一階熱點區的位置由京津冀交界處轉移到了唐山和滄州,二階熱點區在各地級市均有分布,三階熱點區數量在河北省中南部大幅增加。2023年,一階熱點區的位置由2010年的滄州和唐山轉移到了邢臺和廊坊,二階和三階熱點區的數量和位置均無較大變化。總體而言,京津冀商業銀行的集聚格局一直處于動態變化之中。
四、 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集聚特征與動態演化
(一)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集聚單尺度特征
平均最鄰近指數可以測量點分布的集聚程度或均勻程度,因此本文采用平均最鄰近指數分析京津冀區域內商業銀行的空間分布模式。 由于1990年前京津冀商業銀行普遍較少, 本文僅分析了1990—2023年的京津冀商業銀行的平均最鄰近指數(見圖1),發現NNI數值均小于1,表明京津冀商業銀行總體和三地局部均為集聚分布。
利用ArcGIS計算得到1990、2000、2010、2023年京津冀總體商業銀行分布的平均最鄰近指數(見表1) 分別為0.3750、0.3329、0.3530、0.3536,所有數值顯著低于1,表明京津冀商業銀行呈現出明顯的集聚分布趨勢。
(二)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集聚多尺度特征
點數據在不同空間尺度上呈現不同的聚類模式,Ripley's K函數可展示要素質心的空間集聚或擴散在不同鄰域大小下的變化情況。本文借助Ripley's K函數對京津冀商業銀行分布的多尺度特征進行分析, 發現1990、2000、2010和2023年的L(d)值均大于0,并且這些數值高于包絡線上的對應值,同時呈現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見圖2)。這說明京津冀商業銀行的空間集聚特性極為顯著,并且隨著空間距離的擴大,集聚的程度也在增強, 到約290km時達到峰值, 且同樣的鄰域距離下,2010年的京津冀商業銀行分布集聚程度最強。
(三)京津冀商業銀行集聚性演化模式分析
為探究京津冀地區商業銀行集聚程度的演化規律,本文以平均最鄰近距離(m)作為觀測指標,設定CAGR閾值為2%, 將河北省11個城市和北京、天津各區共43個區域劃分成三類(聚集程度穩定型、下降型、增長型),觀察各區域之間的演化模式。通過分析CAGR值發現(見表2和表3),1990—2000年,商業銀行集聚程度快速增加,表明金融服務在區域內迅速擴展;2000—2010年,盡管集聚趨勢依舊明顯,但穩定型區域逐漸增加,表明市場逐步趨于平穩;2010—2020年,集聚增長型區域與穩定型區域數量接近,顯示市場趨于飽和,集聚趨勢減緩;2020—2023年,大部分區域集聚水平趨于穩定,集聚增長型區域顯著減少至4個,分別為北京市房山區、通州區、大興區和延慶區,聚集程度下降型區域個數始終為0,表明市場進入成熟階段,金融資源配置趨于優化。
(四)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分布重心的動態演化
標準差橢圓能夠展現量化空間分布的方向性和擴展性,顯示點分布的中心位置、擴展范圍以及主要分布方向。通過分析標準差橢圓參數(見表4),發現隨著時間推進,標準差橢圓的面積逐漸減小,由1990年的172 072.05km2縮小至2023年的92 224.27km2,說明1990—2023年總體上京津冀商業銀行的集聚水平逐漸上升。1990—2023年京津冀商業銀行分布的中心點均在廊坊,總體趨勢是向西北方向轉移。京津冀商業銀行數量標準差橢圓的方向性減弱,向心力減小,集聚面積減小,說明1990—2023年京津冀商業銀行分布集聚向心力雖有波動,但集聚面積仍在縮小,且集聚向心力較強。
五、 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集聚程度影響因素
(一)指標選取
影響金融機構空間布局的因素眾多,本文參考已有研究成果和理論假設[20,21],從經濟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環境、人力資源、科技投入和社會發展等幾個方面選取了工業化水平、政府行為、經濟發展水平、城市環境、對外交通、區域面積、人力資源、科技投入、城鎮化率和人口密度等10個具體指標構建了京津冀商業銀行集聚程度影響因素指標體系(見表5)。各項指標數值引自《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對于其中存在的缺失值,本文采用了線性插值技術進行處理。
(二)模型構建
本文選取平均最鄰近距離(m)作為被解釋變量,以衡量京津冀商業銀行集聚性。1990年被解釋變量的樣本方差大于平均值,2000、2010和2021年樣本方差小于平均值, 由于被解釋變量數據具有稀疏性和指數型衰減特征, 且存在超離散性, 表現出計數特征, 因此采用泊松回歸進行分析。 為避免被解釋變量的離散性對模型產生影響, 本文通過負二項回歸模型引入超離散性系數α, 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未拒絕“α=0”的原假設,因而采用泊松模型進行估計。 為了避免變量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在構建泊松回歸模型之前檢驗了各解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Spearman相關系數矩陣結果表明, 自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問題,都可納入分析模型。模型設定如下:
式(9)中,i為自變量個數,k遵循均值為0、方差為α的伽馬分布, 用來評估超離散的水平,β0、βi 為變量的回歸系數。
(三)回歸結果
本文采用了廣義線性模型(GLM)分析,其中因變量為平均最鄰近距離(m),模型類型為泊松分布,使用對數鏈接函數進行變換。模型的擬合方法為迭代重加權最小二乘法(IRLS),最終共進行了6次迭代。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1年京津冀商業銀行數量分別為2623、6236、11 809和15 912家,模型的對數似然值分別為-1020.0、-1018.4、-312.78、-135.21,偏差分別為1921.1、1923.6、515.21、161.82,皮爾遜卡方值為1680、1923.6、519、163,偽R平方值均為1.000,表明模型具有良好的擬合度。
泊松回歸模型結果顯示,工業化水平、政府行為、經濟發展水平和城市環境這四項指標對商業銀行集聚的影響顯著,但對外交通、區域面積、人力資源、科技投入、城鎮化率、人口密度對商業銀行集聚的影響不明確(見表6)。其中,工業化水平的回歸系數始終為正,且系數逐漸減小,表明工業化水平在早期對商業銀行集聚有明顯的促進作用,但其效應逐步降低。 政府行為的回歸系數一直為正且較大,均通過1%顯著性檢驗,表明政府財政支出對商業銀行集聚有顯著正向影響,良好的政策引導和市場環境明顯有利于商業銀行發展。2024年是京津冀協同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十周年,十年間三個地區以產業政策為導向, 城鎮化與工業化協同發展,政策引導對于京津冀地區商業銀行的發展戰略決策有著顯著影響。經濟發展水平在1990年和2000年的回歸系數為負,2010年和2021年為正, 且均通過1%顯著性檢驗, 表明經濟基礎逐步成為商業銀行活動的關鍵吸引因素及主要驅動力。城市環境回歸系數在2000年為負,2010年和2021年為正,均通過1%顯著性檢驗,表明隨著國家發展,城市環境對商業銀行集聚的促進作用逐漸增強。對外交通的回歸系數在1990年和2010年為正, 在2000年和2021年為負, 四年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對外交通水平的確會影響商業銀行的集聚程度, 但影響方向不明確。 區域面積的回歸系數在2000年為正,在1990年和2010年為負,2021年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行政區域土地面積對商業銀行集聚程度的影響作用不明確。人力資源的回歸系數在2000年為正,其余年份為負,說明人力資源對商業銀行的集聚影響相對有限,本文在選擇變量時假設城市每萬人在校大學生數能夠反映城市的教育水平,然而實證分析結果顯示這一假設與現實情況不符。究其原因可能是不同專業和教育水平存在多樣性,城市普通高校在校學生數很難完全代表城市的教育水平。 科技投入的回歸系數一直為負,2010年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說明科技投入對商業銀行的集聚影響作用機制不明確.考慮到科技投入一方面會促進商業銀行發展,另一方面科技水平越高,商業銀行電子化程度越高,可以通過網上銀行等形式提供服務,減少實地設址,降低商業銀行集聚性。 城鎮化率的回歸系數在1990年為正,在2000年、2010年和2021年為負,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在商業銀行發展早期,城鎮化率的確是促進商業銀行集聚水平的重要因素,但隨著京津冀的整體發展,城鎮化率開始對商業銀行的集聚水平呈現負作用。 人口密度的回歸系數在1990年和2010年為負,在2000年和2021年為正,2010年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 其余年份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人口密度對商業銀行集聚水平的影響機制不明確。
六、結論與討論
(一)結論
本文利用CrimeStat-IV、ArcGIS10.8、Stata17等分析軟件,通過熱點聚類、最鄰近指數、多尺度空間聚類分析和標準差橢圓等方法對京津冀商業銀行的空間格局、集聚特征和熱點區域等特性進行了全面分析,并利用泊松回歸探究了影響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集聚的因素。本研究主要得到三點結論。
1. 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在京津冀總體及三地局部均呈現空間集聚特征,且隨著時間推移,空間集聚程度逐漸增強。當前京津冀已發展出以邢臺和廊坊為中心的兩個一級商業銀行熱點區域,僅剩北京市房山區、通州區、大興區和延慶區處于集聚程度增長型模式,市場進入成熟階段,金融資源配置趨于優化。
2. 隨著地理距離的擴大,商業銀行的空間集聚程度呈現出先增強再減弱的特征,其中集聚程度的峰值出現在290km處, 以北京故宮為中心點,該鄰域能夠完全覆蓋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區。
3. 泊松回歸結果顯示,工業化水平和政府行為是影響京津冀商業銀行集聚的核心因素,城市環境與經濟發展水平對京津冀商業銀行的空間集聚趨勢影響逐年顯著。
(二)討論與建議
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分布集中在京津冀交界區域以及若干地級市的市轄區,區域內部發展不均衡,這種空間格局的不均衡特點與國內外其他城市群的發展趨勢相類似[5,22-25]。與已有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揭示了工業化水平在京津冀商業銀行空間集聚中的核心作用,以及城市環境對商業銀行空間集聚的顯著影響。 京津冀常年以產業政策為導向,城鎮化與工業化協同發展,河北長期呈現以重化工為主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貢獻了區域內絕大部分的重工業產值和能源消耗[26],與此同時也帶來了相對嚴峻的環境污染問題亟待解決。考慮到工業化水平和城市環境在京津冀商業銀行布局中的顯著作用,為了更好地完善京津冀協同發展體系,促進區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本文針對京津冀商業銀行布局提出四點建議。第一,京津冀商業銀行布局過程中應重點考慮城市環境建設,鼓勵發展綠色金融和可持續金融,各商業銀行應提供更多的低息綠色貸款,為工業企業環保設備更新和工藝技術提升提供融資支持,降低區域內的污染排放,助力“雙碳”目標的實現,重點推動河北省內傳統重工業向高附加值、低能耗的綠色產業轉型,實現產業升級。第二,充分打造河北省“冀中南功能拓展區”,繼續抓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這一“牛鼻子”[27],以邢臺、廊坊兩個一階熱點區為引領,推動綠色產業集聚和區域協調發展,引入高新技術企業和環保產業,形成綠色產業集群。第三,鼓勵金融資源向北京市房山區、通州區、大興區和延慶區等集聚程度增長型區域傾斜, 避免資源過度集中于中心城區造成的浪費,提升金融服務覆蓋率,充分利用金融產業的集聚效應,推動京津冀城市群金融業向高質量發展邁進。第四,繼續發揮天津商業銀行布局相對合理的優勢,利用其沿海地域優勢加大外資引入力度,維持京津冀商業銀行多中心集聚特征,助力京津冀產業協同,促進京津冀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國平,呂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實施成效及其重點方向研究[J].城市問題,2024(2):4-10.
[2]王曉陽,蒙克.經濟全球化、全球金融危機與中國——基于金融地理學的視角[J].地理科學進展,2019,38(10):1482-1489.
[3]潘峰華,徐曉紅,夏亞博,等.境外金融地理學研究進展及啟示[J].地理科學進展,2014,33(9):1231-1240.
[4]趙曉斌,王坦.跨國公司總部與中國金融中心發展——金融地理學的視角與應用[J].城市規劃,2006(S1):23-28.
[5]趙建吉,劉巖,王艷華,等.欠發達地區城市群金融機構空間演化特征及影響因素——以中原城市群為例[J].經濟地理,2022,42(1):70-78.
[6]趙金麗,盛彥文,張璐璐,等.基于細分行業的中國城市群金融網絡演化[J].地理學報,2019,74(4):723-736.
[7]姚曉明,朱晟君.中國銀行業基層網點的空間演化機制[J].地理研究,2020,39(2):384-398.
[8]張杰,盛科榮,王傳陽.中國城市間金融網絡的空間演化及其影響因素[J].熱帶地理,2022,42(6):928-938
[9]潘艷.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基于京津冀地區的面板數據[J]社會科學前沿,2021(8):1992-1998.
[10]宋鳳軒,劉瑩,牛桂草.共同富裕視域下數字金融對區域協調發展的影響研究[J].金融理論探索,2023(2):15-22.
[11]陳小榮,尹繼志,劉潔,等.區域金融協同發展測度及協同機制構建研究——基于京津冀地區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金融發展研究,2020(5):50-55.
[12]冷婧,柳艷紅.西南民族地區村鎮銀行網點空間分布及其影響因素——基于滇桂黔縣域尺度數據的分析[J].經濟地理,2023,43(11):145-153.
[13]李楚海,林娟,盧嘉新,等.中國銀行退出網點的多尺度格局及其影響因素[J].熱帶地理,2023,43(8):1501-1511.
[14]翁鋼民,趙心,潘越.京津冀城市群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水平測度及時空演化分析[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22,38(6):119-125.
[15]唐夢琳,仇方道.基于“企業-行業-開發區”的淮海經濟區產業空間集聚特征[J].地理與地理信息科學,2024, 1-7.
[16]DENG X,GAO F,LIAO S,et al.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s of Urban Heat Island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Urbanization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Bay Area of China from 2000 to 2020[J].Ecological Indicators,2023,146:109817.
[17]LI L,LU L,XU Y,et al.The Spatio 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tel Industry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China[J].PloS One,2020,15(5):1-23.
[18]LIAO Z,ZHANG L.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Accessibility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in Guangdong Province Based on Ripley’s K Function[J].Journal of Mathematics,2022,2022:1-14.
[19]胡建梅,于嘉林,張超. 基于標準差橢圓的中國對非洲援助空間分配問題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24:79-88.
[20]王洋,楊忍,李強,等.廣州市銀行業的空間布局特征與模式[J].地理科學,2016,36(5):742-750.
[21]甄茂成,張景秋,楊廣林.基于復雜網絡的商業銀行布局特征——以北京市中國銀行為例[J].地理科學進展,2013,32(12):1732-1741.
[22]李偉軍,李婷,吳義東.中國三大城市群金融集聚:空間網絡及結構分化[J].經濟體制改革,2020(2):38-45.
[23]茹樂峰,苗長虹,王海江.我國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與空間格局研究[J].經濟地理,2014,34(2):58-66.
[24]萬惠,侯光明,孔德成.我國城市群金融產業集聚影響因素實證分析[J].金融理論與實踐,2017(9):19-24.
[25]段軍山.銀行業的區域布局研究——以廣東省為例[J].金融理論探索,2012(2):20-25.
[26]辜勝阻,鄭超,方浪.京津冀城鎮化與工業化協同發展的戰略思考[J].經濟與管理,2014,28(4):5-8,2.
[27]孫久文.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新特點與新任務研判[J].金融理論探索,2023(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