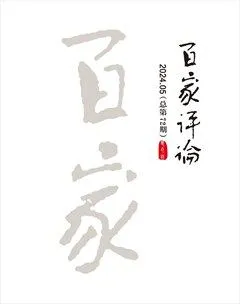走出上海:《繁花》的詞與物創新
內容提要:《繁花》通過雙線敘事將“為政治”與“為人生”編織起來,重新結構改革開放前后作為歷史“中間物”的城市。先是寫物繪圖構造出這一上海形象,然后提取“上海性”形成新言說,將地域性、傳統性、日常性升格為中國性、當代性、文學性,從而走出上海。這樣從寫物繪圖到言文相融、音字聯用的《繁花》經驗,形成建構地方又走出地方的“詞與物”啟示錄。
關鍵詞:《繁花》 走出上海 語言活力 寫物繪圖
從1984年寫作《失去的河流》到1992年出版《迷夜》,再到2011年在“弄堂論壇”發布《繁花》,金宇澄從未停止過對小說內外的探索。他帶著作家“想寫什么”的表達訴求和編輯“該怎么寫”的理性判斷,數次改易《繁花》,使其在網絡連載、雜志發行、成書出版和修訂再版之后,以滬語表述、雙線敘事、圖文并行等最大化地呈現上海形象。這也導致《繁花》一度被定格在上海敘事的傳統上。不過,金宇澄在承繼中國小說傳統、轉借西方敘事學知識的基礎上,以“獨上”(金宇澄在“弄堂論壇”的網名)姿態找尋自己的言說方式,是帶有走出上海的寫作策略和文學抱負的。
一、關于上海的歷史觀
上海之于20世紀中國文學,不僅是空間上的策源地和發生場,還是創作上的題材和形象。早先有三個階段的“海派”,晚近有程乃珊、王安憶等人,他們圍繞上海的前世今生突顯社會問題、表現日常生活等,以革命和后現代兩種書寫范式形構出了具體不同的“上海像”。其中不僅有被二元化的形象,從新文化的對立面到左翼視角下的殖民化場域,再到現代主義流派的西方想象,上海成為新舊思想、中西文化和不同階級對立并存的集結體;還有張愛玲以存在主義進行消解、90年代“傳奇”發展的多元化形象。《繁花》列席于此,必然要與既往的“上海像”對話。如果依照小說從1960年代到新世紀初期的敘事時間,還可將對話的范圍進一步縮小。當代的上海書寫鮮有全面深入1960年代之后的,先只是在個人成長的“文革”講述中有所涉及,而后有程小瑩對六七十年代工廠生活的懷舊書寫,夏商關于七八十年代的浦東紀事等,呈現出某一坐標點、時間線上的城市形態和上海故事。
而金宇澄采用了雙線敘事,1960年代到1970年代末期的故事,是以繁體字標出的奇數章節“壹叁伍柒玖……”;1990年代到新世紀初期的故事,是以簡體字標出的偶數章節“二四六八十……”。兩條線索在第二十九章中實現對接,直至結尾。這看似空置了1980年代,其實小說起始便認同《阿飛正傳》中的“上海味道”a,影片結尾處那半分鐘的“否極泰來”深深觸動了金宇澄。接之的“八十年代,上海人聰明……”一段,可謂精髓式書寫。所以1980年代在小說的精神氣象上,并非留白,而是隱于開篇處,構成故事入場的語境。
這同時形成了1980年代前后時代的十四次對照,不僅具有調節閱讀習慣的作用,還強化了同一群人在不同時代的縱向比照效果。小說扉頁上的題記“上帝不響,像一切全由我定……”即是解鎖之鑰。這句話第一次出現在1960年代敘事層,是春香講述自己第一次婚姻時所說。當時的政治信仰成為人的精神信仰,而春香信奉耶穌,結果并未“一切全由我定”,春香在母親的強迫下無奈嫁給了一個蹺腳的殘疾男人,以離婚告終。這里以個人信仰的上帝對照當時政治信仰的領袖,喻示著人與時代環境、政治意識等外部矛盾的沖突。第二次出現在1990年代敘事層,是小毛在彌留之際所說。此時阿寶下海做了老總,滬生做了律師,陶陶做起了生意,玲子開了大餐館,蘭蘭嫁給了香港人,雪芝做了闊太太……但結局是,汪小姐在產房靜候腹中怪胎的降臨和未知命運的審判,李李看破紅塵出家,白萍在催滬生出國簽離婚協議,陶陶在等到芳妹同意離婚后卻因小琴日記本中的種種事實而萬念俱灰,等等。他們的失敗色彩,是由人在面對精神和物質、感情與欲望時的內面矛盾所致。
如此一來,金宇澄以處于社會主義建設和經濟全球化中間的“過渡時代”(1980年代),表明“我們永處于過渡時代”b的歷史“中間物”意識。同時借1960—1970年代受制于政治、1990年代迷失于經濟的不同生活處境,以及“皮笑”“戲話”“靜穆”“不響”等不同人生姿態,詮釋跨越階層群體、橫亙于變革更迭中不變的市民階層的生命力,揭示“上海味道”和城市精神的根本所在。
事實上,對于1960年代以降的上海,不管是從社會主義革命視角去“為政治”的革命論調,還是從日常視角來“為人生”的新啟蒙論調,都在有意識地強調或走出革命。相比之下,金宇澄非但沒有局限于這兩種造像思路,反而解構了單一向度的現代性,將被宏大革命驅逐的私人瑣事和被人性話語回避的政治意識拾回,從現代主義的層面確立城市的主體性。這并非定性式的結論,是“因人們共有的經驗被建造和被認識”的“存在性空間”c,充斥著復雜糾葛的能動性:既包括歷史進程中的上海,含括了革命喧囂、文學潛流、自由貿易、娛樂言情等,也包括作者經歷過的上海,承載了人生理想、少時記憶、插隊見聞、世態人情等。其中蘊涵著人生與時代、信仰與政治、情感與物質等關于市民經驗與自覺意識的內在關聯,形成重新結構上海的路徑。
這更接近一個階段論,當然不是簡單的前后相繼階段,但必然是金宇澄基于時空意識、生活感知的產物,源自他特定歷史觀的建構。即跳出革命史觀、社會史觀的一元決定論,以聯動革命與啟蒙、綜合社會與日常的多元發展的唯物史觀,構造存在與體驗之上作為歷史“中間物”的“上海”,契合1990年代中國崛起后的主體建構需要,以及全球化時代城市—國家共同體的發展訴求。
二、寫物繪圖與構造“上海”
在將觀念具化為形象的問題上,金宇澄選擇了以物賦形的方式。大到地理坐標,小到衣食住行,物作為背景、符號傳遞出了場景和人物的種種信息。從引子中的靜安寺菜場、大閘蟹、茶、攤位、躺椅等,到尾聲的西蘇州路、長壽路橋、弄堂口、蘇州河等;從1960年代故事中“方臺子叫‘四平’,圓臺叫‘月亮’,椅子叫‘息腳’,床叫‘橫睏’,屏風叫‘六曲’,梳妝臺叫‘托照’,凳子統稱是‘件頭’,方凳圓凳,叫‘方件’‘圓件’”的舊家具,到1990年代故事中以“八冷盆:上海清色拉,四鮮烤麩,咸雞,馬蘭頭腐皮卷,鎮江肴肉,舟山泥螺,老醋蜇頭,蜜汁叉燒”為代表的飲食;從小珍“黑顏色布底鞋,白襪子,咖啡色長褲,白襯衫,米色背心”,到梅瑞“穿新絲襪,換戒指,項鏈,大鏡子前面,橫挑豎揀,再替換淡灰細網絲襪,Ann Summers蕾絲吊襪帶,玄色低胸背心,煙灰套裝,稍用一點粉餅,配珍珠耳釘”;等等。各種物象注解式地給《繁花》打上了上海烙印。
其中最顯著的當屬繪圖,《繁花》2012年在《收獲》發表時配有金宇澄手繪的12幅插圖,2013年單行本出版時增至20幅。包括地圖四幅:1960年至2000年盧灣區局部地圖、1970年代滬西局部地圖、南京西路以北地圖、上海中心城區的坐標版圖,建筑物繪圖六幅:1960年代初的國泰電影院、瑞金路長樂路角的建筑變化、淮海路國營舊貨商店、小毛居住的老弄堂三層屋、曹楊新村“兩萬戶”和春香的婚房,還有皋蘭路房頂、郵票、石擔、鋼琴、汽水扳手等故事場景圖和人物器具圖九幅,另有一幅蛇圖。
一般小說的插圖都由畫家擔任,傾向于裝飾元素,而小說作者的自繪興趣,往往更個人化,在于我,既然表現城市的現實,不能如小說或電視劇虛構比如“臨海市”等等莫須有地名,人物走動的地理路徑,是極有對照意味的表現,此外,因為書寫之局限,一般文字難以表達的內容,用圖【含地圖】解釋等等,是一種自然的理由。d
這些圖顯現出金宇澄認識上海、構造“上海”的創作自覺,具有獨立的表意功能和不同的話語指向。四幅地圖清晰勾勒出了上海的大框架,加上六幅建筑物圖的描繪,不僅全景式地呈現上只角的花園洋房、教堂公園,下只角低矮擁擠的民房、黑瓦濃煙的工廠,以及街巷田舍、老弄堂,還縱向描繪上海的歷史變遷。最具代表性的當屬“瑞金路長樂路角的建筑變化”,是同一地方在不同時段的三聯圖。在1963年名為劍春女子中學,旁有教堂;1967年學校改名長樂中學,教堂被摧毀,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巨大的領袖造像;2000年學校變成了向明中學分校,旁邊建起新錦江大酒店。三圖對比,可見一斑,動態展現出1960年代至新世紀從殖民文化遺存到政治意識主導,再到市場經濟繁榮的上海風貌。
九幅場景圖和器具圖中,有三幅是配合1990年代敘事的,六幅在1960—1970年代的故事章節中。以第一幅“皋蘭路屋頂”圖來看,少年時的阿寶和蓓蒂坐在屋頂觀望,是對第一章中“阿寶十歲,鄰居蓓蒂六歲。兩個人從假三層爬上屋頂,瓦片溫熱,眼里是半個盧灣區,前面香山路,東面復興公園,東面偏北,看見祖父獨幢洋房一角,[……]蓓蒂拉緊阿寶,小身體靠緊,頭發飛舞。東南風一勁,聽見黃浦江船鳴,圓號寬廣的嗚嗚聲,撫慰少年人胸懷”的再現,將文字敘述形象化。器具圖如“石擔”,包括石擔、石鎖、金屬鏍帽彈弓、洋圓、角鐵等。金宇澄在圖旁注釋:“可增加應景物品(除常規武器外)計有:各類徽章,紙質高帽,麻繩,語錄,袖章,銅頭皮帶,軍用書包,水壺,大瓶墨汁,毛筆,排筆,漿糊桶,竹梯,鑼鼓響器,旗幟,廣播喇叭,手提電喇叭,蠟紙,刻蠟紙鋼筆、鋼板,手提油墨印刷機等。”以畫靜物的方式將這一時期的上海具象化。
頗為獨特的是蛇圖,圖中菜刀、耙具、布鞋、木凳等遍地破碎,井口爬滿了蛇。“本書出版是2013年,蛇年,畫蛇憶舊。”這句話傳達出兩層含義:此圖不僅指向上海形象,還關乎個人記憶。因為“這是‘革命’前夜的事,戶主的財產已被剝奪干凈,她想到了長輩遺言,天井里埋有銀元寶。明天群眾就要占據這所大房,當晚必須挖了,沒想到結果挖出的不是什么元寶,是一缸赤練蛇,她大哭起來,人走了大霉運,‘身邊黃金就變銅,翻來覆去一場空’,很詭異的場面。這是少年時代聽我祖母講的。”e金宇澄真正想追憶的是自己的“少年時代”,或者說是與祖母生活在一起的光景。
繪圖不僅僅是寫物的直觀反映,見證了上海形象的建構與發展,還被金宇澄用以表達個人追憶。由此,作為故事背景、象征符號等的客觀之物與作為主體情思的具象存在的兩種物,以圖像的即視感直觀呈現出上海的地標路線、建筑樣貌、生活場景、器具輪廓等,在建構起城市主體的同時賦予“我”的主體性,從而在1960年代至新世紀初期的上海、金宇澄認知中的上海之上構造出《繁花》的上海形象。
三、創新言說以走出上海
《繁花》顯現的城市與作家關系,決定了小說將在城市歷史動能與時代發展特征上形成新的言說方式。因為,從舊上海的洋浜涇英語到革命熔爐時期的現代語匯,從城市化遷移中的方言融合到摩登之都的多語共存,每一時期的上海都擁有獨自的語體風格。新上海同樣具備一套與自主多元、開放發展相匹擬的表達,即兼顧上海獨特性與中國普遍性的新言說方式。這一言說方式的形成,實際上是金宇澄著眼于上海本土和當代中國,創新古今中外語言資源的結果,涉及喚醒傳統、吸納本土、汲取日常等幾個方面。
小說在上海話的基礎上取用蘇州方言、蘇北話等,以人物姓名代替滬語中的“儂”“伊”等人稱代詞,并將普通話、地域方言和日常口語組構起來,打破滬語的地域限制和口語的隨意繁復。這不僅使方言從強化地域色彩、塑造人物的功能中走進小說的敘事話語,還由此分解出敘事者的聲音,強化語言的調性和彈力。同時擯棄了直接引語參與下的敘述方式,讓敘事話語和人物對話(閑談、雜聊)處于同一層級,形成大段落的話本式表達。其中的流水句、話題鏈等不同于受翻譯腔影響的創作和被印歐語支配的語法,自然而真實。而對話讓每個人物都有出場的機會,高頻率的“說”“講”與人應有的生活狀態和情感密度相合,形成語言與人物、與故事、與題旨交融一體的言說方式,即對話構成故事的主體,語言成為小說的生命。這一過程中,傳統話本、吳語方言、日常口語分別從時間、空間和言說者三個維度匯集,金宇澄從中提取“上海性”,將其馴化為話本體、滬語調、漢語腔,為小說語言的生成提供了歷史參照、應用場景和交流邏輯。這顯露出他根于存在與體驗,調用傳統并突圍傳統、借助方言又超越方言、立足當下卻反撥當下的表達思維。
最能集中反映這一特色的是單行本后勒口上的《童謠》:
儂姓啥,我姓吳。//啥個吳,滬生的滬。//啥個生,生梨。啥個梨,離婚。//啥個婚,葷油。啥個油,理由。//啥個理,癩痢。啥個癩,蠟燭。//啥個燭,發作。啥個發,頭發。//啥個頭,壽頭。啥個壽,發愁。//啥個發,毛發。啥個毛,小毛。//啥個小,家小。啥個家,東家。//啥個東,過冬。啥個過,難過。//啥個難,為難。啥個為,啊為。//啥個啊,阿寶。啥個寶,七寶。//啥個七,吃飯。啥個飯,麻煩。//啥個麻,馬路。啥個路,白露。//啥個白,白相。啥個相,香煙。//啥個煙,討厭。啥個討,套鞋……
這是改自上海浦東童謠《儂姓啥?》的順口段子,多出現在地方戲和生活玩笑中。在滑稽戲、獨腳戲里,通常由一人在歸納片段或場次時編說講出,以接口令的形式概括故事梗概。金宇澄通過這一言說方式,一面以“吳”和“滬”指明小說吳語系、“上海性”的語言特征,通過普通話展現異形異音、同音異調字在滬語中的相同發音,如“吳”和“滬”、“燭”和“作”、“飯”和“煩”等;一面以貫口形式表現“你問我答”的講說,其中包含滬生、小毛、阿寶三個主要人物,以及“離婚”“葷油”“發作”“難過”“為難”“吃飯”“麻煩”“白相”等主題詞,既連接貫通,又總結點題。這與其說是歌謠版《繁花》,毋寧說是縮略版《繁花》,直接展現出了小說的語言特質:不同的語言資源和表達形式,在《繁花》里對接、衍新,包括民間語匯與文學敘述、語言形式與故事內容等。
這樣綜合取用書面語體、上海語調、日常口語和傳統言說等多種資源,加以平衡和轉換,鍛造出了《繁花》獨有的語言系統,既保留了方言的獨特性,又打破一地一語言、一方一音調的局限,形成與新上海發展相一致的言說方式,展現出當代中國文學語言的生力。這表明,金宇澄在以語言構造上海形象的過程中,已經成功走出了上海,或者說建構“上海”僅是走出上海的第一步,《繁花》的言說早已逸出構成部分原來的范疇,由地域性、傳統性、日常性升格為中國性、當代性、文學性,并以此叩問人的生命力和城市的主體性問題。這也注定《繁花》不是簡單的反映論文本或現實主義小說,而是以上海為方法同構語言文學與當代中國的創作,應被置于現代漢語小說和中國文學的層面來討論。
四、《繁花》經驗的誕生
因地方與人不自覺的意向性具有同質關系,形成地方性征與言說方式的一致性。所以在“以……為方法”的營構中,作為賓語的“地方”并非寫作的最終指向,而是一個路徑式的突破點或策略性的敘事角度。如果將這一裝置中的上海話換成四川話、湖南話等其他方言,同樣具有一定的文學適用性。語言在從“工具論”到“本體論”的轉向中,可以作為一種能動的存在力量,形成語言即文學的可能。這相比于汪曾祺所說的寫小說就是寫語言,還存在言文處理上的不同。汪曾祺秉持“字本位”理念,認為“寫小說用的語言,文學的語言,不是口頭的語言,而是書面語言。是視覺的語言,不是聽覺的語言。”f而《繁花》借用言與文既非合一也未完全背離的張力,如前文所述,將口語與書面語等相融合,形成獨特的語言表達;同時以另一種音、字聯用的方式,再建設語言。
一方面,小說引入了大量的歌曲和戲劇,如越劇《盤夫索夫》、揚劇《賣油郎》、滬劇《羅漢錢》、評彈《貂蟬拜月》、歌劇《卡門》,以及鄧麗君、梅艷芳、陳升等人的歌曲。第一章中,小毛生煤爐時唱著關于上海吃食的歌謠,與同時出現的曲譜一起激活了全書的發聲細胞;尾聲處,阿寶和滬生沿蘇州河邊散步,夜風中傳來黃安演唱的《新鴛鴦蝴蝶夢》,“看似個鴛鴦蝴蝶/不應該的年代/可是誰又能擺脫人世間的悲哀/花花世界/鴛鴦蝴蝶/在人間已是癲/何苦要上青天/不如溫柔同眠。”阿寶掛斷了雪芝的電話,小說以歌詞的句號結束。這不但展現了不同時代、不同生態的聲音,進行聽覺敘事,而且引起讀者共鳴,使其自覺參與到語言建設中,成為獨特的發聲者。
另一方面,繁體字文句頻頻出現在“毛語體”盛行的1960—1970年代故事層,從繁體字的章節序號“壹叁伍柒……”到《彭公案》《平冤記》的文段,從阿寶哥哥的香港來信到小毛的手抄簿。特別是第五章中引用穆旦的《詩八首(四)》:“靜靜地,我們擁抱在/用言語所能照明的世界裡,/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們沉迷。//那窒息著我們的/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語,/它底幽靈籠罩,使我們游離,/遊進混亂的愛底自由和美麗。”這與社會主義革命“戰歌”“頌歌”的聲潮形成對比,意在重新將文字書寫喚醒,來探索語言的文學空間和表達張力。
這是自黃遵憲“我手寫我口”、梁啟超“新民體”以來就懸置的問題。從早期白話詩人的嘗試到魯迅的實驗,從老舍、趙樹理的轉用到阿城、韓少功的翻新,百余年來作家們圍繞“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上下求索,試圖打破唯“字符中心主義”或唯“語音中心主義”的文學局面。王小波在談及穆旦譯介對自己的影響時說:“我們年輕時都知道,想要讀好文字就要去讀譯著,因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譯”,“他們發現了現代漢語的韻律。沒有這種韻律,就不會有文學。”g與王小波同齡的金宇澄自然知道這個“不傳之秘”,他說自己被穆旦翻譯的《葉甫蓋尼·奧涅金》中的抒情話語深深打動h,《詩八首(四)》反映了寫作時的感受,“一直在黑暗里摸索,用語言和感受摸索,照明小說空間”i,由此獲得一種動力。
穆旦的譯文嚴格遵循詩歌格律,以現代新詩的句法達至古文的精煉,最大程度傳達出原詩的抒情性和韻律美。就《葉甫蓋尼·奧涅金》來看,穆旦避免了原文直譯的生硬和白話轉譯的單調,將現代詩的自由變化和古詩的節奏韻律相結合,采用雙行韻和隔行韻交錯的樣式,展現普希金詩歌的語言特點、表達節奏和抒情狀態,更新了傳統譯介中詩語與詩意的關系。因此,真正打動金宇澄的是穆旦融合口語、散文化句式、書面語,普希金雜糅書面語體、民間語體和口語體的語言韌性。小說四次引用穆旦詩句(第五章、尾聲、跋、單行本封底)隱露著致敬的心語,顯現出金宇澄聯及言文、互動音字,與穆旦、普希金用語言照明世界、燃亮人心同向的語言文學觀。這與構造上海形象的寫物繪圖,一同生成《繁花》建構“上海”又走出上海的寫作經驗。
結語
如何建構地方?怎樣走出地方?20世紀以《子夜》為代表的上海書寫和以《邊城》為代表的湘西敘事,都曾有意識地將鄉村與城市的對照性寫作,扭轉成地方與中國的縮略式表達,做過成功的探索。《繁花》留住“地方感”j又走出地方的寫作經驗,也引發我們對中國文學寫作怎樣在盛產詞與物的21世紀繼續拓展的思考。
關于構詞,從古文到方言、口語,再到現在的網絡詞條,當代文學寫作擁有豐厚的語言資源。但真正的創新不在于直接以新潮流行語、網絡詞入文,或修改意義上從俗語到雅言的變化,應該立足于政治、社會、生活與文學的關系,進行有針對性的思維更新和觀念揚棄,在富有當代性、時代感的語言生態中淬煉文學言說的生命力。關于寫物,隨著西方“物轉向”理論的引入,物逐漸從介質性、裝飾性的符號論走向獨立敘事的本體論。當代中國的物敘事也逐漸豐富起來,有復歸古代博物書寫、名物寫作的嘗試,也有溝通人與物的探索,但根本不在于數量上、類型上的加法,而應重構人與物的文學關系,從認識上、范式上做出質的一躍。
注釋:
a金宇澄:《繁花》,上海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題記。以下引用不另標注。
b金宇澄:《輕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頁。
c[加拿大]愛德華·雷爾夫:《地方與無地方》,劉蘇、相欣奕譯,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58頁、第24頁。
d金宇澄:《〈繁花〉插圖與消逝的上海記憶》,“灰光燈”微信公號,2015年1月10日。
e金宇澄、嚴彬:《金宇澄文學訪談錄:上帝無言,細看繁花》,“鳳凰讀書”微信公號,2014年9月9日。
f汪曾祺:《揉面——談語言運用》,《花溪》1982年第3期。
g王小波:《我的師承》,《王小波文集》第2卷,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頁。
h錢文亮:《“向偉大的城市致敬”——金宇澄訪談錄(下)》,《當代文壇》2017年第4期。
i金宇澄:《〈繁花〉創作談》,《小說評論》2017年第3期。
j[美]段義孚:《戀地情結:對環境感知、態度與價值》,志丞、劉蘇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16頁。
(作者單位:中國海洋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