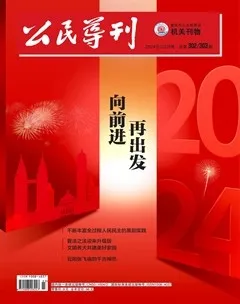AI生成的“作品”著作權應屬于誰
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AI)技術的迅猛發展,用戶只需要輸入一些提示詞,AI大模型就可以產出相應的文字、圖片、代碼等內容。那么,AI生成的內容受著作權法的保護嗎?相應權利的歸屬該如何界定和劃分?人們是否可以自由使用網絡上AI生成的內容?這些涉及人工智能的著作權問題亟待法律有個“說法”。
2023年末,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結了李某與劉某作品署名權和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一案,首次明確了利用人工智能生成圖片“作品”的屬性,并提出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是否構成作品需個案判斷的觀點。本案的判決,對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相關法律問題進行了開創性探索。
2023年8月,原告李某向法院起訴稱,2023年2月24日,他使用開源軟件Stable Diffusion通過輸入提示詞的方式生成了涉案圖片,并將該圖片發布在小紅書平臺上。后原告發現,被告劉某在百家號一篇文章的配圖中使用了涉案圖片。被告不僅未獲得自己的許可,還截去了署名水印,使得相關用戶誤認為被告為該作品的作者,嚴重侵犯了自己享有的署名權及信息網絡傳播權。故請求法院判令被告在百家號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賠償經濟損失5000元。
被告辯稱,涉案圖片具體來源已無法提供,亦無法說明涉案圖片的水印情況,不確定原告是否享有涉案圖片的權利。被告所發布文章的主要內容為原創詩文,而非涉案圖片,而且沒有商業用途,不具有侵權故意。
法院經審理查明,涉案圖片的生成過程為原告下載Stable Diffusion模型,隨后在正向提示詞與反向提示詞中分別輸入數十個提示詞,設置迭代步數、圖片高度、提示詞引導系數以及隨機種子,生成第一張圖片;在上述參數不變的情況下,將其中一個模型的權重進行修改,生成第二張圖片;在上述參數不變的情況下,修改隨機種子生成第三張圖片;在上述參數不變的情況下,增加正向提示詞內容,生成第四張圖片(即涉案圖片)。
北京互聯網法院根據原、被告的訴辯意見和查明的事實,認為案件的爭議焦點和審理難點為:一是涉案人工智能生成圖片是否構成作品,構成何種類型作品;二是原告是否享有涉案圖片的著作權;三是被訴行為是否構成侵權行為,被告是否應當承擔法律責任。
首先,從涉案圖片的外觀上來看,其與通常人們見到的照片、繪畫無異,顯然屬于藝術領域,具有一定的表現形式。涉案圖片為原告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生成的,從原告構思涉案圖片起,到最終選定涉案圖片止,原告進行了一定的智力投入,比如設計人物的呈現方式、選擇提示詞、安排提示詞的順序、設置相關的參數、選定哪個圖片符合預期等。涉案圖片體現了原告的智力投入,因此涉案圖片具備“智力成果”要件。涉案圖片是以線條、色彩構成的有審美意義的平面造型藝術作品,屬于美術作品,應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
第二,原告是涉案圖片的作者,享有涉案圖片的著作權。就涉案作品的權利歸屬而言,我國著作權法規定,作者限于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組織,因此人工智能模型本身無法成為我國著作權法規定的作者。原告是根據需要對涉案人工智能模型進行相關設置,并最終選定涉案圖片的人,涉案圖片是基于原告的智力投入直接產生,而且體現出原告的個性化表達,因此原告是涉案圖片的作者,享有涉案圖片的著作權。
第三,被告侵害了原告享有的權利,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本案中,被告未經許可,使用涉案圖片作為配圖并發布在自己的百家號賬號中,使公眾可以在其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涉案圖片,侵害了原告就涉案圖片享有的信息網絡傳播權。此外,被告將涉案圖片進行去除署名水印的處理,侵害了原告的署名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綜上,北京互聯網法院一審判決被告賠禮道歉并賠償原告500元。對此,雙方均未提起上訴,目前判決已生效。
近年來,學界關于AI生成內容可版權性的討論一直未曾停止,這為本案裁判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路。
北京互聯網法院綜合審判二庭審判員朱閣表示,本案中,涉案圖片系原告利用AI生成,根據著作權法關于作品的構成要件進行判斷,因涉案圖片體現出原告的獨創性智力投入,被認定為作品,相關著作權歸屬于原告。同時本案判決強調,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內容,是否構成作品,需要個案判斷,不能一概而論。本案的裁判結果對學界的討論予以充分吸收,體現出“一個傳承”和“兩點考量”。
“一個傳承”即本案裁判是對此前北京互聯網法院“菲林律所訴百度公司著作權案”的繼承和發揚。本案繼續堅持著作權法只保護“自然人的創作”的觀點,而人工智能模型不具備自由意志,不是法律上的主體,不能成為我國著作權法上的“作者”;本案繼續認定,一般情況下利用AI生成圖片的權益歸屬于利用人工智能軟件的人。
“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我們反復進行‘兩點考量’。”朱閣說,第一,當傳統理論遇到全新應用場景時,是否要進行調適和發展的問題。我們認為,只有秉持面向未來的司法理念才能更好地鼓勵新技術應用、推進新業態發展。在AI這種全新的技術背景下,傳統的著作權理論與技術發展現實已經不相匹配,應當進行調適和發展,更好地滿足權益保護和產業發展的需求。因此,我們不能固守歷史的標準,唯有面向未來進行思考,才能選好當下的路徑。
“第二,作品的認定是否僅有法律判斷,也是需進行價值判斷的問題。在當下我國人工智能產業迅猛發展之際,司法如何立足我國具體實際和我國的價值共識,服務和保障產業健康高效發展,是我們必須回答好的時代之問。”朱閣說,在這樣的背景下,基于對國家、社會、公民等各個維度的價值衡量,我們認為,通過認可人工智能生成圖片的“作品”屬性和使用者的“創作者”身份,更有利于鼓勵使用者利用AI工具進行創作的熱情從而實現著作權法“激勵作品創作”的內在目標,有利于促進相關主體對利用AI生成內容進行標識進而推動監管法規的落實、公眾知情權的保護,有利于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的創新發展和應用。
(來源:中國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