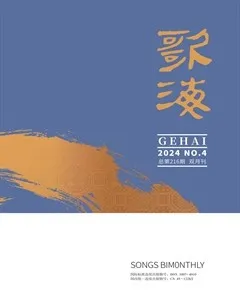黑白鳴奏出心的序曲
[摘 要]《心曲》組畫是黃新波木刻藝術風格全面成熟的代表作品,在中國現代版畫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心曲》組畫中人物形象的動態設計、刀法語言特征以及背景空間氛圍營造等,展現出黃新波中西融合的版畫語言藝術價值,其創作手法和理念對現代版畫創作具有重要啟示。
[關鍵詞]黃新波;《心曲》;繪畫語言;藝術價值
黃新波不僅是新興木刻運動中戰功卓著的健將,也是中國現代版畫史上杰出的代表性版畫家,其代表作品《心曲》組畫創作于1943年,是其蟄居桂林期間完成的一組既抒情又寫實的木刻版畫。《心曲》組畫共計十幅,分別是《孤獨》《掙扎》《淪落》《控訴》《心曲》(又名《信念》)《友誼》《相逢》《回家》《創造》《圣者》,每一幅木刻在敘事結構和內容方面都具有獨立性,不同類型的情感表達被巧妙地設置在主體框架之中,保持著情感的內在連續性。黃新波是在物質極其匱乏的情況下完成《心曲》組畫的創作的,“有時達到揭不開鍋的境地,便只好把自己的木刻原版劈開當柴燒”1。盡管生活條件艱苦,但黃新波仍不斷創作,《心曲》組畫無論是從現實主義的探索還是從木刻語言的實踐而言,都堪稱細致入微的佳作。而從黃新波賦予每一幅木刻的名字可知,該系列作品反映的正是戰時人類的孤獨、淪落、苦難、掙扎。黃新波“以刀代筆”,給予身處絕望的人們以光明,并重新燃起浸沒在苦難中的人繼續戰斗的信念與力量。《心曲》(桂林春草書店出版的個人畫集)《小引》中的論述,透露出黃新波作為現代版畫家的敏感和覺悟:“憑著心底真誠,以還沒有被時間侵蝕盡了底生命力量,希望從中去追求人間的共同的理想,以藝術來消除人間的隔膜,融和著崇高的友愛精神,充沛著永恒的美底生命。”2《心曲》組畫所呈現的藝術魅力深入人心,也是黃新波木刻藝術風格成熟的標志,直至去世,黃新波還在反復闡明其在創作《心曲》組畫實踐中所獲得的觀點:“畫有它的哲理,應該含蓄,而不是一覽無遺的,畫之外還有畫。畫要簡潔,但卻不等于簡單,應該概括著很深的內容和含義。”1
基于此,黃新波堅持“藝術緊跟時代,與人民生活血肉相連”的藝術理想,擺脫“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同時在魯迅先生“謹慎的推敲”藝術見解的指導下,自覺地將詩歌、民間剪紙、傳統墨法語言等融入木刻創作中,并始終圍繞吸收和融合寫實主義,又充分體現傳統刀法“深沉內省”精神特質的創作理念展開后續創作,探索傳統木刻刀法語言與西方寫實技法之間的巧妙融合。
一、人物形象的動態設計
《心曲》組畫中的系列作品畫幅尺寸都較小,內涵卻很飽滿,并都呈現出一個特點:每一幅木刻都有各自的主題框架,每個畫面都具備獨立性,每一幅木刻作品的主體人物的性別、動態以及年齡都存在著差異。其中,《孤獨》《淪落》《控訴》《心曲》《回家》《創造》《圣者》等七幅木刻的畫面主體均為單個人物,且人物動態形象簡潔、單純。《孤獨》一幅,描繪的是在微弱的月光下,一個孤獨佇立的幼女眼神無助又茫然,雪地上的腳印訴說著她來時的艱辛與路途的遙遠,以此可以想象殘酷的戰爭帶給兒童的種種不幸與苦難——她的親人可能已經慘死在敵人的刺刀之下,也可能失散在茫茫的人海之中,自此世間留她孑然一身,無所依仗。系列組畫之一的《淪落》,人物動態設計與《孤獨》相同,畫中的婦人戴著頭巾,如同雕塑般佇立在海邊,神情哀傷,黃新波特意強化了婦人手的造型力度,可以清楚地看到女人手上青筋暴露,緊緊握著一封書信,如同一具望夫石。而《回家》的畫面主體變成了飽經風霜的婦人,斜臥在荒原之中,疲倦的身體靠著滿布蛛絲的房子。
《控訴》與《心曲》所刻畫的人物主體均是青年男子,黃新波有意識地強化人物動態與人物形象,對青年男子的動態與面部神態進行特寫,把背景推遠,以增強對人物情緒狀態的準確表達。例如在《控訴》中,黃新波強調對人物動態的刻畫,通過糊化在渺無人跡的海邊張開雙臂、大聲疾呼的青年男子的面部,轉而對人物動態細致描繪,使人物更具張力,畫面的情緒表達更為充分。《創造》《圣者》兩幅作品,人物主體則變成追求光明的巨人形象,占據整個畫面,人物動態比例成倍地放大,顯得頂天立地。畫面中的巨人搬運著巨石,人物肌肉健美、身材壯碩,呈赤身裸體狀,更加顯露出力量感,同時也體現了人物的體積感。黃新波通過對巨人動態細致入微的描繪展現出必勝的信念和無畏的勇氣。
《掙扎》《友誼》《相逢》三幅木刻的畫面主體均為兩人,與單體人物相比,在構圖上更為考究。《掙扎》描繪了一對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男女,他們身體前傾拉著沉重的貨物,前傾的動態具有瞬間性、永恒性。他們為了活著而掙扎,疲憊得沒有多余的力氣,只剩貧苦、艱辛和無奈。《友誼》則是運用簡潔的排線勾勒出青年男子背著同伴在風雪夜艱難前行的場景。畫面中大量使用點刻,生動地表現了漫天風雪的場景,灰色調子很好地體現了衣服的褶皺起伏,寥寥數刀卻質感豐富,使得畫面細節真實可信。《相逢》描繪的是兩個流浪漢在曠野中相擁的場景——青年用肩膀托住老人佝僂的身軀,行李、人物、石塊、枯萎的樹根等元素在光的折射下形成有節奏的影子,在紊亂中建立了畫面的秩序感,給人以時間停滯的永恒感。
二、刀法語言特征
《心曲》組畫中的刀法呈現出單純、精練、堅實而剛健的語言特征,長短粗細不一的線條和大小各異的黑白色塊在黃新波的刀筆下產生了無窮的變化。如在《心曲》中他用三角刀所刻出的細致線條來表現人物面部、手部與服飾等細微之處,《淪落》中又以長短不一的纖細線條所形成的豐富的灰色層次來區分近景和遠景,展現山與水的空間距離……如此成熟、精湛的刀法語言得益于中西方優秀文化、藝術的熏習。黃新波在早期學習過蘇聯寫實木刻,吸收了蘇聯寫實主義中如何組織刀法以烘托場景氛圍的創作理念,隨后又受到美國版畫家肯特的影響,學習了大量西方現代派的技法,為創作現實主義題材的作品奠定了專業基礎,赴日本留學的經歷更是使他在木刻創作工具、思維觀念與視野上得以更新。此外,魯迅對黃新波在木刻事業上的熱忱支持和細致的藝術指導,使其萌發了木刻藝術創作的熱情,加之黃新波孜孜不倦的辛勤創作,使木刻之花得以綻放。
在人物面部刻畫和手部形態處理上,黃新波一般采取鮮明且強烈的黑白對比,大面積使用黑色,對受光面、白色區域的處理卻是嚴謹苛刻,用高度概括的白形表現人物面部、手部等細微之處。黃新波運刀的基本風格是輕柔細膩、氣脈平穩,重技術,重理性,行刀走線很有神采。 在人物五官的處理上黃新波有意識地做了減法,畫面中只保留對結構、比例有意義的線條,從而保持形體整體上的簡潔。在組織排列整齊的線條時,黃新波始終保持克制與理性,在處理黑與白之間的灰色層次時他嚴格遵循著物體的結構走向,并且有意識地強化了形體的體積感,削弱暗面與亮面之間的強烈對比。如系列組畫之一《心曲》(又名《信念》),畫面中青年人物的面部和手部就處理得異常精細,調子單純而精練,線條工整而不失章法,給人以細膩的美感。對海浪的刻畫也極其巧妙,通過對浪花節奏的歸納與整理,巧妙地表現出海浪的起伏,營造出典雅、協調的氛圍。平靜的暮色下暗流涌動,海燕與風浪的搏斗一觸即發,青年人心中懷抱希望,眼中閃爍光芒,凝視遠方,對未來抱有必勝的信念。
在人物的塑造上,為準確表現人物造型,黃新波強化了人物動態的傾向性和準確度,用類似素描中的明暗排線來勾勒人物輪廓,線條的黑白運用縝密而不顯零碎,這種明暗排線的運用并不完全是對現實的模仿,更多的是根據畫面黑白關系的需要而進行的一種主觀處理。在畫面遠景的處理上,作者有意識地縮小環繞在人物周圍的群山、河流、海洋等物象,擅長運用長短、粗細不同的線條與各種形狀的點刻,使物象在平面性和立體感之間達到某種巧妙的平衡關系,營造出帶有裝飾意味的場景空間,從而使人物始終處于畫面的中心位置,用細膩的技巧處理人物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給觀者傳遞出深沉的質感。
綜上,黃新波通過干脆利落的刀筆、豐富靈動的想象以及黑白轉換的無窮變化創造出詩意的視覺觀感。他的刀法語言特色主要表現為用刀老辣,傳遞出的語言精練、堅實而剛健,從而鳴奏出心的序曲以直面人生的困苦,既符合抗戰時期所提倡的“以生命寫史、以利刀刻畫”的革命斗爭需求,又易于激發人民群眾對作品的共鳴。
三、背景空間氛圍營造
《心曲》組畫在空間氛圍的營造上獨具匠心,展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其一,《心曲》組畫的畫面形式結構是堅固的、穩定的。其畫面形式結構的穩定主要通過兩個方面來體現:一方面,黃新波在構圖上經常采取經典、莊重的三角形構圖或金字塔形構圖,具有較強的穩定性,使觀者在心理層面感受到穩健、深沉的質感;另一方面則是通過對人物動態的細致描繪,塑造主體人物雕塑般的厚重感,給人以一種堅固的永恒感受,如《控訴》中在海邊呼喊的人、《創造》中搬石頭的男子以及《圣者》中抬起石頭的男子等。
其二,《心曲》組畫中常設置虛擬的光。黃新波喜歡用細密排列的線條來表現光感,喜歡在黑色背景下描繪強光照射的主體造型,如《掙扎》中為生活而掙扎的人、《淪落》中路燈下的婦人以及《孤獨》中月光下的幼女,他作品中的月光、燈光、燭火等“光”的設置是非常主觀的、戲劇式的。雖然其作品中的光是虛擬的,但卻給人以心理上的真實,這源于黃新波對月光、燈光、燭火下的真實意境的細致觀察和用心體驗。在這種獨特的光照環境中,白色是實有的,它是長夜中精神的唯一依托,黑色是虛無的,它是有限背后的永不可及的精神荒原。
其三,《心曲》組畫在氣勢上是宏大的。對比強烈的黑白關系是形成《心曲》組畫恢弘氣勢的重要因素之一,還有就是畫面中物象超常的比例設置。例如《心曲》組畫中的人物主體常被藝術家有意識地加以數倍放大,醒目地占據整個畫面,并成為畫面的中心,而背景中的山川、海洋等陪襯物象則常常被縮小,放置于巨大面積的黑幕中,將具體的現實問題擺放在虛擬的超大空間,使觀者有了在黃新波創作的宏大意象空間中圍繞主題去展開幻想、聯想的可能。
其四,《心曲》組畫的審美氛圍是崇高又壯美的。《心曲》組畫中使用大面積的黑色,使畫面充滿神秘感,形成畫面中“虛”的部分。例如藏在黑暗中的地平線常在無盡的遠方接入天際、蒼穹,又常在極端悠遠的地方伸向大海……面積占比不多的白形常被當成主體物象,將鏡頭推向主體的局部進行細致的特寫,體現出畫面“實”的部分。在《心曲》組畫中,白形的人物主體有一種類似中國大佛造像式的宏大氣象,入他畫境,觀之使人沉靜。虛與實的精妙關系形成了難以名狀的史詩感——以沖擊人的思想為目的,具有神秘色彩,表達強烈情感,帶給人身臨其境的審美感受。
其五,《心曲》組畫中的形象暗含某種象征的意蘊或內涵。黃新波善于選取高度凝練的物象,以象征的手法在畫面中隱晦地表達出自己的觀念,使人產生豐富的聯想。黃新波對《心曲》組畫中的物象皆采用了象征性的表現手法,使組畫中的物象都有一種高于具體事物的象外之旨。如《孤獨》中悄然滑落的流星象征著熾熱的希望,《心曲》中翱翔天際的海鷗預示著對自由的向往,《友誼》中雪地上的腳印暗示來路的艱辛,《淪落》中遠處忽明忽暗的燈塔給沉悶的夜空帶來一絲光亮,是對希望的隱喻。再如系列作品之一的《回家》,木屋象征著對家的眷戀,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家是能夠實現居住功能的所在,而在黃新波的作品中,木屋的尺寸小到無法容納下女人的肉身與靈魂,女人疲憊地靠著木屋,而木屋門前布滿蛛絲塵網且久久無人歸來,暗示著此屋的荒蕪,整體畫面平靜卻又讓人感悟到靈魂的無處安放。《心曲》組畫中符號化的造型、浩瀚的氣象和深廣的意境,都使作品暗含著對人生和宇宙禪悟哲思般的意味,從而成為某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終極關懷的精神象征。
結語
《心曲》組畫是黃新波經過不斷尋覓與探索創作出的藝術成果,它標志著黃新波的藝術理念與風格進入到成熟期,畫面中技法與內容完美結合,形成了獨特的個人風格與面貌。《心曲》將文學的意境融入到畫面中,給人以美感,讓人回味無窮。他將西方寫實技法與中國社會現實相結合,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其木刻創作藝術手法和理念也給當下版畫創作帶來啟示:第一,黃新波用刀筆和木板在黑與白之間進行創作,詩意地書寫心中之曲,顯示出恢弘的氣象,撥動觀者心弦,使不同時代的人在欣賞他的作品時都能獲得獨特的感受與發現。同時,其作品中所蘊含的理想與激情永遠激勵著版畫創作的后來者。第二,黃新波注重生活感受,觀察生活細致入微,其作品中充滿詩意的畫面往往取材于生活,并通過詩意的聯想以及嚴謹的反復構思提煉而成。面對信息化時代海量的內容,當代版畫創作者需要主動收集、整理素材,并進行思考、提煉,才有可能將素材內容轉換成獨特的語言運用到自身的創作當中。第三,黃新波廣泛吸收各家所長,糅合并運用西方造型與中國審美理念,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為我們提供了中西結合的考察樣本。然而,如何轉化與創新中國版畫審美和藝術語言,以適應現代生活的表達需求,仍是當代版畫家需要解決的藝術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