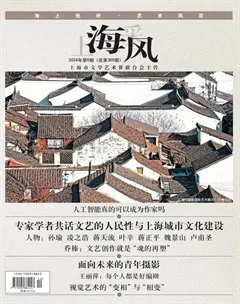人造之景:雕鑄與守望中的生命與文化




2024年11月23日上午,第十五屆中國攝影藝術節開幕式暨金像獎頒獎典禮在河南省三門峽市舉行。中國攝影金像獎是經中央批準,由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攝影家協會聯合主辦的攝影領域全國性最高個人成就獎,是對德藝雙馨攝影工作者藝術成就的最高贊譽。上海市攝影家協會副主席敖國興榮獲第十五屆中國攝影金像獎(藝術攝影類)。
1990年代敖國興在魯迅美術學院藝術攝影系開始系統研習攝影。那時生產圖像的主要方式仍是化學成像,膠片和暗房是必要的材料與成像流程。1999年敖國興考上趙大鵬教授的碩士研究生,開始研究攝影美學。“我是中國第四位攝影專業碩士研究生,當時魯美的攝影專業在國內擁有超前的攝影認知及完整的教學體系,對各國攝影理論和影像語言的系統研習極大程度地拓展了我的視野,為我初步建立了閱讀影像、判斷影像與創作影像的一個較高標準。”畢業后,敖國興先后從事了記者等工作,最后在2002年來到上海大學上海美術學院任教至今。“可以說這30多年來我一直未間斷地在攝影學術理論和當代攝影藝術實踐中鉆研探索。”
關于自己的攝影生涯、對攝影美學的理解、對攝影技術的實踐以及作為攝影工作者的責任與擔當,他這樣說——
記者:您的獲獎作品是如何拍攝的,能否談一下當代銀鹽顯像工藝與其在藝術上的潛能。
敖國興(以下簡稱敖):是用大畫幅相機和中畫幅相機拍攝的。銀鹽顯像工藝是一種不斷生長的媒介,它的潛能就在于它可以承載任何藝術觀念、以自身的獨立特性回應每一個當下的藝術史轉型期。在攝影脫離了純粹紀實的功能性之后,手工制作照片的過程與繪畫思維高度依存,那是一種對畫面內容主動構建而非被動記錄的思維。手工痕跡的完全彰顯賦予作品獨特的個體性和偶發性,也正是這種實驗的特質,讓銀鹽在當代語境下有了更廣闊的表現空間。
我的三系列獲獎作品就使用了黑白銀鹽成像作為底層技術,再用鎢絲燈照射底片,以使化學藥液產生反應。在多年的反復推敲、實驗下,這種自創的顯色工藝技術成為我創作表達最重要的藝術手段,我將其命名為“光化顯色”顯像法。它孕育出的色彩制造了一種夾雜著空氣感,恍似中國傳統山水畫與西方世界相互糅合的黃色,使得游樂場散發陳年跨越時間的氣味,使動物標本獲拂夕陽落下時的暖風、使山石景觀轉化為宛若放置多年的、巨大的干花簇叢。色彩是畫面情緒的控制器,為了追求一種介于現實與虛幻之間的情感狀態,我的攝影工藝在作品中已然成為一種深刻的思想載體。技術構成美學,而美學融于觀念。我所處的時代,工藝純熟追求的已不是某種從一而終的匠人精神,而是一種建立于美學享受之上的“儀式感”。
記者:獲獎作品是想探討個體在環境中與歷史文化的關系嗎?可否介紹一下。
敖:具體來說,這些作品共同探討的問題可凝練為:時間與空間之于生命與文化的意義。我一直強調,存在并非靜態,而是時間性的展開。在獲獎作品中,我以極其客觀的攝影語言呈現三種人造物的存在模式:游樂場、動物標本和人造山石景觀。對客觀的把控則致力于為這些熟悉的事物增添陌生感,將當下與歷史、與未來相互交織,將有關時間的哲學思考具體化地揉捏進作品中。是因為它既是我們創造的人工空間,又充滿了情感記憶。同時,我作為一個浸潤在中華文化中成長的人,如何將其中的深刻意義在東方美學的體系中得以顯現和轉化也是我多年來不斷探討與反思的永久課題。
譬如在《歡樂頌》中,靜止的游樂設備置于空曠的幕景中,形成了時間停滯的視效,然而我拍攝的并不是某個靜止、凝固的瞬間,是這些人造物,是一場記憶與空間的互動。同時,畫面中的游樂場和我童年記憶中的游樂場所處并非同一空間,甚至在時間上的跨度更加遙遠。此時的游樂場覆蓋著巨大的時空,其中給人帶來的歡樂情緒在時間的軌跡中成為一種群體記憶。游樂設施蘊含著的無數片段都在我定格的畫面中并驅齊行,正如畫面中的“長時間曝光”,在時間對光的壓縮侵占中,畫面最終只剩下清晰的主體,其余的喧囂與無限變化的風景則全部在時間中歸為虛無的想象空間,中式留白的具體含義在此刻得以完整詮釋。具體的游樂設施,是我們跨越時間和空間去讀取童年記憶的快捷符號。
又或是《風之谷II》中的動物環境標本。在我定格的畫面中,被攝物的栩栩如生使得它們的本體性質無法被直接分辨,成為靜止與再生并存的畫意美。進入第二層次的觀看后,動物軀體上隱藏的一系列傷痕以及憂懼情態又開始與表現之美發生沖突,生命的動態齒輪再一次轉動。當回首意識到它們僅僅只是冰冷的人造標本時,才透悟時間的流動終使生命的熱烈與狂野化于平靜。我構建了一個模糊、抽象的第三世界,在這個世界里,被攝物脫離了生與死的時空限定,從而在失諧的對抗關系中概括出生命的全部。這里凝聚的不是生命中的某一時刻,而是生命全部的時間,是永恒與堅韌。這就是我認為的:時間概念里的生命與存在。
倘若前二者是對記憶、對生命的致敬,那么《新山水》則是我對傳統文化的致敬。同樣地,我拍攝的依然是人為改造過的山水,即使我脫離了傳統山水景觀中以自然為本的塑造目的,并彰顯了其現代攝影的物質特性,但它們仍然與傳統美學保持著潛在的、內在的相關性,這是介于古典與現代之間的文化連結。橫幅的長卷風格制造了散點透視的意境延展,焦平面的極致壓縮將風景歸納為一種特定的中式紋理,人為活動的痕跡鐫刻在原有的自然景觀之上,我在時間的多維度疊加中闡述山水存在的全部過程。《新山水》想表達的是,自然之道并非永恒不變,而是不斷地在適應、改變與重生。
記者:在創作中是否會考慮到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與融合?
敖:會的,且是在不經意間發生的。這和我的受教育經歷有關系,1990年代,中國攝影創作者還處于以“決定性瞬間”為最主流的表現方式。當時我上大學的魯美是中國最早開設藝術攝影本科專業的藝術院校,也是當時為數不多的與西方攝影教育機構建立實質性聯系的國內高校,很多國外攝影家、藝術家、教育家到魯美開設講座與短期課程。這些課程對我有極大的啟發,尤以德國院校每年寄送來的系刊,還有《德國攝影年鑒》等刊物。其中的那些呆板、單調的仿佛“標本”一般的照片,令當時的我十分訝異。我心里暗忖:“這還是攝影嗎?”研究生期間,我在導師趙大鵬先生那里看到了愈來愈多的國外攝影畫冊與專業書籍,也開始系統研究包豪斯(Bauhaus)及當代德國攝影的脈絡。它們無形之中構成了我對攝影藝術的初步視覺印象,也一定程度上為我日后的作品風格定下了基調。正是在此階段,我察覺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異。而攝影是一個完全西方輸入的媒介,它的早期發展承載了西方現代科學技術、工業化和理性思維的特質,這與強調“意會感知”的東方哲學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悖論,因此我們當時的攝影總是在模仿和學習西方的進程中,且與我們自身的傳統文化相離甚遠。
自那以后,中西方文化的碰撞與融合就成了我創作中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我一直嘗試將西方的產物成為東方哲學的承載體。其二者碰撞與融合絕不是簡單的疊加,而是一個深度互動的過程,涉及對文化差異的理解與超越,要求創作者同時擁有兩套完整的知識體系。傳統中國美學講究“意境”,強調對自然和宇宙的整體感知,所謂的“留白”并不只是一種用來描繪山和水的繪畫方式,而是一種全然的想象無限的空間,是“余音繞梁,三日不絕”的內在感知。《歡樂頌》中的留白代表的是時間和記憶的無限流動,是回憶的痕跡;《風之谷II》則通過留白為物象提供了新的棲息地,賦予其超越具體時空的抽象所指。而《新山水》涉及更加完整的中國美學體系,它制造的中式紋理形成一種我們概念中的美學感知,只此一眼,便立刻能將其定位南宋趙伯駒的《江山秋色圖》中國傳統山水畫卷。再反觀它們的視覺樣式,我的作品常常帶有一種清晰、冷峻的風格,呈現出對事物平靜而深入的凝視。這是我在大學期間德國著名教育家、攝影家托馬斯·呂特格教授,還有去杜塞爾多夫美術學院游學時,“新客觀主義”給我帶來的巨大影響。冷靜的情緒、嚴謹的細節還原,融合中式色彩和寫意留白,即是我作品中的文化融合。攝影作為西方技術的延伸,在中國文化語境下的實踐難以回避其“異質性”,我們很難做到純粹東方或是純粹西方,融合與碰撞是必經的過程。但也正是因為這種外來性,攝影能夠成為觀察、記錄和重新定義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媒介,經過不斷地揉搓過濾,最終孕育出屬于時代的產物。
記者:作為一名攝影教育者,您能否談一下對當代攝影教育的探索?
敖:在任教20多年期間,我一直思考如何在教學中有效平衡傳統與創新、理論與實踐、技術與藝術之間的比重。今非昔比,現在的時代相比我讀書的時代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多媒介的跨界融合、觀念先行的思維模式、令人驚嘆的技術迭代速度等等。這些無不鞭策著我們教育工作者實時更新自己的理念和方法。在我的教學模式中,本科的教學是對技術和基礎理論素養的夯實,研究生才是對藝術思維和社會實踐的深度培養。在研究生一年級的時候,我會讓學生大量翻譯、分析中西方的攝影理論著作和藝術評論,培養文化敏感性與全球視野是這個時期的重點;二年級時,個人創作和社會實踐置于首位,我會帶著他們參與各方面的 創作活動和學術項目,鍛煉個人專業能力和綜合能力,并在連續不斷的創作和研習中找準自己創作的方向;三年級是對所有成果的集中匯總,將注意力放在沉淀自身上,獨立做出完整的畢業論文和畢業創作,最后整合資源選擇未來合適的專業發展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在AI技術迅猛發展的當下,誕生了大量的生成式圖像模型、風格遷移處理和各式各樣的智能編輯,它從思維上更新了傳統攝影的生產方式和創作方式,為藝術創作開拓了一片新土地。近些年,我常常引導學生去擁抱新技術,讓學生熟悉不同的技術在創作中的應用潛力,同時我也在不斷地學習,和我的學生們共同探索這個時代攝影藝術的創新可能性。
我們處在藝術史新篇章的首頁,起到社會藝術引領作用的學院派絕不能止步不前。當代高校攝影教育的目標是培養有思想深度、文化自覺、社會責任感以及符合時代特征的全方位藝術家。在不斷變化的藝術語境中,我希望我能夠通過適配的教育方法,幫助學生找到自己的藝術表達方式,并以攝影創作參與到更廣闊的社會與文化的對話中去。
記者:怎么看攝影工作者的責任?
敖:我認為,攝影工作者的責任遠不止創作本身,更在于以作品雕琢時代,承擔起社會與文化的觀察者、記錄者和思考者的使命。無論是商業攝影、紀實攝影還是藝術攝影,其意義都在于為未來留下可信賴的視覺檔案,為藝術史和文化延續提供鮮活的佐證。同時將我們的研究成果回饋于社會,這份責任是對當下的回應,和對未來的承諾。正如我的導師趙大鵬先生對我的教誨:“要先學會做人,再做藝術。”“你未來的目標不是為了獲得幾個國內外的大獎,而是為中國培養出更多優秀的青年攝影藝術人才。”他的話深深影響了我的職業選擇和發展道路。金像獎是對我個人努力的肯定與鼓勵,但它絕不是我向往的終點。它的含義在于引領我,提醒我始終腳踏實地,在理論研究與創作實踐中不斷精進。我深知自己肩負著傳承與發展的重任,我會銘記初心、牢記使命,為下一代延續金像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