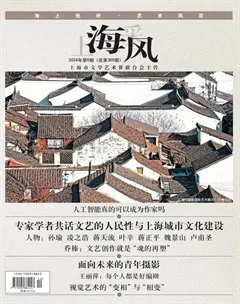手繪海報不了情







上點年紀的人大概都不會忘記當年上海街頭各家影院門前的大幅手繪電影海報。它們常換常新,爭奇斗艷,以其獨有的藝術風采和有別于其他繪畫的自身特點讓人們津津樂道、印象深刻而難以忘懷。
追逐流逝的歲月
都說往事如煙,其實并非如此。有些事你曾為它癡、為它狂,中間的酸甜苦辣都嘗了個遍,它是不會輕易隨風而去的。歲月積淀下來的一定是一壇老酒,慢慢透著醇香;一定是一筆寶貴的財富,由你靜心享受。
我中學畢業分配在房地局工作,當過倉庫管理員,也做過財務。在房地局掛名十年后,跳槽進了文化系統到電影院當上了美工。這期間,我考入上海大學美術學院讀書,有留校當老師的機會,我放棄了;借調到區機關工作,有當公務員的仕途,我也婉拒了。就因為喜歡畫畫,喜歡電影,我一根筋回到電影院,認認真真畫海報、踏踏實實做美工。當時的想法非常單純:就是要在自己喜歡的崗位上圓夢理想。至今我仍對當初的選擇不后悔,因為愛好最終成了我的職業。
記得小時候,只要路過電影院,我都會情不自禁地停下腳步,駐足仰望墻面上的巨幅電影海報許久。畫面上一個人物的大頭像要比真人大很多,當時那種對我的強烈震撼和沖擊,仿佛就在昨天。可喜的是,許多年后,我也有幸調入了電影院,夢想成真,從一個仰望者變成了電影宣傳隊伍中的一員。
當時上海的各家影院都有美工這一崗位,隸屬業務組,主要工作就是畫海報、布置櫥窗。這是當時主要的兩種電影宣傳手段,普通觀眾基本上也是通過這些載體才能獲得電影信息的,所以美工的崗位非常受重視。
由于各家影院的建筑結構不同,外墻海報欄大小不一,所以每家影院的海報尺幅大小、橫豎比例都是由自家美工量身定制。盡管電影公司每月都會派發統一的官方海報和相關圖片資料,但一般只能用于張貼櫥窗,而在影院外墻上的大幅海報還得靠各家影院的美工二度創作、各顯神通。當年上海街頭常常會出現這樣一個場景:每有一部新片上映,各家影院的門前就同時貼出了同名不同樣的新片海報,一時可謂百花齊放,滿城飄香。它既是各家影院美工的作品秀場,也成了一道獨特的電影文化風景。
電影海報的手繪周期一般是兩至三天,因人而異吧。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影院排片每月也就四五部,時間算寬裕。想當年,每個月心無旁騖地畫四五幅海報,真是一種享受。就是每月月初的第一幅海報,要趕一趕,因為月底才明確排片,找素材構思繪制需要時間,還得提前張貼出去,時間上有點緊。
我們美工都有一張《試片入場證》,規定大家在每周二上午,憑這張證去大光明電影院看兩部新電影,這些影片會在下個月或者再下個月上映。這個待遇在旁人眼里是莫大的福利,但對我們而言看電影首要還是為工作,因為只有先了解了電影才能畫出合格的海報。當然光看電影還不夠,畢竟不能憑記憶來畫海報。盡快收集到理想的圖像資料,對我們而言才是最關鍵的。當時官方發放的資料通常是“1+8”,也就是一張整開海報,另外還有8張八開的劇照。一張整開海報質量尚佳,但另八張劇照的質量經常不敢恭維:不是人物太小,就是成像模糊,很難派上用場,這就迫使我們還要在其他相關電影雜志上尋找可用的素材。只要找到一個比較清晰的大頭照或者比較理想的主角完整形象,我們的心就放下了大半。
電影海報本質上就是電影的廣告和代言,它首先從屬于電影,傳播電影信息、引導觀眾看片是它的使命,同時它又是一幅兼具美學價值的設計作品,這正是電影海報有別于其他美術作品不同的地方。因此,除了突出人物形象、烘托背景氛圍外,海報上還必須有片名、主創人員名單、電影屬性、廣告語、出品廠家和上映日期等文字要素。這些必需的電影信息與畫面的完美組合,才構成一幅真正意義上的電影海報。所以,我們在構思畫小稿時,都會對整個畫面上的人物安排、背景處理、字體選擇及色彩運用等進行全盤考慮。小稿自己滿意了才動手放大繪制。
電影海報一般都用水粉寫實的方法來表現,也可根據不同影片的內容風格,采用版畫、裝飾畫,甚至夸張變形的漫畫等樣式,這些樣式我都在實際工作中運用過并證明可行。特別是版畫風格,其簡潔的構圖,明快的色彩對比,具有獨特的藝術效果和吸睛作用。
當年我們的作畫工具,都是大號的油畫筆和各種尺寸的底紋筆,用色也是大瓶裝的顏料。因為一般的海報大多都在七八平方左右,小號畫筆根本施展不開。影院的美工室比較寬敞,那是因為它要容納得下足夠的繪畫墻面和保證繪畫過程中的進退空間。繪制海報,大部分美工的習慣做法,是先把整張白紙依次用圖釘固定在底板上,紙與紙之間交接有一二厘米的重疊,畫完再取下張貼到室外的海報墻上。可要銜接得完美也不容易,不小心有露白,還得美工稍作修補。我后來采用的方法,是先將白紙用化學漿糊裱在底板上,這樣畫面平整不起皺,畫起來也順暢,畫完再把整塊板搬出去掛墻上完事。
常年在美工室里或埋頭構思,或提筆涂畫,是一件辛苦并快樂著的事:找不到合適的素材會心焦,看不中理想的草圖會苦惱。當正式動筆繪制時,因為大底板是不能動的,爬上蹲下變換各種不舒服的姿勢便成了工作常態。無論是站在長條凳上涂頂端的底色,還是弓下身子書寫最下面的文字,都是費神費力的活。好在當時年輕氣盛,苦點累點心甘情愿,加班加點也樂此不疲,因為我始終懷著一顆喜歡電影熱愛畫畫的初心。而當一幅新的海報完成,尤其是自己覺得還算滿意時,心中便會產生一種成就感,張掛到影院外面,迅速引來路人圍觀,聽到旁人的嘖嘖稱贊,那時候真會有點小得意,虛榮心滿滿。
影院美工基本是單兵作戰,個別影院也有兩三位的,但就整個上海而言總數也就百十來位,算是個非常小眾的群體。但我們的工作,面對的卻是真正的大眾。可以說當年影院美工的海報作品,是受眾最廣、更替最快的戶外美術展覽,曾經吸引過無數電影迷和美術愛好者的腳步和目光,它成了電影文化與大眾百姓進行互動溝通的窗口和橋梁。在沒有現代傳媒的推廣下,很難想象一件繪畫作品能直面那么多觀眾,而電影海報,那個時候就做到了。
其實,當年并沒有手繪電影海報一說,加上“手繪”二字,當是后來有別于千篇一律的印刷海報而言。當年家家影院門口的大海報,哪一張不是美工手繪的呀?只可惜,盡管那時影院美工中不乏高手、佳作迭出,但用水粉上色畫在紙上的海報,袒露戶外、歷經風雨且不斷重疊,是很難完整保存下來的。況且當時大家也未必有這個意識,能拍下一張照片留存已是不錯的了。以至于我們現在稱其為“非遺”,是非常遺憾的藝術。其中既包含著無奈,也透出幾許酸楚。
20世紀末,隨著高科技的進步發展、中國電影市場的跌宕變化及影院自身的升級改造,戶外廣告宣傳、傳統手繪電影海報迅速被寫真噴繪等新技術新材料替代。影院門前固定的海報陣地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老美工逐年退休,影院一般也不會再招新人。昔日能寫善畫的在崗美工,在單位也只需要張貼張貼印刷品再無需運筆舞墨。無可奈何花落去,手繪電影海報最終止步于新世紀的門檻前。
當時上海影院系統的宣傳歸口電影放映發行公司。公司會經常組織各類業務技能的評比活動,曾組織舉辦過數屆全市性的電影海報創作展和與外省市的聯展。最后一次則是由當時文廣局主辦的“99上海市電影發行放映系統國產影片海報與美術創作作品展”,地點在梅隴鎮廣場。那是上海影院美工手繪電影海報作品的最后一次集中亮相,順理成章成了千禧年來臨之前的手繪電影海報絕唱。
喚醒海報的新生
沉寂了10多年的手繪電影海報重回觀眾視線,已是新世紀的2014年。那一年我行將退休,滿以為從此將會與手繪電影海報徹底告別,因為我是電影發行放映系統中的最后一代美工,我都退了,今后也不會再有什么上級部門來組織相關活動了。
真是好巧不巧,是年3月,《解放日報》記者欒吟之約我采訪,要我談談這么多年來做影院美工和美術創作的經歷,我們聊了許多,我還給她看了一些我以前畫的海報照片。后來,她的專訪文章見報,標題用的居然是:海報技藝在他手中“重生”。這讓我心中一驚:手繪電影海報還能“重生”嗎?我真沒敢多想。更巧的是,差不多同時,上海電視臺新聞綜合頻道的項目主管王明遠先生也邀請了我們幾位同行商量,說要拍一部有關影院美工的紀錄片,并說這個選題早已敲定,遲遲不開機的原因是訪談類節目總要有相關的影像資料做背景烘托,但他們在資料庫里翻了許久,也找不到多少與電影海報相關的鏡頭,現在不等了,馬上開拍。當時我曾調侃:電影院的美工從來就是“動手不動口、工作在幕后、海報掛墻上、姓名都不留”的角色,誰會把鏡頭對著你呢?但這一次,機會來了,我和幾位前輩同仁應邀出鏡,在這部《電影海報的手繪溫情》專題片中深情講述了自己當年與手繪電影海報的那些事。由于內容比較獨特,最后片子分為上下兩集很快播出。真心佩服現代媒體的傳播力,就是厲害。一時間熟人朋友碰到我,見面第一句話一定是:在電視里看到你了,接下來便同頻共話“老朋友”電影海報。我猛然意識到,原來手繪電影海報離大眾并沒有太遠,許多人還記得它。
同年4月,在一次朋友聚會中,大家又情不自禁聊起我們的老本行電影海報。一群年過花甲的老伙計們感嘆歲月無情,又流露出對手繪電影海報那段激情歲月的無限懷念。我當時就提議,我們可以自己出資來辦海報展,大家都贊成并推舉我拿出個初步方案。我想到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我們可以用自己最拿手的電影海報來紀念抗戰勝利,實現自己的心愿。就畫一批抗戰的電影海報辦展,成了大家的共識。沒想到這個純粹出自同行間私下交流碰撞出來的創意,很快得到了普陀區檔案局的高度重視和介入,有了政府的加持,還得到了資金保證。方案再細化,信心被提振,老美工們的創作激情迅速被點燃。我很快遴選出了40多部優秀國產抗戰影片供大家選擇,其間還和幾位同仁專程到抗戰遺址采風,走訪了臺兒莊、棗莊、冉莊、黃崖洞、麻田、平型關、盧溝橋等地。時值北方隆冬,冰天雪地,一路采風,非常辛苦,但收獲滿滿。回來后投入創作,同樣面臨很大的挑戰:到底10多年不畫海報了,大部分美工都面臨資料匱乏,體力不支,視力下降,創作條件不佳等因素的困擾。但大家都是全身心投入,充滿信心。重拾畫筆,重操舊業的過程是五味雜陳。反復觀看影片,找尋畫面,然后用手機或相機拍下打印出來,再構思構圖繪制。這期間,我曾一次次被經典電影那熟悉的畫面和旋律打動,也常常思緒穿越回到當年的工作場景之中。特別是,為了展覽需要,我們的海報作品都要求畫成一開大小的尺幅,相比當年繪制大海報時的大筆縱橫,難度更大、要求更高。盡管如此,大家還是克服了種種困難,最后如期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創作。
2015年6月9日,正值“國際檔案日”,一個別開生面的電影海報展:“勿忘·前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電影海報新作展”在普陀區圖書館展廳開幕。《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51號兵站》《鐵道游擊隊》《三進山城》等一批經典抗戰電影海報,經老美工們的重新演繹,以整開紙的幅面展現在觀眾面前,迅速引來媒體廣泛報道和觀眾的好評如潮。主流媒體相繼報道了這個凝聚著10多位影院老美工創作心血的特殊展覽,對手繪電影海報在牢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弘揚民族精神、激發愛國情感方面發揮的作用給予了充分肯定。展廳里每天都有不少觀眾自發而來,除了細細觀看深深贊嘆之外,還寫下了厚厚兩本熱情洋溢的留言。觀眾中有在職的公務員、有離退休的老干部老同志、有武警官兵、有社區居民,有東北籍的大學生,也有操著南京腔的新上海人,他們都對畫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有些觀眾還給我們提出了許多中肯的建議。最后這個展覽在巡展多處后,所有海報作品入選上海“民族脊梁——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主題展,在中華藝術宮展出達兩個月之久,影響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著名社會學家、上海大學顧俊教授觀展后著文《電影海報里的歷史》:“面對從小看到大的一部部抗戰電影,從《雞毛信》到《血戰臺兒莊》,在一幀幀海報上次第展開,讓人頓感滄海桑田。”“更別出心裁的是,所有海報都有當年專門制作海報的老畫家創作并執筆。這群曾經活躍在各大影院門口海報欄上的畫家們回來了,重新拿起畫筆,面對塵封多年的老電影再次煥發創作的激情,濃墨重彩地呈現了中華民族那段艱苦卓絕的歷史。他們滿頭華發與電影海報中永不衰老的影片主角相映成趣,訴說著‘以史為鑒’的情懷。為了以史為鑒,我們才將崢嶸歲月留在電影這抹不掉的記憶載體中;為了把老電影留在記憶中,我們才重新舉辦海報畫展;為了讓海報再現當年神韻,老畫家們才重出江湖,而因為再次執筆,才得以留住了他們對中國歷史包括電影史的這一篇章獨特的認知和表現。”
社會的普遍認可,媒體的推波助瀾,一時間手繪電影海報重回觀眾視線,讓我們非常振奮。普陀區檔案局搶救手繪電影海報的智慧決策和責任擔當,使大家的創作欲望越發強烈,第二季的策展隨即展開。
2016年6月6日,“紅色記憶——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手繪電影海報新作展”開幕,表現中國共產黨光輝業績和優秀共產黨人卓越風采的四十余幅電影海報新作齊齊亮相。我們還根據觀眾的提議還原當年工作狀態:我和兩位同仁在展覽現場繪制了一幅十二開大的《開天辟地》電影海報。開幕式當天,主辦方特意請來了拍攝該片的著名導演李歇浦先生,李導在現場心情激動地講起當年拍攝影片的花絮,并高興地與我們一起在大海報上簽名,這幅原作現在已被普陀區檔案館收藏。
2017年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反映人民軍隊光榮歷程的電影非常多,我們便決定第三季就用90幅經典軍旅電影海報向建軍90周年獻禮,向共和國的鋼鐵長城致敬,向所有的電影人致敬。6月9日,還是選在“國際檔案日”,“長城·軍魂——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手繪電影海報新作展”率先在普陀區文化館開幕,6月27日又移展至上海市文聯展廳,隨后還下部隊進社區巡展。連續三年,三個主題電影海報展,留下了100多幅珍貴的原創手繪電影海報,它真的在我們手中“新生”了。
一位觀眾觀展后給我們留言:手繪電影海報不光讓人們得到了繪畫藝術上的享受,還能得到電影中心思想的理解與鼓舞,通俗易懂,是普通市民喜聞樂見的藝術作品和宣傳形式。但現在的問題是你們老一輩在展示手繪電影海報的同時,是否考慮過傳承的問題?這么好的一種藝術形式和宣傳形式,到你們這一代成了絕筆,那就太遺憾了!這個問題我也不止一次地被問到。但我想告訴他:我們慶幸自己曾經是手繪電影海報的參與者,給這座城市留下了一個溫暖的話題和一段值得珍藏的記憶。今天我們重拾畫筆,重繪經典,還能發光發熱,已經非常知足。
2018年1月中旬,受上海電影博物館之邀,我又創作了兩幅手繪電影海報,其中一幅是拍攝于四十年代的老電影《遙遠的愛》,陳鯉庭編導,趙丹和秦怡主演。這幅秦怡老師的電影成名作海報作品,作為特殊的生日禮物,贈送給了96歲的壽星秦怡老師。另一幅是主辦方為我量身定制的一個項目:匠心繪影。要求我在上海中心119層“上海之巔”現場,繪制一幅由秦怡老師編劇并主演的《青海湖畔》電影海報,海報面積六個平方米。經過兩天半的工作,順利完成任務,我榮幸地創造了一項手繪電影海報在中國第一高樓高空作業的紀錄。2月3日下午,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秦怡老師坐著輪椅來到現場,全場報以熱烈掌聲。我和上影演員劇團團長佟瑞欣上臺,徐徐將深紅色的帷幕拉開,《青海湖畔》海報亮相上海之巔,瞬間引爆全場。此時我站在秦怡老師身邊,看到老藝術家眼含熱淚,非常激動,她高興地在海報中央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幅在中國地面建筑最高處完成的海報在“上海之巔”展出后,將作為贈品永久落戶上海中心。
不久,上海國際電影節開幕式導演團隊聯系到我,邀我參加6月16日晚在上海大劇院舉行的第21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頒獎典禮,并希望在之前創作繪制一幅大海報,這幅海報要在“向幕后電影人致敬”環節上亮相。任務艱巨又光榮,但如此巨幅的海報在哪里完成是個難題,幾經協商,最后決定就在大劇院后臺現場繪制。導演問我需要多少時間?我說5天,但接下來畫什么影片卻遲遲定不下來。直到6月11日下午,才確定畫《碟中諜3》。我連夜看片,在電腦上構思設計,半夜完成方案送審。12日方案審定,下午趕到大劇院后臺開始工作,此時給我的時間只有兩天半了。當天的效率不高,手機不停地響,有約訪談的,有約拍攝的,加上大劇院后臺燈光較暗,在礙事的腳手架上繪制非常不便。第二天,九點開工,影響進度的還是腳手架的障礙和燈光,唯一的一盞小太陽燈只能置于后背,畫板上剛好是自己的投影。為了確保完成任務,我盡快畫完了上半部分。到下午兩點,撤除了腳手架,換上了桌子和凳子組合,上上下下便捷多了,工作效率明顯提高。經過兩天半的辛勤勞作,巨幅海報《碟中諜3》終于在上海大劇院后臺身邊嘈雜的搭景調音噪聲中完工。彩排時,當看到自己的勞動成果被徐徐推上舞臺中央,頓時內心充滿了喜悅和自豪。稍覺遺憾的是,這幅巨大的手繪海報,最終沒能在開幕式上推到臺前來,而是改用了背景大屏幕顯示。6月16日晚,當我站在第21屆上海國際電影節金爵獎頒獎典禮的舞臺中央,接受央視主持人任魯豫采訪時,大屏幕上呈現的便是我手繪電影海報的集錦和前兩天剛剛完成的《碟中諜3》。我聽到了全場響起的熱烈掌聲,真切感受到了臺下嘉賓和觀眾對手繪電影海報的熱烈反應。伴隨著鮮花和掌聲,我在現場與嘉賓分享了自己與電影海報臺前幕后的故事。當主持人問我,在那么多年默默付出、畫了那么多海報卻沒有留名的情況下,有沒有遺憾時,我脫口而出:沒有遺憾,只有感恩。我要感謝上海這座城市,感謝電影給了我施展才華的舞臺。不經意間,我們為這座城市留下了一道值得回望的風景、為電影留下了一個溫暖的話題,這足以回報我們的付出。今天的電影節向幕后電影人致敬,其實就是對工匠精神的肯定。這一刻,我知足了!
今年9月,作為上海市文聯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5周年主題活動之一的“大手筆——手繪電影海報特展”在上海圖書館東館開幕。我有幸參與全過程。開幕式上,上海電影家協會主席鄭大圣有一段感言,他說:“放了學,愿意挑經過電影院的路回家,倒不一定是為了看電影,而是為了看新的海報。”鄭導還清楚地記得“小時候那些手繪電影海報的精彩”,并說“這是一份很讓人向往的工作”。很榮幸,我就是一直在做這份很讓人向往的工作,這次特展,我不僅自己有十多幅作品參展,還和同伴在現場手繪了一幅大型舞劇電影海報《永不消逝的電波》,還原了當年我們的工作狀態,每天都會引來一些讀者駐足。特展期間,我多次到展廳導覽,與觀眾互動,在一幅幅述說著家國情懷、洋溢著手繪溫情的海報前,給觀眾和影迷們講解手繪海報的幕后故事,共同回望曾經的激情歲月,希望讓更多的人了解中國電影的歷史和一個時代的記憶。
時光荏苒,往事未曾如煙。
手繪電影海報給了我平凡人生一抹亮色,感恩我曾經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