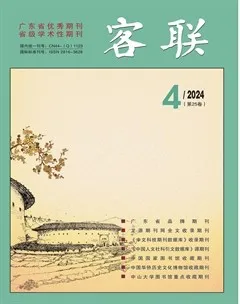人臉識別技術的應用與隱私權的保護
摘 要:近年來,隨著人工智能和計算機視覺技術的飛速發展,人臉識別技術已經在多個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本文在人臉識別技術的應用現狀的基礎上分析其在隱私權保護層面面臨的挑戰,并從法律層面提出相應的建議,以期為人臉識別技術的合理應用和公民隱私權的有效保護提供參考。
關鍵詞:人臉識別技術;應用;隱私權的保護
隨著人臉識別技術的迅速發展和廣泛應用,如何在利用這一技術帶來的便利性和高效性的同時,保護公民的隱私權,成為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人臉識別技術在公共安全、金融支付、社交媒體等多個領域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其可能引發的隱私泄露和濫用風險,對個人隱私權構成了挑戰。因此,探討人臉識別技術的應用與隱私權的保護,對于平衡技術發展與個人權利保護、推動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人臉識別技術的應用現狀
首先,在安防領域,人臉識別技術已經被廣泛應用于公共安全和社會管理中。例如,在機場、銀行、商場等重要區域的門禁系統和監控系統中,人臉識別技術廣泛用于識別和驗證人員的身份,從而保障公共安全。人臉識別技術在社區和樓宇的安全監控層面同樣應用廣泛,有效的提高社區和樓宇的安全性。
其次,在金融領域,人臉識別技術也得到了廣泛應用。例如,在身份驗證和移動支付等方面,人臉識別技術可以用于確認用戶的身份,提高金融交易的安全性。此外,人臉識別技術還可以用于銀行柜臺的客戶服務,提高服務效率和客戶滿意度。
最后,在商業領域的人臉識別技術應用同樣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在市場調研和客戶分析方面,人臉識別技術可以幫助企業了解消費者的偏好和行為,從而改進產品和服務,提高客戶滿意度和忠誠度。人臉識別技術還可以用于零售業的支付系統,實現便捷的刷臉支付,簡化購物體驗。
二、人臉識別技術對隱私權保護的挑戰
(一)商業行為中人臉識別技術對隱私權保護的挑戰
在數字化時代,人臉識別技術的應用日益廣泛,但同時也引發了公眾對人臉信息采集、使用和二次開發過程中隱私權保護的擔憂。例如,許多網絡服務提供者在用戶使用其服務時,強制要求用戶同意采集人臉信息,這往往使用戶處于劣勢地位,不得不為了獲取服務而犧牲個人隱私。這種強制性的做法削弱了用戶的知情同意權,使得隱私保護措施形同虛設。再者,網絡服務提供者在獲得用戶的人臉信息后,可能會超出原始采集協議的范圍,將這些人臉信息轉化為具有商業價值的數據。例如,通過分析用戶數據進行精準營銷,或者將用戶的聯系信息用于推銷活動,這些行為不僅可能侵犯用戶的隱私權,還可能對用戶的日常生活造成干擾。除此之外,一些人臉信息數據被進行二次開發,與其他信息結合以進行深度分析,可能導致用戶的隱私數據被用于戰略營銷等活動中。這種做法如果沒有符合法律規定或未經個人明確同意,將構成對公民隱私權的侵害。因此,在利用人臉信息進行數據二次開發時,必須確保符合相關法律法規,需經過個人明確同意,以保障公民的隱私權益不受侵犯。
(二)公權力行為中人臉識別技術對隱私權保護的挑戰
在公共領域,政府使用人臉識別技術進行治理時常常需要采集大量的人臉信息,但這一行為往往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盡管《民法典》對隱私權和私密信息的處理有了明確規定,強調了法律的明確規定或權利人同意是處理人臉信息等私密信息的前提,但公權力機構在實踐中處理人臉信息時,往往只有少數情形有明確的法律依據,大多數場景都缺乏法律支撐。例如,《刑事訴訟法》和《反恐怖主義法》為偵查機關使用人臉識別技術識別或跟蹤犯罪嫌疑人提供了依據,但在交通出行等其他應用場景中,卻無法律依據的支撐,這對個人隱私保護構成了挑戰。這表明在當前的治安防控體系下,公民個人信息的安全保護仍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按照“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如果沒有法律的明確規定,公權力的行為可能與行政行為合法性原則相違背,從而侵犯隱私權。
此外,在治理實踐中,公權力機構很少遵循“知情-同意”原則來收集人臉信息,這同樣可能導致個人隱私權受到侵犯。“告知-同意”原則旨在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和對隱私信息的控制權,是私密隱私信息保護的基本原則。然而,由于人臉識別技術的“非接觸”和“隱蔽性”特征,公共部門在獲取人臉信息時可能會忽視這一原則。即使公共機關收集的人臉信息符合“告知-同意”的要求,但由于人臉信息可能與其他數據庫進行連接和匹配,這種數據的流轉對比往往屬于暗箱操作,公眾可能并不知曉自己的人臉信息被如何使用,這不僅違反了“告知-同意”原則,也可能違背“目的限制”原則,侵犯公民對隱私信息的控制權。
三、人臉識別技術下隱私權保護路徑的實現
(一)明確人臉識別技術應用的原則
相關法律法規如《民法典》、《個人信息保護法》等都明確規定了知情同意原則,體現了對個人隱私權的重視。人臉識別技術作為生物識別信息的一種,屬于敏感信息,其收集、儲存和使用應遵循知情同意原則,否則將承擔法律責任。然而,實踐中知情同意原則的執行并不理想,原因包括:強制性同意(如在公共場所的使用)、透明度低(用戶對信息用途了解不足)以及信息處理和再次流通時缺乏再次征求同意。為解決這些問題,應提高人臉識別技術使用的透明度,并在初次收集人臉信息后,如需改變用途或進行流轉處理,應重新征求用戶的同意,以保障用戶的知情權和隱私權。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殊情況下,如疫情期間,為了公共利益,個人權利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讓渡,這是知情同意原則的唯一例外。
(二)細化隱私權侵權救濟處罰規定
在人臉識別技術相關的法律案件中,不同國家對于侵權賠償的判決存在巨大差異。例如,中國的“人臉識別第一案”判決賠償金額為1038元,而美國Facebook因違反伊利諾伊州《生物識別信息隱私法案》被判決賠償6.5億美元。這種賠償力度的差距引發了對我國侵權救濟處罰規定的深思。在美國,個人可以提起民事訴訟進行權利救濟,賠償金額既可以是實際損失,也可以是法定賠償,訴訟費用由侵權方承擔。而中國的數據犯罪處罰主要針對違法所得和非法獲利,缺乏對數據利用和獲取的明確規制。盡管《個人信息保護法》規定的罰款有所提高,但對于侵犯個人生物識別信息權益的損害確定和賠償標準仍未作細化規定。因此,為了更好地維護公民隱私權,應當細化現有法律條款,建立更細致的處罰和賠償制度。例如,明確損害要件,不僅涉及財產賠償,還應包括精神賠償,以減少公民維權的成本,增加侵權成本,從而更有效地保護公民的隱私權益。
(三)完善隱私權保護的程序控制
人臉識別技術的應用應通過立法控制和監督機制來確保公民隱私權不受侵犯。在公共領域,公權力組織應明確使用人臉識別技術的界限,采取嚴格保密措施,并遵守“最小必要”原則,以保障公民隱私權。商業領域中,應以個人“知情、同意、選擇”為基準,審慎設計法律制度,確保商業機構采集人臉信息時需經過個人明確同意并有正當合理的使用理由。監督方面,商業領域的監督應采用企業自律加行政監管模式,建立行政監督機構,加強行業自律。公共領域的監督應引入司法監督機制,以限制行政機關的權利,保護公民隱私權。此外,應制定相關法律法規,防止人臉信息被濫用,并確保人臉識別技術在法律范圍內使用,最大限度地保護公民的個人隱私權。
參考文獻:
[1]徐春杰. 人臉識別技術下隱私權保護問題研究[D].貴州大學,2024.
[2]劉嘯宇. 人臉識別技術的應用與隱私權的保護[D].青島大學,2021.
[3]郭暢. 大數據時代隱私權法律保護研究[D].河南大學,2023.
[4]張豫辰.人臉識別技術應用中隱私權風險控制路徑構建——基于場景差異性的考量[J].湖北警官學院學報,2022,35(02):77-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