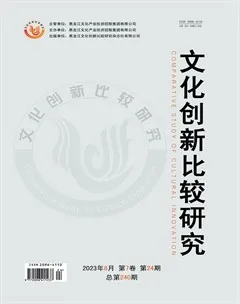論黎紫書《告別的年代》的女性成長敘事
孟玉
(長江大學人文與新媒體學院,湖北荊州 434022)
黎紫書1971年生于馬來西亞怡保,是馬華“七字輩”代表作家之一,有“得獎專業戶”之稱。《告別的年代》曾入選《亞洲周刊》中文十大小說,榮獲第十一屆花蹤文學獎馬華文學大獎、《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和第四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推薦獎等。發生于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是馬來西亞華人沉重的集體記憶和精神創傷,《告別的年代》中杜麗安的命運轉折就始于“五一三”事件,小人物的個體命運與歷史事件交織而成為歷史場域的一部分,黎紫書書寫杜麗安的生存境遇和成長歷程,也是在關照馬來西亞華人女性的在地生活和命運走向。
女性成長是黎紫書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由于性別境遇和文化位置不同,女性成長有明顯區別于男性成長的特點。有學者將女性成長小說定義為“以生理上或精神上未成熟的女性為成長主人公,表現了處于‘他者’境遇中的女性,在服從或抵制父權制強塑的性別氣質與性別角色的過程中,艱難建構性別自我的成長歷程,其價值內涵指向女性的主體性生成,即成長為一個經濟與精神獨立自主的女人”[1]。杜麗安從社會底層的戲院售票女郎成為老字號茶室老板,實現物質和精神富足的過程,也是她主體性生成的成長過程。本文立足女性成長敘事視角,從主體意識覺醒、女性身體解放和主體性生成三方面解讀杜麗安的成長蛻變。
1 主體意識覺醒:“他者”境遇下的掙扎
男權社會中女性是依附男性而存在的客體,“他是主體,是絕對,而她則是‘他者’”。女性實現自我成長首先要確立主體意識,即“女性作為主體在客觀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價值的自覺意識”[2],它是激發女性追求物質和精神自主的內在動機。同時,“女性主體意識的確立和發展是個不斷變化和豐富的過程”[3],《告別的年代》中杜麗安經濟獨立后逐漸擺脫對男性的依附,清醒認知姐妹情誼,這個實現物質與精神雙重自足的過程體現了她主體意識的變化和豐富。
1.1 “前成長”狀態下的主體覺醒
所謂“前成長”狀態是指成長主人公“思想意識處在舊的已去、新的沒來的黎明前的黑暗狀態”[4],“前成長”狀態下的女性仍依賴男性提供的物質條件和精神依托。與鋼波結合是杜麗安身處“前成長”狀態,在主體意識尚未完全覺醒的情況下做出的取舍。“五一三”事件當日,鋼波救下被瘋漢用車鏈襲擊的杜麗安,兩人因此相識。鋼波曾是私會黨的小頭目,比杜麗安大20 多歲,私生活極為荒唐,在老家漁村有妻有兒,在外又終日鶯鶯燕燕。鋼波還曾到杜麗安家里討債,砸掉她老爸的一顆門牙,用熱水把她老爸的手燙得冒煙。杜麗安卻對舊日仇人的追求欲拒還迎,最終拋棄以教師為業的戀人葉蓮生,嫁給鋼波做妾室。
處于“前成長”狀態下的杜麗安雖然已有改變自己命運的意識,但仍將自己置于“他者”境遇下。結婚之初的杜麗安視自己為鋼波的附屬,她在婚姻中極力討好鋼波,試圖以美食和孩子留住鋼波的心。杜麗安改良過母親傳下來的廣西釀豆腐和芋頭扣肉,又學做鋼波喜歡的鹽雞和算盤子等客家菜,讓鋼波吃得贊不絕口。杜麗安曾為鋼波頻繁回漁村看望孫兒深感焦慮,為此她迫切希望用孩子拴住鋼波,曾多次央求鋼波去看醫生。“前成長”狀態下的杜麗安看似懂得憑借婚姻改善物質生活,她不僅有了屋子、平樂居,還有自己的汽車,也是鄰居中最早有彩色電視、電冰箱和錄影機的,但這其實是女性以身體、性別為籌碼換取的所謂主體成長,其本質仍視自己為依附于男性的客體,是“他者”境遇的延續,缺乏明確的主體意識。
1.2 經濟獨立與主體意識明確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女性要想推翻“他者”身份,其中一條就是成為“職業女性”,經濟上獨立于男性。成為平樂居的老板娘,物質上自給自足,是杜麗安實現自我成長、告別“他者”身份的關鍵一步。大伯公會撥下錢后,杜麗安全權操辦生意,從物色地點到看風水取名字都由她一手籌劃。雖然最后鋼波以兩個兒子要搞養魚場為由把一部分資金“抽調”到漁村去,讓原本計劃開酒樓的杜麗安只得開小茶室,但杜麗安卻將茶室經營得生意興旺。《告別的年代》多次提到杜麗安操弄收銀機的情節:“錢箱彈出。滿眼硬幣與紙鈔”“她仍然每天打扮靚麗,坐在平樂居柜臺里按收銀機”“她已掌握了這臺收銀機的節奏,熟練得幾乎可以用它來演奏了” ……錢箱不僅是杜麗安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她經濟實力的象征,經濟獨立后的杜麗安精神上也開始擺脫從屬狀態。
杜麗安操持平樂居經濟獨立后,自我主體意識逐漸明確起來。杜麗安第一次讓鋼波領教她的“意志如鋼”是確定新房前栽種的植物。杜麗安決定在前院種幾棵皇家棕櫚,樹下再擺幾盆蘇鐵和九重葛,鋼波對此不滿,嫌棄這些東西不能結果實還浪費土地。杜麗安卻以低頭算賬的姿態來回應他,讓他明白自己已無法被人左右。“女性爭取話語權的抗爭過程實際上是自我建立的過程”[5],決定栽種的植物不僅是杜麗安爭奪話語權的勝利,也是自我建構的過程,而憑借經營平樂居實現經濟獨立無疑對她主體建構起著很大作用。
1.3 清醒認知姐妹情誼
姐妹情誼是“女性團結一致的強烈情感”[6],女性之間生存體驗相似,能夠分享彼此的悲喜且相互扶持,因此姐妹情誼在女性成長過程中有重要作用。《告別的年代》中娟好與杜麗安因曾同在戲院工作、同為人妾而漸漸親近,特別是弟弟南去都門、母親駕鶴歸西后,無人傾訴心事的杜麗安一度與娟好推心置腹。娟好曾為杜麗安分擔不育的焦慮,不但陪她去看婦科醫生,還每周替她燉滋陰補陽的湯藥。不可否認在娘家無人后,與娟好的這份姐妹情誼曾給生存困境和性別“他者” 境遇下的杜麗安帶來過精神慰藉,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杜麗安主體性建構過程中的艱辛和苦痛。
然而姐妹情誼并非牢不可破,“女性之間總是因為社會角色,包括地位、身份、名聲的懸殊而彼此疏離;女性之間還會因為女性自我心理、氣度、才智的偏狹而彼此輕視”[7]。娟好與杜麗安出身相似,免不了暗中攀比,陳金海死后娟好為陳家所拒,而杜麗安順風順水好不得意。娟好認為杜麗安對她的關照是東家恩施,而非姐妹之情。娟好與潮州佬吵架丟盡顏面,埋怨杜麗安不幫忙而心生嫌隙,后來干脆辭去茶室工作。杜麗安給娟好包了紅包并要私下請她吃飯,但娟好并不領情,一直未曾赴約。娟好再次出現是杜麗安與鋼波分道揚鑣后,她頗有落井下石意味地帶來鋼波的消息,杜麗安深知娟好喜歡在自己人生暗淡時期出現,并未表現出娟好所期望的自憐與憤慨。杜麗安告別對男人的屈服狀態,也清醒認知姐妹情誼的親和與背離,消除精神依附,明確主體意識,這是主體成長的重要一步。
2 女性身體解放:從被凝視到反凝視
男權社會中女性的身體作為被凝視的客體而存在,女性的欲望也是被壓抑的。“女性主義身體論認為,身體的意義和價值不僅在于其物質存在,更重要的是,它與女性主體性的建構有密切關系”[8],因此,正視自我身體也是女性成長的必經階段。《告別的年代》中杜麗安正視身體之欲、反抗男性凝視的身體解放過程,是她走向主體成熟的重要步驟。
2.1 女性欲望復蘇
男權社會過于強調女人的母性、妻性等社會性,卻忽視了女性身體中蘊含的作為自然本性的性欲,男性想當然地認為女性沒有欲望,女性往往也順從男性意愿壓抑自己的欲望。《告別的年代》中杜麗安與鋼波在結婚之初的性愛更多是為取悅鋼波,而與葉望生的偷情則更多是自我滿足。葉望生是杜麗安舊戀人的同胞哥哥,也是繼女劉蓮的現任男友。杜麗安與葉望生于尚在裝修的新房內、鋼波的舊居中、破舊的五月花旅館里縱情歡愉,享受這段不倫婚外情帶來的身體欲望滿足。個體的主體性是身體和欲望的統一,杜麗安正視并滿足自己的欲望是走向主體成長的重要一步。
“性愛作為女性成長過程中最醒目的標志,其中所有的幸福與痛苦都將一起成為女性尋找自我、塑造自我的力量源泉”[9],在與葉望生的情欲糾葛中,性愛不僅給杜麗安帶來歡愉,還給予她塑造自我的力量。杜麗安在滿足欲望的同時并沒有迷失,她將關系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手中。當杜麗安意識到“公子味”的望生與“書卷氣”的蓮生始終是兩個人時,主動結束了這段關系。與大多數文學作品中情欲結束后男性給予女性金錢關照不同,《告別的年代》中曾兩次描寫杜麗安給葉望生現金的情節,在葉望生幫她暗中置業后她遞給葉望生一沓鈔票,在關系結束時她留給葉望生的信封里又是一沓鈔票。對該情節的描寫不僅因為杜麗安經濟實力優于葉望生,也是她在關系中占據主動權的體現,杜麗安并不想與望生繼續,所以用金錢為兩人劃清關系,這也是她主體成長的表現之一。
2.2 身體解放與反凝視
男性凝視“是一種將女性物化、化為景觀并成為可欲對象的心理機制”,在男性凝視下女性被塑造為迎合或滿足男性欲望的客體。《告別的年代》中杜麗安一度成為被男性們凝視的客體,她曾被陳金海用似笑非笑、半醉似的眼神盯得毛骨悚然,也曾被鋼波的兄弟在婚禮上起哄,更有甚者拿“范麗”“狄娜”之名對她的大胸脯意淫和調笑,而大杜麗安20 多歲的鋼波對杜麗安的追求很難說不是源于對她年輕肉體的渴望。凝視還具有規訓身體的作用,“這種外來的目光如同一面鏡子,不知疲倦地提醒著被監控者存在著不足之處,從而使被監控者馴服地接受目光的安排和調控”[10]。在男性凝視的規訓下,杜麗安對身材十分在意,忙于生意后長胖了的她因身材不比以前玲瓏而介懷在心,與葉望生初識時她還曾為自己的臃腫感到難堪。杜麗安此時將自己置于被凝視的客體位置,自覺接受男性目光的規訓,但伴隨主體成長,杜麗安開始反抗男性凝視。
女性成長應該走出男性的目光,擺脫自我客體化的困境。反凝視“立足于消解凝視的權力性”“用對立的抵抗的姿態對權威進行挑戰”[11]。客體通過反凝視,將自己置于能動地位,使自身占據主體位置。杜麗安的反凝視首先體現在對符合男性審美的身材標準的反抗。杜麗安曾一度對身材十分在意,但“領養”孩子后生活愜意的她已不在意身上長肉,她喜歡自己的富態,并覺得如今的體形配上翠綠或蔥白的玉器好看得很。其次表現在杜麗安生育態度的變化。見過繼女劉蓮對鋼波及漁村一家老小的照料后,杜麗安向葉望生提出想要一個女兒,她看穿葉望生的沉默并強調想要自己的女兒,不是“我們的女兒”。此時生育對杜麗安來說絕非男權專制下的奴化與犧牲,而是自我心愿的滿足,甚至在杜麗安看來葉望生是生育工具,是被凝視的客體。身體對個體成長具有重要意義,從被凝視到反凝視的身體解放過程,也是杜麗安正視自己女性身體的生理特征并走向主體成熟的重要步驟。
3 主體性生成:走出婚姻圍城
主體性是人在實踐過程中表現出的能動、主動和自由,主體性是一個動態的生成過程。《告別的年代》中杜麗安主體意識覺醒、女性身體解放再到走出婚姻圍城的成長過程,也是她主體性動態的生成過程。杜麗安在家庭生活權力博弈中取勝,以及其后走出婚姻圍城是她主體成熟的標志。
3.1 婚姻中的權力博弈
女性的成長與其在兩性關系中的位置是緊密相關的。《告別的年代》中杜麗安與鋼波在結婚之初是一種從屬和支配的關系,鋼波處于支配地位,杜麗安從屬于他,杜麗安在鋼波面前謹小慎微,她小心翼翼地處理與繼子繼女的關系。但伴隨杜麗安的生意越做越好,兩人的家庭地位發生變化,家事開始由杜麗安做主。杜麗安得知繼子石鼓仔吸毒后,未與鋼波商議就將鋼波最看重、最疼愛的兒子石鼓仔趕出家門。鋼波結束逃亡生活歸家后,也是杜麗安押著鋼波去給莊爺道歉。在生日宴上莊爺兒子挖苦鋼波并要罰鋼波酒,又是杜麗安上前擋酒。杜麗安由以前順從的被支配者,變為家庭中的掌權者,家庭地位的變換和家庭權力的顛覆,是杜麗安發揮主體能動性的結果。
鏡子作為意象符號在《告別的年代》中多次出現,“女人在整個一生中都會發現,鏡子的魔力對她先努力投射自己、后達到自我認同是一個巨大幫助”[12],杜麗安通過鏡子審視自己和他人,對主體成熟起了重要作用。在成長之初,鏡子像男性眼光的代替物,傳遞著男權凝視的審美標準,無淚風暴后杜麗安“看著被裝在鏡中的自己,臉上也沒淚痕,卻那么憔悴,像突然老了”。鏡子也能成為幫助成長主體實現自我認同的工具,鋼波落魄回歸后,杜麗安一覺睡到傍晚養足精神后,“她朝鏡里的人微笑。嘴角翹得夠高的”,此時杜麗安借助鏡像協調內心感受、確認自我,以積蓄力量來應對眾人的盤問。在主體成長后期,鏡子還成為杜麗安審視他人的工具,“她抬起頭來看著梳妝鏡里一前一后的兩個人影……這男人腦殼中間的頭發全掉光了,剩下的一圈也疏疏落落,半數是白發”“鋼波就在那一面小圓鏡里,多么卑微”[13]。借由鏡子,杜麗安確認自我,也審視他人,與風光無限的杜麗安不同,此時鋼波已是落魄年邁的老者。杜麗安與鋼波家庭地位的顛覆,打破了男權體系下以夫為綱的規范,是杜麗安婚姻權力博弈中的勝利,也是杜麗安主體成熟的體現。
3.2 走出婚姻圍城
鋼波逃亡在外的幾個月,沒有告知杜麗安去向,沒有給她捎信,甚至連電話都沒有打回來,兩人夫妻情分逐漸消耗殆盡,搬到新洋房后分房而寢。其后杜麗安與鋼波達成協議,鋼波不需要再負擔家用和房子供款,并把舊屋子給他,而把大屋轉到杜麗安名下。做完財產分割后,不需要再負擔家用和房貸的鋼波對家庭已沒有貢獻,甚至成為家庭的累贅。經濟早已獨立,精神上也再無依附的杜麗安原本可以結束這段婚姻,甩掉已成為累贅的鋼波,但杜麗安感念鋼波給了她最初的立腳處讓她可以逐步高攀,選擇繼續與鋼波維持這份無愛的婚姻,并履行妻職,在鋼波病倒后還常去病床前照顧鋼波。
杜麗安在病房遇到生面孔的中年婦人和一對少年男女,才知道原來鋼波不知多少年前就瞞著她在甲板小鎮有了“第三頭家”,且當年拿錢資助漁村兩個兒子辦漁場根本就是個謊言,實際用來安置甲板小鎮的家。甲板女人的出現徹底粉碎了杜麗安與鋼波最后的情義,讓她明白曾經的恩情里摻雜了太多謊言。杜麗安結清醫院賬單,留下地址鑰匙,將鋼波交代給漁村的人。最后鋼波被安置在老房子里,只有卡拉OK 伴唱機和老人椅作伴,那一刻他真明白了杜麗安的“恨與意志”,而這“恨與意志”里應當也包含了杜麗安告別過去的決心。以主體性生成為標志的女性成長之路,必然伴隨著對男權的抵制和解構,如果說鋼波的衰老是杜麗安成長路上男權式微的象征,那么杜麗安最后將鋼波從洋房中趕出,則一定程度上象征著女性主體生成后對男權的解構和驅逐。走出婚姻圍城的杜麗安實現了主體性成熟,也最終完成了這場延宕多年的成長蛻變。
4 結束語
《告別的年代》講述了出身馬華社會底層的杜麗安實現物質豐裕和精神蛻變的成長故事。杜麗安的個人成長史也再現了馬華女性艱難的主體生成過程,為我們打開了瞭望海外華人女性生存境遇的一扇窗。有學者指出,黎紫書《告別的年代》塑造的是女性視角觀察下的女性成長史,但又不僅是“成長”這么簡單,重要的是她找回被長期瑣屑生活所遮蔽的“女性身份”。在歷史長河中女性大部分處于緘默狀態,她們無名、無意義、無身份。《告別的年代》中杜麗安的母親姓名不詳,被鄰里街坊喊做蘇記或炒粉婆,大多數馬華女性正如蘇記一樣,長期處于主體懸置、身份遮蔽的狀態,而杜麗安這一代女性則在覺醒和成長中找回了女性主體身份。或許借由《告別的年代》一書,黎紫書想要告別的不僅是杜麗安的過去,也是對馬華女性無名史的告別,是對女性主體性缺失時代的告別,而諸如杜麗安般的成長和成功也寄托了作者對馬華女性未來的美好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