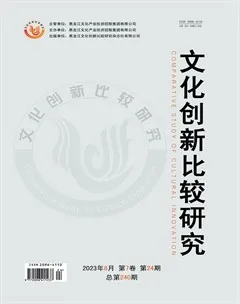《墨子》的廉潔思想及其新時代價值
陳宇,韓劍英
(北京信息科技大學(xué)馬克思主義學(xué)院,北京 100192)
墨子(公元前476 或480年—公元前390 或420年),名翟,是春秋末期戰(zhàn)國初期宋國人、先秦墨家思想的代表,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之一。墨子創(chuàng)立了墨家學(xué)說,墨家與儒家并稱“顯學(xué)”。墨子在吸取時代成果的基礎(chǔ)上,以兼愛為核心,以節(jié)用、尚賢為支點,創(chuàng)立了以幾何學(xué)、物理學(xué)、光學(xué)為突出成就的一整套科學(xué)理論,并且提出了“修身”“兼愛”“非攻”“尚賢”“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樂”“節(jié)葬”“節(jié)用”等觀點。《墨子》作為墨家學(xué)派思想的集大成,共有53 章的內(nèi)容,其思想受到當(dāng)代廣泛的關(guān)注且產(chǎn)生深遠(yuǎn)的影響。習(xí)近平總書記多次在重要會議上引用《墨子》的經(jīng)典治國理政思想,2018年11月26日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xué)習(xí)時講道:“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1],2022年2月25日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體學(xué)習(xí)時提出:“兼相愛”,凸顯出墨子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價值和意義。
學(xué)界研究中,大多研究墨子的治國理政思想或者墨子的科學(xué)與技術(shù)思想,直接涉及墨子廉潔文化思想的研究比較少。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墨子的廉潔思想具有針對性、先進性,以及富含國家層面價值觀的追求,在周蕊[2]、蔣國宏[3]的研究中,從墨子的“義利觀”“兼愛論”及“節(jié)用論”等方面進行廉政研究;在刁川夏[4]的論述中,用墨子的勤儉思想來論述其廉政觀念。通過對《墨子》一書的檢索,發(fā)現(xiàn)直接講到“廉”的思想共有5 處,分別在《修身》《明鬼》《號令》《經(jīng)上、經(jīng)說上》《雜守》篇中提到;間接包含廉潔思想的有《節(jié)用》《所染》《兼愛》《節(jié)葬》《尚賢》《尚同》等篇章。墨子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懷著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貧眾寡、安危治亂的理想,將“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 的根本理想追求作為倡導(dǎo)廉潔文化的最重要目的和方向,“潔廉利民” 是以圣王的教誨為基礎(chǔ),在上符合圣王之道,在下滿足百姓的利益。
本文將從《墨子》中的“潔廉利民”“君子修身”“貞廉任仕”“輕禮節(jié)用”“兼愛貴義”5 個方面去探討墨子思想中蘊含的廉潔思想及其根本價值追求。從而探討《墨子》廉潔思想為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廉潔文化建設(shè)提供歷史資料。
1 《墨子》的廉潔思想
1.1 “潔廉利民”的國家理想
《墨子》中的“明鬼”思想是把廉潔視為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例如:
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為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為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為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間,擬乎鬼神之明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
認(rèn)為從官府行為角度,應(yīng)將廉潔文化賦予更高的神化思想,將廉潔思想與神靈的圣潔和鬼神的壓力結(jié)合使政府官吏做到廉潔,以神靈的角度去推行廉潔文化,真正做到“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 的國家和社會治理思想。“明鬼”是將個人廉德和天下治理思想相結(jié)合,強調(diào)廉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成為善與惡的標(biāo)桿。
墨子思想之中“利”的理論解釋為:利于天下人的大利,才是真正重視人生問題之中的“義”,廉潔文化之中,不僅是簡單的“義與利”之間的分別,墨家主張犧牲個人小利而促成大利,可以說,重義輕利,二者的問題是兼并的,性質(zhì)也是并存的,但墨子決不倡導(dǎo)“因義而棄利”。“利民”[5]作為墨家的民本中心思想之一,所蘊含的廉潔文化不僅是本身的含義。在畢天云的論述中,《墨子》“利民” 思想的目的是 “滿足民欲”[6],為官“潔廉”是在“天人觀”為基礎(chǔ)的哲學(xué)思想上將人民當(dāng)作天地之子,“利民”作為墨子“民本”思想之中的重要理論基礎(chǔ),墨子認(rèn)為對待百姓應(yīng)該做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統(tǒng)治者真正做到對百姓的“兼愛”,對九州萬方一切事物存有仁愛之心,將天地生靈當(dāng)作普遍之愛,就可以控制思想和行為的神圣性。廉潔既是一種文化,也是對人性的一種考驗,將廉潔思想當(dāng)作神圣的思想并進行愛護,便是墨子在“利民”之中所體現(xiàn)的博愛思想。墨子將“天人合一”的思想作為神圣的天地之物,人民生于天地之間,為民求得清明社會,便是廉潔文化之中蘊含的利民思想。“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之利,除去之害。”君子的施政是要以“仁”為治民之根本思想和為政作風(fēng),為天下之大利與百姓之眾利。
《墨子》的政治思想之中,以潔廉為本根,以利民為核心追求,全面體現(xiàn)了治國理政的“底線”便是潔廉從政,充分反映了“民本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社會風(fēng)氣,在管理階層所追求的“利民”福祉下,選拔和建設(shè)一支賢能兼具、德才兼?zhèn)涞墓賳T是政府的首要任務(wù),以“潔廉利民”為核心的雙向性體現(xiàn)在“君子修身”的內(nèi)省、“貞廉任仕”的國家官員選拔,引申出“輕禮節(jié)用”的廉潔方法和“兼愛貴義”的核心價值追求。
1.2 “君子修身”的廉德內(nèi)省
在《墨子》的第二章《修身》中,直接提道:
故君子力事日強,愿欲日逾,設(shè)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于心者,無以竭愛,動于身者,無以竭恭,出于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發(fā)隳顛,而猶弗舍者,其唯圣人乎!
該內(nèi)容提出了個人廉潔的底線,能在貧窮時表現(xiàn)出廉潔,富足時表現(xiàn)出恩義,對生者表示出慈愛,對死者表示出哀痛,這是墨子對“廉潔”一詞的正面解釋。君子所為之事則是貧則廉潔,富則重義。貧窮的狀況下才能認(rèn)識到“廉”的本性。君子修“四行”,在“四行”之中,“廉”為君子之道的基礎(chǔ)。時帥認(rèn)為,墨子的廉潔文化中的修身思想是做到“義取義予”[7]的主要方面。
墨子認(rèn)為君子應(yīng)該做到:“君子察邇而邇修者也。見不修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譖慝之言,無入之耳;批捍之聲,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修身”是君子對自我德行的一種修養(yǎng)和改正,修身和律己是相互統(tǒng)一的。先秦思想的發(fā)展歷程中,“修身”并非是墨家獨有的思想,墨子認(rèn)為“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yuǎn)。君子察邇而邇修者也。見不修行,見毀,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修矣。”君子能夠明察左右的人以提高自己的修養(yǎng),并虛心去改正自己在道德上的不足之處。從廉潔文化來講,“修身”便是對個人廉德的直接審視與監(jiān)察,對為政者的考驗則是“士雖有學(xué),而行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wù)豐末”,即只有學(xué)識是不夠的,還要去身體力行。若想成為君子,一定要勤于修行、堅持修行、真正的修為,“修身”是對自己的“修德”,在德行之中思考人生理想與人生問題中的哲學(xué)理論。墨子主張的“修身”所要最終改變的是:“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修身”真正要做到的不僅是“修德”,也是在做人為官之時對“濁”的現(xiàn)象與行為的遠(yuǎn)離和對自我的行為與精神上的 “自守”,“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嘆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君子修身立命,能做到慎獨并且不受環(huán)境的影響。修身以正思想,是做到“安貧樂道”,為政者在貧窮之時還能堅守住自己的廉潔,不被外界思想所改變,并且做到經(jīng)常反問自己的修為成果,在做人之本中堅定自己的初心。
《墨子》在修身方面的廉潔是對個人廉德方面的嚴(yán)格要求,真正做到自我的廉德,便是將個人的廉德進行修養(yǎng)與反思的同時,把思想的凈化和行為的約束作為修身的最終目標(biāo),并在修身思想之下做到超然脫俗的心靈凈化,進而做到“慎獨自律,修己安人”的修養(yǎng),以修身為清思想,清思想以正朝堂,國家和社會的風(fēng)氣才會正直,會選用真正的廉潔之人成為為政者。國家選仕之根本為政治清明,從“人性論”出發(fā),才是國家選仕“貞廉”的根本出發(fā)點和基本任務(wù)。
1.3 “貞廉任仕”的官員選任
《墨子》書中的真正廉士可以做到:“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墻必三重,墻之垣,守者皆累瓦釜墻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必須太守之節(jié)。葆衛(wèi)必取戍卒有重厚者。”墨子強調(diào)治國者身邊被選用的工作官員一定要正派廉潔、忠誠可靠、正直無私,并且有能力承擔(dān)事務(wù)。不要限制他們的飲食酒肉,金錢、布匹等財物各自保管,謹(jǐn)防盜竊。葆宮的圍墻一定要修三道,在圍墻的外垣上守衛(wèi)應(yīng)堆上破瓦爛鍋之類的東西。城門設(shè)主管官員,負(fù)責(zé)城門和里巷的門,開鎖和上鎖都必須有守城主將所給的憑證。葆宮的守衛(wèi)一定要選拔忠厚的衛(wèi)兵擔(dān)當(dāng),官吏也須挑選忠誠可靠、公正而又有能力勝任的人。同時認(rèn)為統(tǒng)治者作為國家之主,要擁有兼容天下的胸懷,能接受天下賢能意見和建議,選拔忠貞的廉吏便是對國家基礎(chǔ)的重要守護。“貞廉”的官吏在得到統(tǒng)治者和百姓的信任后可以擔(dān)任重要事務(wù)的管理者和任職者,正因為正直官員的“貞廉”的做人根本,不僅符合中國哲學(xué)的“良善”本根論的自覺,也是“人性論”之中對個人廉德的發(fā)掘,選拔正直貞廉的官員也會讓國家和百姓安心、順心,以“貞廉”促進政治治理之中的國家廉政風(fēng)氣。“貞廉”思想在政治中不僅是對官員自身的要求,還是國家取仕的重要思想和原則。
《墨子》一書的“尚賢”說,是需要在清明的政治體系下選拔賢能的官員,而“尚賢”理論是“任仕”實踐的基礎(chǔ)思想[8]。《墨子》所說:“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作為君主的職責(zé),不僅是治理國家和統(tǒng)治萬邦,更要善待國家的賢士。國家無法留住賢能的人,便會讓賢士遠(yuǎn)離,國家要重視人才的發(fā)掘和培養(yǎng),墨子的親士思想是國家思想開放的體現(xiàn)。兼容天下之思想,是廉潔文化之中“尚賢”的重要理論來源,“尚賢”即是要求執(zhí)政者崇尚賢能之士,選拔賢能的人來管理國家和人民,《墨子》主張“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為三公”,對賢能的人要做到“譬之猶執(zhí)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圣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般爵以貴之,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君王對賢能的人給予足夠的信任,賢能的人在為政之時就會做到“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可以看出,統(tǒng)治者在選拔官員之時,以“公心”而“尚賢”,并加以教化考察,賢能的為政者便會廉潔從政。墨子認(rèn)為,“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圣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也”。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夠?qū)徤鞯赜贸缟匈t能的原則來治理天下,以公心取士,而取法于天。
賢能的人在政治、德行、治國等方面的標(biāo)準(zhǔn)是符合制度的,崇尚并任用賢德的人也會將朝堂貪腐的風(fēng)氣變得正直,賢能的官員更會造福一方百姓,真正做到廉德為人,廉政為官,廉禮為民,將愛民、護民進而教化子民之任務(wù)為己任,促進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廉潔清明。國家的清明正直之風(fēng)會引領(lǐng)官員之私德,將“輕禮節(jié)用”作為一種方法貫徹在廉潔路徑之中。
1.4 “輕禮節(jié)用”的潔廉路徑
《墨子》雖然沒有直接提到“輕禮”的思想,但是其所推行的思想與儒家的重禮思想是不相同的,墨子并不注重繁文縟節(jié),他認(rèn)為所謂的禮是人心之中的禮,儒家的“禮樂”文明是對神圣之事的思想上和行為上的“禮”,從儒家之代表戴圣所著的49 章《禮記》中,類似于“樂記”“祭法”等都是儒家重視禮樂之文明的重要體現(xiàn)[9]。而在“禮”的方面,墨子并不重視“禮”的影響力,而更加注重實用主義,在墨子看來,儒家所重視倡導(dǎo)的禮樂大都會耗費經(jīng)濟,《墨子》中提道:“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認(rèn)為“輕禮”是“節(jié)用”的重要方式,繁文縟節(jié)只會使人的心智迷亂。“今王公大人,唯毋為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王公大人,為“禮節(jié)”而設(shè)置活動,一定會掠奪民眾的衣食財物。墨子對葬禮之中的節(jié)約講述道:“今執(zhí)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圣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xí)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輆沭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fù)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xí)而義其俗者也。”在儒家的禮數(shù)教化之下,墨子所提倡的更是物質(zhì)的實用性,墨子的“節(jié)葬”“節(jié)用”思想便是以節(jié)儉而促廉潔,輕禮節(jié)用則是墨子對于修身的更高層次的理解,前文提到墨子并不注重繁文縟節(jié),更注重個人的“節(jié)用”。
《墨子》中對“節(jié)用”所言:“凡其為此物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統(tǒng)治階級注重自身的節(jié)儉的同時,整肅官場的淫逸奢侈的風(fēng)氣,做到“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dāng)?shù)于數(shù)倍乎,若則不難”。將官員的奢靡物質(zhì)節(jié)約到對民眾的滋養(yǎng)之上,順應(yīng)天意去愛護萬民。從統(tǒng)治者的自身節(jié)用影響下,更會達(dá)到墨子所言:“去無用之費,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去除沒有必要的費用,就是圣明君王的治理之道,也是成為天下最大的利益。在國家治理的體系中,圣明的統(tǒng)治者治理國家之時,首先要考慮國家資源的節(jié)約運用,墨子認(rèn)為,要使國家不窮,關(guān)鍵在于節(jié)省開支,節(jié)省了開支,國家、天下就能得到加倍的好處。
是故子墨子曰:“鄉(xiāng)者,吾本言曰,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計厚葬久喪,請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眾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為人謀者,不可不沮也。
該內(nèi)容講述通過節(jié)葬來節(jié)約國家支出,使貧者富、寡者眾、危者定、亂者治的仁愛清廉之風(fēng)氣興起,不過分重視風(fēng)俗禮節(jié),以節(jié)葬的方式來促進為政者的節(jié)用。節(jié)用的思想是從統(tǒng)治階級中自上而下的一種廉德思想,統(tǒng)治階級和官場風(fēng)氣之中的奢靡是導(dǎo)致統(tǒng)治者與上層建筑中的官吏未通過人性之中的考驗而形成的結(jié)果[10]。
《墨子》治國思想在實用主義的影響下,一方面,做到統(tǒng)治者的自身節(jié)儉,以天下的大利為本心的國家治理; 另一方面,對民眾的體恤為大義,“輕禮節(jié)用”的重點就是墨子廉潔文化的經(jīng)濟節(jié)流方面,從物質(zhì)方面看輕禮數(shù)的經(jīng)濟耗費,也是從源頭遏制貪腐的思想。
1.5 “兼愛貴義”的價值追求
“兼愛”作為墨家的中心思想之一,所蘊含的廉潔文化不僅有本身的含義。“兼愛”的思想作為公眾的博愛思想,“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是墨子的根本價值觀念和追求。墨子認(rèn)為對待百姓應(yīng)該做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11],統(tǒng)治者真正做到對百姓的“兼愛”,對九州萬方一切事物存有仁愛之心,將天地生靈當(dāng)作普遍之愛,就可以控制思想和行為的神圣性。廉潔既是一種文化,也是一種對人性的考驗,將廉潔思想當(dāng)作神圣的思想并進行愛護,便是墨子在“兼愛”之中所體現(xiàn)的博愛思想。王雅的論述中,認(rèn)為墨子的兼愛思想是“建立統(tǒng)一的準(zhǔn)則以節(jié)制造成不義的私欲”[12]。可以說,墨子將“仁愛”思想當(dāng)作普遍風(fēng)氣,更將“天人合一”的思想作為神圣的天地之物,人民生于天地之間,為民求得清明社會,便是廉潔文化之中蘊含著的兼愛思想。《論語》言:“泛愛眾,而親仁”[13],自古治理國家,人民是國家運行的基礎(chǔ)和國家治理的主要對象,“民本” 思想中蘊含的“兼愛”理論也逐步地體現(xiàn)出來,《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14],在博愛的思想下所做到的“兼愛”民本思想,正是將“民惟邦本,本固邦寧”[15]作為治理百姓的重要理論支撐。統(tǒng)治階級的民本廉潔正是將民眾作為“兼愛”的目標(biāo),廣泛且無私地對百姓傳播“仁愛”。《墨子》中的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之利,除去之害”,君子的施政是要以“仁”為治民之根本思想和為政作風(fēng),為天下之大利與百姓之眾利而做到“兼愛”,則是墨家在“兼愛”之中所蘊含的廉潔文化。在張岱年的《中國哲學(xué)大綱》[16]中,對墨子的“兼愛”思想進行人生理想方面的探討,認(rèn)為仁者可以做到大義,更加重視所有事物所追求的“眾利”,這便是對義與利之間的“兼愛”。
《墨子》中對“貴義”理論解釋為:利于天下人的大利,才是真正重視人生問題之中的“義”,廉潔文化之中,不僅是簡單的“義與利”之間的區(qū)別,“貴義”思想中的責(zé)任感是個人對社會責(zé)任的認(rèn)同和承擔(dān)。墨家主張犧牲個人小利而促成大利。可以說,重義輕利,二者的問題是兼并的,性質(zhì)也是并存的,但墨子決不倡導(dǎo)“因義而棄利”。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于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于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于義也。”將“義”作為比性命之重要。墨子又認(rèn)為:“今用義為政于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17]。
以利人、利民為義,墨子認(rèn)為義與利是相統(tǒng)一的,所以義是天下治理的優(yōu)良品質(zhì)。從廉潔方面來講,墨子的“義”便是做官之時的個人廉德與社會廉禮和國家治理體系之中的人性之中的廉潔本根,貴義則是重視大義,是人生理論之中價值選擇的基礎(chǔ)。治國之方法為“兼愛”,本性則為“貴義”,實現(xiàn)國家“兼愛”和人性的“貴義”便是墨子廉潔思想的核心價值追求。
2 《墨子》廉潔思想的新時代意義
《墨子》[18]中蘊含的廉潔思想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瑰寶之一,對豐富新時代廉潔文化有著重要理論意義,同時也對廉潔文化建設(shè)提供創(chuàng)新性思想[19]。墨子的廉潔思想不僅體現(xiàn)在“潔廉利民”“君子修身”“貞廉任仕”“輕禮節(jié)用”和“兼愛貴義”之中,在“所染節(jié)葬”“親士非儒”等思想也蘊含著豐富的廉潔思想。新時代視域下,廉潔文化是中國共產(chǎn)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文化載體,也是國家和社會治理的重要理論依據(jù)。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xí)近平總書記指出:“深化標(biāo)本兼治,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shè),教育引導(dǎo)廣大黨員、干部增強不想腐的自覺,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凈凈做事,使嚴(yán)厲懲治、規(guī)范權(quán)力、教育引導(dǎo)緊密結(jié)合、協(xié)調(diào)聯(lián)動,不斷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效能。”[20]中國共產(chǎn)黨廉潔文化建設(shè)必須立足于并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將“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作為思想融匯于黨的廉潔文化建設(shè)之中,在習(xí)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下,我們黨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反對腐敗的機制,在總結(jié)《墨子》廉潔文化精髓的同時,對墨家思想與后世的重要影響進行思考。墨子的“潔廉利民”的為官根本理念、“君子修身” 的修為慎思、“貞廉任仕” 的人才培養(yǎng)選拔制度、“輕禮節(jié)用”貫穿個人思想行為和國家意志,以及“兼愛貴義”的核心價值追求,是現(xiàn)代進行廉潔文化建設(shè)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思考。
3 結(jié)束語
《墨子》的廉潔思想根植于源遠(yuǎn)流長的中華優(yōu)秀廉潔文化,其“潔廉利民”“君子修身”“貞廉任仕”“輕禮節(jié)用”“兼愛貴義” 等思想與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shè)相輔相成,對當(dāng)代中國治理有著重要的作用。《墨子》的廉潔思想和先秦文化《晏子春秋》中的“廉為政本”、《老子》中的“守素抱樸”、《論語》中的“修身齊家” 等構(gòu)成了從個體修身到社會治理及國家治理的理念,形成了個人廉德、社會廉禮和國家廉政的廉潔文化,體現(xiàn)了中華優(yōu)秀廉潔文化的系統(tǒng)性和整體性。在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和文化綿延發(fā)展中,對當(dāng)時的廉潔文化建設(shè)提供理論指導(dǎo)。在中國式現(xiàn)代化廉潔文化建設(shè)中,《墨子》獨特的廉潔思想仍起到豐富和涵養(yǎng)廉潔建設(shè)和實踐的推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