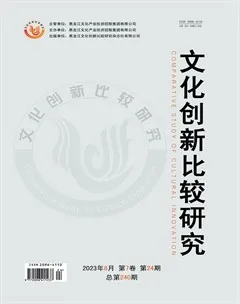日本中小城市的跨文化語言教育實踐
——以三重縣為例
趙超超,袁睿遙
(安徽農業大學外國語學院,安徽合肥 230036)
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上發表了“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從政治、發展、安全、文明和生態5 個層面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內涵和政策方案。要認可文化間的差異,促進文化對話,才能在交流合作中贏得更廣泛的尊重和更深層次的認可[1]。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要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提高國家軟實力。多元文化共生是人類社會實現文明共鑒、和諧共榮的核心理念[2]。多元文化共生也是中華文化的特質呈現,中華文化在多元文化的碰撞和磨合中實現了動態平衡[3]。中國與日本的人口結構相似,文化背景相似,日本的多元文化共生經驗對于完善我國多元文化共生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在日本,隨著20世紀90年代《出入國管理和難民認定法》的修訂,居住在日本中小城市的外國人數量激增[4],從而在多元文化共存方面面臨諸多現實問題。例如,由于語言障礙,外國人無法準確了解日本制度和規則信息,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會與日本居民因一些問題,如垃圾和噪聲等產生沖突,也可能無法獲得與日本居民同等的行政服務。
在中小城市中,要實現多元文化共生,應當如何處理各少數文化群體之間以及群體與日本主流社會之間的關系,這是一個比較敏感的話題。為此,日本通過提高多元文化語言教育水平,促進不同文化群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以及解決文化沖突等方式,努力推進多元文化共生。本文以日本三重縣為例,分析其多元文化的語言教育政策,試圖闡明日本推進多元文化共生的背景和措施。
1 日本推進多元文化共生的日語教育背景
“多元文化共生”一詞最初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日本介紹外國人支援組織的報道中,并逐漸被用作日本地方政府對制定外國人制定政策的口號[5]。《移民管制和困難公民認證法》(修訂版)允許第二代和第三代外國人以永久居民身份工作,導致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數量增加。為了承認生活在日本的不同民族、文化和語言,“多元文化共生”一詞逐漸普及。到了20世紀90年代,“多元文化共生” 的含義已經從“社會變革”變成了“促進外國居民適應日本社會現狀”[6]。2006年,日本總務省關于多元文化共生問題指出,“不同國籍和族裔的群體必須承認彼此的文化差異,并在努力建立平等關系的同時作為當地社區的成員共同生活”。
隨著外國勞動者和留學生數量的增加,三重縣需要制定日語教育政策來實現多元群體的共同工作和生活。同時,還必須重新審視語言的定位。不能把日語看作是一種給予物,而是重新考慮日語的“語言觀念”和“語言權利”。
在中國學界,對于日本中小城市促進多元文化共生的語言教育關注較少。但是,近年來,多元文化共生的理念已經在日本大城市的教育體系中廣泛應用,同時也被日本中小城市所接受。本文以日本三重縣的四日市市和津市為例,分析了推動多元文化共生的語言教育的背景、措施和理念,以期對我國的多元文化語言教育提供幫助。
三重縣位于日本的近畿地區,是一個擁有豐富自然資源的地區,人口、土地面積和人口密度分別在日本47 個地區中排名第22 位、25 位和20 位。三重縣的外國居民數量在日本僅次于東京(3.14%)和愛知縣(2.67%),是排名第三的地區(2.32%)。四日市市是三重縣人口最多的城市,截至2021年12月,其總人口為305 424 人,屬于中小型城市。其中外國居民數量為10 618 人(占總人口的3.41%),前三大人口群體分別是巴西人(27.80%)、韓國人(23.80%)和中國人(20.40%)。四日市市促進多元文化共生的辦公室采取了多種措施,如提供母語支持、向市民傳達信息、進行日語教育等。通過對四日市市和津市的情況進行分析,可以看出,日本中小城市對多元文化共生的語言教育的關注度已經顯著提高。這些城市采取各種措施,促進外國居民與本地居民的交流與合作,從而實現多元文化的共生。日本的經驗對于我國推進多元文化語言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根據2020年日本內閣頒布的《全面有效推進日語教育政策的基本方針》(以下簡稱《基本方針》),本文對日語教育的5 大主要受教育群體進行分析,包括兒童、留學生、勞動者、難民和移民。這5 類文化群體之間相互影響、相互關聯。
2 三重市多元文化共生下的日語教育措施
2.1 三重縣日語教育的現狀和課題
根據2020年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的統計,三重縣四日市市目前有以下以日語教育、日語學習和日語支援為名開展活動的機構:
日語教育機構:2 所大學、0 所短期大學、0 所高等專門學校、2 所日語學校。
志愿者和公民組織:8 個日語教室(其中專為兒童開設的有2 個)。
團體:公益財團法人三重縣國際交流財團。
可以看出,目前四日市市的日語教育主要以志愿者和公民組織開展的日語教室為主,正式的日語教育機構存在很大的發展空間。
2021年3月,四日市市開展了針對外國人居民的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外國人居民的日語水平達到了日語能力測試N3 以上,超過四分之一的人學習日語是為了滿足撫養孩子的需要或參加日語能力測試。同時,由于日語水平不佳,部分外國人在當地工作和生活中用日語交流會遇到困難。
從調查結果看,四日市市為外國人居民提供日語支援服務可能存在以下問題:(1)外國人居民缺乏對學習環境和學習方法的了解,有學習意愿的人無法獲得學習機會;(2)日語學習支援者的年齡存在偏差;(3)不會說日語的外國人在工作中會遇到麻煩;(4)日語教室之間或日語教室與政府、國際交流協會之間未形成協同系統等。
因此,為了實現四日市市外國人居民的多元文化共存,必須考慮“將外國人作為居民”的日語教育,并解決上述問題。
2.2 面向兒童的跨文化語言教育
兒童的日語學習可以大致分為兩個方面:生活語言的學習和學習語言的學習。生活語言是日常生活中交流時使用的語言,而學習語言是在學校課程中使用的語言。根據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兒童用1年左右可以掌握生活語言,但要用5 到7年才能掌握所需的課程學習讀寫能力。部分兒童在生活語言方面沒有問題,但由于較難掌握學習語言,在學校容易遇到學習障礙。這種情況容易導致兒童與日本本土兒童學習成績的差距變大,甚至出現“不登校”等問題[7]。
從2004年開始,四日市市城市發展基金會成立了“四日市多元文化生活沙龍”(原“四日市市國際共生沙龍”),在四日市市多元文化共生促進辦公室人權課的支持下,運營“成人日語教室”和“笹川兒童教室”。教室常年配備會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的工作人員,他們能為居民們提供生活咨詢服務。笹川兒童教室最初是為外國籍兒童設計的,目的是幫助孩子掌握基本學習能力、培養良好學習習慣和支持日語學習。該教室不僅接納外國籍兒童,還接納日本籍兒童。然而由于志愿者人數不足,很難實現有效支援。
2.3 面向留學生的跨文化語言教育
2008年,日本政府實施了名為“30 萬留學生計劃”,計劃到2020年底將赴日留學生人數從14 萬增加到30 萬。這一政策旨在迎合商界雇傭留學生來提高企業的國際化水平,同時減緩日本社會的老齡化趨勢。政策開始執行時,政府立即投入國費向東南亞等中心地區的大使館推薦留學生計劃,并安排每所大學的留學生在畢業后回自己國家在當地日企擔任重要職位。這項作為國際合作的留學生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之后,自費留學生的數量不斷增加,畢業后繼續在日本工作,并成為日本的永久居民。自2000年以來,日本企業開始認識到外國留學生是重要的人力資源,但日企并不愿意接受留學生與日本文化之間的差異,而是希望留學生“同化”。此外,日本的多元文化政策也進一步推進留學生的跨文化交流。留學生被接納為永久居民,與目標社會的文化差異得到反種族主義活動的支援,并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障。然而,留學生在日本面臨的文化適應和就業問題仍需要更多的努力來解決,以實現真正的多元文化共存。
三重縣推廣跨文化交流的語言教育理念和實踐與日本推進多元文化語言教育的主要培養目標高度契合。“通過日語教育,人們的溝通變得更加順暢,使生活更加舒適,從而實現一個尊重不同文化的共生社會。”基于此理念,他們的工作方針包括:一是促進不同國籍的留學生群體、日本學生之間的交流;二是促進高等教育機構與語言學校等機構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從而構筑一個有機多元的交流體系。
根據2021年三重縣的日語教育狀況調查結果顯示,大多數高等日語教育機構都為留學生提供日語教育,其目的是讓學生“能聽懂并理解學校的課程和講座(100%)”,并且希望學生能通過日語能力測試(75.00%)。這些機構為留學生提供生活信息(66.70%),就職信息(77.80%),以及安排住房(77.80%)等具體支持。大多數高等教育機構有在線課程的教學經驗。在以留學生為對象的課程教學中,有88.90%的課程采用了ICT 技術,其中主要使用E-mail(62.50%)和Zoom(25.00%)。然而,這些機構與其他組織的協同合作仍然較少,它們希望能與語言學校合作舉辦日語課程。
三重縣促進跨文化交流的語言教育實踐,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注重整體和細節,通過異文化交流和理解實現新文化的創造。本質上,這種實踐利用多元文化教育,將多樣性的文化轉化為社會建設和國家發展的有效資源。
2.4 面向移民和勞動者的跨文化語言教育
在三重縣,汽車和電器制造業正在蓬勃發展,移民及其后代成為制造業的重要支撐力量。隨著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齡化,日本對外國勞動力的需求逐漸增加。截至2019年,三重縣外國居民占總人口的3.05%(據三重縣“按外國居民國籍和地區分列的人口普查”)。在持有居留身份方面,擁有“永久居民”居留身份的外國人最多,技能實習簽證的外國人數量也在逐年增加(根據厚生勞動省、三重勞動局“在留外國人統計令和2年版”)。此外,2019年10月底,三重縣的外國勞動者人數達到了創紀錄的30 316 人(根據厚生勞動省三重勞動局發布的“外國人就業狀況”通知數據)。隨著外國勞動者人數的增加和中長期居留人口的發展趨勢(定居或永久居留),他們作為當地社區的一員的存在變得越來越重要。
根據《基本方針》,居住在該地區、工作和生活的外國人的日語水平需達到“獨立語言使用者” 的水平,相當于歐洲共同參照框架最新版的B 等級水平(CEFR)。因此大多數由國外進入日本的外國人在國外進行日語研修。但是,有人指出,在進入日本之前進行的日語研修存在很多問題,不能期待其效果。因此,在三重縣的日語教育政策和實踐中,需要考慮到外國人的實際情況和需求,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日本語言學習機會和支持。
根據《三重縣日語教育實態調查》的數據顯示,約70.00%的企業雇傭外國人勞動者。在雇傭的外國人中,巴西籍勞動者中“定期雇員(兼職等)”及“臨時工和合同工”居多,而越南、中國、印度尼西亞和泰國的勞動者則多從事“技術實習生”的工作。在雇傭外國人時,約有6 成到7 成的企業較看重外國人的“能與日本人溝通的日常會話能力”和“問候等基本會話能力”。還有約3 成的企業強調雇員的“日語能力測試的認證水平” 和“熟練掌握工作所需要的技術用語”。在日語學習支援方面,約有3 成的企業為外國員工提供日語學習支援,有7 成企業為外國員工提供專門的日語研修,還有很多企業會為員工介紹當地的日語教室。然而,一些人認為實行日語研修的目的是讓員工更好地工作,但在教學方式和員工學習意愿方面存在挑戰。超過3 成的企業希望和其他組織進行協作,近4 成企業有興趣和政府合作舉辦日語教室。從文化共生的角度看,建立起進入日本后的日語教育機制對于外國人勞動者非常必要。
3 三重市推進多元文化共生的日語教育的經驗與啟示
在我國實現文明互鑒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背景下,日本的相關經驗將對我國中小城市多元文化共生立法、政策制定有積極的借鑒意義。
3.1 多元文化語言政策的頂層設計與協同實施
推進多元文化共生是一個需要漫長時間的過程,實現多元文化共生往往需要幾代人的共同努力[8]。客觀來看,日本在推進多元文化共生方面的政策缺乏積極性和戰略性,主要依靠高等教育機構和地方志愿者的實踐。日本缺乏全國性的政策綱領作為法律依據。例如:雖然奈良縣、宮城縣和三重縣有促進多元文化共存的相關條例,但是埼玉縣卻沒有。在中小城市如三重縣等地,由于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很多與多元文化共生有關的項目(如日語教室、兒童學習支援和人工咨詢等)嚴重依賴支援者和非營利組織機構。
然而,這種情況也有其優勢。地區日語教育不僅要學習旨在融入社會的日語,而且要同時開展活動,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9]。中小城市社區日語教室承擔了“場所”“交流”“社區參與”“國際理解”“日語學習”等功能和作用,特別強調了“面向社會參與的日語學習”,能讓外國人在參與文化交流的同時提高日語能力。為外國人進入日本后的日語教育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人力上的支持和職業規劃等,使外國人能夠在三重縣享有更好的生活和發展機會。
此外,日本中小城市倡導市民“共創城市”的理念。這種觀點為市民間建立關系、表達意見提供了機會,能夠讓不同文化的群體進行對話。例如:北海道的秩父別町,以多元文化交流為目的舉辦了“千人峰會”,以此為契機開始思考地區日語教育,并致力于推進與外國居民的共生[10]。又如,北海道的東川市以市立日語學校為契機,通過培養市民的能力,推進外國人力資源的開發,致力于將外國人作為城市未來生活、工作和發展的重要載體。可以看出,實行多元文化語言教育政策對于實現“共創城市”的目標至關重要。
3.2 語言教育協作模式
日本中小城市的多元文化日語教育主要由地方上的日語教育機構負責。這些機構的教師都持有資格證書,主要通過課堂教學的形式進行日語水平測試、升學和就業指導。除此之外,日本中小城市還充分發揮了高等教育機構和研究機構的作用,通過產業—政府—學術協同合作,建立培訓模式和實習場所,并與公司和其他組織合作,共同開展日語教育,制定和實施更符合外國人居民的日語教育計劃。我們可以借鑒日本的經驗,加強各級教育機構之間的協作,建立更為完善的多元文化語言教育體系,提高外國人居民的語言水平和就業能力。
3.3 “同化”還是“多元文化共存”
在推進多元文化共生的政策中,外國人居民通常尋求的是“共存”,而本國居民則希望實現“同化”[11]。這種差異看似微小,但卻可能引發矛盾。例如:日本媒體對外國游客的偏見性報道,可能導致本地居民對外國人居民的歧視,從而阻礙多元文化的共存。此外,日本企業在招聘國際學生時,更傾向于接納被日本文化“同化”了的留學生,而不是主動了解其他國家的文化。對此,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已經開展了多元文化教育,但主要圍繞本國文化進行贊美和自夸,缺乏對外國人在文化適應中遇到的困難和基本人權保護的關注。因此,我們需要從外國人的視角出發,理解他們的價值觀和需求,并培養一種共同思考文化問題的態度,以實現文化共生和文化自信的雙重目標。
4 結束語
三重縣在推進多元文化共生的語言教育時,提出了要打破“心靈的墻壁”,即讓本國居民認識到多元文化共生的重要性,克服歧視和偏見。同時,三重縣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設立多元文化共生促進委員會,加強國際合作,建立多元文化共存中心等,促進外國人居民的積極參與,并解決他們與本國居民交流的不足。我們可以借鑒這些措施,加強政策制定和實施,營造一個更加包容和友好的多元文化共生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