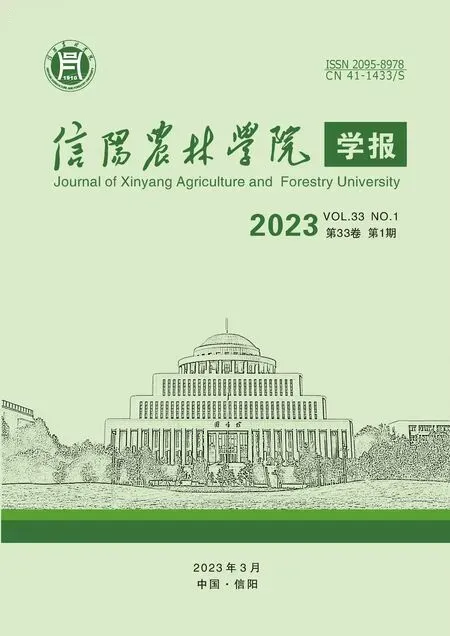新時代共同富裕與西方福利社會比較研究
王代靜
(東華理工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步入新時代,促進共同富裕的歷史進程迎來新的挑戰。通過澄清新時代共同富裕與西方福利社會的區別,有助于正確認識新時代共同富裕的理論范疇、富裕途徑,在借鑒西方福利社會的經驗與吸取教訓的基礎上,有效避免落入“福利陷阱”、形成不良社會風氣。新時代共同富裕與西方福利社會的區別主要體現在理論支撐差異、發展歷程差異、實踐效果差異方面。二者各自具備獨特的國家形態,具有一定的對立屬性。西方福利社會是由福利國家改革而來,福利國家是經由戰爭苦難的“戰爭國家”發展而來。社會主義國家大多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福利思想,形成民生國家,民生國家是通過政治民主、經濟高效和社會公平的方式保障改善民生、實現民生幸福的國家形態,集政府主導性、目標層次性、制度公平性、動態發展性、共建共享性五大特征于一體,是一種新的國家治理形態,又是一種增進民生福祉為目標的民生保障政治體制[1]。福利國家與民生國家的執政黨都需要解決好民生問題來取得執政支持;福利事業覆蓋面廣、發展較為復雜,需要多元主體共同推進,而不能僅僅依靠政府推進。
1 問題的提出
在我國明確提出“共同富裕”之前,西方世界就已經提出了“福利國家”及西方福利社會等概念。分析兩者之間具有怎樣的聯系與區別,將有利于二者內涵與外延的把握,厘清二者實踐過程中采取的道路,明確未來發展的趨勢。首先,存在部分群體對于新時代共同富裕與西方福利社會概念理解不清晰、不明朗的現象。促進新時代共同富裕是否蘊含“福利陷阱”?是否會助長社會形成“等靠要”或“養懶漢”風氣?針對這些疑難問題,一部分人存在片面化、碎片化的理解。其次,一些富裕群體或階層擔憂新時代共同富裕的推進會影響他們的獲益。他們認為,后富群體的富裕一定程度上建立在他們的損益上,將會影響正當合理且合法的收入,這其實是將西方福利社會里面的要素混淆進來,沒有充分澄清新時代共同富裕與西方福利社會之間的區別。最后,學術界對于西方福利社會的研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以“福利社會”為主題詞在知網進行搜索,期刊論文不足三百篇,以“西方福利社會”為主題詞搜索則更少。通過充分的外部研究,具備國際視野才能更好地把握當前西方福利社會實施的現狀、存在的特征、與新時代共同富裕的聯系與區別。
2 理論支撐差異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思想是行動的指南。新時代共同富裕與西方福利社會都具有雄厚的理論支撐,分別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福利思想與西方福利思想。除開二者的階級性差異外,西方福利思想的理論支撐還具有相對穩定與不穩定性的特征差異。西方福利思想歷經數個世紀的跨越,存在各種流派思想且同時發生作用,呈現“非此即彼,爭奪主流”的內部斗爭,一定程度上帶來了執行的分歧,從而致使落實不順暢,效果與預期存在較大差距,這也是為什么后來折中的“第三條道路”誕生的原因之一。
首先,西方福利思想具有一定的不穩定性。新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第三條道路”交替,總是在經濟危機出現時失靈。西方福利思想呈現較大變動性,這與其福利國家的兩黨制存在一定關系,其中存在內生分歧與對立的邏輯。民主社會主義(又稱社會民主主義)倡導國家干預經濟,促進充分就業,建立完善的社會福利,甚至達到收入均等。在這一點上,與凱恩斯主義十分契合。二戰后出現了經濟蕭條,自由放任的經濟思想無法應對這一時期出現的經濟發展窘境。20世紀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福利國家發生的石油危機,使新自由主義又成為社會福利思想的理論主流流派。
其次,西方福利思想其中的一些流派思想存在內生對抗性。新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這一對流派思想是典型代表。社會民主主義作為社會改良主義思潮的一種,其本身是一種較為溫和的理論,在政治上發展社會民主,強調階級之間調和與合作,有利于勞工利益的改良。主張國家對公民福祉承擔責任,政府的角色是為社會中有需要的人提供資金與服務,維護社會公平。由此,資源再分配上奉行平均主義目標,也促使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概念具有社會主義特征,在社會分析與方法上和自由主義具備相同點。社會民主主義重視社會福利制度,認為是資本主義社會極其重要的方面。福利制度一定程度上縮小了貧富差距,緩和了階級矛盾,維護了社會穩定。同時,它本身也明白福利制度只是“緩沖”了社會矛盾,并未真正解決矛盾。20世紀初,其作為改良主義思潮之一在西歐盛行,但二戰后才廣為傳播并被運用。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在新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折中的“第三條道路”成為主要社會福利理論流派,并且這兩種流派也依舊盛行[2]。
新自由主義則表現較為激進,其基本原則包括: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私有化。新自由主義還從個人、國家、國際三個層面推崇自由。首先,推崇個人自由主義,認為這是自由市場制度存在的基礎與經濟自由的基本出發點。國家不應該干預個人在市場中的選擇,個人擁有自由選擇權才能保證社會進步與創造。其次,推崇競爭市場經濟,反對國家引導與計劃經濟體制。主張市場經濟是民主的基本堡壘,通過財產所有權分離,防止權力集中于少數人手中。要遵循市場本身運行的規律,國家調控是造成經濟不穩定的因素,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最后,主張私有化,推進全球自由化。認為私有制經濟具有內在穩定性,通過市場調節就能實現經濟均衡,各國應該取消經濟保護,實現生產要素、貿易和金融的完全自由化與國際化,這樣有利于資源的高效配置和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
新時代共同富裕充分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福利思想,較之于西方福利思想的多流派具有相對穩定性。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社會福利思想貫穿著對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分析,對社會主義社會本質特點的分析,從而具有革命性、批判性。限于歷史局限性,在他們的時代資本主義社會保障制度還未完全確立,因此,這一思想是較為原則性的。馬克思從生產資料占有的歸屬出發,認為加強和完善社會主義社會保障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題中應有之義。他還指出,社會保障的基金來源于六項扣除并且從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角度說明了設立社會保險基金的必要性。同時,他剖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保障基金的來源是剩余價值的一種扣除,工人階級所得到的社會保障是自己剩余勞動的一部分,而不是源于資本家的恩惠。他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保障的欺騙性,資本主義社會保障不是為了改變工人階級的工作與生活狀況,而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掩蓋資本主義剝削工人工資的本質。
3 發展歷程差異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通過回顧西方福利社會的生成邏輯與理論范式有助于推動當今世界福利事業的發展。從歷史進程看,西方福利社會起源較早,自英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福利國家之后,西歐其它國家(法國、瑞典、挪威、丹麥、聯邦德國、意大利等)紛紛進行了追趕,相繼建立福利制度[3]。考斯塔·艾斯平1990年出版的《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首次提出了“福利體制”概念,由此開啟了比較福利國家研究的新架構。他采取了“全景”的研究并使得福利國家研究“社會學化”,從三種不同體制類型來認識福利國家,即:以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福利體制;以意大利、德國、奧地利、法國為代表的保守主義福利體制(包括歷史上的合作主義國家與德國俾斯麥以來的家長式威權國家);以瑞典、挪威、丹麥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福利體制[4]。金佳厚認為,因受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以及社會結構性變遷的影響,西方國家人們的社會福利觀在適時地調整變化,形成了“福利國家-政治經濟”范式、“福利社會-道德經濟”范式、“福利組合-混合經濟”范式、“福利網絡-社會經濟”范式,并旨在通過幾類范式的系統梳理與分析,為中國社會福利制度轉型與構建提供一定啟示[5]。伏佳佳指出在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思想誕生以前,中西方具有一組相似的社會政治概念,即中國傳統社會“均貧富”觀念與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福利國家”觀念,將兩者進行梳理有利于我國新時代共同富裕的高質量發展[6]。林閩鋼指出“福利社會”是用來代替“福利國家”的政治改革口號,體現了從一元主體到多元主體的轉變,從政府單一主體向國家、市場(包括企業)、社會主體(個人、家庭、慈善機構、民間組織)轉變,通過對西方福利社會的經驗吸取與教訓總結來構建中國式的福利社會[7]。
新時代共同富裕的提出是基于對已有社會福利實踐經驗的豐富總結,經歷了從部分到整體的過程。2003年科學發展觀的提出開啟了我國“社會政策研究”時代,社會政策是社會發展的主要工具,科學發展觀強調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平衡,社會政策由此備受重視。科學發展觀提出之后,中央文件先后提出了社會政策發展的幾個原則,即:適度普惠、公共服務均等化、社會福利社會化、創新社會治理、社會政策要對經濟形勢相適應與協調[8]。共同富裕從鄧小平時期就已經注重物質與精神雙重富裕,他提出了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兩個文明”建設,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黨的十六大在這一基礎上提出“三位一體”理念,即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缺一不可;黨的十七大增添“社會建設”,形成“四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黨的十八大將生態文明建設與四方面并列,形成“五位一體”總體布局;黨的十九大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與全民共富;黨的二十大指明了中國式現代化即全民共富的現代化,體現了全面性。
4 實踐效果差異
首先,新時代共同富裕與西方福利社會的“福利初衷”與實踐途徑不同。從時空上看,西方社會的福利制度最早建立,英國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福利國家,較早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福利制度體系。威廉·貝弗里奇被公認為福利國家理論的主要建構者,他在英國工作時,就較為關注失業問題,并隨后撰寫了《貝弗里奇報告》。他闡述了民眾需要社會保障的八種原因,即:失業、傷殘、失去生計、退休、婚姻需要、喪葬需求、對16歲以下的少年或兒童接受全日制教育補貼、身體疾病或失去勞動能力。并且提出了由社會保險、國民救助、自愿保險三個層次構建的現代社會保障體系框架,為民眾勾畫出“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思想和實施方案。西方福利國家所構建的福利社會主要依靠兩招:一是公共產品供給,教育、醫療、社保等體系比較完善;二是財稅政策保障,累進稅制及轉移支付力度較大。西方福利國家呈現高稅收、高財政支出、高財政轉移等特點。高福利制度本質是為了緩和階級矛盾,維護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生產剩余價值的統治地位。高稅收對富裕階級的資本家以及中產階級進行征收,遺產稅等直接稅稅種往往使得富裕階級的資本家以及中產階級繳納高額賦稅,使得財富代際之間的轉移削弱,福利制度的實施讓他們收益有限,卻更多惠及的是社會底層低收入群體,所有人不是平等地享有社會公共財富,形成西方式“劫富濟貧”。高福利制度并未觸及資本主義私有制、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與市場經濟,因此,不能夠抑制貧富兩極分化。
新時代共同富裕是民生國家福利的集中體現,其中具有豐富的制度體系。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邏輯起點,以社會保障體系為民生依托,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為了逐步實現人民對于高質量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以全體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為提升民生福祉而不斷努力。黨的十七大后才明確提出“中國福利社會”一詞[9]。雖然時間上對于社會福利的明確起步較晚,但卻呈現出“后來者居上”的態勢,隨著“五位一體”高質量發展,中國的福利制度體系將不斷完善。
其次,新時代共同富裕與西方福利社會的實踐效度不同。西方福利社會的高福利制度為資本主義生產的不斷絕創造了條件,促進資本主義市場的活力,確保資本主義生產的可持續性。市場容量在一段時間內基本上是固定的,而工人階級與社會底層群體是消費的主力軍,富裕的資本家其本身的消費存在一定的限度且這類群體本身就只占福利國家的少數,因此,高福利制度能夠促進市場消費,只有完成消費這個環節,商品的生產才會顯得有意義。高福利制度使得民眾懶于勞動,光是國家福利就足夠他們生活,呈現“躺平”之勢。高福利在西方福利國家的政治選舉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被選舉人在選舉前常常為了高支持率而作出高福利保證,選舉后因為高福利代價巨大而“失信”,只能通過一些政治手段避重就輕,延緩福利的落實速度。而當民眾發現時,這一代人已被換代更迭,高福利引起的弊病傳導至新的當權者手中,形成政治上的頑疾。福利國家財政收入的有限與人民福利要求的無限增長越發明顯[10]。高度依賴高福利的民眾對福利程度較為敏感,福利降低觸及他們的直接利益,民眾懶于勞動導致國家整體收入降低,同時,高福利制度使得國家財政支出年年加大,容易造成財政赤字。國家為了緩解這一狀況常常向他國借款,擴大國家債務,甚至形成債務危機、信任危機,最終導致惡性循環,陷入“福利陷阱”,導致國家發展止步不前。
新時代共同富裕是逐步提升福利程度。立足國情,人口眾多、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現狀注定不能實行高福利制度;社會保障制度是確保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通過脫貧攻堅戰來扶志扶貧;通過按勞分配原則,有勞動能力者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避免“養懶漢”現象的出現。同時,倡導共建共享,廣大人民群眾既是社會主義事業成果的享有者,又是建設者。一方面,能夠使得人民群眾為社會主義事業出一份力,為社會需要而實現個人人生價值;另一方面,唯物史觀指出人民是創造歷史的力量,應該匯集人民的力量共同建設,創造新的社會主義事業。同時,又通過公益事業與慈善活動,關愛那些喪失勞動能力的人,使弱勢群體感受到溫暖,體現人文關懷。
最后,新時代共同富裕與西方福利社會的實踐廣度不同。西方福利社會看似福利內容覆蓋面廣,但卻存在一定的欺騙性。西方福利社會雖然福利范圍涉及人的全過程生命周期,但卻十分缺乏精神層面的內容,這樣就導致了人的單向度發展。即使福利中的教育與假期方面也只是僅限于維持勞動力的自身再生產,而不是真的從勞工身心健康出發,《資本論》就揭示了這一成因。沈斐指出,社會民主主義的最大不足在于忽略人的全面發展需要,試圖用物質生活需要代替人民群眾的全部需要,試圖用片面的物質主義發展觀推動經濟與社會發展[11]。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追求的是高額剩余價值,資本家們并非沒有注意到民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他們占有大量社會財富卻不愿投資精神產品與公共服務的原因在于:精神產品與公共服務并不能有助于剩余價值的生產與實現,投資這類產品不如物質產品獲利更快更多。此外,物質層面的福利是有形的,看得見、摸得著、見效快,更能獲得選民的支持,候選人往往通過物質層面的福利獲得選民的青睞從而贏得競選。西方福利社會還在生態層面具有短板,那就是割裂了經濟、社會、環境“三個子系統”的邏輯關系,沒有達到“三邊平衡”。我國學者明確提出了構想,一種以生態主義為導向,注重經濟、社會與環境三邊平衡的共同富裕治理體系必將形成,走向一個可持續的綠色生態致富體系[12]。“三邊平衡”實際上把物質文明納入“經濟”,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會文明納入“社會”,把生態文明納入“環境”。這就是可持續發展觀所強調的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念。新時代共同富裕不僅重視生態文明建設,還積極致力于生態治理,倡導生產、生態、生活“三生合一”的系統治理,注重整體性,達到“三邊平衡”。在強調經濟、社會、環境三個子系統的可持續性的同時,還強調三個子系統之間的互相協調,運用這種可持續性與協調性達到共同富裕治理目標[13]。
新時代共同富裕貫穿新發展理念,通過“五位一體”高質量發展來實現物質層面與精神層面的全面發展,是“以人為本”的人本邏輯發展。著名福利經濟學家庇古在其所著的《福利經濟學》中明確提出了“經濟福利”和“非經濟福利”[14]。狹義的福利就是經濟福利,廣義的福利包括經濟福利和非經濟福利。文化繁榮、社會安全、生態優越都是非經濟福利。通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推進,已經形成的“五位一體”涵蓋了庇古的“經濟福利”和“非經濟福利”,是全面的福利。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只有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都搞好,國家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強,全國各族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順利向前推進[15]。新時代共同富裕是全面的富裕,這個全面性不僅體現在全民共享發展成果,更體現在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文明程度的全面提升,構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這將是對西方福利社會的全面超越。
5 未來展望
福利是影響人口遷移的重要因素。共同富裕要切實推進戶籍改革,確保福利落實。我國由于快速城鎮化形成了城鄉二元對立的發展結構,城鄉之間的發展水平與程度差異較大,也相應地導致了城鄉之間福利水平的差異。共同富裕勢必要不斷縮小城鄉發展差距,縮小城鄉福利差距,不斷促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大量人口流動既為城市建設貢獻了力量,又一定程度上帶動了區域經濟發展。城市既對人口流動具有吸引效力,又存在一定排斥力。福利磁吸假說就表明了低福利水平流出地作為排斥力,高福利水平流入地作為吸引力,當兩地之間的福利差異達到一定程度,低福利水平地區居民將會被吸引,遷入高福利水平地區[16]。我國的福利享有存在城鄉分離的現狀,通常以戶籍進行綁定。農民工群體工作在城市,戶籍大多在農村,本應享有的福利保障因城鄉分離問題形成堵點,往往因為身在城市,福利需要在戶籍所在地才能落實,導致存在福利落實不到位甚至錯失的問題。此外,由于大量流動人口或農民工無法獲得應有的福利待遇、福利保障,他們容易被社會邊緣化,進而在原有的城市人口過多與農村人口空心化、老齡化的問題上滋生新的治理問題。福利待遇的缺乏,使得農民工群體陷入社會底層,子女可能無法獲得城市公立學校的教育,失去教育公平,喪失階層流動性,導致階層固化問題加重,從而影響社會和諧與穩定。學者蔡昉指出,戶籍改革唯有與城鄉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相協調才能取得實質性進展,才能有效推進我國城市化進程[17]。我國人口眾多,戶籍制度的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雖困難重重但卻是未來落實社會福利、促進公平正義的必行一步。
綜上所述,新時代共同富裕所達到的福利水平呈現逐步提升、城鄉福利差距不斷縮小的特征,并且實現方式、實現手段都與西方福利社會中的福利存在差異,不能夠完全等同。澄清這一差異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限于西方諸多福利國家的具體狀況與成果差異,基于新時代共同富裕與西方福利社會的中西方比較研究存在研究角度的狹窄性,這一比較研究存在一定不足。需要不斷與時俱進并針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既要立足于歷史現狀的邏輯分析,又要著眼于當今時代的研究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