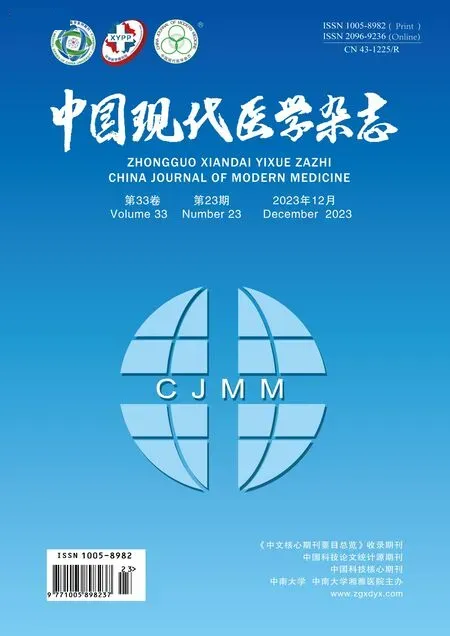川崎病患兒丙種球蛋白耐藥列線圖模型的構建與驗證*
宋美璇,劉斌,劉東
[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 1.普通外科(胃腸),2.兒科,四川 瀘州 646000]
川崎病是一種以自限性全身血管炎為特征的急性發熱性疾病,與冠狀動脈病變(coronary artery lesion,CAL)的發展密切相關,嚴重者可引起冠狀動脈瘤和心肌梗死,甚至猝死,目前已成為兒童獲得性心臟病最常見的原因[1]。雖然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能有效降低CAL 的發生率[2],但約15%~20% 的患兒對首劑IVIg 治療不敏感,發生CAL 的風險顯著增加[3-6]。由于川崎病發病后1 個月的冠狀動脈病變嚴重程度對晚期冠狀動脈病變預后至關重要[2],因此有必要及早識別IVIg 耐藥,以便患兒可以在更積極的治療中受益。
近年來,國內外學者通過川崎病患兒的臨床資料建立了多個IVIg 耐藥的早期預測模型[7-10],但多以單因素分析篩選研究變量為主,在不同人群中的預測效能仍不夠理想[11-12],并且在預測模型的使用方面極不方便。Lasso 回歸方法通過在模型估計中引入懲罰系數,可以獲得更高的模型概化能力和準確度,也能有效地處理各研究變量的過擬合和多重共線性問題[13];列線圖(Nomogram)模型能綜合分析患兒預后的危險因素,并能夠以直觀、可視化的方式提供個體化的預后風險評估[14-15],方便臨床使用。因此,本研究對474 例川崎病患兒進行回顧性調查,使用Lasso 回歸篩選模型的納入變量,建立并驗證新的IVIg 耐藥Nomogram 模型,以期為患兒提供個體化的風險評估及臨床治療提供幫助。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收集2014年7月—2020年7月在西南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住院確診為KD 患兒(474 例)的臨床資料。川崎病的診斷和IVIg 耐藥標準依據2017年美國心臟病協會發布的標準[16]:①川崎病的診斷。發熱≥ 5 d及具有≥ 4 項主要臨床特征(肢端變化、皮疹、結膜炎、口唇變化、頸部淋巴結炎);②不完全性川崎病的診斷。兒童發熱≥ 5 d并具備2 或3 項主要臨床特征,或者嬰兒發熱≥ 7 d 且無其他原因可以解釋者,同時包括任意1 項陽性超聲心動圖結果(LAD 或RCA Z 值≥ 2.5;冠狀動脈瘤;具有3 個及以上診斷意義的特征:左室功能降低、二尖瓣反流、心包積液、LAD 或RCA Z 值為2.0~2.5);③IVIg 耐藥。初次注射完IVIg 后仍持續發熱≥36 h,或者再度發熱。冠狀動脈病變診斷標準:冠狀動脈Z>2.0[16];<5 歲兒童冠狀動脈內徑≥ 3 mm,≥ 5 歲兒童冠狀動脈內徑≥ 4 mm,或冠狀動脈內徑>鄰近節段1.5 倍[17]。排除入院前曾在其他醫療機構接受IVIg治療、住院期間未接受IVIg 治療及臨床資料不完善的患兒。全樣本人群隨機分為訓練集(339 例)和驗證集(135 例)。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定批準(KY2020194),患者及家屬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評估指標
根據國內外相關文獻,收集并篩選患兒的一般信息(性別、年齡、體重)、臨床表現(是否完全性川崎病)、心臟表現(心包炎、心肌炎、心內膜炎、心律失常、心包積液、冠狀動脈病變、左心室內徑增大、二尖瓣、主動脈瓣、三尖瓣反流等)、心外并發癥[間質性肺炎、無菌性腦膜炎、消化系統癥狀(腹痛、嘔吐、腹瀉、麻痹性腸梗阻、肝腫大、黃疸等)、關節痛和關節炎[18]]、首劑IVIg 使用時間、IVIg 使用前最近一次的實驗室指標[中性粒細胞比例(neutrophil ratio,N-R)、紅細胞分布寬度-標準差(red blood cell distribution width-standard deviation,RDW-SD)、血小板壓積(Thrombocytocrit,PCT)、C 反應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白蛋白(Albumin,ALB)、系統性免疫- 炎癥指數(system immune-inflammation index,SII)、C 反應蛋白/白蛋白(CAR)]。SII=血小板計數×中性粒細胞計數/淋巴細胞計數。
1.3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采用采Stata/SE 15.0、R 4.0.2 及RStudio 1.3.1056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或中位數和四分位數間距[M(P25,P75)]表示,比較用t檢驗或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構成比或率(%)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應用RStudio軟件對訓練集數據進行Lasso 回歸分析,篩選出重要的影響因素,并導入構建Nomogram 模型,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線、Calibration 校準曲線和DCA 曲線評估模型的區分度、校準度及臨床有效性。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患兒臨床資料比較
共474 例患兒納入此項研究,按照患兒耐藥情況分為IVIg 敏感組429 例、IVIg 耐藥組45 例,比較兩組的性別、年齡、體重、是否完全性川崎病、心臟表現、心外并發癥、首劑IVIg 使用時間、N-R、RDWSD、PCT、CRP、ALB、SII 及CAR,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IVIg 敏感組與IVIg 耐藥組心外并發癥、N-R、PCT、ALB、SII 及CAR 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訓練集與驗證集在以上相關因素間的比較,除首劑IVIg 使用時間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兩組余相關因素間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2。

表1 IVIg敏感組與IVIg耐藥組臨床資料比較

表2 訓練集與驗證集臨床資料比較
2.2 Lasso回歸分析
對訓練集數據以IVIg 耐藥為結局進行Lasso 回歸分析,為兼顧變量數量和質量,圖1A 是對各變量壓縮估計后的曲線圖,得到心臟表現、心外并發癥、IVIg 使用時間、N-R、RDW-SD、PCT、ALB、SII、CAR是川崎病患兒IVIg 耐藥的預測因素。本研究選擇最小lambda 作為懲戒系數(見圖1B)。

圖1 訓練集Lasso回歸分析
2.3 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將Lasso 回歸分析篩選出的9 個IVIg 耐藥預測因素納入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建模,得到Nomogram預測模型。見表3。

表3 訓練集IVIg耐藥的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參數
2.4 建立Nomogram預測模型
將Lasso 回歸分析篩選出的9 個預測因素導入構建Nomogram 模型,其中IVIg 使用時間、N-R、RDW-SD 和PCT 所占分值較高,說明其對預測結果相對重要。從Nomogram 模型圖中各變量在“分值”線上對應的得分相加,得到總分,然后將總分在“總分”線上的點對應到“IVIg 耐藥”線上,得到該患兒發生IVIg 耐藥的概率。見圖2。

圖2 KD患兒IVIg耐藥Nomogram模型
2.5 預測模型的驗證
2.5.1 區分度ROC 曲線分析結果顯示,訓練集ROC 曲線下面積(area under the curve,AUC)為0.784(95% CI:0.701,0.867),當最佳閾值取0.045時,相應的特異性和敏感性分別為0.490(95% CI:0.434,0.546)和0.935(95% CI:0.849,1.000);驗證集的AUC 為0.784(95% CI:0.643,0.925),當最佳閾值取0.142 時,相應的特異性和敏感性分別為0.851(95% CI:0.788,0.915)和0.714(95% CI:0.478,0.951)。見圖3。

圖3 預測模型在訓練集和驗證集人群的ROC曲線
2.5.2 校準度通過對Nomogram 模型繪制Calibration 校準曲線,結果顯示,該模型在訓練集和驗證集的C 值分別為0.784 和0.784,兩者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反映出預測值與實際值的良好一致性及擬合度。見圖4。

圖4 預測模型在訓練集和驗證集人群的Calibration校準曲線
2.5.3 臨床有效性對預測模型在訓練集和驗證集繪制DCA 曲線,結果顯示,當訓練集閾概率為0.01~0.58 時,患兒有凈獲益。通過驗證集的ROC曲線分析,閾概率值0.142 在DCA 曲線閾概率0.04~0.23 時,模型具有臨床有效性。在驗證集中,當設置0.142 作為診斷IVIg 耐藥并采取干預措施的閾概率值時,每100 例運用此模型的患兒中,有4.9 例能從中獲益且不損害其他人的利益。見圖5。

圖5 預測模型在驗證集和驗證集患兒的DCA曲線
3 討論
川崎病的治療主要依靠大劑量IVIg,但是IVIg耐藥的川崎病患兒發生冠狀動脈病變的風險顯著升高[19],首次使用IVIg 或診斷為IVIg 耐藥后,額外的治療不能快速有效地減少血管炎癥[20]。而針對IVIg耐藥高風險的人群在初始治療中聯合小劑量激素和IVIg,其冠狀動脈病變率可明顯下降[21]。因此,在首次使用IVIg 治療前篩選出IVIg 耐藥高風險患兒并給予更積極的治療,有利于川崎病的預后。
目前建立的多個預測模型多以單因素分析篩選變量為主,在不同人群中的預測效能不夠理想,且模型的使用極不方便。Lasso 回歸方法在模型估計中引入懲罰系數,可有效地處理各研究變量的過擬合和多重共線性問題,能獲得更高的模型概化能力和準確度[13];列線圖(Nomogram)模型能綜合分析患兒預后的危險因素,并能夠以直觀、可視化的方式提供個體化的預后風險評估。目前已有列線圖模型用于預測川崎病患兒IVIg 耐藥的研究[14-15],但不同模型在不同人群中的預測效能存在差異。因此,本研究以Lasso 回歸方法篩選模型納入變量,以Nomogram 圖的方式展現本地區人群IVIg 耐藥預測模型,極大地方便了模型的臨床使用。
既往IVIg 耐藥川崎病的預測模型的危險因素包括<6月齡,男性,皮疹、肛周改變、四肢水腫、淋巴結腫大,發病后4 d 內使用IVIg,N-R、PLT、NLR、PLR、CRP、ALT、AST、ALB、總膽紅素、血清鈉等[12,22-26]。本研究結果中男性、CRP 等在IVIg 敏感組和IVIg 耐藥組之間單因素分析時同樣存在差異,但未能進入本研究最終的回歸模型,可能是由于IVIg 敏感組和IVIg 耐藥組之間的單變量分析的結果在不同的人群中可能會有所不同,同時,由于Lasso回歸并非簡單的組間單變量的比較,在納入懲罰系數后,其統計學指標發生了變化。
本研究建立的新Nomogram 預測模型包括9 個預測指標:心臟表現、心外并發癥、IVIg 使用時間、NR、RDW-SD、PCT、ALB、SII 及CAR,其中心臟表現、心外并發癥、RDW-SD、PCT、SII、CAR 等是以往的模型中沒有被確定為IVIg 耐藥的預測指標。心臟表現,特別是冠狀動脈病變是川崎病的主要嚴重并發癥,本研究中心臟表現的發生率在IVIg 敏感組和IVIg 耐藥組之間并沒有差異,但在心外并發癥的發生率上IVIg 耐藥組顯著高于IVIg 敏感組,這可能是由于IVIg 耐藥組的血管炎癥程度高于IVIg 敏感組,因此更容易出現臨床可見的心外表現。經Lasso 回歸分析,最終這2 個指標都被納入Nomogram 模型。RDW-SD 是能客觀、準確地衡量外周血紅細胞大小變化范圍的指標,以往常用于貧血相關疾病的臨床鑒別。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RDW-SD 的升高與心血管疾病的發生相關[27-29]。本研究結果顯示,RDWSD 在IVIg 敏感組和IVIg 耐藥組之間沒有差異,但納入最終模型后,對IVIg 耐藥概率的評分有較大的影響。既往研究顯示,血小板計數減少是川崎病發生IVIg 耐藥的危險因素,但其界值各有不同[10,22];川崎病患兒在高熱期時,血小板分布寬度和血小板平均體積均明顯降低[30-31]。PCT 是血小板平均體積與血小板計數的乘積,受到血小板分布寬度、血小板計數和血小板分布寬度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PCT納入單因素分析,顯示其在IVIg 敏感組和IVIg 耐藥組之間具有差異,且其變化在Nomogram 模型中對預測評分影響較大,提示IVIg 耐藥的川崎病患兒的血小板形態發生了明顯變化。SII 是反映全身炎癥狀態簡便和可靠的指標[32-33],CAR 則被認為是比單獨的CRP 或白蛋白更強的炎癥反應指標,據報道CAR與大動脈炎的活動性呈正相關[34],IVIg 治療前的CAR 有助于川崎病患兒IVIg 耐藥性的預測[35]。本研究中IVIg 耐藥組的SII 和CAR 低于IVIg 敏感組,提示IVIg 耐藥的KD 患兒可能存在更嚴重的全身炎癥和血管炎。
本研究對Nomogram 模型的預測區分度、校準度和臨床有效性進行了檢測。訓練集和驗證集兩組人群的ROC 曲線的AUC 均>0.75,顯示出較好的區分度;通過對模型在訓練集和驗證集繪制Calibration校準曲線,其C 值分別為0.784 和0.784,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反映出預測值與實際值的良好一致性及擬合度;最后通過對驗證集繪制DCA 曲線,顯示當閾概率在0.04~0.23 時,患兒有凈獲益,且驗證集的ROC 分析得到的最佳閾概率值0.142 在DCA 曲線閾概率范圍內,因此模型具有臨床有效性。
綜上所述,心臟表現、心外并發癥、IVIg 使用時間、N-R、RDW-SD、PCT、ALB、SII、CAR 是川崎病患兒IVIg 耐藥的預測因素,通過構建個體化列線圖預測模型,預測模型在訓練集和驗證集人群中均具有良好的區別度、校準度及臨床有效性,能較準確、方便地個體化預測川崎病患兒的IVIg 耐藥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