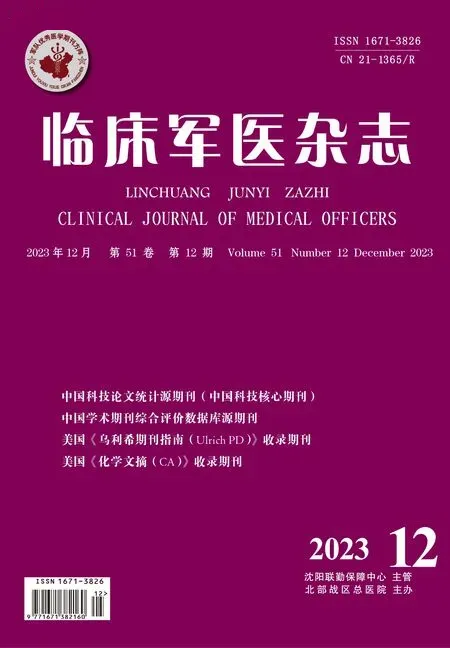黃芪多糖輔助治療對胃癌術后化療患者外周血Th1/Th2細胞平衡及不良反應影響
張紅英, 吳安定, 余 潔, 杜 恒, 劉 苑, 詹 月
黃岡市中心醫(yī)院 胃腸外科,湖北 黃岡 438000
胃癌(gastric carcinoma,GC)多發(fā)于50~80歲中老年人群,為常見的消化道惡性腫瘤,起源于胃黏膜上皮細胞病變,以腺癌為主,患者早期無典型癥狀,多見于反酸、腹脹、腹痛等癥狀,確診時往往為中晚期,腹痛明顯加劇,還可能伴隨黑便、嘔血、惡病質等癥狀,嚴重影響患者生活質量[1-2]。GC病理病機復雜,臨床治療GC主要采用GC根治術,術后以化療作為輔助治療[3]。由于手術創(chuàng)傷,加上化療對GC患者正常細胞的影響,容易導致其出現(xiàn)不耐受問題,引起多種不良反應[4]。有研究報道,中藥可以緩解化療藥物的不良反應,還可以改善機體免疫功能[5]。黃芪為傳統(tǒng)中藥材,具有益氣補虛的功效,其有效成分黃芪多糖(astragalus polysaccharide,APS)對治療腫瘤有一定效果,且可以減輕化療毒副作用,但在GC術后化療患者的應用效果尚未明確[6]。本研究探討APS輔助治療在GC術后化療患者中的應用效果,以期為GC術后化療患者的治療提供思路。現(xiàn)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黃岡市中心醫(yī)院自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收治的84例GC術后化療患者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符合GC診斷標準[7];符合GC西醫(yī)脾胃氣虛型辯證標準[8];初診;年齡≥18歲。排除標準:嚴重感染相關疾病者;凝血、免疫系統(tǒng)疾病者;對本研究藥物過敏者;器官功能不全者。根據(jù)隨機數(shù)字表法將患者分為A組和B組,每組各42例。A組:男性23例,女性19例;年齡35~77歲,平均年齡(56.34±11.75)歲。B組:男性26例,女性16例;年齡34~79歲,平均年齡(57.56±10.24)歲。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jīng)醫(y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治療方法 A組患者采用常規(guī)化療方案治療,卡培他濱片(南京優(yōu)科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223015)口服,1 000 mg/m2,2次/d,注射用奧沙利鉑(杭州中美華東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113457)靜脈滴注,130 mg/m2,2次/d,持續(xù)治療2周,3周為1個療程。B組在A組基礎上,靜脈滴注250 mg黃芪多糖+5%葡萄糖溶液,2次/d。兩組患者均治療6周。
1.3 觀察指標及療效評價標準 比較兩組患者的臨床療效和不良反應發(fā)生情況。療效評價標準[9]:完全緩解,病灶完全滅亡,且無新病灶出現(xiàn),持續(xù)時間≥4周;部分緩解,瘤體最長徑總和縮小≥30%,且無新病灶出現(xiàn),持續(xù)時間≥4周;病情穩(wěn)定,瘤體最長徑總和縮小<30%或增大<20%,且無新病灶出現(xiàn),持續(xù)時間≥4周;疾病進展,有新病灶出現(xiàn),或瘤體最長徑總和增大≥20%,持續(xù)時間≥4周。記錄并比較兩組患者治療前后中醫(yī)證候積分、營養(yǎng)指標[白蛋白(albumin,ALB)、前白蛋白(prealbumin,PA)、生長激素(growth hormone,GH)]、炎癥指標[干擾素-γ(interferon-gamma,IFN-γ)、白細胞介素-4(interleukin-4,IL-4)、IFN-γ/IL-4]。根據(jù)《中醫(yī)量化診斷》評估患者中醫(yī)癥候積分,分數(shù)越高,癥狀越重[10]。
總有效率=(完全緩解+部分緩解)例數(shù)/總例數(shù)×100%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A組:完全緩解9例,部分緩解16例,病情穩(wěn)定10例,疾病進展7例。B組:完全緩解17例,部分緩解19例,病情穩(wěn)定4例,疾病進展2例。B組患者治療的總有效率為85.71%(36/42),高于A組的59.52%(25/42),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2.2 兩組治療前后中醫(yī)證候積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者中醫(yī)癥候積分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患者中醫(yī)癥候積分均下降,且B組均低于A組,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中醫(yī)證候積分比較積分/分)
2.3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ALB、PA及GH水平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者ALB、PA及GH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患者ALB、PA及GH均上升,且B組均高于A組,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ALB、PA及GH水平比較
2.4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IFN-γ、IL-4及IFN-γ/IL-4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者IFN-γ、IL-4及IFN-γ/IL-4比較,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患者IFN-γ、IFN-γ/IL-4均上升,IL-4均下降,且B組IFN-γ、IFN-γ/IL-4均高于A組,IL-4均低于A組,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治療前后IFN-γ、IL-4及IFN-γ/IL-4比較
2.5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fā)生率比較 A組:皮疹2例,感染4例,骨髓抑制2例,惡心嘔吐5例,肝功能損傷3例。B組:皮疹1例,感染2例,骨髓抑制1例,惡心嘔吐2例,肝功能損傷1例。B組患者不良反應發(fā)生率為16.67%(7/42),低于A組的38.10%(16/42),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
3 討論
絕大多數(shù)GC患者確診時處于進展期,通過手術治療難以達到根治效果,術后不可避免會殘留可見或不可見病灶,導致GC復發(fā)或轉移[11]。奧沙利鉑為常用的鉑類抗癌藥物,可以抑制DNA復制與轉錄,降低腫瘤活性,從而消除癌細胞[12]。卡培他濱在肝內可以變?yōu)槊撗醴?并最終轉化成氟尿嘧啶,可以競爭性抑制DNA復制,延緩腫瘤細胞增殖,且能靶向性選擇病變組織[13]。奧沙利鉑聯(lián)合卡培他濱可以發(fā)揮協(xié)調作用,對腫瘤細胞具有較強的殺傷效果,消滅術后殘余病灶,但同時會抑制患者吸收營養(yǎng)物質,對造血細胞、白細胞、肝細胞等正常細胞也會造成一定損傷,從而導致其出現(xiàn)骨髓抑制、肝功能損傷、惡心嘔吐等不良反應[14-16]。中藥在安全性方面具有獨特優(yōu)勢,可以減輕化療的毒副作用[17]。中醫(yī)將GC歸于“噎嗝”“胃痛”范疇,認為GC病位在胃,且與脾相關,脾胃為氣血化生之源,如果脾胃氣虛,水液難以排泄,血不得運化,痰飲、淤血結而成塊,久之成瘤,而術后正氣受損加重,加上癌毒阻滯于胃,脾胃升降失司,導致氣滯血瘀[18]。因此,GC治療的關鍵在于調理脾胃氣虛。黃芪治療氣虛證歷史悠久,為益氣補虛良藥[19]。APS是黃芪的主要活性成分,具有抗腫瘤、抑炎、增強免疫功能等多種生理功能[20]。
本研究結果發(fā)現(xiàn),APS治療可以改善臨床療效和中醫(yī)癥狀。另外,治療后,兩組患者ALB、PA及GH均上升,且B組均高于A組,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這說明,APS可以提高營養(yǎng)狀態(tài),可能是由于APS通過抗腫瘤作用,增強患者的消化功能,減輕胃腸道癥狀,從而提高患者對營養(yǎng)物質的吸收與利用,促進營養(yǎng)指標的改善。Th細胞可以分化Th1與Th2細胞,其中,Th1細胞可以生成IFN-γ等細胞,參與機體的細胞免疫,而Th2細胞可以生成IL-4等細胞,介導體液免疫。機體抗腫瘤作用的發(fā)揮主要依賴于細胞免疫,當Th1/Th2細胞失衡,并向Th2細胞漂移,會降低機體抗腫瘤免疫作用,出現(xiàn)腫瘤逃逸現(xiàn)象,通過IFN-γ/IL-4能夠評估Th1/Th2失衡情況[21]。本研究結果顯示,治療后,兩組患者IFN-γ、IFN-γ/IL-4均上升,IL-4均下降,且B組IFN-γ、IFN-γ/IL-4均高于A組,IL-4均低于A組,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這證實,APS可以改善Th1/Th2細胞失衡狀態(tài)。APS可以激活Toll樣受體4信號傳導通路,增強巨噬細胞功能,調節(jié)Th1/Th2細胞平衡,促進IFN-γ釋放。此外,B組患者不良反應發(fā)生率低于A組,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這說明,在常規(guī)化療方案治療的基礎上聯(lián)合APS可以減輕不良反應。推測APS通過抗腫瘤與改善營養(yǎng)狀態(tài),增強患者的機體功能,可以提高患者對化療的耐受性,降低不良反應發(fā)生風險。
綜上所述,APS輔助治療GC術后化療患者,能夠有效改善臨床療效,減輕中醫(yī)癥狀,促進營養(yǎng)狀態(tài)提高和Th1/Th2細胞平衡,且可以降低不良反應發(fā)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