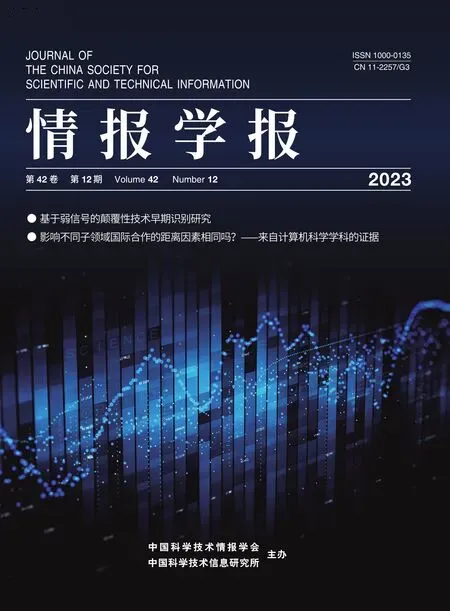融合論文顛覆性與鞏固性的學者二元影響力測度
楊杰,孔嘉,張藝煒,王昊,鄧三鴻
(1. 南京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南京 210023;2. 江蘇省數據工程和知識服務重點實驗室,南京 210023)
0 引 言
科學的進步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系統[1],大部分研究需要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展開工作[2],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3],這種方式構成了科學知識的繼承與流動[4]。然而,與常規論文不同的是,高顛覆性(disruption)影響力的研究往往能打破科學知識網絡中既有的研究范式[5],進而開辟出新的知識領域。近年來,發表于Nature和Science的多篇研究論文基于大樣本專利或文獻網絡數據深入刻畫與分析了科學領域中產生顛覆性影響的研究分布與趨勢[6-8],國內的學者也從顛覆性技術[9]、顛覆性創新[10]等視角來測度范式轉變型的創新研究技術與成果。與顛覆性這一概念對應的是鞏固性(consolida‐tion)[7],顛覆性反映了對既有范式的破壞式創新,鞏固性則反映了對傳統領域的繼承性延續,顛覆性和鞏固性影響力的研究已經成為情報學、科學學和計量學領域的一個重要研究議題[11]。
顛覆性和鞏固性是從引文網絡的深層信息定量體現的,其公式化表述來源于Funk等[12]在專利文獻中提出的鞏固性和顛覆性指數(consolidating/dis‐ruptive index,CD index),用于衡量專利是否鞏固或顛覆了現有的技術趨勢。Wu等[6]和Park等[7]分別將其拓展到科學文獻領域,通過衡量論文的深層次引用網絡結構,對科學研究的鞏固性和顛覆性影響力進行測量[13]。顛覆性和鞏固性影響力的概念在知識實體的滲透與流動[14]、科研成果的演變規律[7]、諾貝爾獎論文的特征[15]等方面得到了廣泛的實證與應用,為衡量科學影響力提供了新視角和新維度。
顛覆性和鞏固性的思想可以應用于學者層次的影響力測度與評價[16],學者影響力的測度在基金申請與評審[17]、績效評估[2]、職稱評定與獎懲制度[18]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隨著論文數量的指數級增長[11],學者影響力的測度和評價面臨著巨大的挑戰:一方面,傳統的學者計量指標被證明缺乏收斂有效性,且難以衡量學者的創新水平;另一方面,同行評審制度在效率和結果上存在缺陷,難以應對日益增長的論文數量。科學逐漸陷入顛覆性停滯的陷阱[7],為解決學者的創新評價難的問題,本文基于顛覆性思想將學者的影響力進行二元劃分——顛覆性影響力和鞏固性影響力,以二元視角刻畫和測量學者的影響力[19]。其中,顛覆性影響力作為學者創新水平的直接反映,在評價效度上顯著優于基準指標,對于未來人才評估的方法和科技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具體而言,本文從顛覆性影響力和鞏固性影響力出發,構建二元測度體系,以更全面地刻畫學者的影響力,設計4種定量的計量指標:顛覆性被引量、鞏固性被引量、顛覆性h指數和鞏固性h指數,基于此構建學者層次的二元測度矩陣。基于顛覆性影響力思想對學者影響力的二元劃分,為學術評價和績效評估提供新方法、新指標和新視角,以期為學者的學術評價和績效評估提供新的視角和測度方式,提升學者創新水平與潛力評估的合理性和科學性。
1 文獻綜述
1.1 顛覆性與鞏固性概念內涵
顛覆性的概念起源于Bower等[20]的著作Disruptive Technologies:Catching the Wave,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劃分為顛覆性的創新和鞏固性的繼承。國內學者對顛覆性技術的概念和內涵進行了新的闡述[9],從技術維度、市場維度和影響效果維度定義了顛覆性。在科學技術方面,顛覆性與鞏固性最大的區別在于是否具備變革的潛力,鞏固性技術在既有范式下,將知識以現有軌跡進行推進[21];而顛覆性技術則對不同領域知識進行了新穎性的融合[22-23],或進行科學技術的原始創新[24],產生范式變革的新知識[5]。
在科學和技術領域,新知識的產生與已有的智慧儲備密不可分。變革性的概念往往預示著一些顛覆性知識實體的出現,這些實體的核心從根本上偏離了先前的狀態[25-27]。例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徹底改變了傳統的科學框架[28],沃森和克里克發現的DNA雙螺旋結構則從根本上重塑了我們對生命本質的認識[29],BTW(Bak-Tang-Wiesenfeld)模型[30]為物理學領域引入了突破性技術。這些開創性研究都成功顛覆了既有范式,并提出了新的范式,體現了顛覆性創新和科學突破的本質[6,7,31]。顛覆性概念的思想脈絡可以追溯到庫恩的顛覆性變革觀點[5],即挑戰和超越既定范式作為科學進步的基石,科學進步往往萌芽于違背現行范式的反常現象,而變革性突破則體現為解決這些復雜且反常現象的新思路或新方法的誕生[32]。這一思想與Bower等[20]所闡釋的破壞性創新概念巧妙融合,形成科技創新的重要理論。
顛覆性的科學在整個科學進步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表示范式的巨大轉變。這體現為在科學或技術的知識擴散網絡中,顛覆性的科學往往形成了網絡結構的中斷和再生。基于這種理念以及評估科學創新的需求,Funk等[12]提出的顛覆性指數(CD index)以錯綜復雜的科學技術網絡為分析基礎,評估研究的新穎性及其催化變革性創新的潛力。在論文或專利的局部網絡層面深入分析知識的前向和后向擴散,以知識在網絡前后的擴散相互作用表征科學動態演化中的關鍵轉變節點[33-34]。
Azoulay[35]對顛覆性指數的直觀解釋為,對于某一核心文章FP(focal paper)而言,如果許多引用FP的論文也同時引用了FP的大部分參考文獻,那么FP可以被視為鞏固了其學科范式;相反地,當FP的未來引文并不承認FP的參考文獻時,其可以被視為顛覆了其學科領域的研究范式,甚至開創新的領域。
1.2 學者影響力測度
學者影響力的傳統測度指標一般包括發文量、被引量和h指數[36]等,這些指標具備公式簡潔、易于計算[37]等優勢,但也存在維度單一的局限性,難以衡量學者影響力的深層價值與內在含義[38]。從引文網絡的視角出發,傳統的計量指標通常只包含引文網絡的局部信息,而忽略了高階信息,難以直接衡量科學研究的顛覆性影響力或鞏固性影響力[21]。既有研究也表明,基于引文量的計量指標在測度和評價“里程碑”研究和頂尖學者的影響力時缺乏收斂有效性[39-40]。近年來,學者們通過《舊金山宣言》[41]和《萊頓宣言》[42]提出對傳統指標的抵制,并呼吁更全面的計量指標。
從學者視角出發,在目前的學科體系下,與現有范式不符的創新性成果往往難以發表[43]。Jia等[44]認為,鞏固性研究更適應于當前的學者評價體系,因為其通常是基于現有范式下被認可的成果,發表的概率更大,并且往往能在短期取得一定的引用。從長遠來看,顛覆性研究往往能取得更大的影響力,但是顛覆性研究的高難度、超高的時間成本與其他沉沒成本[11]、項目失敗以及被拒稿的高風險[17]等因素阻擾了很多的學術創新[45]。對于個體而言,專注于傳統領域研究可能是高效而省力的[46],但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這種行為會阻礙整體科學領域與科學研究范式的開創性發展。對于科學研究而言,現有的評價指標與體系無法準確刻畫學者的創新貢獻與價值,越來越多的學者放棄顛覆性的研究,最終致使科學陷入顛覆性停滯[7]。
近年來,盡管學界在逐步推進、完善“代表作”測度制度[47]以更科學地衡量學者的創新貢獻,然而“代表作”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專家的認知偏差、同行選擇以及人情關系[47-48],隨著論文呈現指數增長,同行評議和專家評審制度受到效率的局限[48]。在不斷呼吁測度體系改革和破“五唯”的當下,急需一種收斂有效性良好的定量指標來精確衡量學者的創新能力和真實貢獻,從根本上解決創新評價難的問題。
1.3 顛覆性與鞏固性影響力測度研究
自鞏固性和顛覆性指數(CD index)[12]被提出以來,產生了大量基于顛覆性和鞏固性影響力的研究。比如,Ruan等[49]定量分析了參考文獻數量和數據庫規模對顛覆性相關指標的影響;Bornmann等[50]基于F1000Prime數據庫,對顛覆性指數及改進顛覆性指數[51]進行了收斂有效性分析。還有研究針對論文的顛覆性與科研合作的關系[52]、在里程碑研究中的測度有效性[53]、與基石研究的關系[3]等進行了探索。
鞏固性和顛覆性指數是一個值域為[-1,1]的單維度指標,并且容易受到參考文獻數量等因素的影響[49],在論文的影響力測度方面具備一定的局限性[49-50,54]。為此,Leydesdorff等[54]和Chen等[55]在顛覆性指數的基礎上,將科學研究的影響力劃分為兩大維度:顛覆性影響力和鞏固性影響力;Bu等[19]則進一步探討了基于顛覆性和鞏固性的論文評價框架。在最新的研究中,顛覆性和鞏固性影響力的思想被應用于各個領域和層次,如顛覆性知識實體的滲透與流動[14]、顛覆性科研成果的演變規律[7]、鞏固性和顛覆性在諾貝爾獎論文中的分布[15]、在復雜網絡中對關鍵節點排序和識別的應用[33]等。
然而,顛覆性和鞏固性的思想尚未在學者層次的影響力測度與評價領域得到充分應用。為此,本文將填補此領域的研究空缺,創新性地提出基于顛覆性和鞏固性的學者影響力計量指標,實現對學者顛覆性與鞏固性影響力測度,構建二元影響力評價框架,以更全面地評估學者的學術影響力。
2 方法與數據
2.1 指標構建
本文沿用Funk等[12]、Wu等[6]以及Leydesdorff等[54]學者對論文顛覆性衡量的思想,首先,將引證網絡中論文的引用模式進行二元劃分,得到顛覆性引用和鞏固性引用。如圖1a所示,在文獻引證網絡中,考慮某一篇核心論文FP,設FP的參考文獻集合為R={r1,r2,…,rm},FP的被引文獻集合為C={c1,c2,…,cn},集合R、FP以及集合C共同構成了連貫的知識流動子網絡,涵蓋了引文網絡中心節點前向和后向的深層引用信息。為進一步地挖掘文獻間的隱式關系,考慮集合R的被引文獻集合RC={rc1,rc2,…,rck}。由此,FP的鞏固性被引文獻集合可表示為CC=RC∩C;顛覆性被引文獻集合可表示為DC=C-CC。其中,鞏固性被引文獻依賴于FP的知識基礎,反映了FP對既有范式的繼承性;而顛覆性被引文獻則獨立于FP的知識基礎,反映出FP顛覆既有范式的程度。因此,本文將FP的顛覆性和鞏固性被引文獻集合中的元素數量分別定義為顛覆性被引量和鞏固性被引量。

圖1 顛覆性與鞏固性影響力測度與評價框架(彩圖請見https://qbxb.istic.ac.cn)
從論文的影響力和顛覆性角度出發,具備顛覆性特征的科學突破可以映射為科學知識網絡中對既有范式的破壞和挑戰趨勢[5,56],由此可以基于顛覆性被引量的大小或比例,反映科學研究開創“新范式”的能力[33]。顛覆性被引量融合了研究的顛覆性程度和總體影響力,得以定量表征科學研究的顛覆性影響力;與之對應地,鞏固性被引量則直接反映了科學研究對既有范式繼承的影響,即鞏固性影響力。顛覆性被引量和鞏固性被引量提供了對引文網絡中錯綜復雜的知識流的全面理解[5],能夠對科學研究的顛覆性和鞏固性影響力進行二元劃分。通過融合論文的顛覆性、鞏固性和影響力,顛覆性被引量和鞏固性被引量對科學研究在多大程度上顛覆或鞏固了既有范式進行了定量表征,并進一步闡明了塑造科學進步軌跡的潛在動力,促進了對于科學知識創造和傳播的動態性質的認識。
科學家的總影響力可以反映為其全部研究成果影響力的分布[57-58]。基于此,本文在論文的顛覆性和鞏固性被引量的基礎上創新性地提出學者層次的衡量指標。從學者發表的全部論文出發,針對每篇論文的被引文獻,分別基于其顛覆性或鞏固性引用鏈接特征進行劃分,得到顛覆性被引量和鞏固性被引量,進一步可以將該學者的總被引量分為兩大類別,分別由兩種維度的被引量——學者顛覆性被引量(scientist disruptive citations,SDC)和學者鞏固性被引量(scientist consolidating citations,SCC)來表示,形成二元對立關系,即一名學者的顛覆性被引量與鞏固性被引量之和等于其總被引量。考慮學者A在一定的時間窗口內發表了x篇論文,則A的學者顛覆性被引量(SDC)以及學者鞏固性被引量(SCC)分別定義為
無論是顛覆性被引量,還是鞏固性被引量,均是基于被引次數的影響力衡量,而被引次數僅僅是影響力的一個維度,另一個重要的維度是發文數量。因此,將發文數量納入研究范圍,提出學者層次的顛覆性h指數(disruptive h-index)和鞏固性h指數(consolidating h-index),考慮某學者P的全部發表論文集合X={x1,x2,…,xr},分別將其按照論文的顛覆性被引量(disruptive citations,DC)和鞏固性被引量(consolidating citations,CC)降序排列,即
基于h指數的初始定義[36](學者發表的論文集合中至多有h篇論文的被引量大于或等于h),將顛覆性h指數和鞏固性h指數分別定義為
定義1.顛覆性h指數是指學者S發表的論文集合XSDC中至多有disruptiveh篇論文的顛覆性被引量大于或等于disruptiveh,即
定義2.鞏固性h指數是指學者S發表的論文集合XSCC中至多有consolidatingh篇論文的鞏固性被引量大于或等于consolidatingh,即
顛覆性被引量與鞏固性被引量之代數和即該學者的總被引量,因此,可視為對學者的影響力進行了二元劃分。與傳統指標類似,顛覆性被引量和顛覆性h指數可用于衡量學者的顛覆性影響力,而鞏固性被引量和鞏固性h指數可用于衡量學者的鞏固性影響力。在以上指標的基礎上,構建結合顛覆性和鞏固性影響力雙重維度測度矩陣(圖1b),進而將不同影響力的學者類型凝練為兩種學術特征:“顛覆型學者”和“鞏固型學者”。基于顛覆性和鞏固性這一組獨特而新穎的學者影響力視角,研究人員能夠更深入地了解科學內在的變革性影響力,進一步促進了我們對科學的“范式顛覆”和“范式繼承”二元復雜相互作用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礎上科學家對研究界的真實影響力和塑造未來科學進程的潛力。
2.2 APS引文數據
本文基于美國物理協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APS)提供的引文數據①https://journals.aps.org/datasets,包括Physical Review系列期刊在內的19種期刊,涵蓋了1893—2021年的全部文獻及引證數據,共包含700035個節點(研究論文)和9370286條引證鏈接。為確保充足的引文時間窗口以計算相關指標[59],并且為獲取較為一致的學者生涯區間與引文模式[21],本文僅考慮發表于2010年之前的463348篇論文。基于Pythonigraph-0.10.2和Python-networkx-2.8.8構建大型引文網絡,并建立大規模鄰接矩陣。在該網絡中,入度(indegree)表示引用次數,出度(outdegree)表示參考文獻的數量。在此分析過程中,基于Pythonscipy-1.10.1等程序計算相關指標,進一步對指標一致性檢驗和收斂有效性進行分析。
2.3 作者消歧
消歧(disambiguation)是定量學者測度與評價計算過程中的重點、難點和關鍵步驟[17,21,60]。在APS數據集中,同一作者可能采取不同的署名,或者出現不同作者署名相同的情況。為此,本文采取Sinatra等[58]的研究思路進行作者消歧,先提取出APS數據集中的全部名稱對,即任意兩個作者的名稱,然后使用正則表達式將其配對,僅保留完全符合以下要求的名稱對:①兩個作者的姓氏相同;②名字的縮寫和中間名相同;③兩個作者互相引用至少一次,或者兩個作者共同作者或具有類似的機構隸屬關系。對于配對后的歧義學者,結合Physics Tree數據集②https://academictree.org/physics/進行對比消歧。最終得到234086位不同的學者,縮減為原始作者名稱數的46.6%。
3 結果與討論
3.1 獲獎學者抽取與統計
為進行指標的收斂有效性測度,本文收集了物理學領域部分重要國際獎項的獲獎者數據,包括諾貝爾獎(Nobel Prize)③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physics/④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chemistry/、沃爾夫獎(Wolf Prize)⑤https://wolffund.org.il/home-page/和狄拉克獎(Dirac Medal)⑥https://www.ictp.it/prize/dirac-medal。將APS數據庫中經過消歧的作者姓名與這些獲獎者進行匹配,匹配過程包括使用獲獎者主頁、維基百科和Physics Tree的介紹或簡歷信息,篩選條件包括在APS數據集中發表了至少5篇文章。最終,得到130位物理學領域的獲獎學者。
獲獎學者與APS數據內其他學者的各項指標差異與分布如圖2所示。其中,基于雙尾Welch'st檢驗比較各項指標差異的顯著性,包括發文量、h指數、顛覆性被引量、鞏固性被引量、顛覆性h指數和鞏固性h指數(圖2a~圖2f)。顯然,獲獎學者的各項指標均顯著高于非獲獎學者(t>7,p<0.001),可以進行后續的指標一致性分析和收斂有效性檢驗(圖2g~圖2h)。從分布來看,獲獎學者的樣本量遠遠小于非獲獎學者,而各項指標的平均值和標準差都更大。即使在75%分位,非獲獎學者的各項指標仍處于較低的值,這可能是源于優先連接效應[61]和馬太效應[62]導致的冪律分布。

圖2 獲獎學者與非獲獎學者的指標差異與分布
3.2 一致性分析
本文選取肯德爾秩系數[63](Kendall's tau)作為指標測度一致性的衡量,肯德爾秩系數可用于離散數據的相關性分析,適用于本文的數據,其公式[63]為
其中,nc和nd分別表示存在一致序列和存在不一致序列的樣本觀測組數;nx和ny分別表示某樣本序列值相同的觀測組數。τ值越大,說明兩組樣本相關性越強;當τ為0時,代表兩組樣本完全獨立。
選取學者的總被引量、總發文量和h指數作為基準指標,指標一致性的結果如圖3所示。結果表明,無論是獲獎學者(圖3a),還是非獲獎學者(圖3b),本文提出的新指標(即顛覆性被引量、鞏固性被引量、顛覆性h指數和鞏固性h指數)均與h指數和總被引量呈高度相關,從而證明了新指標與傳統指標的測度一致性。另外,發文量這一指標與其余指標的一致性較差,且與顛覆性被引量的相關性最低(獲獎學者為0.54,非獲獎學者為0.57),說明顛覆性被引量受到文章數量的影響最小。

圖3 指標一致性——肯德爾秩相關性分析
顛覆性影響力和鞏固性影響力雖然是兩個不同維度的衡量指標,兩者之間卻存在較強的相關性。具體而言,獲獎學者樣本和非獲獎學者樣本中,鞏固性被引量與顛覆性被引量的相關性系數分別為0.69和0.61,鞏固性h指數與顛覆性h指數的相關性系數分別為0.72和0.65,這可能是由于學術領域的馬太效應[62],學者的高顛覆性成果為其積累的學術聲譽[64],使得該學者的鞏固性研究也能收獲更高的影響力,而鞏固性影響力又隨之降低了該學者顛覆性研究的發表難度,如此,二元影響力形成互相促進的效應機制。
3.3 收斂有效性
為進一步驗證新測度指標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對比基準指標進行收斂有效性的分析。指標的收斂有效性表征了該指標有效衡量其目標對象的范圍大小與效率[50]。本文綜合采用兩種計量指標的評價方法進行指標的收斂有效性評估,分別是獲獎學者的識別比率(identification proportion,IP)與獲獎學者的平均排名(average ranking,AR)。將獲獎學者賦值為1,非獲獎學者賦值為0。對于某個特定的指標,IP表示該指標識別出的排名最高的前n%學者中的獲獎學者占比,IP值越高,說明指標的收斂有效性越強。借鑒Xu等[65]的做法,將排名前1%的學者作為測度區域,計算該指標的召回率,并綜合驗證不同閾值下的指標魯棒性。
不同于IP,AR一般表示為特定指標下的全部獲獎學者的平均排名,但是簡單地取均值會受到其他學者排名的影響。為此,借鑒Mariani等[66]的研究思路,將不同指標下的單個學者的排名進行標準化處理,在引文網絡G=(V,E)中,考慮指標集合{m1,m2,…}和關鍵節點集合{v1,v2,…},取排位最低的獲獎學者和排位最高的獲獎學者的排名之差作為分母,得到標準化的平均排名,即
其中,m表示指標;vi表示獲獎學者;的平均值為AR。AR值越低,說明指標的收斂有效性越強。IP主要從召回率的角度測量了指標識別出的重要學者中獲獎學者的比例,AR則從全部獲獎學者的平均排位出發,兩者均能夠定量反映計量指標的收斂有效性[67]。
選取學者的總被引量、總發文量和h指數作為基準指標,收斂有效性結果如圖4所示。獲獎學者的平均識別比率(IP)和獲獎學者的平均排名(AR)結果均表明,顛覆性被引量和顛覆性h指數均具備優異的收斂有效性,并且明顯優于基準指標;與之相反的是,鞏固性被引量和鞏固性h指數的收斂有效性弱于h指數等基準指標。對于顛覆性影響力的兩個測度指標,即顛覆性被引量與顛覆性h指數,在不同的評價任務上各自具備更大的優勢。具體而言,顛覆性被引量在獲獎學者的識別比率更高,而顛覆性h指數對于獲獎學者的平均排名更低,在總體上兩者間差距很小,且均優于其他指標,因此,可以認為這兩個指標均能作為學者創新水平和真實影響力的有效測度。

圖4 指標收斂有效性——獲獎學者的識別比率(IP)與平均排名(AR)
為驗證本文結果的魯棒性,將獲獎學者平均識別比率(IP)的z值(前z分位中獲獎學者占比,即IP值)分別設定為0.001、0.005、0.02和0.05,如圖4b所示。從魯棒性檢驗結果來看,顛覆性被引量和顛覆性h指數的收斂有效性全面優于鞏固性影響力指標和基準指標。此外,在識別最頂尖的學者時,顛覆性被引量和顛覆性h指數相對于其他指標具有巨大優勢,但是隨著z的增大,這種識別優勢逐漸降低,但仍然全面優于基準指標。
值得注意的是,發文量在識別最頂尖學者時的IP非常低(圖4b,z=0.001和z=0.005),說明這項指標難以反映學者的創新能力與真實影響力,一致性分析已經表明發文量與顛覆性影響力指標的相關性較低,因此,應當避免使用發文量作為學者創新水平的測度指標。另外兩項基準指標,即總被引和h指數,在識別獲獎學者上各有優劣。其中,總被引在識別比率上領先h指數,而h指數在平均排名表現更優。這兩個基準指標的收斂有效性全面弱于顛覆性影響力的測度指標,這表明相較于傳統指標,顛覆性影響力指標是一種更佳的測度方式,有望在未來成為現有評價體系的重要補充。
3.4 二元影響力與學術特征
不同層次學者的二元影響力分布情況及學術特征如圖5a所示,其中橫軸、縱軸數據均作為常用對數(common logarithm,log10)進行處理。以顛覆性被引量和鞏固性被引量的90%分位數值(圖5中藍色橫縱虛線)作為劃分依據,將這些學者的學術特征劃分為“顛覆型學者”和“鞏固型學者”。顯然,獲獎學者的學術特征主要為“顛覆型學者”,而鮮有學術特征為“鞏固型學者”的學者能夠成為獲獎學者。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對于獲獎學者的二元影響測度,還是對于非獲獎學者的二元影響測度,高顛覆性影響力往往伴隨較高的鞏固性影響力,一項證據在于學術特征為“顛覆型學者”的科學家總數量多于“鞏固型學者”。結合上文分析,這種現象可能是源自基于馬太效應形成的二元促進機制,導致高顛覆性影響力學者也具備較高的鞏固性影響力,同樣地,高鞏固性影響力學者也具備較高的顛覆性影響力。

圖5 二元學者影響力測度矩陣及顛覆性被引量與鞏固性被引量最高的學者之學術特征(彩圖請見https://qbxb.istic.ac.cn)
為進一步對比顛覆型影響力和鞏固型影響力的差異,選取二元影響力最頂尖的科學家進行對比。圖5b和圖5c分別展示了顛覆性被引量和鞏固性被引量最高的5位學者。諾貝爾獎和沃爾夫獎是公認的頂尖榮譽,反映了學科內最高的創新水平和真實貢獻,而狄拉克獎章則專門為未被授予上述兩種獎項的學術泰斗頒發。在物理學領域,獲得這些榮譽的學者都對該學科做出了最突出的貢獻[68]。顛覆者被引量最高的5位學者均是獲獎學者。而鞏固性被引量最高的5位學者中只有2位獲獎學者,進一步分析發現,圖5c中的獲獎學者也具備很高的顛覆性影響力(這兩位學者同時出現在圖5b中),可以初步推斷:高鞏固性被引量與學者的真實創新貢獻的關系可能較弱,而高顛覆性被引量則與學者的真實影響力直接掛鉤。
上述結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顛覆性影響力更能衡量學者的創新水平和潛力,而鞏固性影響力則可能是學者總影響力中的低效組成部分。在顛覆性與鞏固性二元測度框架中,更應注重顛覆性影響力,它能夠更直接地反映學者的真實學術貢獻。
4 總 結
探索更加科學、合理的學者測度指標與框架有助于指導未來科學研究的高效開展。本文基于引文網絡中的節點鏈接關系,創新性地提出了學者層面兩大維度的影響力衡量指標,即顛覆性被引量(DC)、鞏固性被引量(CC)、顛覆性h指數和鞏固性h指數,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學者影響力的顛覆性和鞏固性二元測度框架。基于APS數據的463348篇論文以及234086位消歧后學者以及諾貝爾獎等3種重要獎項得主數據進行實證研究。從指標一致性和收斂有效性出發,驗證了顛覆性被引量和顛覆性h指數與傳統測度指標高度一致,并且在收斂有效性方面優于總被引、h指數等基準指標。此外,本文探索了物理學領域獲獎學者和非獲獎學者的學術特征分布,并對高顛覆性被引量的學者和高鞏固性被引量的學者的各項指標進行分析,發現這兩類學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模式。研究結果表明,顛覆性被引量和顛覆性h指數是測度學者創新影響力的可靠指標,二元測度體系能夠更準確地反映學者的影響力維度。
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提供了一種科學、可靠、有效的學者測度新視角,從顛覆性影響力和鞏固性影響力進行學者的二元測度。其中,顛覆性能夠反映學者的創新影響力,是衡量學者學術水平的有效指標。本文基于物理學領域深入探討了該指標的科學性、一致性、有效性、可行性與合理性,并進一步對二元測度框架進行了分析與討論。從學者的顛覆性影響力出發,對學者、項目和機構進行評價是破除“五唯”的一種有效途徑,也是在以“四個面向”為指導的新評價體系下的一個重要內容,本文的研究結論對于未來創新科學家的早期識別、學者績效與獎勵制度的改革、基金項目的評審與評價、科研激勵政策的制定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最后,對本文的局限性進行總結,并提出對未來的展望:①本文所探討的相關指標僅基于APS數據集的內部引證,實證結果較大程度上受限于數據庫的數據廣度。未來可以考慮更大樣本的實證,比如,針對WoS(Web of Science)和MAG(Micro‐soft Academic Graph)等數據庫涵蓋的全部學者及其論文數據進行研究,或者基于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和CSSCI(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等數據集研究國內學者的顛覆性影響力。另外,受限于引文網絡深層指標的算法,顛覆性和鞏固性相關指標的計算復雜度較大,未來需借助并行計算、分布式計算等以支撐更大樣本量的研究。②本文未考慮引文時間窗口這一重要因素,早期的學者可能會收獲更高的測度值。未來可以考慮設定時間窗口,從而對不同年份學者的影響力進行有效比較。③本文只收集了物理學領域的部分重要獲獎數據,以定義獲獎學者,這導致獲獎學者和其他學者的數量差異很大。未來可以考慮院士數據集等其他數據集以進行更全面的收斂有效性檢驗,或者基于CEM(coarsened exact matching)方法[39]進行精確匹配。另外,除了物理學這一領域外,相同的模式是否能夠應用于其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及交叉學科領域,仍有待后續研究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