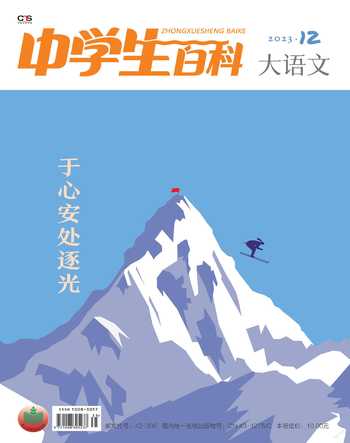長卿山下綠樹映紅墻
連續兩次核武器實彈爆炸成功,讓中國徹底擺脫了國外的核威懾陰影。盡管全世界的報紙都在用大量篇幅報道這震撼人心的成果,但沒有人知道究竟是誰創造了奇跡。他們是誰?他們在哪里?他們如何在技術封鎖下找到正確的路?
正當國外情報人員用衛星在中國西北一寸寸“翻找”時,中國原子彈和氫彈的設計與制造者們已經在按部就班地準備轉移事宜。他們完成了核彈的早期研究設計和實驗,接下來的工作重心是將其武器化定型,并且研制新一代核武器。
1969年,這群功勛卓著的無名英雄離開奮斗了十多年的青海金銀灘草原,內遷到長卿山南麓,即今天的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舊址,也叫兩彈城。相比高原的極端氣候和過于艱苦的環境,這里顯然更適宜他們開展后續工作。
當我走進兩彈城時,發現許多建筑還完整地呈現出半個世紀前的樣子。保留下來的宿舍是由紅磚青瓦構成的多座小院,每座小院住兩位專家。居所的布局全都一樣,入門先是一間警衛室,往里走是一間辦公室、一間廚房、一個衛生間,最里面是臥室。每個房間都顯得狹小而局促。臥室里只有一張單人床,有的甚至只是一張行軍床,簡單得不能再簡單。靠窗的地方擺著寬大的書柜與辦公桌,上面堆滿了書籍、資料和辦公用品。說是臥室,不過是又一間辦公室罷了。
在王淦昌居住過的房間的墻壁上,還留著他寫的幾幅字,其中最顯眼的地方寫著:“科學雖然沒有國界,但是科學家是有祖國的。”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兩彈一星”元勛幾乎都曾遇到過這個問題。他們青年時期在國外進行過前沿物理學的深造和研究,在那里可以接觸到最好的導師、最先進的理論、最強大的計算機,會有在大多數人看來更好的前途。但是,他們毅然放棄了這一切,頂著巨大的阻力回到祖國,扎根在家人都不知道的地方,為一項偉大的事業奉獻畢生熱血。當他們的導師或者朋友試圖以“科學無國界,留在這里可以更好地進行科學研究”作為理由勸他們留下時,他們首先想到的始終是“祖國需要我”。
宿舍區的另一頭是鄧稼先舊居,門口的字是鄧稼先的夫人許鹿希女士題的。
許鹿希記得1958年的那一天,鄧稼先突然告訴她,自己工作上有調動。她問他調到哪兒去,他回答“不能說”。她問他調去做什么工作,他還是回答“不能說”。無奈之下,許鹿希只好讓鄧稼先留一個地址,將來通信用,結果他說通信也不行。一切,都是保密的!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許鹿希會把一些親友寫給鄧稼先的信通過組織轉交給他,但并不是每一封信都會得到回復。久而久之,親友們與鄧稼先的聯絡就中斷了。鄧稼先似乎也不屬于許鹿希。他們結婚33年,朝夕相處的日子只有6年。其余時間,許鹿希除了思念就是每日惴惴不安的擔心。
1985年,鄧稼先的身體接近崩潰,他才不得不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回北京接受治療。有一天,他拉著許鹿希的手,用微弱卻堅定的聲音說:“我不愛武器,我愛和平,但為了和平,我們需要武器。”
次年6月,題為《“兩彈”元勛鄧稼先》的專題文章見報,揭開了當初鄧稼先對妻子許鹿希保守的秘密。那一天,失去鄧稼先消息多年的朋友們紛紛給許鹿希打去電話,問題出奇的一致:“鄧稼先,還活著嗎?”他們一面震驚于鄧稼先竟悄無聲息地完成了這樣的豐功偉績,一面又很清楚,他的身體可能出了狀況。結果,僅僅一個多月后,鄧稼先便與世長辭。
在兩彈城,再讀鄧稼先的故事,似乎多了激蕩和澎湃。許許多多像他一樣的元勛,已走進大眾視野。而更多的,是默默奉獻、默默發光的人。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或許兩彈城也不知道。但這里的磚瓦,記住了他們走過的路。
我在院部辦公樓舊址內找到了曾經的院長辦公室,與其他研究員的辦公室并無區別,除了常用的資料和工具之外,筆筒內還有14支用壞的鋼筆。一陣清風透過窗戶吹進來,吹動半個世紀前的報紙。我仿佛透過歲月的帷幕,看到那時的他們在演算紙上奮筆疾書,看到他們穿越長長的走廊去閱覽室翻查資料,看到他們在會議室內與同事激烈探討,看到他們在深夜冥思苦想……
我順著他們曾經的目光看向窗外,那時種下的小苗早已長成參天大樹。
故鄉人|王永強
筆名封塵,出生于四川省威遠縣,雙魚座男生;文風不定,喜歡我手寫我心的真實,時而唯美青春,時而憤世嫉俗;《中學生百科》特約作者,在《萌芽》《格言》等雜志發表作品,曾獲第十二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