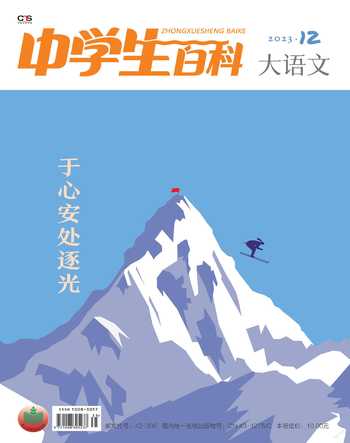不是渠畔過客,是歸人

我的故鄉位于豫北太行山余脈的一個小山坡上。故鄉沒有河,但有一條紅旗渠攔腰而過。如今,我知道她被稱為“人工天河”,是“中國的水長城”。我就是那渠岸上光著屁股長大的孩子,常常與伙伴們在渠里捉魚捕蝦,戲水歡樂,度過童年。聽母親說,以前很多人家就吃渠里的水,常常像吃黃河水一樣,一碗水,半碗沙。
時代的暗影,生活的艱辛,倒像跟我們沒有太多關系。我們只是無憂無慮地享受著紅旗渠帶來的歡樂。午睡時間,我們常常在渠岸上沐浴陽光。我記得那些兒時伙伴,記得那些時光,也記得等夏天一過,我們的皮膚就會像換了一種顏色。
說起故鄉,說起紅旗渠,有太多記憶浮現在眼前。那些兒時伙伴,每一個名字,都與紅旗渠有關。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紅旗渠的兒女,每一戶林縣人家都是渠畔人家。紅旗渠里的水,自然地流,往低處流,在該繞彎的地方繞彎,去灌溉冬小麥,灌溉玉米和白菜。紅旗渠滋養著她身下的土地,滋養著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生靈,讓過去年代里外出逃荒的人們得以重返故土。
后來,我迎來了“放牛班的春天”。那一年,身為農民工的父親有幸混出了名堂。我們舉家搬遷至鄰省山西,居于紅旗渠的源頭濁漳河流域。如此看來,我的人生大概是沒辦法與紅旗渠相離的。只是,那些光著屁股一起長大的伙伴,他們過早地接觸了來自現實的直接考驗,我則有幸待在學校里接受教育。我與他們之間的距離,與故鄉之間的距離,似乎不僅僅停留在空間層面上了。
大學畢業后,我終于有機會重返故鄉,方式卻獨特而別扭——我竟然跟團到故鄉去旅游,去參觀故鄉的紅旗渠,參觀西坡村那個我曾經以為熟悉她的一草一木的地方。
寬闊的紅旗渠竟有一絲雄壯,如一條巨蟒橫臥在太行山間。我看到這一幕幕,靈魂微微戰栗。我感覺一切熟悉又陌生、親切又疏離。林州市黨史辦原主任給我們當導游。他說,林州的包工頭在全國各地都很多,這與修筑紅旗渠有關。你看,那段渠是當年“張官營大隊”承包的。大家自帶干糧,小米加步槍換成了小米加镢頭。李云龍當年攻占了很多山頭,而修建紅旗渠削平了一千多座山頭。紅旗渠精神與革命精神一脈相承!當然,修渠的艱難不只太行山之堅。那些修渠人寫就的破壁精神,如今依然響徹這里的每一寸土地。
我這個故鄉的孩子,就這樣站在人群中聽別人介紹故鄉的事。我竟然對故鄉無知到了令自己感到諷刺和驚訝的程度。難怪離開多年以后,我發現我與故鄉之間多了一層無形的隔膜,心里存有熟悉與親切,面目卻模糊了。如今彼此面對,似乎有一種難以啟齒的感覺。置身于故鄉人之中,我顯得不倫不類。我已經難以融入他們、體會他們了,然而心底依舊有一絲絲莫名的喜悅。
我想這就是故鄉帶給我的美好——盡管這個小村莊如今變了模樣,我卻仿佛還有根。“故鄉”這兩個字在我心里總帶著濃濃的情味,關系到我來自哪里。至少在看得見的層面上,在物質的層面上,故鄉是我的邊界。在這個邊界面前,思緒從親人延伸到腳下的土地,延伸到遠處的山脈和日出。我開始理解歷史,理解空間、時間。我站立在那片土地上,不必再問“我來自哪里”。
現在,穿過故鄉的紅旗渠已經是國家5A級景區。作為故鄉的孩子,作為一名“旅游者”,我對她的了解也是今年才多了一些。我曾經自以為對她有多熟悉,誰知離開故鄉之后,很多事物便化成了記憶,連紅旗渠也只是那個掛在嘴邊用以區分他人故鄉的標志。即使這樣,我也覺得很好。至少我順著記憶的脈絡,總是能不偏不倚地找到故鄉,找到生命的根和精神的源頭。
我是山坡上長大的孩子,本性中有著對奔跑、對自由的無盡渴望。故鄉的山野,故鄉的紅旗渠,助我攝取知識、探求思想、追求信仰。很多時候,我甚至覺得,不只是可以說我的故鄉有紅旗渠,也可以說紅旗渠就是我的故鄉。那個從小便熟悉的地方,那條浸染著童年時光的人工渠,幫我理解生活,理解世界,理解許許多多抽象的存在。理解并熱愛,或者說理解然后熱愛。
在我心里,紅旗渠就是兩千多年前的長城、都江堰,修筑她的兒女就是故事里的愚公。她蘊藏著祖輩的智慧和堅定的求生意志。一切的一切都來之不易,然而小時候的我們并不知道。我們就那樣無憂無慮地享受著她的恩澤,而且常常調皮地往她的懷抱里扔石頭,全然忘了眼前的龐然大物是祖輩血汗的結晶,有些人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當歷盡千辛萬苦終于通水的那一刻,當所有的渴念與欣喜被澆灌,他們一定激動而虔誠地跪下,謝天地,也謝自己。
記住過去,就意味著記住來路,我想這才是紅旗渠真正應該在今天被保護的原因。我并不想羅列關于紅旗渠的資料,我只想說,我對紅旗渠是有感情的。這種感情大概是我曾經生于斯長于斯而天然具有的,畢竟故鄉的土地正是被紅旗渠所澆灌。甚至可以說,每一個林州人的血脈中都流淌著流過紅旗渠的水,都回響著紅旗渠的回響。這是信念的傳遞,是對紅旗渠締造的破壁精神的傳承。
紅旗渠已經成為林州市的精神象征,這讓林州的紅色精神有了一種特別的意蘊。當年帶領林縣(州)人修建紅旗渠的楊貴老書記正是革命軍人出身。小時候只是聽說村里面打過仗,“游覽”過故鄉之后,在“導游”的介紹下,我才知道,原來鄧小平同志曾在那里坐鎮指揮過一場戰役。知道這些,我便覺得自己和整個世界聯系起來了,和歷史聯系起來了,而且一直都聯系著。
還有那條巷子,當年鄧小平同志曾經帶著兩個警衛員在星空下走過呢,他們所走過的路,也正是我和兒時伙伴一起走過的路。這算不算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巧遇與相逢呢?由是我也懂了,原來紅旗渠精神與紅色精神是一脈相承的。甚至可以說,紅旗渠精神不是從劈開太行山上的第一塊巨石開始的,也沒有在修建完成后結束。就像許多年后回到故鄉、回到紅旗渠,我觸摸得到過去,也望得見將來。
故鄉人|閆志浩
筆名明斌浩,字做己,別號行之。自幼生長在河南省林州市紅旗渠沿岸任村鎮西坡村,后移居山西長治平順。2016年畢業于晉中信息學院。愛好讀書、思考、作文,關注精神、心靈、靈魂,喜歡閑聊漫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