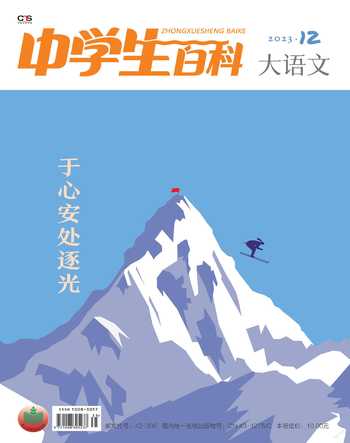與十八洞村隔著時光河

電影結束,我輕輕仰頭,淚流滿面。是被故事打動了嗎?是,又不全是。我想起了故鄉。有多久沒有回去了呢?大概有二十年甚至更久吧。長遠的疏離,讓心上有一處被忙碌所掩藏的隱痛。可明明就在剛才,我隨鏡頭在故鄉停留了124分鐘。我在電影開始的那一刻回家,又在電影結束的瞬間被推離。記得母親帶我離開的那天,外婆與我一起走出那棟木質瓦房,然后去了山上采藥。她沒有送我到村口,也沒有朝我揮一揮手。你能明白那種悵然若失的感覺,是嗎?
一個有雨溫柔敲窗的夜晚,我在電腦上看完了《十八洞村》。我不在十八洞村出生,但在山寨里的外婆家度過了近四年。我最美好的童年記憶,以及對湘西這幅山水畫卷的初始印象,都與這里有關。所以我總認為,外婆家才是我真正意義上的故鄉。就像這部并未大熱的電影,不為我而拍,卻毫無疑問地屬于我。它把所有的山巒還給了我,把所有的青翠還給了我,把隱約的鄉音和古老的民俗統統還給了我。記憶和情感毫無理性地在熟悉的電影畫面中穿行,我仿佛聽見外婆又搖響那清脆的鈴鐺。外婆以這種方式找我,喚我回家。
聽母親說,因為外公去世得早,外婆只生了她一個孩子。自從母親十幾歲外出打工,外婆大部分時間都是一個人過。后來,母親有了自己的家,有了我,卻因為要隨父親走南闖北跑貨運,只好托外婆看管我。母親送我去外婆家的情景我全然忘記了,我猜是年紀太小的緣故。其實我可以去條件更好的爺爺奶奶家,但母親怎么也不愿意。后來,我曾問過她,是不是想讓年幼的我給外婆做伴。母親搖了搖頭,沒有回答。那時候我剛上高中,而外婆早已在那片她熱愛過也憎惡過的山水間長眠。
就像電影《十八洞村》里所鋪陳的那樣,湘西這片神奇的土地果真就是一首醉心的散文詩。連綿起伏的群山,恣意繚繞的云霧,如夢如幻的梯田,每個角度都有詩意的敘事。但對于祖祖輩輩在這里掙扎著求生存的人而言,這種詩意是殘缺的,有濕漉漉的底色,天生帶著傷口。曾經,在外婆身上,在山寨的每個人身上,我看見美與痛就那么毫不違和地結合在一起。他們的腳深深陷在泥土里,一點點扎根,但土地生長樹木,似乎并不生長他們向往的生活。
和其他人一樣,土地也是外婆的命。外婆家的旱地很少,水田也很少,它們是年復一年的生活寄托。在我稍大一些的時候,外婆會帶著我到梯田勞作。我站在田埂邊,看見外婆在自家田里彎下腰,別人在別人家的田里彎下腰。因為沒有男人,外婆很累,但我并沒有發現別人就很輕松。我把采摘到的野果裝進口袋里,緊緊捂著,仿佛犯錯的孩子偷了大山的秘密。我曾問過外婆為什么要種田種地,為什么不可以每天只吃山上的野果。外婆笑了笑,什么也沒說。
在電影里,有不少關于梯田的航拍鏡頭。我這才知道,十八洞村的梯田,如果在高處看,其實也是連成片的。它們見縫插針一般在大山里延展,然后又在無路可去的時候停下。這多像山里人的抗爭與無奈。電影中的楊英俊是“最喜歡種地的人”,他放棄了去油田當工人的機會,也不愿外出打拼,一心只守著家里的一畝三分地。他的執著,一如外婆的執著。而按現在的理解,我更愿意認為那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對土地的敬畏。
外婆一生清貧,也甘于清貧。她用自家的玉米喂養自家的雞,把自家的雞下的蛋煮熟了放進我的小碗里。如此,她就覺得所有的辛勞有了意義。外婆那輩人的性格,大概是隨了生養他們的大山,沉默而敦厚,雨時不悲泣,晴時無歡喜。他們是不會在山林間迷路的人,也是忘了困惑的人。電影里的楊英俊卻不一樣。“一輩子都在種地,怎么種成了貧困戶?”這是楊英俊的天問,是外婆那輩人所不能理解的覺醒,但他們對于土地的那種復雜情感沒有區別。
還記得晴天里,我跟著外婆到地里鋤草。她對每一株雜草恨之入骨,對自己種下的瓜果蔬菜悉心照顧。許多年后,回憶起陽光下已經有些模糊的情景,我竟覺得外婆對我的愛,并未勝過對莊稼的憐惜。只是,我終究明白,在那樣的生活現實里,土地之于生命,就像繞不過的因果。
外婆是在我離開后的第三年去世的,在山河入秋的時節。母親說,安排好外婆的后事,她就去了來不及收割的稻田。那年天旱,收成并不好,但在那丘鑲在山腰的稻田里,看不到一株野稗。金黃的水稻一排排地站著,整整齊齊的隊伍,風吹不亂,雨打也不亂。依母親的推算,外婆應該在插秧的季節就已病重。但她與土地最后一季的親近,依然每個細節都做得一絲不茍。貧瘠的土地未曾厚待她,但她至死都沒有說過土地的壞話,至死都在給予土地最深情的告白。

電影中,楊英俊后來成立了楊家班,一心想著如何帶動一家人致富,如何帶動整個村寨致富。他對土地最后的倔強,超越了土地和莊稼本身。這是外婆所做不到的。但是啊,那塊收養我童年時光的外婆家的土地,終究有著相同的質地和養分。所以,當楊英俊說“人生一輩子,過完了都要走,只有田土不得走”的時候,我抑制不住號啕大哭。這句話,外婆可以說,每一個十八洞村的人可以說,唯獨我不可以說。那方水土之于我,除了玩樂,還剩什么?
因為家鄉沒了親人,在外婆去世之后,母親也是幾年才回去一趟,每次都匆匆忙忙。而我,求學,工作,總是陰差陽錯,竟沒再回去看一眼。后來,又聽母親說,那間守護我入夢的木質瓦房,也在一場大雪過后倒塌了。那是我記憶里最清晰的存在,也是最后的念想。在電影結束后,我在網上瘋狂地搜索與十八洞村有關的一切,想抓住所有。我知道那里依然有最美的山水和質樸的鄉風鄉情,但無數新鮮事物正在高高低低的土地上生長。一切如常,一切又已經不一樣。

如果單純用物質來衡量,母親作為十八洞村出來的人,也算得上成功。她讓我在城里上學,讓我穿漂亮的衣裳,讓我住在寬敞明亮的大房子里。但是,她與電影里的楊英俊不一樣,與依然生息在山寨里的兒時伙伴不一樣。她寫下的散文詩,對外婆,對那片土地,有虧欠。
我給母親打電話,說想回去看看。母親竟絲毫不意外,好像一直在等這天。她問,準備什么時候出發?我說,明天,又或許還需要一段時間。是的,我很堅決,卻也猶豫。是近鄉情怯嗎?是,又不全是。電影里青石板路的鏡頭在腦海里反復,它們纏繞著村寨,有時寬,有時窄。我光著小腳丫,牽著外婆的手,踩過一塊塊冰涼。我害怕已經找不到回家的路,聽不見外婆搖響的鈴鐺,害怕聞一聞包谷燒的香,就會一醉不醒。珍貴的過去存于記憶里,而我越不過時光河。
母親發來信息說:我小時候,你外婆每次喚我,都會嗚嗷嗚嗷地嘶吼,常常被人取笑。我不知道她帶你的時候,怎么就想到了搖鈴鐺。我回復說:如果外婆還活著,如果她能開口說話,如今十八洞村變得更好的一切,會是她所愿吧!
故鄉人|程語
湖南岳陽人,曾在十八洞村度過一段彌足珍貴的童年時光。大學畢業于湖南師范大學,先后任職于《南方都市報》《特區文學》等報刊社。現居深圳,從事自由寫作,作品見于《讀者》《美文》《兒童文學》等,出版散文集三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