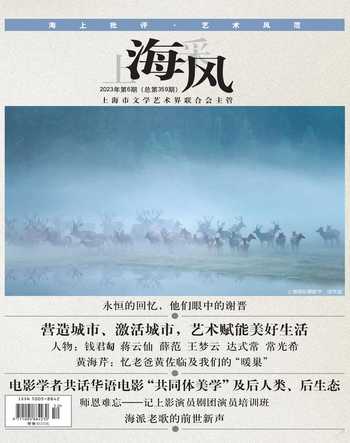他們待我們就像孩子
陳鴻梅

演員培訓班招生的時候,我還在讀高中,是學校的播音員,與同學相比,普通話還比較標準。那天,我們舉辦一個大型的活動,我看見兩個人圍著我們的場子轉,她們不像是我們學校的老師。等她們走了以后,學校的老師對我說:“你知道她們是誰?著名電影演員王丹鳳和朱曼芳。你到上影廠去一次,她們想看看你。”我說:“好啊!”但心里很擔心,覺得自己恐怕不行,后來覺得,去玩一把也好。到了上影,洪兆森老師給我排了一個小品《送貨路上》,跟我搭戲的是張建民,臺下坐了很多劇團的老師。其中有一段戲,我在送貨的路上,收到一封信,說是爸爸病了,一開始我不信,可打開信之后,真的是爸爸病了,也許見不到了,我一下子號啕大哭起來。演完之后,我就記得洪老師跟瑞芳老師說了一句:“哎?這個小丫頭演得挺投入、挺真實的。”
沒過多久,我就要畢業了,在那個年代,我的兩個哥哥姐姐都在國企,我理所當然會被分配去農村。但是,比較幸運的是,我考取了南空。于是,我們家里就開了一個小型的座談會,爸爸問我,你自己怎么想?我說我也不知道。他就說:“算了,南空不去了,整天在天上飛危險,還是去上影吧,如果演員干不了,以后還能干別的。”我就一心想著去上影,可是其他同學的通知陸陸續續都來了,我的還沒有。當時有一個說法,叫工農兵學員,我以為我不屬于工農兵,就沒戲了。這時,學校把我分到奉賢星火農場的食堂,我就在那兒待了半個月。有一天,我在洗菜的時候看見一輛上海牌的小車駛過,第二天,場部的領導告訴我,是張瑞芳老師和鐵牛老師來送我的錄取通知書了,要我明天就把東西拿好,到上影去報到。
培訓班的時光是終生難忘的,我們遇到了很多老師,除了臺詞課、表演課,還有觀摩課。梁明老師和朱曼芳老師告訴我們,除了多讀書、多觀察生活細節以外,還要學會去看畫,因為人物最經典的美往往都在畫里表現了。這些老師真的就像自己的母親那樣,毫無保留地教我們。
我從學員班畢業之后,演的第一部戲就是和秦怡老師合作的《風浪》。秦怡老師每天都帶著她的兒子小弟,后來我們去青島、威海出外景,小弟也跟著我們一起。我就覺得秦怡老師特別不容易,她是女主角,還要照顧兒子。
最讓我欽佩的是,秦怡老師的每一場戲都要做功課,金焰老師當時生病住院,但秦怡老師一天不落到船廠去學電焊。我說:“秦怡老師,您不用來了!”“那不行,演出來是假的。”秦怡老師說得很堅決。
要說的老師太多了,韓非老師請我吃西餐,張鶯老師陪我買過鞋,朱莎老師也請我到她家做過客……這些老藝術家待我們就像自己的孩子。我們班一共18位男生,6位女生,我可以代表這些培訓班同學說,我們一輩子都會感謝我們這些老師和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