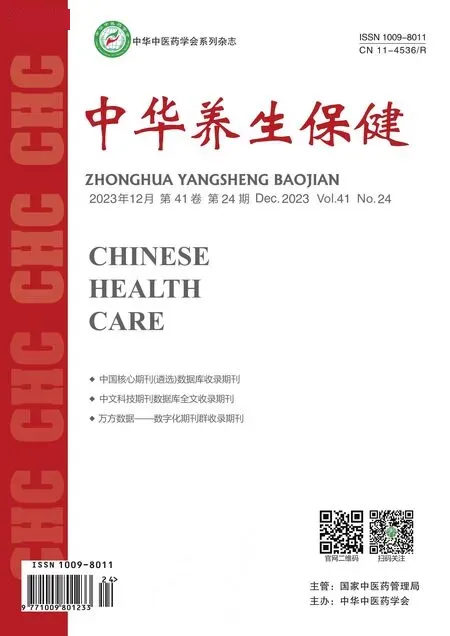撳針干預手術后呃逆臨床療效的RCT研究
涂 娟 涂店紅 歐陽騫
(江西省腫瘤醫院頭頸腫瘤外科二病區,江西 南昌,330029)
呃逆,即膈肌痙攣。該病表現為喉嚨處出現呃呃連聲,不能自制。當連續發作時間48 h,則為頑固性呃逆[1]。盡管導致呃逆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手術后繼發出現呃逆還是較為常見[2]。手術后出現呃逆影響術后的康復進程,延緩傷口的愈合,嚴重者會影響患者情緒,導致其出現焦慮或者抑郁[3]。目前臨床上多采用藥物治療,但藥物治療效果有限,且個體差異較大,獲得療效不同,不良反應也不容忽視。因此需要進一步探尋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療方法。
現代醫學認為手術后呃逆形成原因較為復雜,例如腹部手術,呃逆的形成可能與術中刺激膈神經,誘發膈肌發生痙攣,水電解質失衡,術后因切口疼痛及置管等多種原因有關。也有中樞原因導致呃逆,腦血管病、腦腫瘤,腦外傷、脊髓高位損傷和炎性反應等刺激呃逆中樞,釋放異常信號產生膈肌痙攣或不自主運動。中醫學認為,術后呃逆為氣血不足、氣血瘀滯、脾胃受損或情志不暢等因素引起,其病位在膈,病機在于胃失和降、胃氣上逆。盡管目前國內外已有不少用非藥物治療技術,如針刺、電針、經皮神經電刺激及穴位刺激等替代止吐藥物的研究。但是為了進一步提高患者依從性,研制干預方便、效果持久、安全有效的護理干預措施勢在必行。因此,本研究選擇耳穴撳針作為治療手術后呃逆的主要護理干預措施,臨床療效顯著,現匯報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納入2020 年9 月—2022 年9 月在江西省腫瘤醫院施行全身麻醉手術患者20 d 內出現呃逆癥狀的患者60 例。采用隨機數表法隨機分成兩組,分別為試驗組和對照組。試驗組30 例,其中男性16 例,女性14 例;年齡39~71 歲,平均年齡(48.70±16.25)歲;手術部位:頭頸部手術12 例、胃部手術11 例、結直腸手術7 例;呃逆持續時間2~8 d,平均(3.22±0.90)d。對照組30 例,其中男性17 例,女性13 例;年齡40~75 歲,平均年齡(49.36±17.60)歲;手術部位:頭頸部手術13 例、胃部手術9 例、結直腸手術8 例;呃逆持續時間 3~7 d,平均(3.01±0.86)d。兩組受試者性別、年齡分布、手術部位、呃逆持續時間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及家屬均知情同意參與本研究,且本研究已被江西省腫瘤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西醫診斷符合《慢性呃逆的診斷與治療》[4]中呃逆的診斷標準。中醫診斷依據國家中醫藥“十四五”規劃教材《中醫內科學》[5]中呃逆的診斷標準。患者術后出現呃逆,且呃逆癥狀持續48 h 以上;②患者術后生命體征平穩;③年齡18~75 歲,性別不限,無對照組藥物過敏史。
排除標準:①精神疾病患者,存在溝通障礙、認識功能障礙者;②暈針或不接受針刺治療者,治療部位皮膚有破損、血腫、感染、皮疹者;③嚴重過敏體質者;④合并其他系統嚴重疾病或并發癥需緊急治療者。⑤中途退出者。退出(脫落)標準:受試者不愿意繼續進行臨床試驗,提出退出臨床試驗;出現嚴重不良事件或嚴重不良反應者;病情惡化必須采取緊急處理措施者;受試者在臨床試驗過程中出現嚴重的并發癥、合并癥者,不宜繼續進行試驗;臨床醫生認為有其他情況而應該中止者。
1.3 方法
兩組均采用常規護理措施,健康宣教,加強病情觀察,及時去除誘因,做好日常護理和飲食護理等。
試驗組采用撳針耳穴治療,選擇的主穴有耳中(膈)、胃、神門。配穴采用交感、皮質下、相應點(手術點或患病器官的反應穴位)。每次選3~4 穴,先用碘反復消毒兩側耳穴,用0.5 寸毫針刺入一側耳穴,留針并間斷行中強度捻針治療,呃逆明顯減輕或停止后用鑷子夾住撳針刺入另一側主穴,再用6 mm×6 mm 方塊橡皮膏固定,囑患者自行按壓每日數次,以有痛感為佳,先側耳穴可出針。撳針1 次/3 d,3 次1 個療程,6 次2 個療程。
對照組對癥采用化學合成藥物肌肉注射治療,如利他林10 mg 等。上述治療均1 次/d,連續治療20 次評估治療效果。
1.4 觀察指標
①呃逆頻率定義為以平均每天每小時呃逆最多次數;②起效時間定義為受試者開始接受治療,到呃逆發作次數明顯減少或間隔時間明顯延長的時間段作為起效時間,以h為單位;③呃逆癥狀評分,依據參考《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試行)》[6]中的呃逆癥狀積分表。0 次/d 計0 分;呃逆≤5 次/h,且患者能耐受,不影響患者進食者計3 分;(6~10)次/h 或≤5 次/h,但患者難以耐受,影響進食者計6分;>10 次/h 或≤10 次/h,但不能進食或呃逆時伴胃食管反流者計9 分。以每小時最高呃逆頻率計算。
1.5 療效標準
參考《臨床疾病診斷依據治愈好轉標準》[7]中的療效評定標準。顯效:癥狀評分減少6 分以上或呃逆消失,治療后2周無復發;有效:癥狀評分減少3 分以上或呃逆持續時間及發作次數明顯減少,或治療后2 周內偶有復發;無效:呃逆持續時間及發作次數均無明顯改善。治療總有效率=(顯效+有效)例數/總例數×100%。
1.6 統計學分析
2 結果
2.1 兩組呃逆頻率比較
試驗組治療前呃逆頻率為(11.20±0.58)次,對照組治療前呃逆頻率為(11.35±0.46)次,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試驗組呃逆頻率為(2.60±0.47)次,對照組為(5.21±0.50)次,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撳針耳穴治療手術后呃逆在減少發生頻率方面優于對照藥物組,見表1。
表1 兩組呃逆頻率比較 (±s,次)
組別 例數 治療前 治療后試驗組 30 11.20±0.58 2.60±0.47對照組 30 11.35±0.46 5.21±0.50 t 1.249 22.320 P 0.270 0.0001
2.2 兩組止呃起效時間、治愈時間比較
試驗組止呃起效時間為(3.36±0.22)h,對照組止呃起效時間為(4.65±0.31)h,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試驗組止呃治愈時間為(34.85±0.47)h,對照組為(45.21±0.50)h,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撳針耳穴治療手術后呃逆起效和治愈時間方面均優于對照藥物組,見表2。
表2 兩組止呃起效時間、治愈時間比較 (±s,h)
組別 例數 起效時間 治愈時間試驗組 30 3.36±0.22 34.85±0.47對照組 30 4.65±0.31 45.21±0.50 t 18.580 82.690 P 0.001 0.001
2.3 兩組呃逆癥狀積分比較
試驗組治療前呃逆積分為(8.20±0.24)分,對照組治療前呃逆積分為(8.31±0.32)分,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試驗組呃逆積分為(3.72±0.33)分,對照組為(4.50±0.28)分,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撳針耳穴治療手術后呃逆在減少發生頻率方面優于對照藥物組,見表3。
表3 兩組呃逆癥狀積分比較 (±s,分)

表3 兩組呃逆癥狀積分比較 (±s,分)
組別 例數 治療前 治療后試驗組 30 8.20±0.24 3.72±0.33對照組 30 8.31±0.32 4.50±0.28 t 1.510 10.120 P 0.130 0.001
2.4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試驗組顯效20 例,占66.67%;有效6 例,占20.00%;無效4 例,占13.34%;對照組顯效15 例,占50.00%;有效4 例,13.34%;無效11 例,占36.67%,采用非參數檢驗,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撳針耳穴治療手術后呃逆臨床療效優于對照藥物組,見表4。

表4 兩組臨床療效比較 [n(%)]
3 討論
呃逆是由于膈肌和相關肌肉群突發不自主的痙攣性收縮所引起。本病為神經反射活動,受到延髓呼吸中樞的控制,其反射弧向心路徑為膈神經、迷走神經及第6~12 胸交感神經向心纖維,中樞為第3~5 頸髓膈神經、呼吸中樞、延髓網狀結構與下視丘間互相作用。手術后引發呃逆的原因較為復雜,既有中樞因素,也有周圍神經因素[7]。但是不論哪種因素,盡快采取有效的護理干預措施消除呃逆是臨床護理最為關鍵的步驟。否則頑固性呃逆長期存在會嚴重影響患者的預后和生活質量[8]。呃逆往往會加重患者的傷口疼痛,影響患者休息,使其情緒不穩定,不利于患者的康復。護理人員要密切觀察病情變化,積極查找呃逆發生原因,進行對癥處理[9]。
臨床針對手術后頑固性呃逆治療的方法較多,包括行為干預、神經阻滯療法、體外膈肌起搏器治療、西藥治療等[10]。最常用的還是藥物治療,目前主流的有利他林、加巴噴丁、利多卡因等,但是長期服用會有副作用。加巴噴丁耐受性雖然好,但是易發生不良反應,包括嗜睡、眩暈、行走不穩、疲勞感等。因此要尋找更為安全有效的干預措施積極治療手術后呃逆。
中醫學認為,術后呃逆的關鍵病機在于胃失和降,胃氣上逆,治療應以調理氣血、和胃降逆為主[11]。本研究納入的受試者,往往全身屬虛,局部屬實,病機虛實夾雜。實者大多由于手術損傷胃絡,致胃氣上逆,氣機升降失調,氣血瘀滯所導致;虛者則由于術后或腫瘤所致正氣虧虛,耗傷胃陰,損傷中氣,致胃失和降,胃氣上逆動膈所引發。針刺是中醫治療術后呃逆的重要手段。撳針也稱為埋針法,是皮部理論和腧穴理論相結合的具體運用,通過神經末梢的傳導,可產生持續而穩定的刺激,促進經絡氣血有序運行,激發人體正氣,起到行氣活血、通經活絡的作用[12]。通過耳穴貼壓可以起到調節臟腑功能、疏通經絡、調和陰陽的作用,且作用持久緩和,操作簡單,是治療術后呃逆的有效方法。本研究所選耳穴耳中,又稱膈,迷走神經點,可以解痙降逆,止呃止嘔,是治療呃逆的主要耳穴;胃能和胃降逆;神門能安定心神;交感可以抑制膈肌興奮;皮質下能抑制大腦皮層興奮,均可起到抑制呃逆的作用[13-15]。
本研究結果顯示,治療后試驗組臨床療效優于對照組(P<0.05),呃逆程度輕于對照組(P<0.05),止呃起效時間短于對照組(P<0.05),說明撳針耳穴用于手術后呃逆,可以有效減輕患者的呃逆程度,且起效快。當然本研究的樣本量有限,且投入人力資源有限,在今后的研究中,將納入更多樣本,針對中醫自身特點,在證候分型、整體觀念,給予更加個體化的治療方案,以促進更為高質量研究的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