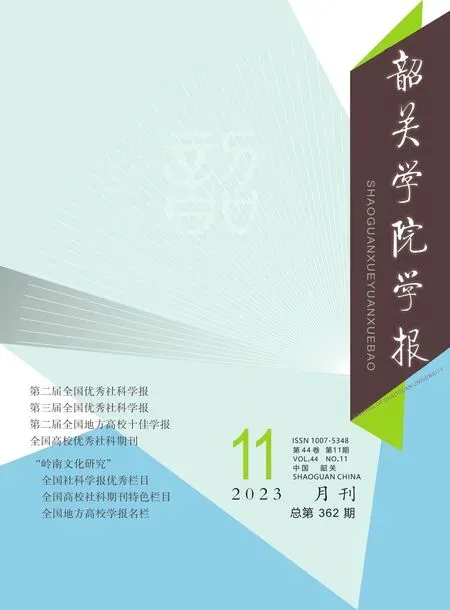中國傳統內觀療法對大學生生活滿意度和生命意義感的干預效果研究
蔡瑤瑤,占丹玲
(韶關學院 心理健康教育學院,廣東 韶關 512005)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以為當代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優質資源。2018 年8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不僅是我們中國人思想和精神的內核,對解決人類問題也有重要價值”。因此,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角度探討大學生面臨的思想、心理與行為問題,增強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認同與傳承意識,引導其踐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蘊含的提升“心性修養”的理念與方法,對于促進大學生心理健康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黃熹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本質是關于“心”的文化[1]。內觀正念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提升“心性修養”的方法,是一種遠早于西方心理干預方法的重要實操方法。
內觀又稱內省或覺察[2],是個體對自己正在進行的心理過程進行有目的的觀察。內觀時個體將意識重新指向自己的軀體和內心世界,有助于觀察自己的本心本性。內觀和正念關系密切,是個體進行正念練習的重要步驟[3]。正念是指個體以有意識的、不加評判的方式,將注意力集中在當下所獲得的心理體驗[4]。中國傳統的儒釋道等文化中蘊藏著豐富的內觀正念的智慧。“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儒家的人生理想。關于修身養性,儒家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盡心知性知天”與“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等理念,充滿了深刻的內觀智慧。佛教認為眾生皆苦,通過正定、正念等修煉方法,可以擺脫一切煩惱,正定與正念是與內觀最為接近的方法。道家認為修行應效法自然,無為而無不為,其修行方法中的“心齋”與“坐忘”蘊含了豐富的內觀智慧。國內外眾多研究表明,內觀正念可以提升個體的自我覺察水平,促進對自己的心理和行為反思,有助于糾正個體的不良認知觀念與行為,降低負性情緒的發生頻率,改善自己的心理健康狀態[5-7]。
生命意義感是“個體對自身存在的意義和自我重要性的感知”,它維護著個體的身心健康。其本質上是一種主觀體驗,和情緒關系密切[8]。生命意義感充足的個體則會有更高的生活滿意度等積極心理[9]。研究發現,正念可以通過生命意義感影響個體的身心健康[10-11]。這種影響符合正念的情緒調節模型[12]。也即正念可以通過不評判的方式減少負性情緒,增強情緒調節能力,增加積極情緒,間接提升個體的生命意義感,增加其生活滿意度。
國內雖然內觀正念資源豐富,但較為成熟的心理干預方法卻較少。廣州中醫藥大學邱鴻鐘教授基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觀”理念[13]與“內觀認知療法”整合創新出了中國傳統內觀療法[14]。該方法以內觀正念為核心,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儒釋道諸子百家中所包含的“心學”思想為基礎,通過內觀正念知識傳授、意念的止觀練習、內觀正念身體掃描練習等方式,引導個體認識外界事物與自身想法的本質,從而摒棄執念、重建認知、抱樸守真、回歸本心,進而保持良好的身心狀態。李學盈應用該方法對40 名大學生的焦慮狀態進行干預,初步驗證了其在緩解個體焦慮方面的有效性[14]。該方法的有效性和正念的情緒調節模型的內在是一致的。
綜上,本研究擬采用隨機對照前后測實驗設計,并以內觀正念、生命意義感、生活滿意度為心理健康的參考指標,驗證中國傳統內觀療法對大學生心理健康的提升效果。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設:(1)中國傳統內觀療法可以提升個體生活滿意度和生命意義感水平;(2)相對于控制組,實驗組后測的正念水平、生命意義感、生活滿意度顯著提升;(3)中國傳統內觀療法對于個體生活滿意度的改善是通過提升內觀正念水平,增強生命意義感實現的。
一、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2022 年11 月至2023 年7 月,調研組采用網絡報名與隨機抽樣的方法,在韶關學院選拔70 名無正念或冥想經歷的學生作為實驗組。采用單盲方式選拔控制組,并在8 周后對其進行追蹤調查。實驗組與控制組男女各35 人,且不存在宿舍關聯。實驗組被試分布如下:大一20 人,大二25 人,大三25 人;文科生30 人,理科生20 人,醫學生10 人,藝術類10 人;控制組被試分布如下:大一20 人,大二35 人,大三15 人;文科生25 人,理科生20人,醫學生18 人,藝術生7 人。
(二)研究工具
1.三因素內觀正念水平量表[14]。該量表由內觀正念訓練方案提出者邱鴻鐘編制,共20 題,采用Likert 1~5 級(“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計分,共包括3 個維度:內觀、正念、放下。代表題目如“我總是反省自己言行的對錯”。總分越高,表明內觀正念水平越高。本次研究中前測內觀、正念、放下維度與總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61、0.74、0.73、0.74,后測分別為0.69、0.71、0.68、0.68。
2.生命意義感問卷[15]。本問卷由Steger 等人編制,王孟成等人修訂,共10 題,采用Likert 1~7級(“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計分,包括意義體驗、意義尋求兩個維度。代表題目如“我總是在尋找自己人生的目標”。分數越高則表明生命意義感越強。本次研究中前測意義體驗維度、意義追尋維度與總問卷的內部一致性系數分別為0.88、0.84、0.86,后測分別為0.87、0.90、0.87。
3.生活滿意度量表[16]。本量表由Pavot 等人編制,共5 題,采用Likert 1~7 級(“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計分。代表題目如“我的生活大致符合我的理想”。分數越高則表示對當前生活越滿意。本次研究中前后測內部一致性系數均為0.90。
(三)干預流程
采用隨機對照前后測實驗設計,自變量為是否接受內觀正念干預,分為實驗組和控制組。因變量為內觀正念水平、生命意義感、生活滿意度的問卷得分。內觀訓練一般采用集中訓練與分散訓練相結合的方式進行。由于分散訓練已被證明有效[17],故實驗組以分散訓練為主(不低于6 周,每周3 次),集中訓練為輔(兩周,共2 次)。
實驗組成員訓練前通過參加內觀正念知識宣傳與講座,基本理解了中國傳統內觀療法的原理、內涵與實操方法。正式訓練共持續8 周,第1 和第4周為集中訓練與反饋,其余時間為分散訓練。集中訓練場地位于校內團體心理輔導室,每次持續時間90~120 分鐘。第1 次(訓練第一周,90 分鐘)訓練內容詳細介紹中國傳統內觀療法涉及的關鍵術語與操作方法,第2 次(訓練第四周)訓練內容為干預方案中的止觀練習音頻內容(不含30 分鐘的訓練情況反饋檢查)。分散訓練地點為參與者宿舍,訓練材料為干預方案中的訓練音頻,每周不低于3 次,每次不少于30 分鐘。為減少干擾,集中訓練與分散訓練均在晚上進行。本研究中的訓練指導老師為具有10 年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經驗的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且接受過中國傳統內觀訓練療法培訓。
實驗組70 人分別于2022 年11 月(20 人)、2023 年3 月(30 人)以及2023 年6 月(20 人)進行前測并開始練習;控制組70 人于2023 年3 月進行前測并開始觀察,間隔8 周后收集后測數據。訓練指導老師在第4 周訓練時對參與情況進行線下追蹤,以此評估訓練者的訓練狀態是否存在偏差,其他時間為線上追蹤。追蹤過程中,實驗組因無法堅持訓練、無法進入內觀狀態等原因流失18 人(三個批次分別為7 人、5 人、6 人),有效數據52 人;控制組流失6 人,有效數據64 人。
(四)干預方案
使用邱鴻鐘教授開發的《內觀正念訓練》方案,方案包括錄制好的音頻與電子文本,共分為5部分,分別為基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觀正念介紹、內觀正念操作要領、意念的止與觀、內觀正念身體掃描、內觀正念練習的根本法則。根據團體設置與心智技能學習的階段,制定訓練方案,每個單元用1 周完成練習,訓練方案見表1。

表1 訓練方案
(五)統計方法
使用SPSS 23.0 進行數據分析,采用獨立樣本t 檢驗比較兩組前測差異,采用配對樣本t 檢驗比較組內前后差異,采用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探究內觀正念訓練對大學生內觀正念水平、生活滿意度、生命意義感的影響,采用SPSS PROCESS 的宏程序的模型6 進行鏈式中介效應檢驗,以P<0.05 為存在統計學差異。
二、結果
(一)干預前實驗組與控制組內觀正念水平、生活滿意度、生命意義感比較
由于實驗組與控制組前測數據收集時間存在差異,我們首先對各組前測數據進行檢驗,確保不同組別數據在前測同質。結果顯示,干預前實驗組與控制組在內觀正念各維度(內觀、正念、放下)與總分的獨立樣本t檢驗值分別為-1.11,-0.58,-1.80,-1.67,P>0.05;生活滿意度t值為-0.47,P>0.05;生命意義感各維度(意義體驗、意義追尋)及總分t值分別為-0.94,1.62,0.23,P>0.05。數據表明,前測中兩組成員各項心理狀態數據均無統計學差異,即干預前實驗組與控制組組間同質。
(二)干預后實驗組控制組內觀正念水平、生活滿意度、生命意義感比較
內觀正念訓練干預后,實驗組心理狀態均有改善。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除生命意義感的意義追尋維度不存在顯著差異外,內觀正念水平、生活滿意度、生命意義感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控制組內觀正念水平、生活滿意度、生命意義感前后均無統計學差異,詳見表2。
表2 實驗組控制組前后測得分及配對樣本t 檢驗結果(±s)

表2 實驗組控制組前后測得分及配對樣本t 檢驗結果(±s)
組別 時間 人數 統計值內觀正念生活滿意度生命意義感內觀正念放下總分意義體驗 意義追尋總分實驗組后測 5218.50±1.98 27.60±2.98 24.21±3.24 70.31±5.59 21.69±5.96 24.42±5.05 28.02±3.91 52.44±7.06前測 5217.58±2.03 26.52±3.25 22.62±2.87 66.71±5.63 18.37±6.77 22.29±5.43 27.06±4.39 49.35±7.49 t3.402.783.846.274.182.941.803.72 P0.0010.008<0.001<0.001<0.0010.0050.078<0.001

續表2
分別以內觀正念水平、生活滿意度、生命意義感總體情況作為因變量,時間(前后測)為被試內因素,組別(實驗組與控制組)為被試間因素,進行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由于本次樣本大于50,故采用K-S 進行正態性檢驗。經檢驗可知,不同組別前后測數據服從正態分布,P>0.05。內觀正念總體水平上,時間的主效應顯著(F=23.91,P<0.001,偏η2=0.17),時間×組別的交互作用顯著(F=38.32,P<0.001,偏η2=0.25);簡單效應分析顯示,前測組別差異不顯著(F=2.80,P=0.10,偏η2=0.02),后測組別差異應顯著(F=7.29,P=0.008,偏η2=0.06),實驗組后測水平顯著高于控制組;實驗組前后測差異顯著(F=55.63,P<0.001,偏η2=0.33),后測水平顯著高于前測,控制組前后測差異不顯著(F=0.94,P=0.33,偏η2=0.01)。生命意義感總體水平上,時間的主效應顯著(F=88.23,P=0.004,偏η2=0.07),時間×組別的交互作用不顯著(F=2.59,P=0.111,偏η2=0.02);生活滿意度總體水平上,時間的主效應顯著(F=18.09,P<0.001,偏η2=0.14),時間×組別的交互作用顯著(F=4.62,P=0.034,偏η2=0.04);簡單效應分析顯示;前后測組別的差異均不顯著(前測F=0.22,P=0.64,偏η2=0.01;后測F=2.17,P=0.14,偏η2=0.02);實驗組前后測差異顯著(F=18.57,P<0.001,偏η2=0.14),后測水平顯著高于前測,控制組前后測差異不顯著(F=2.47,P=0.12,偏η2=0.02)。
(三)內觀正念訓練的中介效應分析
根據正念的情緒調節模型可知,內觀正念訓練可以提升個體的內觀正念水平,增加積極情緒,增強生命意義感,實現對個體心理健康的干預。基于此,根據研究假設,為進一步探索內觀正念訓練對大學生內觀正念水平、生活滿意度、生命意義感的影響,將實驗組與控制組后測的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后,以是否接受內觀正念干預作為自變量(虛擬變量,控制組=0,實驗組=1),以生活滿意度作為因變量,以內觀正念與生命意義感作為中介變量,在控制性別、年級等人口學變量后構建“訓練組別→內觀正念→生命意義感→生活滿意度”的中介效應模型,采用Hayes 的SPSS PROCESS 宏程序中的模型6 進行鏈式中介效應分析,樣本量選擇5 000,置信區間為95%。詳見表3。

表3 間接效應分析(以控制組為參照)
根據表3 可知,以控制組為參照,實驗組后測的間接路徑“訓練分組→內觀正念→生命意義感→生活滿意度”的95% CI為(0.001~0.189)不包括0,也即內觀正念和生命意義感的間接效應顯著,其他間接路徑不顯著。實驗表明,內觀正念訓練對實驗組大學生生活滿意度的改善是通過提升內觀正念水平、增強生命意義感這一方式實現的。
三、討論
(一)內觀正念訓練的干預效果
本研究采用隨機對照前后測實驗設計的方法,將大學生分為實驗組與控制組,以基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觀正念訓練為基礎,對實驗組進行為期8 周的心理訓練,控制組不做干預。結果顯示,實驗組大學生在進行內觀正念訓練后內觀正念水平、生命意義感(不含意義追尋)、生活滿意度均得到了明顯提高,控制組則無顯著變化。這說明基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觀正念訓練與其他內觀或正念訓練一樣可以達到對于個體心理健康的干預。該結果也和前人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18-20],內觀正念訓練可以提升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內觀正念訓練對于個體心理的干預效果可以從正念的情緒調節模型[12]來解釋。人既有生物性,也有社會性。這決定了個體在現實生活中會經歷欲望無法被滿足、期待落空進而產生各種心理的煩惱與痛苦的情緒。內觀正念訓練將個體的關注點轉向內心世界,通過“不評判與接納”的態度覺察自己的非理性認知(執念),減小負性情緒的發生頻率,促進積極情緒的產生,這可以間接提升個體的生命意義感。同時,積極的體驗與生活滿意度在內在存在共性,因而個體可以覺察到生活滿意度的提升。另外,內觀正念訓練的效果也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靜能生慧”“放下我執方得自在”的修身理念與效果。
本研究發現內觀正念訓練對于生命意義感的干預效果僅在意義體驗維度與生命意義感總分有所體現,在意義追尋維度并不存在。我們內觀正念訓練無法提升個體意義追尋的這一結果和該方法的局限有關。人的心理活動可以從知、情、意三方面來理解。內觀正念訓練改變了個體不良的認知方式(知),削弱了消極情緒,增強了積極情緒(情),提升作為感受的意義體驗的水平,因此對意義體驗的干預有效。但是,意義追尋強調個體對自己認為有價值或意義目標的追尋(行)[4],涉及更深層次的價值取向問題與動機激發問題,且內外影響因素眾多,因此單一的方法較難在短期實現。
(二)中介效應分析
中介效應分析發現,實驗組生活滿意度的提升是通過內觀正念水平提升,增加個體的生命意義感這一間接路徑實現的,這與前人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10],且與內觀認知理論、正念的情緒調節模型與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吻合。張軍良等人的研究顯示,正念可以通過提升個體的生命意義感間接實現對個體心理健康的干預。內觀認知療法認為內觀可以減少個體心理問題帶來的負面體驗,增加自信水平,帶來更多積極體驗,間接提升了個體的生命意義感,因而可以實現對個體心理健康水平的干預[6]。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需求不滿足會導致個體的心理問題。內觀訓練通過調整注意力方向、引導個體察覺自己的內在體驗,可以讓個體體會到更多的歸屬與愛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被滿足。而被滿足的需要會帶來個體的生命意義感,成為個體心理健康的促進因素[21]。
四、研究局限
本研究中實驗組與控制組抽樣時間與批次存在差異,且未能詳細統計實驗組累計的訓練時長,這些額外變量可能會對結果造成一定影響并導致結果推廣受限。另外,本研究使用的中國傳統內觀療法,訓練方案中關鍵術語是通過對儒釋道的典籍解讀展開。但部分解讀為了強調知識的共性,使用了現代心理學的解釋,這可能導致練習時按照自己方便理解的規則執行,客觀上可能造成訓練過程中操作標準的不一致,導致訓練結果受到部分額外的影響。最后,中介效應分析部分,雖有內觀正念理論作為基礎支撐,但被試量相對較少,結果的參考性受限;后續應該加大被試量,進行更多的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