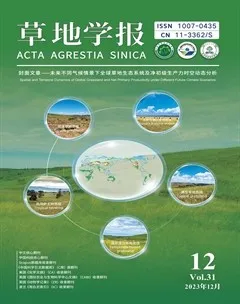基于InVEST與FLUS模型的準格爾旗水源涵養功能分析
劉 濤,張雪梅,林長存
(北京林業大學草業與草原學院,北京林業大學中國草原研究中心,北京林業大學草地資源與生態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水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資源,其來源是大氣降水、地表水和地下土壤水。在我國,由于地形改變、土壤結構破壞及植被破壞等多種原因,大量的水不能進入生物地球化學循環,而是形成地表徑流裹挾大量泥沙流入河道,造成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災害[1]。水源涵養功能是指通過林冠層、枯落物層、土壤層阻擋蓄積雨水,達到涵養水土[2]、調節河流水量的目的[3]。同時,水作為自然界最主要的物質載體,對生態系統的其他功能,如生產力,營養元素循環等,都有很大的影響。近年來,在全球變暖背景下,世界水循環速度加快,區域水資源涵養能力下降,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已成為眾多國家高度重視的問題[4]。2020年2月,國家基于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的目標下達了內蒙古黃河生態保護的要求,準格爾旗地區為此大力推動生態環境的治理,修復了大面積的廢棄礦山與土地,為準格爾旗進一步的生態修復和治理奠定了基礎。已有研究探討了準格爾旗的生態發展情景[5-6],但是對準格爾旗的水源涵養及功能提升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的探索。
目前,人們利用多種模型對區域生態系統的水源涵養功能進行定量、可視化、精細化的研究和評價,如MIKE SHE模型、TOPMODEL模型、SWAT模型、InVEST模型等[7]。InVEST模型具有參數調整靈活、評估結果具有較好的空間表達能力,并可實現時空間與多目標的折衷[8]。該模型是斯坦福大學、自然保育學會、WWF等國際知名科研單位聯合開發的,其目的在于平衡開發與保護的關系,并將其應用于對多個生態系統服務的定量評價[9]。InVEST模型的水源涵養模塊是根據水資源均衡的原則,充分考慮了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的滲透率和地形、地表粗糙程度等因素的影響,通過網格作為單位,對不同地形類型的水源供應進行了量化。該模型以地理信息系統為基礎,通過圖形化的方式,實現了對生態系統的定量化,避免了繁瑣的計算公式和冗長的文字描述,并對許多復雜問題進行了優化[10],現已在北京山區[11]、黃土高原[12]、三江源[13]以及白龍江[7]等地的生態環境評價和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InVEST模型的水源涵養模塊中土地利用變化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制約因素,針對土地利用變化的評估也是近些年研究的熱點,德國在19世紀初期就開始了以城市規劃和可持續發展為目標的土地利用研究[14]。土地是生態系統服務基礎,土地利用類型、方式影響著區域生態環境的變化、生態系統的穩定[15]。對于大范圍土地利用變化的仿真,目前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粗分辨產物[16]。例如,IMAGE模型[17]、LUSs模型[18]、CLUMondo模型[19]、FLUS模型等。其中IMAGE模型、LUSs模型、CLUMondo模型還沒有完全投入使用,有的甚至是不完整的,因而不能很好的評價土地利用的變化和對生態的影響。而FLUS模式則是將人與自然因素結合起來,可以將“自上而下”的系統動態與“自下而上”元胞自動機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了未來大規模土地使用變化的精細模擬[20]。劉曉娟等[21]以FLUS-InVEST模式為基礎,對中國2100年來的土地使用狀況進行了數值模擬,研究了陸上生態系統的碳儲量及其空間分異。朱志強等[22]利用FLUS-InVEST耦合模型對廣州市1990-2018年度的土地、碳儲量的空間和空間變化進行了研究,并對其發展趨勢進行了預測。
本研究利用FLUS模型對準格爾旗2000-2020年土地利用變化的歷史和現狀進行研究,進而對2040年自然發展、城市發展與生態保護三種情景下的土地利用狀況的空間格局進行模擬,在此基礎上運用InVEST模型預測2040年三種情景下準格爾旗的水源涵養能力的時空動態變化,通過對準格爾旗水源涵養功能的空間分布特征及影響因素的研究,分析研究區水源涵養功能對不同發展模式的響應規律,結果能夠為準格爾旗的生態修復和環境治理提供相關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數據來源
1.1.1準格爾旗范圍 依據相關文獻,主要使用DEM數據(空間分辨率為30 m)提取準格爾旗區域的范圍。DEM數據和下述相關遙感影像數據均來源于地理空間數據云。本文用到的準格爾旗地圖數據從自然資源部標準地圖服務網站(http://bzdt.ch.mnr.gov.cn)下載的審圖號為蒙S(2017)029號的標準地圖作為分析底圖。
1.1.2土地利用類型的分類與檢驗 使用2000年和 2020年的ASTER GDEM遙感影像為主要數據源在Arcgis軟件中,對影像進行幾何校正、影像融合和影像裁剪等預處理,采用目視解譯法與監督分類法相結合的方法提取土地利用類型。數據來源于地理空間數據云。
1.1.3降水量數據 利用國家青藏高原科學數據中心收集周邊氣象站 1990-2020年的降水量數據。用Arcgis得到降水量的空間柵格數據。
1.1.4年潛在蒸散量 基于氣象數據的潛在蒸、散發量采用哈格里夫斯修正方程計算,所需數據來源于國家青藏高原科學數據中心(http://data. tpdc. ac. cn)。
1.1.5根系深度數據 使用2000年和2020年根系深度數據,根系深度數據根據中國科學院內蒙古草原生態系統定位研究站測定的準格爾旗土壤剖面數據獲得的。
1.1.6植被可利用水分 使用2000年與2000年植被可利用水分,數據來源于世界土壤數據庫。
1.1.7流速系數 流速系數根據各期土地利用/覆被情況結合模型參數表獲取。
1.2 研究區概況
準格爾旗地處山西,陜西,內蒙古三省區交界之地,位于鄂爾多斯高原的最東端,國土面積7 692 km2,該地區的地貌類型主要為黃河沖積平原、沙漠、丘陵溝壑、黃土丘陵等,該地區遠離海洋,大陸性氣候突出,屬于典型的半干旱地區,年平均氣溫為6.2℃~8.7℃,降水少而集中,年降水量300 mm左右,多集中在7-9月。在中溫帶大陸性氣候的作用下,冬季漫長而寒冷,春季氣溫起伏變化較大,多風少雨,夏季炎熱短暫、雨水集中,易發生局地性短時強降水、冰雹、大風等強對流天氣,并誘發洪澇災害。這里的植被以沙生植被和退化的草地為主。

圖1 準格爾旗位置圖Fig.1 Location map of Junggar Banner
1.3 研究方法
1.3.1FLUS模型 FLUS模型是用于模擬人類活動與自然影響下的土地利用變化以及未來土地利用情景的模型。本實驗采用隨機采樣策略提取2000年數據的10%作為訓練樣本,設置訓練隱藏層數為10,通過歸一化驅動因子,利用神經網絡算法計算得出2020年準格爾旗土地利用類型適宜性概率圖層。同時,設定模型的鄰域影響因子和轉換成本,鄰域影響因子用以反映不同用地類型之間以及鄰域范圍內不同用地單元間的相互作用,轉換成本表示當前用地類型轉換為需求類型的困難度。鄰域影響因子的計算需要設定鄰域因子參數,其范圍為0~1,數值越大表示該用地類型的擴張能力越強。借鑒已有鄰域權重參數成果,結合準格爾旗土地利用現狀,設置鄰域因子參數(表1),生成2020年準格爾旗土地利用模擬結果,并使用“Precision Validition”模塊對土地利用模擬結果進行精度檢驗.同理,生成2040年土地利用模擬結果。

表1 領域因子參數Table 1 Neighborhood factor parameters
1.3.2多情景設定 影響城市發展和用地變化的因素很多,在對土地利用變化進行模擬時,必須綜合考慮各種環境因素。依據準格爾旗歷史年份土地利用變化特征及其未來區域空間發展規劃,本文分別設置自然發展情景、城市發展情景、生態保護情景三種情景模式對準格爾旗2040年土地利用變化情況進行預測(表2)。

表2 未來土地利用變化情景模式及原則Table 2 Future land use change scenarios,patterns and principles
1.3.3轉換成本矩陣 轉換成本矩陣表征由當前地類轉換為需求地類的難度。轉換成本矩陣中只存在兩個值0和1,本文需對應不同情景設定3個轉換成本矩陣(表3)。

表3 研究區土地利用轉移成本矩陣Table 3 Land use transfer cost matrix in the study area
1.3.4InVEST模型 InVEST模型主要包含陸地生態系統服務評估、海洋系統和淡水系統三大模塊,本文主要應用其中的陸地系統相關模塊,利用其中的水源涵養模塊對準格爾旗的生態系統進行定量評估,可視化顯示結果。
(1)產水量
InVEST模型產水模塊基于水量平衡原理,通過各柵格單元的降水量、蒸發量、土壤深度、土壤質地和植被根系深度等參數估算產水量。具體公式為:
式中:Y(x)為柵格單元x上土地利用類型的年產水深度(mm);AET(x)為柵格單元x上土地利用類型的單位面積年實際蒸發量(mm);P(x)為柵格單元x上土地利用類型的單位面積年降水量(mm),ω為氣候土壤非物理參數。
(2)水源涵養計算
基于InVEST模型產水模塊計算結果,綜合考慮不同土地利用/覆被類型的土壤滲透性、地形差異等對地表徑流的影響,利用地形指數、土壤基礎數據計算得到各單元水源涵養量及深度,能夠較好地表達流域水源涵養量的空間分布狀況及影響水源涵養量的主要因素。

式中:WC為水源涵養深度,mm;V為流速系數,無量綱;D為地形指數,無量綱;K為土壤飽和導水率,cm·d-1; DA為流域匯水量,mm;SD為土層厚度,mm; PS為百分比坡度,無量綱。
2 結果與分析
2.1 土地利用模擬預測
利用2000年和2020年兩期土地利用數據,模擬2040年土地利用分布格局,選取了高程、坡度、坡向、降水、到城鎮中心的距離、到鐵路的距離等6個因素。三種情景下所得出模擬數據與真實2020年數據在10%隨機采樣模式中,計算出Kappa系數分別為0.87,0.88和0.83,均大于 0.80,說明FLUS模式能夠很好地模擬研究區的土地演替過程,其所設定的參數與研究區的土地利用狀況相一致,可以很好地預測2040年的土地利用變化(圖2、圖3)。

圖2 2000年和2020年土地利用現狀圖Fig.2 Land use status map in 2000 and 2020注:a為2020年,b為2020年Note:a was landuse in 2020,b was landuse in 2020

圖3 三種情景模擬下2040年準格爾旗土地利用預測圖Fig.3 The land use prediction map of Junggar Banner in 2040 under three scenarios simulation注:a為自然發展情景;b為城市發展情景;c為生態保護情景Note:a was the ordinary development scenario,b the urban development scenario,c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scenario

圖4 2000年和2020年準格爾旗水源涵養量空間分布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ater source conservation in Zhungeer Banner in 2000 and 2020

圖5 2040年三種情景下準格爾旗水源涵養量空間分布Fig.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ater source conservation in Junggar Banner under three scenarios in 2040注:a為自然發展情景;b為城市發展情景;c為生態保護情景Note:a was the ordinary development scenario,b the urban development scenario,c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scenario
2.2 土地利用類型時空演變
根據上述得出的2040年準格爾旗土地利用結果,對準格爾旗2000-2040年的土地利用面積進行統計,可得出自然發展、城市發展與生態保護三種情景下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筑用地以及未利用地的面積變化(表4)。自然發展情景的結果表明,準格爾旗的建筑用地逐年上升,其用地面積占比由1.7%快速增長至7.4%,耕地面積小幅度增加,林地、水域的面積相對保持穩定,草地、未利用土地的面積都在不同程度上減少。在2000-2020 年期間,城鄉、工礦、居民用地面積有較明顯增加且分布在北部地區。

表4 三種情景下準格爾旗土地利用類型面積變化Table 4 Changes of area of each land use types in Junggar Banner under three scenarios
城市發展情景下,整體趨勢與自然增長態勢類似,城鄉、工礦、居民用地有了大幅度提升,由最開始的1.7%增長到9.2%,中心城區較為明顯,此處的城鄉、工礦、居民用地擴張與人口擴散趨勢保持一致,而草地、林地、耕地面積都相對有所減少。
生態保護情景是未來土地利用變化的理想情景,該情景假設準格爾旗已步入中高速、高質量的發展時期,城鎮擴展速率減緩導致土地使用效率的提升。《準格爾旗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0-2035年)》提出,要嚴格執行耕地與永久基本農田的保護,并將耕地面積反饋調整機制納入協調發展情景,以保持研究區的耕地面積高于基準水平,而從預測結果中可以看出林地、耕地、草地面積減少態勢得到有效遏制,很好的實現了上述目標。
從2000年到2020年以及三種情景模擬下的土地利用變化中可以看出,在過去的20多年以及未來發展的過程中,準格爾經濟開發區土地變化十分顯著,由2000年的未利用土地占據大多數演變為2020年的耕地,城市、居民用地居多,到2040年在城市發展以及自然發展情景下城市、居民、工礦用地已經基本占據該開發區全部的用地面積。在準格爾經濟開發區,有很多以產業發展帶動城市建設,以城市建設支撐產業發展的企業。該預測結果更好的說明了經濟發展對于土地利用變化的影響也為今后準格爾旗建設新的經濟開發區提供一個很好的理論支撐。
2.3 準格爾旗水源涵養模擬
考慮到數據可獲取性,本研究以2000年為代表,選取準格爾旗的年徑流量,來調試和驗證模型,準格爾旗年徑流量為2.04×108m3,通過模型反復模擬計算水源涵養量,得出Z系數為15時,準格爾旗2000年水源涵養量為1.90×108m3,相比誤差為6.86%,可見模型模擬結果具有良好的健壯性。
就InVEST水源涵養量模型模擬的2000年和2020年準格爾旗水源涵養量空間分布來看,準格爾旗在全局范圍內的水源涵養量表現為“東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基本分布模式,結合區域地形地貌特征來看,高水源涵養量區域主要分布在海拔相對較低的區域,而地勢較為平緩的區域水源涵養量相對較高(圖3)。結合研究區各用地類型空間分布來看,耕地、林地、草地用地類型具有相對較高的水源涵養量,而水域、建設用地分布區域水源涵養量總體較少(圖2)。在數量變化方面,準格爾旗2000年的水源涵養量為1.90×108m3,2020年的水源涵養量為3.16×108m3,相比2000年增加了1.26×108m3。根據各用地類型的水源涵養量及其變化的比較,草地具有最大的水源涵養總量,并且草地水源涵養量變化顯著,水源涵養量增加了0.70×108m3(表5)。

表5 2000,2020和2040年不同土地利用類型水源涵養量Table 5 Water conservation capacity of different land use types in 2000,2020 and 2040
2.4 水源涵養對不同土地利用情景的響應
根據2020和2040年準格爾旗土地利用與水源涵養的變化情況看出,自然發展情景下,水源涵養量較2020年增加了0.05×108m3,耕地、林地、居民用地的水源涵養量均有一定程度的增加,草地、未利用地的水源涵養量下降了(表4,表5)。20年間面積增加幅度最大的城鄉、居民用地類型水源涵養量對應增加了0.06×108m3,面積下降幅度最大的草地用地類型水源涵養量減少0.05×108m3。
城市發展情景下,水源涵養量較2020年減少了0.18×108m3,城鄉、居民用地水源涵養量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耕地、林地、草地的水源涵養量均下降了。水源涵養量增加最多的是城鄉用地,增加了0.08×108m3,增加幅度是36%,水源涵養量減少最多是草地,減少量為0.39×108m3,減少幅度為22%。
生態保護情景下,水源涵養量較2020年增加了0.21×108m3,耕地、林地、草地的水源涵養量均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城鄉、居民用地的水源涵養量下降了。水源涵養量增加最多的是耕地,增加了0.06×108m3,增加幅度是11%,水源涵養量減少最多是城鄉、居民用地,減少量為0.04×108m3,減少幅度為25%。
綜上,自然發展與生態保護情景下水源涵養量較2020年均增加了,城市發展情景下水源涵養量降低了,根據各土地利用類型單位面積水源涵養能力的差異,其強度按照以下順序排列:草地>林地>耕地>水域>建設用地>未利用土地。對水源涵養影響強度最大的草地用地類型面積增加1 km2,水源涵養量增加0.7×104m3,對水源涵養影響強度最小的建設用地類型面積增加1 km2,水源涵養量相應只增加0.04×104m3。
3 討論
3.1 土地利用變化對水源涵養影響效應
土地利用變化主要是通過改變下墊面的類型和結構,對水源涵養過程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23]。它的作用方式主要體現在:改變土壤的質地和結構,通過對土壤孔隙度的影響,從而對水源涵養量產生影響[24]。其次,下墊面的類型和性質會對水源涵養過程產生影響,比如,下墊面的變化,會引起下墊面的變化,從而對下墊面的水分來源產生影響。再次土地利用變化還會對其它因素產生影響,進而對生態系統的水源涵養服務產生影響,比如說土地開發利用造成的生態系統退化[25]。根據土地利用變化對水源涵養的作用方式,可以看出,它是一個多途徑復合的過程。因此,生態系統水源涵養變化呈現出其多元復合性,它是包括土地利用變化在內的多種影響因子共同作用的結果[12]。不同類型的土地利用對水量有不同的影響。土地利用的變化首先會改變土壤條件、土壤侵蝕和生物多樣性,然后會改變下層地表,影響地表徑流。林地的產水量較低,因為森林植被較深的根系可以有效攔截降水,同時樹木具有很強的蒸騰作用。林地還可以通過林冠攔截降水,在枯落物層吸收降水,在土壤層滲透降水,從而減少地表徑流。因此,森林面積的增加會減少該地區的產水量。耕地和草地對降水的調節作用與森林相似。不過,由于植物密度和根深不同,耕地的調節作用要小于草地和森林。草地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截留部分降水,但這種作用比耕地弱。因此,草地的產水能力大于耕地。建筑用地通常覆蓋混凝土、瀝青和水泥,形成不透水層[26]。
本研究依據InVEST模型計算的準格爾旗2000年的水源涵養量為1.90×108m3,2020年的水源涵養量為3.16×108m3,增長幅度為66%,預測的三種發展模式下2040年水源涵養量與2020年相比,自然發展與生態保護發展情景下,水源涵養量分別增加了0.05×108m3和0.21×108m3,增加幅度分別為2%,7%,城市發展情景下,水源涵養量減少了0.18×108m3,減小幅度為6%,這主要與土地類型的轉變密切相關,對水源涵養影響強度最大的草地、林地、耕地所占比例呈增加趨勢因此水源涵養量也逐漸增加。潘韜等[8]在三江源流域開展的生態系統服務產水研究中發現,土地利用改變將引起地面反照率、局地水汽循環和地面徑流量的改變,并通過改變區域氣候,進而影響流域水源涵養。張福平等[4]在黑河流域上游的水源涵養研究中,發現地表覆蓋、土壤物理性質等會隨水熱條件的轉變而產生相應的變化,從而導致地表粗糙度、地表土壤環境的改變,從而對地區的實際蒸散和水源涵養量產生影響。準格爾旗的耕地面積由2000年的1 379 km2縮減到2000年的1 337 km2,2040年的1 331 km2,呈現出縮減的趨勢,耕地的產水量卻相應減加,表明耕地的縮減導致了耕地的產水層增加。森林面積由485 km2增至499 km2,森林的平均產水量增加,同理本研究結果表明,準格爾旗水源涵養量的變化與林地、草地、建設用地面積變化呈現出正比例關系,而與耕地、水域面積變化呈現出反比例關系,由此可以看出,水源涵養的變化隨著土地利用類型的變化而發生變化,這與趙亞茹等[27]的研究結論一致。本研究結果顯示,準格爾旗草地的水源涵養量比林地和耕地高,這是由于草原是準格爾旗土地利用的主體,2020年,草原面積占到了全域總面積的57.1%,分布在全旗的各個地區,盡管草原可以利用表層截留和枯落物層的吸收來對降水進行再分配,但是因為草原的廣泛分布,而且都集中在了降水量高值區,所以整個流域草原的平均產水深度很大,它在整個流域的產水總量中所起的作用也很大。
3.2 水源涵養對三種情景下土地類型變化分析
在自然發展情景模擬下,為了解決因人口增長而帶來的食物需求問題耕地面積有所擴大,在高速發展的同時,沒有注意到對水域的保護,造成了水域面積的減少。這與史名杰等[28]研究結果相似。在城市發展情景模擬中,城鄉和居民用地規模擴大顯著,這與準格爾旗城市建設策略和地區經濟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與許小亮等[29]揚州市研究區的研究結果略有不同,因為他們選擇的研究區和本研究研究區的地理特征和地區經濟地位存在較大差異,但是模型研究方法相似,可以作為互相驗證的基礎。生態保護情景模擬下,由于準格爾旗各級自然保護區、林草等自然資源管理部門、城市綠化部門等進行了長期的科學規劃,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相應的保護措施,使自然保護地的生態效果逐步顯現,實現了草地面積退化減緩,林地、水域土地類型的穩定。在這種情況下,受限制的保護地主要傾向于林地和草地,這與張麗芳等[30]對天山北坡景觀格局模擬的研究結果相一致。
本研究通過三種土地利用模擬情景預測得到的水源涵養量,自然發展與生態保護發展情景下水源涵養量增加了,城市發展情景下水源涵養量減少了。這一結果與王保盛等[31]的研究結果相似。他們所研究的閩三角城市群的水源涵養量結果表明閩三角城市群的耕地、林地、草地和其他用地類型的面積減小的同時水源涵養也在減小,建設用地、水域和灘涂類型的面積增大,水源涵養也在隨之增大。而郭洪偉等[32]的研究顯示,南四湖流域2000年后,流域內的城市化進程加速,城鎮建設用地明顯增多,從而引起了流域內的水源涵養量增加。而開展環湖生態保護,在湖區周邊建設 300 m林地緩沖區卻引起了流域水源涵養量的下降,這主要是因為,構建生態防護林,不僅能夠有效減少地表徑流,還能發揮出減少土壤侵蝕、攔截入湖泥沙的效果。
3.3 降水量及土地變化對水源涵養的影響變化分析
研究區降水量由東向西迅速遞減,并且平均產水深度相差巨大,這是由于研究區東部受中溫帶大陸性氣候影響,該區域降水量十分豐富,但氣流在自東向西途中受到高海拔山脈阻擋,研究區整個西部降水量很低,從而使得研究區降水量東部與西部形成鮮明對比;經驗證,蒸散發的年際變化很小,而 2000-2020 年研究區降水量呈整體上升趨勢,這與水源涵養量的整體趨勢相同,說明降水量是水源涵養量年際變化的影響因素。除降雨量外,土地利用類型的草地、林地對產水的作用較大,這也反映了雖然草地與林地與總體水的響應上中并不明顯,但由于子流域之間的相互作用起到了總體平衡的作用,總體上間接抵消了類型變化對產水變化的效應,這一結果與王保盛等[31]對閩三角產水量模擬研究結果相似。童瑞等[33]研究得出,黃河流域56.5%的區域蒸散發量呈減小趨勢,在降水顯著增加而實際蒸散發減少的情形下,水源涵養量必然呈增加趨勢。
4 結論
三種情景下FLUS模型的Kappa系數分別為0.87,0.88和0.83,均大于 0.80,說明FLUS模式能夠很好地模擬研究區的土地演替過程。InVEST水源涵養量模型模擬的2000年和2020年準格爾旗水源涵養量分別為1.90×108m3,3.16×108m3,而基于FLUS模型預測的三種情景下2040年準格爾旗土地利用變化再利用InVEST模型得出的水源涵養量,城市發展情景下水源涵養量最低為2.98×108m3,與2020年相比下降了5%,生態保護情景下水源涵養量最多為3.37×108m3,與2020年相比增加了7%。全局范圍內的水源涵養量總體表現為“東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基本分布模式。各土地利用類型單位面積水源涵養能力的強度為草地>林地>耕地>水域>建設用地>未利用土地,草地面積占全域總面積的一半以上,且集中在了降水量高值區,整個流域草原的水源涵養大,因此,草地的水源涵養量高于林地和耕地。對于未來的土地利用規劃和相關的土地利用和生態保護政策,InVEST模型與FLUS模型相結合,可以更好地實現流域生態系統的最優管理,其結果可為區域生態恢復、城市發展及生產實踐提供很好的理論與現實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