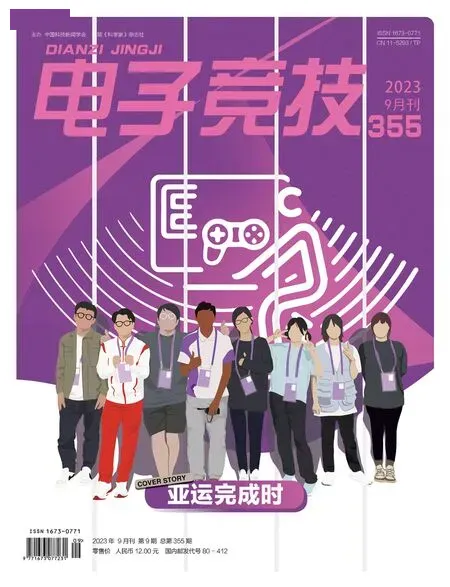公共舞臺上的個體魅力
文 楊 直

先說9 天賽期里我個人覺得最精彩的兩場比賽。第一場是9 月28 日晚上舉行的街頭霸王5:冠軍版本的決賽。44 歲的韓國運動員金管禹4:3 戰(zhàn)勝了44 歲的中國臺北運動員向玉麟獲得金牌。這場比賽讓我最感動的其實不是雙方展現出的技藝,而是向玉麟防守上的突然崩潰。
事實上,在當晚更早時候舉行的半決賽里,向玉麟將防守反擊發(fā)揮到了極致,在以毫秒計的反應周期里,在不斷相互猜測下一個動作的博弈里,最終勝出。但或許是休息時間不夠,或許是達到了生理的極限,當決賽進行到后半段時,他就像突然用盡了最后的精力,再也防不住金管禹花樣百出的進攻。
當一名老將終于輸給了時間,輸給了自己時,我反而覺得榮譽不再是衡量他亞運之旅的唯一標準了,因為他展示出了個體的魅力。

另一場比賽自然是最后一天的刀塔比賽。可能是我對比賽的理解太膚淺,我始終覺得,中國隊贏下那場比賽本質上就是充分發(fā)揮了“肌肉刀塔”的優(yōu)勢,外在多了一點點耐心。我不知道在比賽里的某一刻他們是否暫時忘卻了所有的外部因素,比如輸贏對應的榮譽,或隨之而來的褒貶,而是單純地沉浸在技藝的展示與對抗里。
換句話說,依然是短暫地剝離了公共性之后個體的魅力。為何一定要強調個體的魅力,因為亞運會本身就是一個公共屬性被放大到極致的舞臺,任何一屆都是如此。國家榮譽感、民族自豪感、運動員的使命感,這些詞匯不斷強化著已有的宏大敘事,短暫但強烈地激起情緒的洪流,呼嘯沖刷過去。
每一屆綜合性運動會的賽期都是如此。公共的意義當然很重要,這也是體育必須要起到的作用。但公共討論和意義的大放異彩卻掩蓋不了個體千差萬別的魅力。事實上,隨著比賽開始,不只是場上的運動員,所有的工作人員在我看來都或許短暫地進入了一種狀態(tài)。滿場飛奔的攝影師希望找到最佳的拍攝角度,我猜想在某一刻,他們的眼里只有拍攝對象,腦海里只有構圖,按下快門的動作幾乎是下意識的。
低頭碼字的文字記者希望抓住一些充盈在場館里的情緒,將這些不可名狀的東西用文字具象化地傳遞出去。在某一刻,他們的眼里只有觀察的對象,腦海里只有諸多文字不斷進行排列組合,敲動鍵盤的動作幾乎是機械性的。攝像師、OB、導播……所有的工作人員我想都會短暫地進入一種類似的狀態(tài)。籠統(tǒng)地形容起來,運動員和所有的工作人員其實都明白,在亞運會的舞臺上他們所做的一切本身就因為被傳播、被觀賞、被討論而具有必然的公共性,他們也一定想拿出在公共層面收獲認可的作品。
但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會不自覺地退回到個體的層面,只思考一件事,那就是將過往在某項技藝上的磨煉與積累盡可能全部、完美地釋放出來。
這反而是比較有意思的地方。所有的參與者,在準備的過程里,無時無刻不被公共性籠罩。運動員需要注意自己的儀表、行為是否得體,要接受面對媒體的表達培訓,講合適的話。工作人員既想要在公共性推動的流量洪流里分一杯羹,也要考慮在一個充滿公共性的舞臺上如何妥善地找到一個不打擾整體運行的空間,充分發(fā)揮自己的能力。在參與的過程里也一樣。
但恰恰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當比賽開始的“哨聲”響起,運動員想贏,攝影師想拍出流傳度最廣的照片,文字記者希望寫出傳播量最高的評論,攝像師想給到最好的鏡頭……當每一個人都處在一個真實或假想的競爭環(huán)境中時,比賽的氛圍就從舞臺上擴散至全場。于是,一場高水準比賽的背后,實際上是參與其中的所有人都可能進入了名為“心流”的狀態(tài)。
盡管推動他們進入這種狀態(tài)的誘因是公共性,但喚起的卻是對技藝的熱愛。起碼在那一瞬間,場上的運動員和場下的工作人員沒有太大的區(qū)別。
當然,你依然可以說他們共享一種狀態(tài),所以也自然而然地回歸到了公共性的范疇里,這可能是另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點。不過,對于每一個個體而言,這種感覺一定是難以長久維系的,但可能也是最難忘的。

圖源:攝影師 任軼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