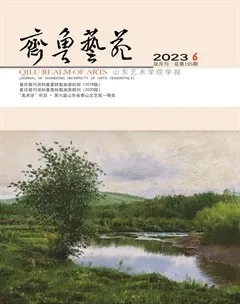漢傳佛樂“十方腔”通用性特征實證研究
陳 芳
(臺州學院藝術與設計學院,浙江 臺州 318000)
一、佛樂“中國化”學理繼承
佛教自古印度傳入中國大部分地區(qū),形成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教派,包括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及云南上座部佛教。漢傳佛教吸收中國傳統(tǒng)倫理觀念、適應社會禮儀法規(guī),積極依附封建皇權、廣泛發(fā)展民間信仰基礎,從開始翻譯西域佛經到逐漸創(chuàng)立起多種獨立的思想體系,而成為中國宗教本土化的成熟典范。漢傳佛樂在佛教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和特殊的藝術價值,其在中國及東亞地區(qū)的傳承與遠播,備受國內外學者的關注。特別是近年來中、日、韓、越等國學者,加強了佛樂傳播及區(qū)域化研究的國際交流。
隨著世界宗格局的發(fā)展,近年來“宗教中國化”命題提出(1)2021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佛樂“華化”在音樂學界作為早期的一個重要研究論域,主要聚焦于“魚山梵唄”傳說的真?zhèn)慰急妗L锴嘞壬?0世紀80年代提出“華化”范圍應界定為“非漢族音樂的漢族化、中原化”(2)參見:田青.佛教音樂的華化[J].世界宗教研究,1986,(3)。,將日后佛教音樂的學理化研究引向深入。音樂學界前輩學者多認同“曹植創(chuàng)制梵唄”之說,認為早期佛樂或為天竺風格,南北朝時期開始華化,唐代佛樂華化全面完成。另一方面,宗教學界也提出了不同觀點,或認為曹植反對方士(3)參見: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史(第一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P171。,其時亦無創(chuàng)制聲律的條件(4)參見:陳寅恪.四聲三問[G]//金明館叢稿初編[M].南京:譯林出版社,2020,P338。,造梵制契于《魏志》無載等(5)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M].北京:中華書局,1983,P89。;或結合曹植制唄傳說的發(fā)展史,認為曹植制魚山梵唄應為神道設教的造勢之說(6)參見:金溪,王小盾.魚山梵唄傳說考辨[J].文史,2013,(1)。。
該問題學界雖未達成共識,但佛樂從印度西域傳入中國內地,囿于中原地區(qū)的語言及音樂傳統(tǒng)之差異,僧人采用民間音樂或宮廷樂曲改編印度佛曲或直接創(chuàng)造新曲,由此形成中國佛教音樂的歷程則為學界普遍公認(7)參見:方立天.中國佛教與傳統(tǒng)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P361。。這為近年來佛樂中國化論題推向縱深及細致化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國化”概念賦予漢傳佛教音樂“華化”概念更宏觀的視域、更深層精準的內涵以及更全面寬廣的外延系統(tǒng)——對漢傳佛樂的風格類型、結構層次、傳播特點、傳承方式等問題展開綜合性研究,這些問題已然成為新的學術增長點。
審思佛樂“中國化”的研究范圍,一方面應充分審視對佛教音樂進行創(chuàng)制、改編及傳承的主體;另一方面應關注佛教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的融攝、演化兩個方面的深層機制。因此,不宜照搬“華化”概念,也不宜局限于“疆域”“民族”或“主權國家”等單一表述。縱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國”一詞,實指源于華夏文明、認同中華文化傳統(tǒng)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其次,對于佛樂的創(chuàng)制、流變,傳承及傳播方式等亦是破題的關鍵。方立天先生對佛教“中國化”的學理性闡釋,認為其包含了“民族化、地域化、時代化”三層含義(8)參見:方立天.方立天講談錄[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P317。,或適用于佛教音樂的中國化研究。比如佛教音樂民族化維度,已經涉及到漢傳佛樂、藏傳佛樂及南傳佛樂三種類型的音樂,音樂學界已有前輩學者取得了許多矚目的成果。佛教音樂的時代化維度,涉及佛教音樂斷代史與通史的綜合性研究、漢傳佛樂在各歷史時期的發(fā)展特點、當代佛樂對音樂傳統(tǒng)的繼承與保留等問題研究尚顯薄弱。佛教音樂的地域化維度,考察佛樂的傳播特征、流變方式、地域性風格分野等問題,或可追溯并揭示佛樂現狀之歷史成因,還原佛樂中國化的歷史脈絡。
基于上述思考,筆者對長期關注的沿長江流域傳播的“十方腔”展開實地調研,旨在探明這一流傳廣泛的佛樂唱腔有何傳播特點、是何地域風格等問題,為佛樂中國化理論提供一例實證。
二、“十方腔”流傳區(qū)域的多點調查
自近代以來,南方叢林寺院依照慣例,沿用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唱腔”概念。囿于歷史變遷及口傳的原因,有的名存實亡、有的則名不副實,以致當代佛樂唱腔概念雜而多端,常常干擾我們對漢傳佛樂歷史的深入探索。長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寺院自稱“川腔”,重慶地區(qū)的華巖寺自稱“華巖腔”,羅漢寺則稱“十方腔”。長江中游及下游地區(qū)的佛樂概念相對統(tǒng)一,如武漢歸元寺、寧波天童寺、天臺山國清寺、杭州靈隱寺等亦自稱“十方腔”。南方稍遠端地區(qū)的稱謂則又帶有地方特色,如福建稱“福州調”,廣東稱“香花板”“廣府板”等。那么,“十方腔”與這些唱腔概念彼此之間有何關聯?它們的旋律特點或音樂風格的現實狀況如何?
前輩學者對各地寺院佛樂唱腔的描述,呈現出一些規(guī)律可供總結。田青先生對全國佛教音樂的情況有廣泛的研究,對僧界大德的口碑傳說有直接的調查。1992年,在由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發(fā)起的,對江蘇、浙江、福建等地的佛寺唱腔進行搜集整理工作之后,提出近代以來叢林較公認的漢傳佛樂統(tǒng)一唱腔,當推崇江蘇常州天寧寺為范本(9)參見:田青.梵音海潮音 勝彼世間音——《朝暮課誦規(guī)范譜門》前言[J].佛教文化,1995,(1)。。尼樹仁調查河南省開封市大相國寺,其為宋代皇家寺院。佛教儀式中的聲樂部分如“贊”“偈”曲調,和全國(包括臺灣省在內)的絕大多數寺院音樂基本相同,亦屬于江蘇常州天寧寺的音樂流派。(10)參見:尼樹仁.大相國寺音樂的構成[J].中國音樂,1986,(4)。
長江中游的湖北地區(qū)保存佛樂傳統(tǒng)較好的黃梅縣五祖禪寺,具有代表性的課誦儀式音樂與天臺山國清寺的梵唄曲調亦大同小異。而焰口儀式音樂運用“九腔十八調”,受師承及地方音調影響較多,風格有變(11)參見:周耘.五祖禪寺佛教音樂述略[J].黃鐘(武漢音樂學院學報),1993,(4)。。再往西南地區(qū),始建于唐朝南詔時代的圓通寺距今逾1200余年,是云南昆明最古老的寺院之一。在各類佛事中使用的音調,亦主要來源于浙江天臺山國清寺,被稱為“寺院傳統(tǒng)梵唄”(12)參見:梅佳.昆明圓通寺佛教音樂調查[J].民族藝術研究,1993,(1)。。其與筇竹寺、華亭寺并列為昆明三大漢傳佛教十方叢林,均統(tǒng)一用圓通寺的唱誦曲調。但也有一些地方性的曲調,可見于曲靖地區(qū)的陸良、會澤等縣的佛寺。
南方如廣東的佛教音樂,原本存在三種地方特色的唱腔。即具有粵曲風格的“廣府板”與“禪和板”,二者同源異流,分別受到不同民間樂種的同化,各自向民間發(fā)展;“香花板”則屬潮州音樂風格。但目前廣東各寺院采用了國內統(tǒng)一的“叢林板”,廣東稱為“外江板”,“以其原從江浙一帶傳來之故”[1]。亦有研究直指流行于廣東地區(qū)的“北腔”,即為全國通行的漢傳佛樂“十方腔”(13)參見:陳華麗.充滿神秘色彩的廣府佛教儀式音聲[J].百科知識,2020,(33)。。可見,廣東的“叢林板”“外江腔”應指的就是江浙“十方腔”。比如重慶地區(qū)的僧人,因居長江上游而自稱其唱腔為“上江腔”,對于長江中下游地區(qū)如湖北、浙江等地的唱腔則稱“下江腔”。這種以自處地域位置為參照,對本地唱腔進行區(qū)別命名的方法,如出一轍。
此外,王耀華先生認為佛教有其自成系統(tǒng)的唱誦音樂腔系,他在對東南沿海地區(qū)的閩南佛樂研究時,發(fā)現當地存在兩種類型的唱腔,即源于福建本地民間音樂的“本地調”和“福州調”,而外地傳入福建的曲調“外江調”則為全國各地所共有。(14)參見:王耀華.福建南曲中的《兜勒聲》——《摩訶兜勒》考證研究的參考材料[J].人民音樂,1984,(11)。
通過對各地佛樂現狀及田野獲得的口碑材料進行總結分析,不難發(fā)現漢傳佛教內部存在一種比較統(tǒng)一的唱誦風格。其來源,比較一致的說法或從江蘇常州天寧寺,或從浙江天臺山國清寺,亦有個別認為由福建南普陀寺相傳而來。雖然來源地尚存分歧,但總之皆源于長江下游地區(qū)。總結起來就是“十方腔”從東部地區(qū)向西部、西南部和南方地區(qū)輻射、傳播。但是在傳播的路線上,各地寺院基本存在“十方腔”與地方腔兩種風格或并存,或較量的局面。較遠端的云南、廣東等地的地方腔生命力更頑強,距離長江流域越近則“十方腔”風格越盛。基本可以確認“十方腔”傳播路徑主要沿長江流域,向中上游或南方部分地區(qū)發(fā)散。學者們藉由豐富的經驗感知,或采用僧界自述,說明了“十方腔”存在的普遍性,只是尚需更多實證及可靠的音樂分析。
三、“十方腔”通用性特征的田野調查
筆者曾經對川渝地區(qū)的佛教音樂展開實地調查,發(fā)現重慶華巖寺的佛樂唱腔與浙江寧波天童寺的“十方腔”十分相似,并撰文揭示“華巖腔”旋律體系的相似性原理(15)參見:陳芳,蒲亨強.華巖腔現狀研究[J].中央音樂學院學報,2015,(4)。。最終發(fā)現“華巖腔”系“十方腔”傳播到重慶地區(qū)的變體曲調,雖然在傳播途中沾染上沿途的一些地方音調色彩,但與十方腔保持了較高相似度。近年來,筆者一直探訪于江、浙、閩寺院,試圖揭示各地“十方腔”相似性特征的深層原理。為何佛樂樂種傳播到各地區(qū)之后,不像民間音樂一般受方言聲調的左右,言必稱地方特色?如何能夠不受或較少受到地方音調的影響,而保持基本統(tǒng)一的音樂風格?
以天臺山國清寺為例,單就早晚課及焰口儀式中的曲調群進行統(tǒng)計分析,不難發(fā)現他們保持風格統(tǒng)一的方法與“華巖腔”如出一轍,也是重復使用相同曲調演唱多首經文贊詞。旋律的發(fā)展手法也是較多使用相同或相似的腔句或主腔,通過旋律片段的組合或展衍等方式創(chuàng)腔。但有一些曲調類型,可以通用于江蘇、浙江等地的十方叢林。這些不同寺院的曲調可以保持整曲旋律大同小異。換言之,江浙地區(qū)的“十方腔”,使用了類型化的曲調、腔句和主腔。
以下是筆者調查浙江天臺山國清寺時,統(tǒng)計的通用性曲調類型。整曲通用是指曲調旋律基本相同,唱詞各異;腔句通用是指曲調中存在相同或相似的腔句。

表1 天臺山國清寺通用性曲調統(tǒng)計表
這些類型化的旋律不僅在一地寺院內部各種儀式中可通用,其在江浙十方叢林基本可以通行,且行腔細節(jié)、音樂結構等參數基本一致。1992年,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以江浙通行的唱誦風格為基礎,江蘇常州天寧寺唱腔為底本,采錄了11首早晚課誦儀式曲調。其中《韋陀贊》用于早課儀式,若將其與國清寺晚課儀式的《楊枝凈水》進行比較(16)《韋陀贊》譜例來源于中國佛教文化所編《朝暮課誦規(guī)范譜本》第15頁第一樂句,《楊枝凈水》譜例為筆者采錄記譜。,很容易發(fā)現兩曲旋律基本相同,只是行腔細節(jié)稍有變化。
譜例1

以國清寺《楊枝凈水》為例,試分析十方腔音樂風格之分布。此曲作為晚課第一首曲目,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楊枝凈水,遍灑三千,性空八德利人天,亡靈早升天,滅罪消愆,火焰化紅蓮。南無清涼地菩薩摩訶薩。[2](P571)
全曲正詞六句,曲終連綴《菩薩陀》,為長短句結構,是一首“六句贊”。其旋律細膩婉轉,字疏腔密,以sol—mi—re為核心音調,采用五聲級進式旋法鋪陳樂句,極具江南音樂婉轉、柔美與佛教圓融、通透之風格特色,為典型的江南音樂風格。不難判斷其源出南方,在吳越之地尤為可信。實地考察發(fā)現,沿長江流域傳播的叢林唱腔大有趨同之勢,而長江以北的地區(qū),如五臺山、北京智化寺京音樂及東北等地佛曲,多冠以南北曲牌名,風格相去甚遠。南方地區(qū),距離長江流域較遠端的西南山區(qū),及廣東、廣西、福建等地則為“十方腔”與地方腔并存。
由此可見,一些類型化的曲調在不同寺院、不同儀式甚至不同宗派皆可通用,這是“十方腔”能夠較好保持音樂風格不變味或少變味的主要原因。因而,曲調具有通用性是“十方腔”的一個顯著特征,亦是鑒定“十方腔”的重要標準之一。它使“十方腔”對于漢傳佛樂整體而言,具有全局意義和統(tǒng)轄地位。由于這種特性,“十方腔”才能頑強地保持佛教音樂之正統(tǒng)。但是這種旋律的相似性及曲調的通用性,仍屬于音樂形態(tài)的表層因素。隨即而來的問題是:“十方腔”曲調群能夠超地域傳播的深層機制是什么?為何是長江流域?它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向吳越以外的地區(qū)發(fā)散、傳播的?
四、“十方腔”溯源
“十方腔”這個歷史上形成的概念,雖鮮見于文獻,但標志性的江南音樂風格已是完全地域化了的產物。筆者根據此概念隱含的文化內涵并結合其形成的歷史邏輯,嘗試作一假設。通常概念與內涵總是相對應地出現,有其名則必有其實。因而,“十方腔”概念的產生必須同時滿足至少三個方面的條件方能成立:其一,最初流傳的范圍,大致應是能夠孕育江南音樂風格的長江中下游地區(qū),這是它的生成條件;其二,能夠通用于各類儀式、各地寺院,則保守地估計應晚于宗派佛教形成之后,才能依附于儀式從而獲得表演實踐的條件;其三,該唱腔冠以“十方”之名,或與十方寺寺廟制度的形成有密切關聯,標志著它是某一個時代宗教文化的產物,從而獲得比較成熟的傳播條件。據此三條,即便通過相關文獻線索的推敲,亦可嘗試追溯其來源。
首先,“十方腔”的江南音樂風格,不少學者已有體認及較多形態(tài)論證,茲不贅述。需要注意“十方腔”最初的面貌應是“名”符其“實”,因此音樂風格的形成應早于概念的形成。本文僅限于討論概念之由來,至于唱腔系統(tǒng)的發(fā)展、流變另撰文詳述,這里稍作分析以供參考。“十方腔”屬于南方佛教音樂體系,但“南方”范圍太大。故綜合考慮佛教南北宗派的發(fā)展,認為南北朝時,北方少數民族政局動蕩、皇權更迭頻繁,北魏太武帝與北周武帝為鞏固政權,限制寺院經濟迅猛增長,采取拆毀寺院塔廟、強迫僧尼還俗,甚至誅殺僧侶等極端手段削弱佛教勢力。而南朝歷代皇權對待佛教的態(tài)度不同于北方,宋齊梁陳四代皇族皆崇佛教,至梁武帝蕭衍(502—549)時達到全盛。蕭衍出身于南齊士族,甚至親自為《水陸法會》創(chuàng)制儀軌。南宗佛教音樂伴隨著晉室、宋室兩次南遷,以六朝古都健康(今南京)為起點,自江蘇向浙江持續(xù)南移,始終活躍于長江下游地區(qū),理由是很充分的。
其次,考查宗派佛教之形成。佛教于兩漢之際傳入中原,論其發(fā)展主要是在歷代皇權支持下的譯經事業(yè),及開鑿石窟、修建寺院等。至隋唐(581—907)達到鼎盛,中國漢傳佛教賴以形成宗派的經典翻譯事業(yè)基本完成。隋唐之后,佛教開始朝著創(chuàng)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宗派,逐漸形成獨立的思想體系之方向發(fā)展,形成天臺宗、三論宗、律宗、凈土宗、法相宗、華嚴宗、禪宗、密宗以及三階教等中國佛教宗派(17)參見:張岱年主編.中國哲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P236。。
天臺宗是第一個中國化宗派。據《天臺縣志》記載,三國時天臺山已有寺觀及僧道活動蹤跡,且備受歷代帝王、名士、富豪的匡助。陳隋之際智顗駐錫天臺山,并以《妙法蓮華經》的思想體系為依據,建構天臺宗核心教義。智顗弟子灌頂繼而提出傳法譜系,至湛然一舉將天臺宗確立為具有獨立宗派意識的佛教派系。而禪宗亦是典型的中國化佛教,分南北兩宗。中唐之后,南北爭勝,北宗不傳,慧能的南宗取得禪宗正統(tǒng)地位,以江南、四川為活動中心(18)參見:張岱年主編.中國哲學大辭典[M].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P400。,即是說禪宗仍然以長江流域為主要活動區(qū)域。禪宗義理在天臺山繁衍不絕,宋高宗時期甚至下詔“易教為禪”,臺宗和禪宗于唐五代至北宋大盛。回顧歷史,吳越地區(qū)能夠融攝臺宗、禪宗兩大中國宗派之道統(tǒng),統(tǒng)儒釋道三教合一而成為文化的核心區(qū)域,除天臺山無出其右。此外,臺州自唐代成為兩浙交通的重要驛站,向北至明州,向南至廣州,皆處于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jié)點,為佛教音樂文化向海外如日本、朝鮮等國傳播,提供了優(yōu)越的地理條件。
再次,考查吳越地區(qū)中國化叢林制度的發(fā)展。早期禪宗僧人多游方,或依巖石而居,或寄宿于律宗寺院。道信、弘忍開始定居山寺,提倡“農禪并重”的修行生活方式。
佛教入中國四百年,而達磨至又八傳。而至百丈,海公唯以道相授受,或巖居穴處,或寄律寺,不聞有住持之名。百丈以禪宗浸盛,上而君相王公,下而儒老百氏,皆鄉(xiāng)風問道,有徒實繁,非崇其位,則師法不嚴。始奉其師為住持,而尊之曰長老。[3](P328)
佛教漸至中唐,禪宗及禪寺發(fā)展迅速,自百丈懷海禪師開始,奉其師為“住持”,尊稱為“長老”,為叢林法嗣傳承制度化的開始。
律有《四方僧物鈔》言“十方常住”。有師釋云:……長老、知事人并不用本處弟子,惟于十方海眾,擇有道眼德行之者,請為長老,居正寢,朝晡說法誨人。或有才干懼因果道心之者,堪任知事。皆鳴犍稚集眾請之。洎居其位,或道德不實,才力無取,行止弊惡,亦白眾揖退,別請能者。凡度弟子,惟長老一人。諸僧無各度別者之事,或有僧務一切同作,謂之各出一手。或有利養(yǎng),一切均行。故云十方住持也。[4](P302)
律宗對“十方住持”則有所不同,長老人選并不從本寺弟子產生,即不以師徒傳承。而是從“十方海眾”中,挑選道行品德俱佳之人。若德才不匹,言行舉止惡鄙,則告知于大眾摒棄而另選賢能之人。這一制度于初唐時創(chuàng)立,至晚唐時已十分盛行。其與唐以前的寺院制度是相對的。
唐大中元年,咸啟禪師請以天童景德寺充十方住持。據司馬光《稽古錄》:“大中元年春,復天下佛寺及僧尼”。時,咸啟禪師從徑山來天童開法,因有此請。另據延慶寺使帖內云:“本院僧請依江南、湖南道山門體式,永作十方住持。準中書省劄子:奉圣旨:宜令本院依久(疑為舊)例、指揮具結供申。據僧司勘會:本州天童山景德寺、大梅山仙居院兩處,亦是十方住持;即依得上項江南、湖南道山門體式。如勘會天童、大梅兩處不是十方住持,甘深罪者。奉圣旨:依天童、大梅兩處體式施行。”是天童寺準十方住持為明州之先。[5](P58)
司馬光《稽古錄》記載,晚唐時期天童寺延請咸啟禪師充任十方住持的事情。這段文字傳遞了三個信息,一是江南、湖南道山門體式,最遲唐末五代已經是禪宗十方寺院體制;二是天童寺尊奉圣旨及僧正司的審核,永為十方住持即遵守十方寺制,接受官方管理;三是天童寺成為寧波最早施行十方制的表率。
從唐末至宋代,十方叢林寺院在浙江已經形成制度化,接受官方管理。宋代不同于唐以前的法嗣傳承,通常只是在本寺僧徒之間、師徒之間傳遞。其弊端在于極易滋生腐敗,尤其是對寺產的管理不同。甲乙制、子孫廟,寺產獨立分房別食。而宋代十方制下寺產公有,官方以公選的方式延請名僧住持,甚至將科舉制度用于住持人員的選拔,任用賢能之人,寺院多得振興。自北宋開始,官方任免十方寺院住持,逐漸形成制度化,從而對南方佛教發(fā)展規(guī)模進行掌控。
五、結語
基于田野考察發(fā)現,漢傳佛教十方叢林寺院內部的儀式用樂,潛在一種形態(tài)風格近似的旋律體系。經實證研究及多點調查發(fā)現,該旋律體系多被稱為“十方腔”。它是一個古老而常新的樂種,用于佛教儀式,為宗教神學信仰服務。經過歷史的積淀與傳承,在音樂實踐方面,逐漸發(fā)展為結構層次復雜的聲腔系統(tǒng)。十方腔曲調群、腔句群可不同程度地通用于南方各地十方叢林、各類儀式,且保持音樂風格基本不變味。在傳播的路線方面,源于古吳越地區(qū)的江浙叢林,并沿長江流域向中上游或南方地區(qū)發(fā)散傳播。此路線上的各地寺院佛樂或用“十方腔”,或用地方唱腔概念,兩種音樂風格或并存,或較量。
進而通過文獻考證,唐五代至兩宋第一個中國化宗派天臺宗源于浙江,禪宗與臺宗皆盛于天臺山。宋代兩浙寺院由甲乙廟、子孫廟的法嗣傳承,向十方叢林選賢制度轉變,由此奠定了官方對寺院管理并逐漸形成制度。這對日后相繼引發(fā)高僧大德規(guī)范十方叢林唱腔并為其命名、規(guī)范制定儀式用樂、儀式程序,乃至形成佛樂傳承制度等具體實踐方面的變革,提供了實質性的內涵。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十方腔”概念伴隨十方寺制的逐步健全而產生,或為符合歷史邏輯的推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