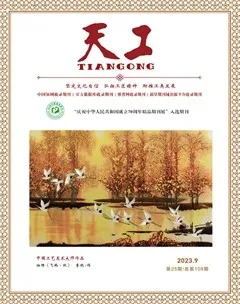湛江市傳統手工技藝類非遺文創產品“再設計”途徑研究——以雷州葛布技藝為例
陳 瑤 任婧媛 藍婉婷 肖 瑤*
湛江科技學院
一、湛江市非遺文創發展的現狀
從2007 年湛江市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評定公布起,已進行了八批的評選,所推選的非遺種類繁多、涵蓋面廣,包括民俗、民間文學、傳統音樂、舞蹈、戲劇、技藝、醫藥、美術、體育等10 個門類。類別較多集中在民俗、傳統技藝及傳統舞蹈上[1]。2018年,湛江市文化廣電旅游體育局和湛江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舉辦了湛江首屆“匠心非遺,禮遇湛江”非遺文創設計大賽,鼓勵非遺創作;2019 年,湛江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組織非遺文創產品參加深圳文博會;2022 年6 月11 日,由湛江市相關部門牽頭制作的非遺宣傳紀錄片《我們誕生在湛江》首發當日點擊閱讀量超130 萬人次;2023 年,“戲韻湛茂·非遺探索”成為廣東省文旅廳推出的10 條非遺旅游精品線路之一。隨著湛江市對非遺保護、非遺振興、非遺創新發展的日益重視,民間非遺文創潮流興起。非遺多樣化傳承、非遺“互聯網+”傳播、非遺文旅方案的推行都使湛江市非遺的轉化熱度不斷升級。
然而,目前對非遺文創的關注點依然集中在單個熱門非遺的宣傳上,不同非遺之間的關聯度較低,各美其美的局面沒有形成網狀的非遺文創轉換結構,沒有形成規模化的產品轉換和集中性的市場及消費群,使得湛江非遺文創發展具有不均衡性和不相關性。
二、湛江市傳統手工技藝類非遺發展情況和雷州葛布產品轉換現狀
(一)湛江傳統手工技藝類非遺
湛江傳統手工技藝類非遺源于飲食文化、養生習俗、家具器物、服飾、民俗節慶等傳統生產生活領域,有著天然的地域性關聯。作為臨海城市,湛江非遺充滿獨特的海洋生活氣息:如海味月餅制作技藝、湛江干魚制作技藝、海鹽古法曬制技藝、雷州蒲織技藝、遂溪制糖技藝、彩扎技藝(遂溪獅頭)、石花菜糊裝裱技藝、井華酒傳統釀造技藝、海味雞仔餅制作技藝[2]等,地方特色和地域關聯性是湛江非遺整體發展的潛在價值因素。
(二)湛江市傳統手工技藝類非遺文創發展不均衡
根據傳承熱門程度和品牌產品衍生程度,筆者將目前的湛江市傳統手工技藝類非遺大致分為四種情況,即熱門、較熱門、較冷門、冷門四類(見表1)。

表1 湛江市手工技藝類非遺(部分)發展熱度歸類
由表1可知,與當代生活關聯度較高的如食品調味、家居器物、民俗文化類型的非遺技藝傳承發展熱度高,海味月餅和雷州蒲織等已發展成文創大IP;依托民俗節慶和戲曲活動開展的非遺技藝,如遂溪獅頭彩扎和吳川木偶雕刻等也傳承較好,但雷州葛布制作技藝發展緩慢,面臨被時代遺忘甚至技藝斷層的尷尬處境。
針對非遺發展不均衡的情況,本文將以雷州葛布技藝作為研究切入點,探索和挖掘非遺的再生創意價值并促進非遺均衡發展,探討湛江市傳統手工技藝類非遺文創產品“再設計”途徑。
(三)雷州葛布產品轉換現狀
通過對茂德公大觀園的實地調研,筆者了解到當下雷州葛布技藝傳承發展的近況:雷州葛布技藝依賴的原材料以藤蔓長且順的非野生葛藤最佳,通過藥水的浸泡,脫去葛藤植物膠質后清洗晾曬,余下的白色纖維才能作為紡織材料。當代的農戶早已拋棄種植葛藤紡布的生活模式,葛藤的原材料稀少;從葛藤到布匹的制作過程耗時長且細節繁多,手工曲絲和手工織布的生產方式非多年的能工巧匠不能勝任;即使消耗大量葛藤,最終的紡布成品只有幾米,無法機械化生產,也無法量產;當前的雷州葛布織造難以達到曾與香云紗齊名時“質地輕薄”的布料質感,布匹接線頭明顯,拙樸有余而工藝精美不足;雷州葛布技藝傳承人劉迎老師去日本系統地學習了脫膠與織染技術,提升了面料柔軟度[3],雖然改善了粗糙的布匹質量,但造價成本頗高。這些因素導致雷州葛布技藝發展受限。
在雷州本土的產品開發上,目前已嘗試制作帽子、扇子、包具、茶席等文創產品,但產品類型比較單一,產品設計創作簡單,未融入地域文化和特色符號,未投入市場進行規模化銷售,未開展品牌建設和營銷方案籌劃等后續工作。雖然開班招募和培養葛布織造技藝人才,但沒有形成固定的分工團隊。總之,雷州葛布技藝傳承和產品開發都局限在比較小眾的領域。
在高校的研究中,劉春雨認為雷州葛布作為人文與自然完美的結合體,是雷州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4]。李佳穎以雷州葛布織造和黔東南葛布織造工藝為基礎,結合國內外葛布利用狀況分析,對葛纖維面料的織法、材料混紡、花紋設計進行了創新,并嘗試將葛纖維材料與多種材料融合,在壁掛、抱枕、桌旗、燈具等室內紡織品中進行再設計[5]。但李佳穎的研究側重點是葛布材料,而非雷州葛布產品開發。石云總結了雷州葛布織造技藝的傳承與發展需要專業的藝術管理人才制定長期有效的管理機制,以制作出更適合現代人審美與消費需求的服飾品和生活用品。
三、雷州葛布產品開發中的困境和革新發展方式
(一)雷州葛布產品開發中的困境
雷州葛布在傳承發展中面臨以下困境:技藝的斷層使布匹質量較次;只能手工織造且成本高,使產品無法批量生產;取材單一、織造方式單一、成品設計單一、傳承制作方式單一,限制了目前產品的開發“再設計”;產品無法開發量產,無法走向市場形成規模的局面,造成了難做品牌、難組建團隊、難進行藝術創作管理、難擴大影響力等后續的問題。
(二)生產技藝和布料的革新
非遺的“原真性”可能是不可見的,也可能由某些可見的物質材料所決定[6]。如今,雷州葛布的價值不再是物理特性的使用,更多是文化和地域符號性的特色,其可見的原材料特性需求低于不可見的文化符號。因此,在這個時代,是否絕對地保持完全由雷州葛藤材料織造的布才叫雷州葛布?材料的革新或許是非遺發展可突破的觀念屏障。想要得到造價更低、更軟和更多類型的布,可以嘗試引入機械生產,摻入棉、麻、絲、化纖材料,豐富布料種類、花色、織法、紋樣、肌理,融入地域圖案紋飾和文化符號豐富布料紋樣,從而給受眾群體帶來更多新意和選擇。
(三)推動地域性的非遺網狀產業鏈形成
作為比較冷門的非遺項目,雷州葛布產品開發要與湛江植物染、雷州石狗紋飾、雷州蒲織竹編等地域非遺文化符號和技藝結合,借助其他地域非遺的熱度打破湛江非遺文創發展的不均衡性和不相關性。由政府干預,社會團體參與,企業投資生產,高校培養創新人才,建設鄉村工坊,發展文化旅游和非遺產品展銷等一系列地域非遺產業活動,促進地域性的非遺網狀產業鏈形成。
四、雷州葛布文創產品開發模式探尋
(一)雷州葛布的產品特點
雷州葛布是綠色生態材料,受當代人追捧。因輕、堅、涼、滑的特點適合作為夏季服飾,成衣在古代稱為夏衣;未著色時,其外觀給人雅致樸質的感受;其纖維因可紡織、可編織、可染色、易分割的特點,可制成樣式豐富的葛布衣帽、腰帶、草鞋、包囊配飾等,總之,就產品設計而言,雷州葛布具有多樣化的開發潛力。
(二)整合地域價值的雷州葛布文創產品“再設計”
歷史上精紡的雷州葛布是進貢的禮品,被稱為正宗葛布,其地域價值不言而喻。非遺又是一種“身體遺產”[7],在傳統工藝類非遺的生產過程中,制作者與地域材料、地方環境、行為、語言、情感交織構成的日常實踐活動和社會關系也是非遺價值的重要部分。手工技藝類非遺是一個民族在漫長的社會演化過程中積累的勞動和智慧結晶,其蘊藏的文化價值和地域歷史價值體現在非遺的在地性和地域生產聯系上。
雷州葛布與雷州本土地域文化一脈相承,產品“再設計”可融合地域文脈作為文創元素:以“雷州石狗”“雷劇”“雷州裝飾紋樣”等作為衍生裝飾圖案元素來豐富文創產品設計題材,結合“雷州蒲織”“雷州竹編”“雷州陶藝”等多元材料進行混合設計。
(三)雷州葛布文創產品“再設計”的創意發散
雷州葛布材料經過編、拼、縫、繡、繪、印、染后,可兼容的文化藝術題材豐富,如民間傳說、典故、神話、古典名著、傳奇和反映雷州地域風土人情的題材都能組合到設計創作中,具有很強的藝術張力和包容性[8]。
雷州葛布文創產品“再設計”涉及高級定制類服裝服飾、家裝家具、家紡家飾、屏風、靠墊抱枕、高檔禮盒、筆記本、杯墊、杯套、包具等,具有廣闊的產品衍生空間(見圖1、圖2)。

圖1 雷州葛布裝飾于筆記本(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圖2 雷州葛布裝飾于杯墊(圖片來源:作者自攝)
五、結束語
目前湛江市手工技藝類非遺發展具有不均衡性,但其海洋文化特色和地域文化符號能作為未來非遺融合發展的方向。雷州葛布技藝屬于比較冷門的非遺項目,在開發文創產品時應充分挖掘地域文脈價值,搭建雷州地方性非遺工坊,孵化地域文創品牌和整合地域文化資源,這是拓寬文創產品“再設計”的發展新思路。
雷州非遺融合“再設計”可以與高校進行合作,提升產品創意設計內涵,以多領域、多類型、綜合性強的創意產品拓展市場寬度,并適時抓住節假日和文旅機遇對非遺產品進行關聯設計,推陳出新,從而實現湛江非遺的可持續發展。希望不久的將來,雷州葛布這種獨特的地域文化遺產也能成為湛江非遺的代表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