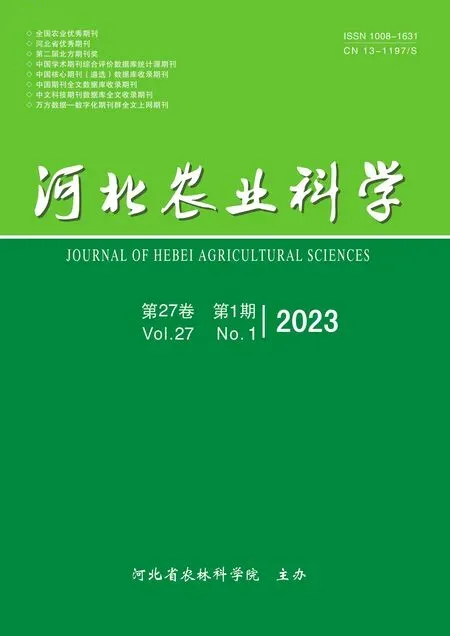我國鄉村內生發展研究進展與展望
謝正峰,馬林兵
(1.嘉應學院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廣東 梅州 514015;2.嘉應學院鄉村振興研究院,廣東 梅州 514015;3.中山大學地理科學與規劃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為我國農村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契機。鄉村發展根據其動力來源,可分為外生發展和內生發展,發達國家率先提出鄉村發展的外源性發展模式,即外生發展模式;后來又提出了鄉村內生發展模式。鄉村內生發展是一個多層次、多因素和多面向的概念,強調動員和利用地方內部資源作為經濟活動和生計發展的基礎,重視理解自然、人力、文化等地方特征以及這些特征對可持續經濟活動的支撐[1~3];2001 年英國學者Christopher[4]基于內生潛力、發展社會資本和促進地方參與性民主等三大支柱,提出了新內生發展的概念。我國開展鄉村內生發展的相關研究較晚,主要是從鄉村內生發展的概念、影響因素、內生發展能力、動力機制等方面進行探討。通過對我國鄉村內生發展研究的文獻進行分析,旨在把握相關研究的進展,指出未來的研究方向。
1 對于鄉村內生發展的內涵與特征
內生發展作為區域發展的一種模式,并不僅限于鄉村發展。內生式發展意味著一個動員本地各種利益團體聯合起來追求符合本地意愿的發展規劃以及資源分配機制的過程,其最終目的是提升本地在技能和資格方面的能力[1]。Garofoli[5]認為,內生式發展是在本地層面進行創新的能力,包括轉換社會經濟系統的能力、應對外界挑戰的能力以及引進符合本地層次的社會規則的能力。可見,內生發展的核心是區域內生發展能力的提升。
1.1 鄉村內生發展的內涵
Michael 等[6]認為,鄉村內生發展的內涵包括發展意愿來自5 個方面:內源驅動,發展過程由本地控制,發展路徑方向的選擇由本地決定,發展的利益留在本地,內生發展并不排斥外部要素的投入;張環宙等[1]、周怡岑[7]認為,鄉村內生發展主要是指以村莊自有的資源、技術、產業和文化為基礎,以技術進步為發展動力,以提高村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為目標,促進村莊經濟可持續發展;張慧等[8]認為,中國鄉村社區基于內生發展的營建模式,包括內生自主性組織建設、社區產業建構、村民主體地位與發展等3 個方面。
1.2 鄉村內生發展的特征
Sabine 等[9]認為,鄉村內生發展需要具備內生潛能、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地方參與和地方認同5個特征。方勁[2]認為,內源性農村發展模式包括強調發展的內源性潛力、倡導開放性的區域經濟、追求農村發展的可持續生計、注重地方民眾的自主參與、構建地方民眾的區域認同5 個基本特征。章志敏等[10]認為,在鄉村內生發展目標上,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最終目標;在發展形式上,堅持國家的自主發展,尊重發展選擇的多樣性;在發展動力上,通過對本土知識、文化傳統、資源等要素的整合利用推動發展;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堅持走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在發展主體的內部關系上,充分尊重地方的自主性和參與權。不同學者對鄉村內生發展特征的表述存在差異,但認識上具有明顯的共通之處,都追求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注重內生潛力的挖掘,強調地方的參與性、自主性和認同,堅持開放式發展。
2 鄉村內生發展的主體
鄉村內生發展需要明確其主體,從歷史發展歷程與目前發展現狀來看,不可無視農民的主體地位和作用[11]。劉曉雯等[12]認為,鄉村振興的主體是農民;基本特征為獨立自主性、自覺性、選擇性、創造性[13]。張國磊等[14]將鄉村振興的主體分為外部嵌入主體和村莊內生型主體;仲崇建等[15]認為,鄉村振興需要激發不同主體參與的積極性、能動性和創造性;針對農民的分散化、原子化特征,通過農民的組織化重建鄉村的主體性[16],培育農村的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新鄉賢,有效構建鄉村振興內生主體的基礎[17]。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分為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4 種類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分為內生型主體與外生型主體,內生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內生于農村社會,來自當地村莊,與當地的文化價值與社會關系網有較密切關聯[18]。因此,鄉村內生發展的主體是農民,其中新鄉賢是新主體的基礎。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新型農民形成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成為鄉村內生發展主體的新形式[19]。部分學者通過主體權利和主體能力重塑農民主體性,并提出實現路徑[20~22]和提升途徑[23~25];對于農民主體的“增權賦能”,可分為個體賦權、組織賦權和政治賦權[23];鄉村價值再造有利于農民主體的重塑[26]。
3 鄉村內生發展的影響因素
耿言虎[27]認為,政府職能部門幫扶、鄉村精英引領、鄉村優勢資源挖掘、多利益主體合作等對農村內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李凌漢[28]基于扎根理論的分析發現,影響鄉村內生發展的因素包括村莊領導內生發展動力、村集體產業規模化水平、技術人才梯度開發、內生發展資源平臺式整合和農村內生發展能力;可以將影響鄉村內生發展的因素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內部因素包括內生自主性組織建設、鄉村精英引領、鄉村優勢資源的挖掘、鄉村治理人才、鄉村新型經營主體、現代農業發展,外部因素包括政府職能部門的扶持、外生資源的引入。
從鄉村內生發展可獲得資源的角度看,影響鄉村內生發展的資源因素包括內生資源和外生資源,外生資源包括中央政府和其他非本地的政策、資金以及技術等[9],內生資源主要包括農村的水土環境、地理位置、生態條件等生態環境狀況,地方開發程度、經濟發展狀況以及經濟資源等經濟狀況,地方的歷史人文環境、風俗習慣以及文化傳統等社會文化條件,地方民眾能力素質以及精神氣質與心理特征等狀況[29]。袁宇陽等[30]又進一步將內生資源分為顯性的內生資源(包括鄉村自然資源、經濟資源、實體性人文資源)和隱形的內生資源(包括人力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一般來說,內部資源由地方提供,外部資源來源于政府、非政府組織等[29,31]。內生資源的關鍵在于穩定的社會資本[32]。鄉村振興的內源系統與外源系統之間的邊界并不是完全封閉的,而是交互流動的狀態。外源系統的條件因素可能轉化為內源系統的動力因素,如鄉村人才、技術工具等[33]。
4 鄉村內生發展能力
卓蓉蓉等[34]認為,鄉村發展能力是推動鄉村發展的因素集合及其關系耦合,主要涉及外源驅動和內部響應2 個層面,具體包括城鎮化驅動及響應、工業化驅動及響應、全球化驅動及響應和市場化驅動及響應4 個方面。鄉村內生發展能力是一個能力體系[35],主要包括資本自我積累能力、資源及要素優化配置能力、產業發展能力、環境治理能力、社區治理能力與文化軟實力等。要深入理解鄉村內生發展能力的內涵,明確農村內生發展能力的來源主體,明確增強農村內生發展能力的實現路徑[35]。鄉村內生發展能力是在于周圍環境的互動中鄉村系統的自適應能力和學習能力,是一種獲取能力的過程,而不是結果[36]。基于農村自身資源、勞動力、資金、生產技術、體制要素等因素或條件所決定的自主發展能力,是推動農村發展的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是農村發展的內因[35]。郭勁光等[37]認為,農民的內生發展能力是人能自由獲取所需資源的駕馭性力量,其所依力量源于自身,是一種內生性的發展能力,包括經濟能力、政治能力、文化能力和社會能力4 個維度;陳軍民[38]基于可行能力理論,將鄉村振興的內生發展能力分解為政治參與能力、村集體經濟能力、獲取社會機會能力、防護性保障能力和透明性保障能力。
李凌漢[28]認為,增強我國農村經濟社會內生發展能力,是解決“三農”問題、推動農村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有效手段;方勁[39]認為,內源性能力建設應以內源發展為基本理念,以能力建設為核心手段,更強調基于地方性知識來塑造自主發展的價值觀念、理解能力、組織能力、反思能力以及創新精神等“軟實力”;鄭有貴[40]認為,需要構建增強農村經濟社會內生發展能力的社區集體行動理論;江劍平等[41]認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是增強農村內生發展能力的最優選擇;王進文[42]認為,把“主體性”視角帶回鄉村振興發展的第一現場,是破解“鄉村久振而未興”困惑的根本之道,是激活鄉村內生發展能力的必由之途。不同學者從各自角度給出增強鄉村發展能力的方法,這也說明了鄉村內生發展能力的多維度和實現途徑的多元性。
5 鄉村內生發展的動力和機制
鄉村內生發展的動力可分為外部動力和內部動力。李鑫等[43]認為,外部動力包括城鄉基礎設施融合與公共服務融合2 方面,內部動力包括鄉村吸引力與要素集聚。曾穗平等[44]將城市邊緣區鄉村發展內生作用機制歸納為生產方式決定就業選擇和土地流轉需求,居民就業選擇影響區域產業布局及設施配給,土地流轉需求影響居民點空間建設模式3 個方面。李承喜[45]認為,鄉村的內生式發展策略包括鄉村的參與和推動、地方認同的建構、鄉土資源的利用。陳昕昕[46]認為,應以激發農村地區內生動力為基本內核,大力培育農業新型經營主體,改革現有財政支農機制,加快創新農村金融體系,賦予農民更多的權利。新型城鎮化被看作鄉村內生發展的途徑,其核心與本質是給予鄉村社會足夠的動力和權力,發展鄉村的自我控制能力,以實現鄉村的自我維持機制和應對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中的挑戰,最終實現中國城鄉的統籌均衡發展[47]。汪錦軍等[48]認為,要激發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需要建立鄉村振興和城鎮化相互融通的認知體系,實現城鄉真正的有機互動。綜上所述,農村內源性動力難以實現鄉村振興,需要將外部先進的生產要素、發達的產業和公共服務嵌入到鄉村發展的動力結構中,實現外源動力的內源化,突破原有的動力結構格局,帶動鄉村發展動力結構的高級化[49]。立足于農村實際需要,整合內外部發展資源,才是推動農村地區內生發展的有效方式[28]。為了協調更多的有效的外部力量,減小外部力量對本地經濟社會破壞的可能性,需要進行地域身份建構[50]。
6 結論與展望
6.1 研究結論
基于文獻分析法,對我國鄉村內生發展相關研究進行了梳理和歸納,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1)從鄉村內生發展的內涵來看,鄉村內生發展的意愿來自于鄉村內部,不受控于外界。
(2)從鄉村內生發展的特征看,鄉村內生發展強調內生潛力[51,52],發展的內容不是唯經濟。
(3)從鄉村內生發展的主體來看,農民是鄉村內生發展的主體,隨著時代的發展,農民主體的具體形式也在發生變化。針對農民主體性缺失的問題,需要通過增權賦能,重塑農民的主體性。
(4) 影響鄉村內生發展的因素,不僅有內生因素,同樣還有外生因素。
(5)鄉村內生發展能力是能力體系,是一種內生性的能力和自適應能力,同時也表現為能力獲取的過程。鄉村內生發展能力同時也是內生因素和外生因素之間關系的耦合。提升鄉村內生發展能力具有內涵的多維度和實現途徑的多元性。
6.2 展望
6.2.1 加強鄉村內生發展的時空尺度研究 由于鄉村的尺度性,空間上可分為農戶、村域、鎮域、縣域到市域等不同空間尺度,每個尺度都有各自的特點和運行機制;在時間上,鄉村內生發展表現為過程性和階段性,由于發展的不可逆性,在不同階段有不同的任務、目標以及行動要求。這就需要探討鄉村內生發展不同尺度間的影響、協同、效應等問題。
6.2.2 深入探討鄉村內生發展過程中內部因素與外部因素的關系 鄉村內生發展并不是僅靠內部力量,還需外部力量的參與。在鄉村內生發展過程中,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之間的內在關聯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
6.2.3 加強鄉村內生發展能力建設研究 鄉村內生發展能力的建設受到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在城鎮化、工業化、全球化和市場化背景下,處在開放環境中的鄉村如何才能加強鄉村內生發展能力建設,鄉村內生發展能力作為一個能力體系,如何促進不同能力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協同發展,未來研究中還應加強不同尺度上的研究以及鄉村內發展能力的系統構建。需要構建外生動力和內生動力互動的動力體系。
6.2.4 深化鄉村內生發展的動力機制研究 目前對鄉村內生發展的機制研究仍處于定性研究階段,缺少對其機制的系統性分析。尤其是需要揭示將外部要素嵌入到鄉村發展的動力系統中,實現外部動力轉化為內部動力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