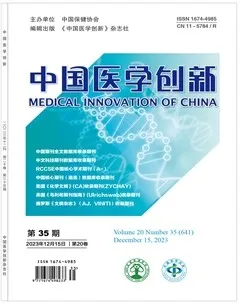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手術入路選擇對臨床治療效果影響
歐陽根
腹股溝疝又名“疝氣”,其發病機制主要是腹股溝區域腹壁組織出現缺損或組織間隙閉合較差,腹腔臟器通過空隙向體表突觸,進而在患者體表形成包塊[1]。該病為臨床常見疾病,相關研究指出,腹股溝疝在我國具有較高的發病率,并且如未及時對患者進行有效治療可嚴重降低患者健康水平[2]。現階段,手術修補術仍為腹股溝疝治療的主要手段,并且隨著微創相關技術的不斷發展,腹腔鏡下腹股溝疝修補術已成為臨床應用主流,其在降低手術創傷、縮短患者術后康復周期方面效果明顯,同時疝氣治療效果及手術安全性得到多方認可[3]。目前腹腔鏡下疝氣修補術存在完全腹膜外入路及腹膜前入路兩種入路形式,兩種入路在臨床均有所應用,但是針對不同患者選擇何種入路方式尚無統一的標準[4]。為不斷提高腹腔鏡下腹股溝疝修補術的臨床應用效果,本研究開展分組對照試驗,對比分析不同入路的臨床應用效果,以期為臨床選擇手術入路提供參考價值,現將試驗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抽取江西省中西醫結合醫院2021 年1 月—2022 年1 月收治的腹股溝疝且選擇進行腹腔鏡疝氣修補術治療患者66 例,納入標準:經臨床相關檢查,明確診斷為腹股溝疝且選擇在本院進行腹腔鏡下疝氣修補術治療;認知、語言功能正常,可配合完成相關調查;腹股溝處存在明顯包塊。排除標準:凝血功能障礙、貧血、造血功能異常或合并其他血液系統疾病;肝、腎等臟器功能嚴重衰竭;合并全身感染性疾病;惡性腫瘤性疾病;合并腸梗阻、泌尿系統結石;嵌頓性疝氣、絞窄性疝氣;腹腔鏡疝氣修補術禁忌證;妊娠期及哺乳期女性。將患者隨機均分為對照組33 例、試驗組33 例。本研究經本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后開展。患者均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對照組 采用腹腔鏡前方入路行疝氣修補術治療,具體手術方法為:麻醉方式選擇全身麻醉,患者體位選擇仰臥位,麻醉起效后常規進行消毒、鋪巾。肚臍下緣做切口,長度1.5 cm,取12 mm 戳卡插入,建立氣腹,置入腹腔鏡,搖船姿勢并用鏡頭分離Retzius 和Bogros 間隙,直至恥骨與Cooper韌帶結合。擇5 mm 戳卡置于肚臍下5 cm 和10 cm位置,持續擴展腹膜前間隙,疝囊分離后置入補片,完全覆蓋可能發生疝部位,關閉氣腹,監測關閉腹膜前間隙,取出戳卡,釘槍固定直疝補片。
1.2.2 試驗組 采用腹腔鏡腹膜外入路行疝氣修補術治療,具體手術方法為:麻醉方式、體位選擇同對照組。常規消毒、鋪巾后,肚臍下緣做切口,長度1.5 cm,取12 mm 戳卡插入,建立氣腹,置入腹腔鏡,基于腹腔鏡引導,下降5 mm 戳卡置入麥氏點和反麥氏點,距離疝環邊緣4 cm 位置,沿疝環切開腹膜,充分暴露,肌恥骨孔,直疝剝離后回收疝囊,斜疝疝囊較小,完整剝離,離斷疝囊;放置補片,完全覆蓋疝內環口和直疝三角,直疝腹膜缺損超出3 cm,采用釘槍固定,斜疝補片可不固定,縫合腹膜采用3-0 可吸收縫線。
1.2.3 術后處理 兩組術后均常規禁食5~6 h,6 h后使用少量流質飲食,無不適感受則逐步恢復正常飲食;術后常規應用抗生素預防感染。
1.3 觀察指標
1.3.1 手術指標 對兩組手術相關指標進行統計,包括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后下床時間及住院時間。
1.3.2 炎癥指標 分別于術前及術后次日,采集患者上肢空腹靜脈血5 mL,4 500 r/min 離心處理15 min,獲取血清后送檢。應用酶聯免疫吸附法對患者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白細胞介素-6(IL-6)水平進行測定,試劑盒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相關檢查操作嚴格按照試劑盒說明書進行。
1.3.3 并發癥 對兩組手術相關并發癥發生率進行統計,包括感染、腹腔出血、腸道損傷、尿潴留、腸梗阻。
1.4 統計學處理
本研究數據應用統計學軟件SPSS 26.0 進行處理。研究中計量資料,包括年齡、手術相關指標、炎癥指標水平等以(±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 檢驗,組內比較采用配對t 檢驗;計數資料,包括性別、發病位置、病理分型、并發癥發生率統計結果等以率(%)表示,進行χ2檢驗。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一般資料比較
對照組男18 例,女15 例;年齡43~62 歲,平均(53.05±5.13)歲;腹股溝疝類型:斜疝21 例,直疝12 例;發病位置:單側22 例,雙側11 例;病理分型:Ⅱ型17 例,Ⅲ型8 例,Ⅳ型8 例。試驗組男19 例,女14 例;年齡43~64 歲,平均(53.85±5.32)歲;腹股溝疝類型:斜疝24 例,直疝9 例;發病位置:單側20 例,雙側13 例;病理分型:Ⅱ型18 例,Ⅲ型6 例,Ⅳ型9 例。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2.2 兩組手術相關指標比較
試驗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后下床活動時間、住院時間均明顯優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手術相關指標比較(±s)

表1 兩組手術相關指標比較(±s)
組別手術時間(min)術中出血量(mL)術后下床活動時間(d)住院時間(d)對照組(n=33)48.53±8.6512.53±5.533.25±1.328.52±1.36試驗組(n=33)44.06±7.3210.32±2.652.36±1.437.36±1.28 t 值2.2662.0702.6273.568 P 值0.0260.0420.0100.000
2.3 兩組炎癥指標水平比較
術前,TNF-α、IL-6 水平組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兩組TNF-α、IL-6水平均升高,但試驗組均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炎癥指標水平比較(±s)

表2 兩組炎癥指標水平比較(±s)
*與本組術前比較,P<0.05。
組別TNF-α(μg/mL)IL-6(pg/mL)術前術后術前術后對照組(n=33)3.83.±0.406.31±0.23*5.61±0.2654.20±4.22*試驗組(n=33)3.78.±0.366.05±0.26*5.52±0.2428.02±3.20*t 值0.1494.3030.18615.273 P 值0.8810.0000.853 0.000
2.4 兩組并發癥發生率比較
試驗組并發癥發生率為6.06%(2/33),略低于對照組的15.15%(5/33),組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1.438,P=0.230),見表3。

表3 兩組并發癥發生率比較[例(%)]
3 討論
腹股溝疝為臨床常見疾病,手術疝氣修補為該病治療的主要手段,既往臨床主要應用開放手術進行治療,其手術切口較大,對患者健康組織的損傷較多,術后恢復周期長、并發癥發生率較高[5]。隨著微創相關技術在臨床廣泛的應用,腹腔鏡下腹股溝疝修補術已逐漸取代傳統開放手術,其可有效彌補上述傳統手術的缺點,使得手術安全性得到顯著提升[6-7]。現階段,腹腔鏡下疝氣修補術存在兩種應用廣泛的入路形式,分別為完全腹膜外入路及腹膜前入路,兩種手術入路方式具有相似的原理,均是采用補片對患者腹壁損傷、缺損部位進行修補,進而起到腹股溝疝治療的目的[8]。
腹腔鏡下腹股溝疝氣修補術臨床應用效果已得到廣泛的認可,但是不同手術入路行腹腔鏡下腹股溝疝氣修補術的效果如何仍需進行相關研究,鑒于此,本研究分組對照試驗,對比分析了不同手術入路行腹腔鏡下腹股溝疝氣修補術的效果,結果顯示:試驗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術后下床活動時間、住院時間均明顯優于對照組;試驗組并發癥發生率略低于對照組,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IL-6 是誘導肝細胞合成CRP 主要細胞因子,術后IL-6 水平和手術損傷程度呈現正相關,早期反映組織損傷程度,敏感性突出,本研究中,試驗組IL-6水平低于對照組,結果表示,術后吞噬細胞和淋巴細胞被激活,有炎癥反應,但試驗組明顯低于對照組,證明其引發的炎癥反應較輕。TNF-α 是通過活化單核細胞或巨噬細胞生成,增殖和分化細胞,屬于重要炎癥介質。腹腔鏡腹膜外入路行疝氣修補術為新型技術,實施中可避免直接進入腹股溝區域,從而減少對該區域的創傷和刺激,進而降低炎癥因子水平,同時該手術方式具有更佳視野和操作空間,可展開準確修補。本文研究結果顯示,術后試驗組的TNF-α 低于對照組,表明腹腔鏡腹膜外入路行疝氣修補術能夠有效降低炎癥因子水平,緩解全身炎癥反應,減少局部組織液積聚,發揮抗炎作用。相比于傳統手術,本文采用腹腔鏡術式可改善炎癥狀態,復原腹部組織和臟器的正常解剖結構,因此腸道黏膜屏障功能有效恢復,降低手術創傷影響,同時腸黏膜屏障功能恢復可對機體炎癥狀態予以抑制,加之術后抗感染處理,有效緩解機體炎癥。腹膜前入路是將患者腹腔打開后,在腹股溝位置放置疝氣修補補片;而腹膜外入路則不需要進入患者腹腔,通過腹腔前間隙完成補片放置,因此對于患者腹腔臟器的損傷可降到最低,進而術中出血、術后恢復、炎癥指標等得到有效的控制[9-10]。但是相關學者提出,腹膜外入路由于手術空間得到壓縮,術中對組織的分辨難度得到提升[11-13]。但是由于腹膜外入路不需要對腹腔進行關閉處理,因此可在一定程度內縮短手術時間,對于麻醉的要求也明顯低于前方入路[14-17]。由于腹膜外入路手術操作對患者健康組織的損傷小、術后恢復快,理論上其并發癥發生率將得到有效控制[18-20]。但本研究結果并發癥發生率組間比較無統計學差異,對其原因進行分析:本研究納入樣本量較少,針對并發癥方面的調查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后續仍需擴充研究樣本量進行深入研究,以獲得更加準確的研究結果。但本研究對臨床選擇腹股溝疝修補術手術入路仍存在一定的參考價值。
綜上所述,腹膜外入路下行腹腔鏡腹股溝疝修補術,可有效降低手術創傷,縮短術后康復周期,減輕術后炎癥反應,對于降低手術相關并發癥同樣具有一定效果,使得手術安全性、有效性得到明顯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