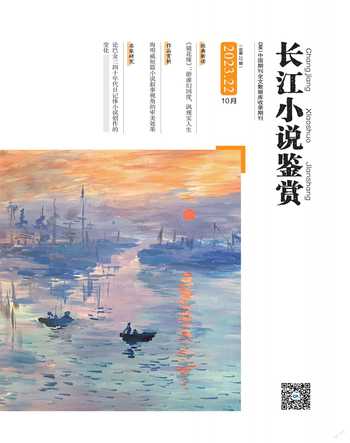論莫言《生死疲勞》的敘事特征 □
[摘? 要] 《生死疲勞》中展現的“物”“我”合一的視角疊加,超越了《變形記》中簡單的動物視角,不同敘事者的多重交流和對話,也不同于巴赫金所說的復調敘事效果。多種敘事技巧的創新使用,使其獲得了極大的敘事自由,由此體現的對敘事技巧的探索創新以及始終如一的人文關懷,正是莫言小說的魅力所在。
[關鍵詞] 《生死疲勞》? 敘事特征? 莫言
[中圖分類號] I1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22-0011-05
莫言的《生死疲勞》自2006年1月出版,便受到學界持續的關注①,從敘事層面探究小說的藝術魅力,更是成為學者熱衷的研究方向之一。然而,在此過程中,理論的濫用與誤用情況也隨之發生,以巴赫金著名的“復調”理論為例,如《當代文壇》2006年第2期刊登的《“大我”與“大聲”——〈生死疲勞〉筆記之一》一文,論者在談及三個敘述者之后,稱“這是對話,是復調”,并提出“復調的真正志向:從總體上想象和理解世界”,并在這一維度上,肯定了《生死疲勞》“說書人般的總體性的‘大聲”[1]。《當代作家評論》刊載的《敘述就是一切——談莫言長篇小說中的敘述策略》一文,則借用巴赫金長篇小說“多語體”“多聲部”等理論對《生死疲勞》進行透視分析,肯定其展現的多層次的敘述空間[2]。當然,在這其中,還有一些文章并未直接提及其使用的是巴赫金的復調理論,僅在文中使用了“復調”一詞,如《多元敘事策略成就巨大敘事張力——莫言小說〈生死疲勞〉敘事藝術分析》一文,認為“具有差異的敘事視角形成不同敘事風格, 更以雙重的敘事腔調促使此文本具有了復調敘事的效果”,“第一、第二、第三人稱敘述的交替進行, 同一故事被從不同的立場、以不同的視角講述, 呈現出復調形態”[3]。但“巴赫金的‘復調理論從提出到譯入中國,已成為一個經典化的概念”[4],個人化解讀以及未標明理論歸屬的做法,對于分析小說文本無疑起著反作用,正是在此背景下,我們似乎有必要重新回到文本,從文本出發,對《生死疲勞》的敘事特征做進一步辨析。
一、“物”“我”合一的視角疊加
胡亞敏在其著作《敘事學》中對“視角”概念有過明確的定義:“視角指敘述者或人物與敘事文中的事件相對應的位置或狀態,或者說,敘述者或人物從什么角度觀察故事。”[5]該定義從空間位置的角度,將敘述者從故事文本中抽離出來,并將二者置于同一平面,認為敘述者和文本之間的位置關系便是所謂的“視角”,同一事件會因為觀察角度的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可以說,視角在敘事過程中占據著重要地位。
《生死疲勞》中,故事以“我”為第一人稱的回憶性敘事視角展開——“我的故事,從一九五零年一月一日講起”,西門鬧在經歷投胎轉世為驢、牛、豬、狗、猴之后,最后轉世為人,成為故事最開始的敘述者藍千歲。在此過程中,故事的敘述視角是當時的西門鬧以及投胎轉世后的驢、牛、豬等動物,而敘述者則是故事發生若干年后,終于轉世為人的藍千歲,故事的親歷者同時又參與對故事的描述,又因為重生輪回之后仍保有前世記憶的設定,導致敘述者始終保持著物性+物形+人性的多重視角。
所謂“物性”和“物形”指的是動物習性和外形,西門鬧轉世成為動物后,縱然保留著前世為人的情感記憶,但身心都受到了來自動物習性和形體的限制,一方面日常行為只能借助動物形體進行,說出的話只能變成驢叫、犬吠,另一方面心性也受到動物習性的左右,驢的倔,牛的犟,豬的貪,狗的忠,種種動物特質始終影響著敘述者的觀察角度。“人性”則是指西門鬧的情感記憶以及作為人所擁有的社會關系。前兩者多是感知性視角,即通過眼耳口鼻等感官來獲取信息,后者則多為認知性視角,即敘述者的推測、回憶以及對人或事的看法等。當然,正如感知性視角和認知性視角在敘述過程中不能嚴格分離,“三性”也在彼此融合,形成“物”“我”合一的獨特視角。
在第五章《掘財寶白氏受審,鬧廳堂公驢跳墻》,當洪泰岳威逼白氏說出金銀財寶的埋藏地,白氏(原名白杏兒,西門鬧之妻)“連聲告饒”,此時,已轉世成為驢的西門鬧,看見妻子求饒感覺“我心悲傷,我心如熾,仿佛有烙鐵燙我屁股,仿佛有刀子戳我的肉”,而當西門鬧想通過親吻安撫白氏時,卻又困于驢形。于是,在外人看來,親吻就變成了——“白氏的頭被驢咬破了”。驢折騰,牛犟勁,豬撒歡,狗精神,動物的習性和外形,加上西門鬧的情感記憶,使敘述者不斷掙扎在人和動物、過去和現在之間。
西門鬧,去你媽個西門鬧,不要來擾我好事,我現在是一匹欲火中燒的公驢,一扯上西門鬧,哪怕是沉浸在他的記憶里,也必涉及血肉模糊,腐爛發臭的歷史場面。[6]
一邊以西門鬧情感記憶為代表的認知性視角,影響著此刻投胎為動物的“我”的敘述,使敘述者沉浸在過往回憶以及身為人的社會倫理關系之中,另一邊動物習性也在限制“人性”的過度膨脹,敘事視角的接連切換和彼此融合導致了敘述者的自身矛盾,“人性”和“物形”的撕扯也加快了整體的敘事節奏。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物”“我”合一的敘事方式使敘述者“我”兼具人性和物性,但隨著轉世投胎次數的增加,“人性”與“物性”之間的矛盾對立性也在逐漸消解,且呈現出“物性”壓倒“人性”的趨勢。同樣以對待白氏的態度為例,在第一世投胎為驢時,西門驢會因為發妻受辱,怒鬧公堂,當在第三世西門鬧作為豬十六重生時,對白氏卻只有模糊的印象——“因為土墻間隔,我看不到她的形象,但能聽到她的聲音。她的聲音那樣熟悉,那樣悅耳,但我卻回憶不起她的容貌和名字”[6]。西門鬧轉世成為狗小四后,小說著重描寫其嗅覺靈敏,送幼童上學,成為狗王等內容,雖然有描繪其狗兄弟姐妹的對話,但屬于西門鬧的仇恨與屈辱已鮮有出現,而轉世成猴之后,外貌的兇狠丑陋已經是這一世全部內容。
人與物的視角疊加,讓人聯想到卡夫卡的《變形記》,故事中格里高爾變成甲蟲后,雖然生活習慣上已經成為甲蟲,但仍具有人類意識,會關心妹妹的上學問題以及父親的債務糾紛。這與《生死疲勞》中所運用的“物”“我”合一的敘事方式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后者顯然更為復雜,主要表現在視角歷時性的積累上。作者首先讓藍千歲以追憶性的方式,再借用輪回的概念,使西門鬧每一世轉世成物的敘述,都是前幾世情感經歷的重疊,人與物的敘事情感上形成互補與重疊,正是這種視角的多重疊加、轉換和積累,才使得敘述者本身形象更為飽滿,形成巨大的敘事張力。
二、雙重序列的敘事時間
“敘事文屬于時間藝術”,“是一個具有雙重時間序列的轉換系統”[5]。其包含著兩個維度的時間:一,“被敘述故事的原始或編年時間”;二,“文本中的敘述時間”。作者可以抓住敘事文的這種雙重時間性質,通過調整時序,限制時限以及敘述頻率等方式,賦予敘事文可以根據一種時間去變化乃至創造另一種時間的可能,進而擴大文本的敘述空間。
在《生死疲勞》中,這種可能性具體落實為線性時間和循環時間的雙重組合,線性時間簡單來說就是時間呈一條直線發展,即過去—現在—將來,其特點是無始無終,單一同質可度量,海德格爾稱其為“流俗的時間”,循環時間最直觀的體現便是輪回,其特點是死生相續,不斷重復。
文本開篇說到“我的故事,從一九五零年一月一日講起”,隨即便展現了“我”在陰曹地府里被下油鍋的場景,閻王爺在“我”的痛苦哭喊中法外開恩,決定送“我”生還。當“我”在鬼差的押送下,以為能夠重返人間時,卻不料被鬼差抓住胳膊,將“我”用力往前一送,就此西門鬧便成了西門驢,故事也由此展開。此后每一世投胎時,這一過程都在不停地重現。并且,作者故意將結束語和開篇語設定為相同的一句話,使得故事在被講與被聽之間,開始和結束之間,又形成一次循環。這樣的時序安排以及刻意的高頻重復,構成了文本大致的外部敘述結構,而在分別敘述每一次投胎的故事時,《生死疲勞》又根據歷史的時間順序,依次安排土地改革、農村合作化、改革開放等重大歷史事件,填充文本的結構框架,形成文本的具體內容。由此,《生死疲勞》中“故事套故事”的特殊結構也逐漸清晰起來。
“故事套故事”的敘事結構在文本敘事中并不罕見,《一千零一夜》《十日談》便是如此,多體現在敘述者和故事內容的相互關系。如《一千零一夜》中,敘述者固定不變,而故事內容是不斷變化的。《十日談》中敘述者和故事相伴變化,不同敘述者講述不同的故事。或者如《在竹林》,不同敘述者從各自視角出發講述同一故事。而《生死疲勞》的敘事模式則有所不同,其一形成原因不同,其二造成的敘事效果不同。“輪回”和“線性”雙重時間序列,導致的嵌套式敘事模式,不僅極大地擴寬了文本對時間的包容力,勾勒出中國農村社會近五十年的變化與發展,更將歷史變遷囊括在個體生命的話語空間之下。
當西門鬧轉世投胎為驢、牛、豬、狗、猴,在每一世結束時,原本的故事節奏便由此中斷,陰間的鬼差、閻王爺便重新登場,為西門鬧開啟重生。在二十一章《再鳴冤重登閻羅殿,又受瞞降生母豬窩》中,冤憤交加的西門鬧“大鬧”閻羅殿,直言“那些沉痛的記憶像拊骨之蛆,如頑固病毒,死死地纏繞著我,使我當了驢,猶念西門鬧之仇;做了牛,難忘西門鬧之冤”。當西門豬因救兒童溺死時,面對鬼差,他仍怒氣沖冠,“你們這兩個混蛋,快帶我去見閻王,我要跟這條老狗算賬。”而當西門鬧作為狗小四死去時,他又來到了閻王殿前——
“西門鬧,你的一切情況,我都知道了,你心中,現在還有仇恨嗎?”
我猶豫了一下,搖了搖頭。
“這個世界上,懷有仇恨的人太多太多了,”閻王悲涼地說,“我們不愿意讓懷有仇恨的靈魂,再轉生為人,但總有那些懷有仇恨的靈魂漏網。”
“我已經沒有仇恨了,大王!”
“不,我從你的眼睛里,看得出還有一些仇恨的殘渣在閃爍……希望你在這兩年里,把所有的仇恨發泄干凈,然后,便是你重新做人的時辰。”[6]
從兩人的談話和后續情節中,我們可以看出,閻王并沒有采取強硬措施,直接消除西門鬧關于仇恨的記憶,而是讓其在一次次的輪回中逐漸淡化,直至完全消除才投胎為人。結合故事最前端的引言——“生死疲勞,從貪欲起。少欲無為,身心自在”,長達五十多年的歷史紛擾,在輪回的敘述機制下,似乎只是人的貪欲\仇恨等本性,在歷史上的一次輪回。作者在此使用輪回的敘事方式,并非將故事引入因果循環之中,而是在荒誕的形式下,講述現實的人的故事,并將具體的歷史統攝在個體生命之中,展現出對人自我情感、生命發展的關注。
三、敘事者之間的多重對話
文本主要采取三線并行、分頭敘述的敘述策略。三條敘事線索,分別是擁有前幾世記憶的大頭兒藍千歲、藍解放以及莫言。三位敘述者既是故事的參與者,也是故事的講述人,如在第一部驢折騰、第三部豬撒歡中,西門驢、西門豬為主要敘述者;第二部牛犟勁,以藍解放的視角敘述這一世;第五部結局與開端,則由莫言展開。三位敘述者雖各自承擔不同的敘述任務,但不同敘述聲音之間卻存在著互動和對話,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故事小說的引述。莫言雖然是第三個敘述者,但在前四部中,更多是故事中的一個人物,并未與藍千歲、藍解放進行直接溝通,而主要通過作品引文的方式,間接參與到對話交流之中。藍千歲在敘述過程中14次提及莫言的小說,其中《太歲》《黑驢記》《養豬記》《杏花爛漫》《撐桿跳躍》更以引文的形式出現在文本中。但藍千歲在引述過程中,總是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持調侃或質疑的態度。如《苦膽記》中,“用熊膽治病的事很多,但用人膽治病的事從沒聽說,這又是那小子膽大妄為的編造。他小說里描寫的那些事,基本都是胡謅,千萬不要信以為真”[6]。藍千歲的勸誡既是針對受述者藍解放,也是對萬千讀者而言,因此,小說的引述不僅借莫言之文,對故事情節作進一步補充,更悄然地將三位敘述者以及讀者相互關聯,引述的人是藍千歲,質疑的內容是莫言的作品,告誡的對象是藍解放與讀者。同時,既然藍千歲多次質疑莫言小說的真實性,那又為何要反復提及莫言的小說呢?并且這第三位敘述者的姓名、身份與現實中作者的筆名、身份相同,這似乎是在有意切斷現實和故事的界限,力圖打破“第三面墻”,將讀者引向更大的真實,試圖在讀者心中進行深層的情感對話。
其二,敘述者身份的轉換方式。分頭敘事以及內視角的敘述方式,導致三位敘述者必定面臨敘述身份的變換,即講述者和受述者之間會產生變化。在《生死疲勞》中,這樣的轉換時而直白,如在第五部開篇便直言不諱,“那么,就讓我們的敘事主人公——藍解放和大頭兒——休息休息,由我——他們的朋友莫言,接著他們的話茬,在這個堪稱漫長的故事上,再續上一個尾巴”[6];時而又隱晦模糊,如第二章《西門鬧行善救藍臉,白迎春多情撫驢孤》,在前章以及這章的大部分中,“我”始終代指的是承載著西門鬧的情感記憶的西門驢,而在本章結尾,敘述者的身份突然改變,“我”不再單指故事中的西門驢,而是在對話中,形成多個敘事主體。
“你知道誰是藍解放嗎?故事的講述者——年齡雖小但目光老辣,體不滿三尺但語言猶如滔滔江河的大頭兒藍千歲問我。”
“我自然知道,我就是藍解放,藍臉是我的爹,迎春是我的娘。這么說,你曾經是我們家的一頭驢?”
“是的,我曾經是你們家的一頭驢。我生于一九五零年一月一日上午,而你藍解放,生于一九五零年一月一日傍晚,我們都是新時代的產兒。”[6]
這樣的對話和互動,在第四部狗精神中呈現得更為清晰。第四部共有十七個篇章,首篇以西門狗的視角講述輪回為狗、“隨母進城”的故事,其次又以藍解放的視角,簡單介紹其生活狀況。此后,西門狗和藍解放的敘述視角便依次隔章變化,在此過程中,“我”時而是為情所困的藍解放,時而是盡忠職守的狗小四。接力式的交替敘述,形成一種對話、互證的關系,而在第五十章和五十二章中,藍解放和狗小四更是直接對話:
“你兒子繼續往前走。龐鳳凰跳到他面前,瞪著眼睛說:‘你聽到沒有?!”
“我們當時并沒有想到要遠走他鄉,我們只是想找一個僻靜地方避避風頭,然后通過法律程序,解決我的離婚問題。”[6]
兩位敘述者的同時出現,既打破了第一人稱視角的限制,又提供了第三者的旁觀視角,一人一狗“你一言我一語”地還原事件原貌,使其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節更加飽滿。同時,敘事者身份的轉變,中斷了原本的敘事節奏,將讀者從故事中短暫抽離,帶來多樣的閱讀體驗。
多樣的敘述聲音以及敘述者之間的溝通對話,讓人很容易聯想到巴赫金著名的復調理論,但深入探究后,會發現這僅僅是該理論泛化后的誤讀。巴赫金雖然曾經指出復調小說的特點在于“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7]。但倘若一部小說塑造出各色性格鮮明的人物且彼此之間互有對話交流,就能憑此判斷該小說具有復調敘事的特征嗎?這顯然過于武斷。實際上,巴赫金對此有過更為明確的敘述:“主人公的自我意識總是以別人對他的感知為背景。‘我眼中的我總是以‘別人眼中的我為背景。因此,主人公談論自己的語言,是受到他人議論他的言語的不斷影響才形成的。”“所有的主人公都激烈地反駁出自別人之口對他們個人所作的類似定論。他們都深切地感到自己內在的未完成性。”[7]由此可見,敘述者之間的對話交流只是復調小說的表象,更為重要的是,通過此種對話和交流,展現自我意識和他人意識的掙扎,以及主人公在掙扎中對自我意識的探尋。
因此,《生死疲勞》并非完全是巴赫金意義上的復調小說,人物之間雖有各樣的對話,但卻并不存在通過對話確證真實自我的樣貌,更多是通過對話形成情節上的互證和補充。當然,《生死疲勞》展現出來的對不同敘述者之間如何進行對話交流的嘗試,為小說敘事寫作提供了范例。
四、結語
從《酒國》中對倫理道德的擔憂和對物欲橫流社會的諷刺,到《蛙》對生育問題的反思,再到《生死疲勞》展示不同歷史進程下人“異化”的生存狀態,莫言始終保持對現實的關懷和對人的思考,并在此過程中,不斷進行形式上的探索。無論是“物”“我”合一的敘事疊加,還是雙重時間序列的運用,或是對敘述者多重對話形式的創新,都極大地擴展了小說的敘事空間,使其既能最大限度地呈現中國農村的變化發展史,又能展示人性中的變與不變。這樣的創新和堅持不僅在形式技巧方面對小說寫作技法提供具體可參考的范例,也在更高維度上為寫作者提供精神上的引領。
注釋
① 《當代文壇》2006年第2期便刊登了對《生死疲勞》的研究論文,《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緊隨其后,在第2期同時刊登兩篇針對《生死疲勞》的分析文章,而《當代作家評論》更是在第6期刊登十一篇針對莫言及其作品的文章。2012年隨著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莫言小說更是水漲船高,成為研究熱點,2015年《生死疲勞》的相關研究論文達95篇之多,此后雖然熱度稍退,但仍保持在年均30篇左右。
參考文獻
[1] 李敬澤.“大我”與“大聲”——《生死疲勞》筆記之一[J].當代文壇,2006(2).
[2] 周立民.敘述就是一切——談莫言長篇小說中的敘述策略[J].當代作家評論,2006(6).
[3] 皮進.多元敘事策略成就巨大敘事張力——莫言小說《生死疲勞》敘事藝術分析[J].文藝爭鳴,2014(7).
[4] 王璐.理論的迷霧——巴赫金“復調”小說理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運用[J].文藝研究,2015(7).
[5] 胡亞敏.敘事學[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6] 莫言.生死疲勞[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7.
[7]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M].白春仁,顧亞鈴,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8.
(責任編輯 夏? 波)
作者簡介:游雪瑩,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