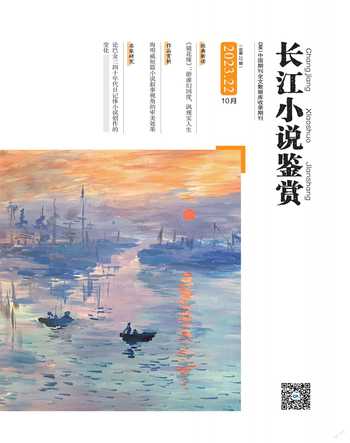無法進入的“城堡”與無處安身的“天堂”
[摘? 要] 卡夫卡的代表作《城堡》,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出卡夫卡無處安放的內心世界,也折射出一個“無家可歸者”的孤獨感、異己感與漂泊感。在《城堡》中,卡夫卡重點凸顯的是主人公K為尋求進入城堡而做出的倫理選擇,以及承擔不同選擇導致的各種后果。K的選擇是一種自身的內在倫理所致,也正是在這種不切合“城堡世界”實際的倫理選擇中逐漸虛耗自己的生命。使用文學倫理學切入小說,是從一種新角度觀照K的飄零命運與“城堡世界”中的非人倫理環境,亦是從一種新視域洞悉主人公K悲劇命運的主要成因——矛盾的倫理選擇。
[關鍵詞] 卡夫卡? 《城堡》? 文學倫理學? K
[中圖分類號] I1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22-0032-05
卡夫卡的作品經過譯介傳入中國后,國內文學界便掀起一陣又一陣“卡夫卡熱”。卡夫卡成為對中國當代文學影響最為持久、深遠的一位外國作家。卡夫卡140周年誕辰之際,仍有眾多學者試著對他具有“神秘感”的作品進行多元化解讀。此前,學者對小說《城堡》的研究集中于敘事特征、主題探究、人物分析及其“現代性”表現上,從文學倫理學角度對此小說進行研究的文章幾乎沒有。隨著文學倫理學批評在中國的發展與演進,有必要使用此種新興的文學批評理論對此前的經典文學文本進行再研究。《城堡》中主人公K的飄零命運在很大程度上與其自身的倫理選擇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正是K“不合常理”(不符城堡世界的常理)的倫理選擇使他永遠進入不了城堡,正如卡夫卡對猶太教搖擺不定的態度使他永遠找不到能夠放置心靈的“天堂”。
一、《城堡》中的倫理環境
文學倫理學中的倫理環境強調的是歷史存在的倫理環境也即文本中展現的倫理環境,故不能用如今的倫理眼光去看待先前文本中呈現的倫理環境,正如聶珍釗教授所言:“文學倫理學同傳統的道德批評不同,它不是從今天的道德立場簡單地對歷史的文學進行好與壞的道德價值判斷,而是強調回到歷史的倫理現場,站在當時的倫理立場上解讀和闡釋文學作品,尋找文學產生的客觀倫理原因并解釋其何以成立,分析作品中導致社會事件和影響人物命運的倫理因素,用倫理的觀點對事件、人物、文學等問題給予解釋,并從歷史的角度做出道德評價。”要研究主人公K的悲劇命運成因,就應該回到小說原有的倫理環境中。卡夫卡的小說《城堡》作為表現主義文學的代表作品,其文本本身就對時代、環境進行了模糊與隱藏,使得對其倫理環境的判斷與重構具有極大困難。但是,這并不代表無法從文學倫理學的角度出發對其進行解讀。聶珍釗教授在一次線上課程交流中表示,“文學倫理學”在文學表征形式破碎不堪的現代主義文學中依然是適用的,即文學的內在核心是由各種倫理因素構成,而現代主義以及后現代主義文學亦是如此,這些文學類型也無法逃離文學創作的基礎構成而單獨存在。
通過文本細讀,可以發現卡夫卡將小說的中心環境放置在城堡腳下的一個村莊內。城堡中官僚們制定的制度約束著村民,村莊中的人們對城堡極為畏懼。小說中,村民們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正如小說開頭所寫:“K到達時天色已晚。村子被厚厚的積雪覆蓋著。城堡山蹤影皆無,霧靄和夜色籠罩住它,也沒有一絲燈光顯示出這座大城堡來。K久久佇立在從大路通往村子的木橋上,仰視這看似空蕩蕩的一片。”城堡腳下的村莊呈現出與世隔絕的狀態,村民們無條件聽從城堡內官員的命令,在無意識中成為絕對權力的奴隸。而城堡對村民的控制可以分為顯性和隱性兩種形態。在小說中,城堡官員克拉姆對K的拒斥態度表現為一種顯性的控制。巴納巴斯的姐姐阿瑪利亞拒絕城堡官員馬爾蒂尼的求愛信以后,村民們對巴納巴斯一家的疏離則體現為城堡官員對巴納巴斯一家的隱性控制。可以看出,小說提供的倫理環境中充斥著人們的麻木不仁以及互不信任,城堡在人們無意識的情況下便完成了對村民的規訓,使村民成為極端權力下的奴隸。人們對權力的畏懼以及崇拜在文本中隨處可見。如大橋酒家的老板知道K有一層城堡內官員委任的身份后(“流浪漢”轉變為“老爺”),表現得誠惶誠恐。文中寫道:“老板坐在K對面窗臺的邊沿上,他不敢坐得更舒適些,并在這段時間里一直瞪大著他那雙棕色的眼睛戰戰兢兢地望著K。先前他向K身邊湊近過來,現在似乎他巴不得走開呢。他害怕K向他打聽伯爵的情況?他害怕他認為是‘老爺的K不可靠?K必須轉移他的注意力。”此外,村莊的整體倫理環境還體現出明顯的排外意識,謝瑩瑩教授論述道:“首先,它是個封閉而多禁忌的社會。在這封閉社會里,人人謹小慎微,生活在恐懼中。小說一開始我們就見到村民對陌生者的態度。他們排斥外來者不愿意接待K,拉澤曼說‘我們這里沒有好客的風俗我們不需要客人‘我們小人物謹守法規您不要見怪。可見與陌生人接觸是禁忌之一,這是他們的共識誰也不敢逾越禁忌界線。”至此,文本中的倫理環境也較為清晰地呈現出來——極端權力統治下的村莊,村民排斥異鄉人,同時十分懼怕城堡官員。此種環境深刻影響著人們的倫理價值選擇,而作為“異鄉人”的主人公K被卡夫卡放置進此種倫理環境時便產生巨大的矛盾沖突。正是在這種環境下做出的倫理選擇導致K怎么也進入不了城堡的悲劇命運,因為他是個身份飄忽不定的“異鄉人”,是一個從本源上被“城堡世界”所拒斥的人。值得注意的是,K飄忽不定的身份可以與卡夫卡自身結合來看。卡夫卡所處的環境使他成了一個“無家可歸者”,卡夫卡始終找不到屬于自己的合適位置與內心歸屬,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漂泊者、流亡者。總之,卡夫卡同K一樣無法真正確定自身身份,轉而成為“異鄉人”。
在當時的布拉格乃至整個奧匈帝國的倫理環境下,卡夫卡清醒地認識到猶太人生存的艱難,并且將這種生存困境通過一種類似于《饑餓藝術家》或者《變形記》中所運用的“異化”手法使其在《城堡》中具體體現。城堡中的倫理環境與卡夫卡所處的社會倫理環境密不可分。在這種倫理環境下,人們拼盡全力而艱難求生。不幸的是,無論他們如何掙扎,也只能漸漸淪為極端權力統治之下的奴隸,淹沒在“城堡世界”極端權力的洪流中。可見在小說的畸形倫理環境中,到達村莊的異鄉人K陷入了兩難境地。在這種困境中,K試圖進入不可能到達的城堡。歸根到底,K始終沒有融入這種倫理環境之中,所以他的倫理選擇也只能是一種徒勞之舉。
二、《城堡》中的倫理選擇
倫理選擇是文學倫理學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文學作品的一大主要構成要素。倫理選擇是人物面臨倫理上難以解決的矛盾沖突時,做出的一系列選擇。人物所做出的選擇,必然帶來相應結果,而人物也不得不承擔屬于自己倫理選擇的相關結果。傳統的文學道德研究,注重以今人之道德論前人之胸懷,而文學倫理學所強調的倫理選擇則是從當時的、歷史的以及文本中的倫理環境出發所做出的倫理選擇,即“在歷史的客觀環境中去分析、理解和闡釋文學中的各種道德現象”。小說重點突出的是主人公K的倫理選擇及其所承擔的后果,但是為了還原文本歷史語境中的倫理選擇,有必要研究其他兩位人物,大橋酒店老板娘嘉黛娜與信使巴納巴斯的姐姐阿瑪利亞。
大橋酒店老板娘嘉黛娜作為書中重要的人物,與主人公K有著明顯的聯系,正是她“病態”的倫理選擇給K帶來了有關“城堡世界”的重要信息判斷,影響到K自身的倫理選擇。嘉黛娜是城堡官員克拉姆遺棄的舊情人。20年前,克拉姆曾經召見過嘉黛娜三次,并且讓她帶走了幾樣信物。自此克拉姆再也沒有召見過她,而嘉黛娜卻始終惦記克拉姆,文中寫道:“白天我們沒有時間,我們接管這家酒店時酒店的狀況很糟糕,我們必須設法把酒店辦好,可是在夜晚呢?一年一年地我們夜里談話都只是圍繞著克拉姆和他改變主意的原因轉。如果我的丈夫談著談著睡著了,我就叫醒他,我們就接著談。”嘉黛娜與丈夫漢斯結婚后,夫妻兩人晚上的談話內容居然是何種原因導致了她與克拉姆失聯。在“第二次與老板娘談話”一章中,從嘉黛娜與漢斯步入婚姻的倫理選擇來看——僅僅是因為漢斯舅舅認為嘉黛娜是克拉姆的舊情人,從而沾染了些城堡內官員的“味道”,最后認同了這門婚事。這是畸形的倫理觀給人們帶來的病態倫理選擇,這種病態的倫理選擇揭示出“城堡世界”的倫理觀對村民的影響極其深刻。
信使巴納巴斯一家在文中承擔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小說正是通過敘述巴納巴斯一家由興盛到衰敗的悲劇命運揭示了城堡極端權力的恐怖。正是城堡官員對巴納巴斯一家的隱性控制,使得村民都疏離、排擠這個家庭,最后間接導致了這一家五人的悲劇。造成巴納巴斯一家悲劇結局的主要原因是阿瑪利亞拒絕了城堡官員所送的求愛信,于是這一家開始被村民排斥。與嘉黛娜接受克拉姆召見的倫理選擇不同,阿瑪利亞拒絕官員求愛的倫理選擇在“城堡世界”是一種“另類的”倫理選擇。城堡腳下的村民為了接近城堡、為了討好城堡的官僚階級可以不擇手段,做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倫理選擇,如弗麗達和嘉黛娜為了接近官員心甘情愿成為他們的情婦,又如巴納巴斯與他的父母為了得到官僚的原諒而不惜做盡一切喪失尊嚴的事。若是在這畸形的倫理環境中做出恰到好處且符合人性的倫理選擇,得到的往往是懲罰。而阿瑪利亞正是做出正常的倫理選擇后得到了“不正常的懲罰”。
嘉黛娜與阿瑪利亞的倫理選擇呈現出“城堡世界”的荒誕倫理,并且可以從中窺見主人公K的悲慘命運。主人公K作為異鄉人被放置到“城堡世界”之初,就反復做出“錯誤”的倫理選擇,強烈地反抗城堡官僚們所制定的規則。K從進入村莊后就開始打破村莊原有的倫理環境,反抗大橋酒店老板以及施瓦爾策的要求,反對大橋酒店老板娘以及村長的教導。K一直按照自己的判斷去努力尋求進入城堡的方法,他做出的各種倫理選擇與城堡強權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馳。此外,最為值得關注的便是在敘事的推進過程中,K做出的一個關乎其命運的倫理選擇,即拐騙城堡官員克拉姆的情人弗麗達。K拐騙弗麗達的目的是激起克拉姆的憤怒、吸引克拉姆的注意。歸根到底,K是想借助弗麗達這個女人來接近克拉姆,以實現自己進入城堡的目的。但是,自從與弗麗達通奸之后,K卻離自己的目標越來越遠,得不到進入城堡的一絲機會。K選擇與弗麗達通奸,從倫理選擇上已經是一個明顯的錯誤。
卡夫卡深受猶太教的影響,在猶太教徒所堅信的教義“摩西十誡”中,上帝借助摩西之口明確訓誡人類“不可貪婪,不可圖謀鄰人的房舍、仆傭、牛和其他屬于鄰人的一切財物”。這也正是要求人們保持內心的純凈,不允許通奸行為的發生,犯下此罪行的人們必定受到上帝的懲罰,也必然無法接近天堂的安樂。這既是一種宗教教義,也是一種約束世人的倫理價值標準。主人公K明顯犯下通奸罪行,這也使他永遠進入不了自己的“天堂”。正如有學者論述道:“小說以樸實的語言為讀者描述了一個神秘莫測的城堡。它時刻存在著,卻又無法看見;它是一個實體,卻又是一個幻象;城堡如同一扇門,它將人類生存的空間劃分成兩個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一個是非現實世界,而它正是現實世界與非現實世界的連接點。”小說的文字本身便具有明顯的象征意味,“城堡”此意象也有著闡釋不盡的含義,筆者認為“城堡”的存在形態與人們腦海中的“天堂”形象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世上的人們從沒有見過“天堂”,卻一直為了能夠窺探天堂或者進入天堂而做出種種沒有結果的行動。正因如此,K注定永遠無法進入城堡。K貫徹到底的倫理選擇便是反抗城堡所制定的規則,這種倫理選擇下的K離自己的目標越來越遠,進入城堡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三、《城堡》中的倫理身份
在《城堡》一書中,主人公K的倫理身份隨著敘事推進而發生改變。來到異鄉的K,首先就對自己的身份產生了疑惑,而在“城堡世界”的混亂倫理環境中生活得越久,就越是加重了K對自身身份的懷疑。城堡自身存在的絕對神圣性(猶如天堂般的“神圣性”)讓K堅信“城堡”這一模糊的形象是自身在身份認同過程中的終極“他者”(借用拉康“鏡像”理論來說,“自我”的建構過程中必然存在作為“鏡子”的他者),只有進入城堡才能夠真正確證自己的身份,達到一種倫理層面的身份認同。在《城堡》一書中,故事的主線是以K尋找自身“土地丈量員”的身份作為線索的。主人公K倫理身份的幾次轉變,使其進入一種矛盾的循環,最終導致了K的悲劇。“在文學文本中,所有倫理問題的產生往往同倫理身份相關”,K矛盾的倫理身份導致了他的倫理困境。
K的倫理身份隨著故事的推進,發生過幾次變化。首先,在K來到大橋酒店時,他的倫理身份處于建構期,其總體身份是“無人知曉的外鄉人與官員欽定的土地測量員”。此時,“城堡世界”的村民因K的雙重身份對他產生一種矛盾心理,既想要疏離又不敢招惹。所以,在這種矛盾的倫理身份中,主人公K始終找尋不到自己合適的位置,在大多數情況下他的倫理身份仍然是經過漫長旅途來到此地的“異鄉人”。正如曾艷兵教授論述道:“他們散居在世界各地,始終是外來人,陌生人,他們也因此而受盡了排斥和歧視。對于K而言,他就是這樣一個永遠的陌生人。他找不到適合于自己的工作,尋覓不到愛他的妻子,沒有家,沒有兒女,沒有歸屬,永遠是一個孤獨的不被人理解的‘漂泊者。”在這“異于他者”的倫理身份之下,K得不到他人的信任與理解,更無法證明自己身份的純潔。其次,便是K被村長、大橋酒店老板娘與教師等眾人排斥的階段。此時,K丟失了自己的土地丈量員身份(或者說是丈量員身份被刻意模糊化),K的倫理身份進入真正意義上的停滯期。他的總體身份轉變為“克拉姆情人的戀人與學校的校役”。在這種倫理身份下,K任人宰割,不管是村長還是學校里的男女老師,都可以隨意指使與侮辱他。K就此進入一種倫理困境。由于倫理身份的主體層面是克拉姆情人的戀人,他遭受了各種敵視。在城堡腳下的村莊中,村民的倫理判斷是,與城堡官員作對便是與自己作對,K帶走官員克拉姆的情人弗麗達,這一做法明顯觸怒了村莊中的眾人。最后,K與弗麗達分開并且重新審視自己來到城堡世界的目的,恢復“異鄉人”的倫理身份。正是在此階段,K與城堡重新保持了距離,也正是在這種間隔中,K才能再次審視城堡的存在。小說最后寫到K來到貴賓酒家,洞察到官僚階層運作的隱秘一角。至此,K終于感知到自己行動的徒勞,進入了一種持久的困頓期。在這個時期,K因為種種條件的束縛而感到疲倦,甚至與一位官員的重要會面都感到索然無味,全無心思與其進行交談。最終,K從一個“異鄉人”的倫理身份轉化為“流亡者”的倫理身份。流亡比死亡更加可怕,因為流亡時的絕望感、孤獨感、飄零感猶如冬日凜冽的寒風吹入流亡者的脊髓。卡夫卡在此對猶太人的命運進行了深思,將飄零、孤獨與流亡的猶太人群體形象凝聚到主人公K一人身上,這一過程也正是猶太群體經驗在主人公K這一客體的投射。
本雅明針對卡夫卡的作品評論道:“卡夫卡的作品像一個圓心分得很開的橢圓;這兩個圓心一個被神秘體驗(尤其是傳統的體驗)支配著,一個被現代大城市居民的體驗支配著。”K在城堡腳下村莊的離奇經歷切合本雅明所說的神秘體驗,伴隨著這種神秘體驗的便是K變幻莫測的倫理身份,并且在身份的不斷轉換中留給讀者漂泊、異己與孤獨的總體感受。而正是這些感受,使讀者不得不聯系作者的身份。卡夫卡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的布拉格,對倫理身份進行著深刻思考。也正是這種“無家可歸”的倫理身份,造就了卡夫卡筆下眾多漂泊與孤獨的人物形象。
四、結語
K始終不能進入城堡,他只能作為一個異鄉人永遠地困在城堡腳下的村莊。這種漂泊命運之下,潛藏的是“城堡世界”不合理、非人的倫理環境。K面對種種阻礙他進入城堡的人與事時,做出了自己的倫理選擇,但也正是這種矛盾的倫理選擇與不斷轉變的倫理身份使他逐漸走向生存困境與悲劇命運。小說中,K竭盡全力也無法進入城堡與卡夫卡心中的漂泊感、異己感與孤獨感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卡夫卡身為奧匈帝國統治陰云下的一個小職員、小人物與“地洞式”作家,就如同K無法進入城堡一樣,無法尋覓到屬于自己的“天堂”。通過文學倫理學對《城堡》進行觀照,可以洞悉主人公K的矛盾倫理選擇與悲劇命運成因,也是從全新角度對卡夫卡經典作品的重新發掘。
參考文獻
[1]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基本理論與術語[J].外國文學研究,2010,32(1).
[2] 卡夫卡:城堡[M].張榮昌,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
[3] 謝瑩瑩.卡夫卡《城堡》中的權力形態[J].當代外國文學,2005(2).
[4] 田俊武.論宗教倫理學與文學倫理學視域下的卡夫卡小說[J].外國文學研究,2016,38(4).
[5] 李靚.論《城堡》的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雙重特征[J].當代文壇,2017(6).
[6] 曾艷兵.為什么是土地測量員?[J].文藝理論研究,2019,39(5).
[7] 阿倫特.啟迪:本雅明文選[M].張旭東,王斑,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
(責任編輯 夏? 波)
作者簡介:陳宇昕,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