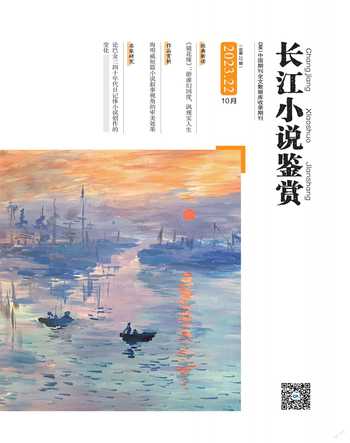從創傷角度解讀石黑一雄《上海孤兒》中的延宕
[摘? 要] 《上海孤兒》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偵探小說,其中的案情也并非撲朔迷離,只要尋回關鍵的記憶,當年的真相就能水落石出,不過主人公班克斯總是延宕對父母失蹤事件的回憶,讓真相的揭示一再推遲。班克斯的延宕不僅表現在其回憶上,還表現在他麻木和不正常的狀態上。小說人物的延宕實際上與創傷有關,創傷具有延宕性。為了塑造出一個創傷人物,作者使用了延宕手法,而在敘事中,創傷與延宕也是無法割裂的。
[關鍵詞] 石黑一雄? 《上海孤兒》? 創傷? 延宕
[中圖分類號] I106?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文章編號] 2097-2881(2023)22-0059-06
在小說開篇,石黑一雄就設下了班克斯父母失蹤謎團的懸念,還給班克斯設置了著名偵探的身份,給讀者以心理期待,不過主人公卻因為未明說的某種原因拖延上海破案之行。而在主人公到達上海之后,作者又故意設下障礙,讓人物花費大量時間追查一條錯誤線索,繼續擱置事件的進程,無限制地拉長延宕的距離,距離越長,緊迫感就越強。最后班克斯在交戰區尋找房子的驚險過程使情節達至一個小高潮,不過在這之前,種種跡象暗示班克斯進行了一場無意義的冒險。班克斯被日本軍官護送出交戰區,情節暫時緩和,故事發展至此,作者結束了延宕。在英國領事館,班克斯在市政局官員格雷森的安排下見到了“黃蛇”菲利普,父母失蹤的真相以菲利普直接告知的形式揭開,并且與班克斯所相信的虛構真相截然相反。父母的失蹤與反對鴉片貿易無關,父親與情婦私奔,母親則是被軍閥顧汪擄去。
以偵探破案為主線的小說卻通過“機械降神”的方式揭示真相,班克斯作為一名著名的大偵探,卻固執地沿著錯誤的線索尋找父母,行事缺乏理性,這些都讓人產生疑惑。不過小說的日記形式已經暗示出其重心不在破案,而在于描寫主人公受到童年經歷的影響以及與痛苦和解的過程。小說的全部內容是由班克斯的記憶拼湊起來的,主人公尋親的線索主要依靠記憶的拼接,可以說,記憶才是破案的關鍵。在童年經歷的陰影下,班克斯的記憶明顯是不正常的,存在著缺失、固著和真假相混的情況,他需要較長時間逐步找回真正的記憶,因此人物記憶明顯有著延宕的特征。受到童年經歷和記憶的影響,小說人物處于一種麻木和非正常的狀態,總是延宕尋親的進程。小說的敘事也是延宕的,表現為混亂的邏輯,敘事的延宕實際上正好與人物和記憶的延宕相配合,而小說中人物及其記憶明顯受到童年創傷事件的影響,所以小說中的延宕都與創傷密切相關。
一、延宕與人物的創傷記憶——虛構、空白和停滯
虛構的故事與真實的事件交織在班克斯的童年記憶中,班克斯與朋友哲在偵探游戲中編造的故事混入了原本的記憶,父母被囚禁在一所房子并受到尊敬和優待的想象與原初破碎的記憶拼接,他已經分不清真實和虛假。雖然模糊的記憶中有諸多疑點,他仍篤定地把父母被綁架的原因歸結為反對和阻撓英國傾銷鴉片的正義行為。
班克斯在偵探游戲中不斷地演繹父母失蹤案的過程及各種可能性,最終在諸多想象的偵探劇本中選擇了自己最能接受的一種,而將自己不能夠承受的可能性忽略。一方面班克斯知道菲利普的某些話語和行為頗有嫌疑,但是他不愿意去細想和深究。另一方面他把父母的遭遇美化,賦予父母的失蹤以正義因素,也因此誤以為父母會受到尊敬和優待,父母被虐待的種種可能對班克斯來說過于刺激,他不自覺地逃避此類的猜測。“當意識選擇最理想的解釋一遍又一遍敘述給公眾或自己聽時,久而久之,記憶很有可能產生丹尼爾·謝克特所說的‘錯源。”[1]班克斯為了尋求心靈的安慰,把自己幻想的記憶當成真實的情況,模糊虛構與真實的邊界。之后,班克斯以失真的記憶為依托,在上海開展偵探工作,而虛假的記憶線索必然會導向錯誤的方向,并進一步導致真相的延宕,同時也延遲了真實記憶的恢復。
在回憶過去時,班克斯總是有意或無意地逃避某些會引發痛苦的創傷記憶,這造成了記憶的多處空白,也即創傷記憶的延宕。他對一時安寧的尋求又造成了行為和情節上的延宕。班克斯故意拖延對菲利普叔叔記憶的回想,他曾明確地表明自己的心跡:“即便是今天,回想起我同菲利普叔叔的關系是怎么結束的,心中仍感到隱隱作痛。”[2]與菲利普相關的記憶總是牽連著心中的創傷,當回憶初次涉及菲利普時,班克斯明顯采取了逃避的方式,他拒絕繼續深入回想:“但此刻我不希望回憶菲利普叔叔……這么想也許很傻,不過我向來覺得菲利普叔叔還是繼續以不太具體的形象只留在我記憶中為好。”[2]班克斯還總是逃避父母爭吵的相關記憶。父母的矛盾和父親的異常表現讓他感到不安,所以他常常中斷回憶,轉而回想與童年玩伴哲的快樂時光。父母的婚變給年幼的班克斯帶來創傷,再度回想會給現在的他帶來痛苦,所以他為了緩解痛苦,以與哲的回憶替代對父母的記憶。弗洛伊德研究創傷神經癥時發現,病人不是主動地抗拒講述自己的故事,而是被動地遺忘了過去的經歷。“在病人的歇斯底里癥狀的背后,潛藏著一些處于‘被扼殺狀態的痛苦情感,這種情感與一種從意識中被切斷的記憶相關。”[3]病人阻滯了創傷記憶,直至與創傷相似或有關聯的事物或信號出現,如初次體驗般的痛苦情緒就會被激活。無論是神經癥患者還是正常人,在處于焦慮、緊張等不良的心理狀況時,都會不自覺地以各種方式逃避那些刺激而恐怖的記憶,以尋求內心的安寧,班克斯就是這樣,在這種情況下,其創傷記憶被延宕,在意識層面的記憶痕跡中呈現為一個個“空洞”。
人類的記憶可劃分為敘述記憶和創傷記憶兩種。創傷記憶不能以正常的方式保存,停滯在意識中,經過很長時間也不發生改變,因此“許多受創者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就如同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中,即創傷的世界和當前正常的世界,通常他們很難將這兩個世界聯系起來。”[4]童年時的父母失蹤事件停留在班克斯的記憶中,多年過去,上海局勢巨變,曾經的家早已易主,而他仍然認為父母還生活在他們失蹤的地方,還被囚禁在那座幻想的房子中,他絲毫沒有意識到這種想法的荒唐,有時還計劃著找到父母后該如何安排。“創傷停止了時鐘,使得那一刻永遠停留在記憶和想象中,絲毫不受時間推移的影響。”[5]在他的意識中,創傷事件停留在發生的狀態,與他的現實生活不處于一個時間維度,潛意識里他不愿去思索事件會隨著時局的惡化將如何發展,從而以為事件還停留在30年前的狀態,可以擱置,慢慢地尋找線索。記憶固著在意識中,沒有時間感,所以班克斯一再拖延到上海的計劃,而不去上海就可以不用直面創傷,這拖延亦是創傷延宕期防御作用發生的體現。作為一個著名的大偵探,班克斯不講究邏輯,不直接追查關鍵線索,將不相干的“武昌樓槍殺事件”和父母綁架案聯系起來,莫名地認為父母就在那所未被搜查的房子里,他甚至不顧危險,穿越交戰區,抵達房子后,還執意在不可能有人的廢墟里翻找。班克斯在停滯的創傷記憶的影響下做出了許多浪費時間和精力的無關行為,延遲了真相的揭示。
二、延宕與人物的創傷表現——班克斯的麻木和非正常
創傷以其巨大的精神破壞力使當事人無法正常運用認知和理解的能力,因此創傷事件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無法真正進入人的意識和記憶,受害者往往沒有意識到發生了什么,更認識不到創傷的發生意味著什么,從而在表面上呈現為正常的狀態,也就是一種“麻木”的狀態。《上海孤兒》中,班克斯對父親的失蹤沒有什么激烈的反應,反而他更在意自己與好友哲的諾言,這是因為班克斯只認識到與哲失約會破壞兩人的友誼,而父親失蹤的嚴重性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疇。班克斯還未走出父親失蹤的陰影,母親就繼而失蹤,之后,他很快被人們安排回到英國,由姑媽收養。班克斯雖然是英國人,但是他自小居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英國對他來說是陌生的地方,算不上故鄉。父母失蹤后,班克斯被迫離開最親密的朋友和“家園”。接二連三的打擊讓班克斯一時之間無法理解在他身上發生的事情,再加上班克斯尚且年幼,認知能力有限,他從未想過父母不會再出現了,而是天真地相信上海的偵探們能很快把父母找出來,因此他沒有感到悲傷,反而表現出異常的冷靜。在創傷的潛伏期,由于對創傷的不可理解,創傷的后果被延宕了,不過創傷終會再次出現,之后則是連續的延遲和回歸。班克斯選擇與莎拉私奔,在菲利普講述真相時陷入痛苦,找到母親后放棄相認,這些都是班克斯創傷再次出現的表現。
麻木不等同于正常,受害者正常的表面下潛藏著一些異常的端倪,而這些端倪也暗示著受害者正處于創傷延宕期和潛伏期。班克斯表面上是個事業頗為成功的正常人,不過在其表面的正常中可以發現許多端倪,這些端倪就是班克斯諸多異常的行為和不可靠的記憶。班克斯初到英國的異常行為通過姑姑的評價間接呈現:“這種年齡的男孩,老這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對身心健康不會有什么好處……我是說我得阻止他繼續這樣自我反省。”[2]班克斯在初到英國的幾個星期里常常扮演哲的角色,模擬在上海時同好友玩偵探游戲的情景,在想象中一遍遍地上演解救父母的戲碼。自父母失蹤后,班克斯一直表現得很冷靜,沒有撕心裂肺的痛苦,這一點讓他周圍的大人們很驚訝,不過姑姑發現了他的異常。班克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通過偵探游戲在想象中解救父母,以此逃避潛藏的內心痛苦,通過幻想編織記憶,將父母的處境美化,在創傷的潛伏期,殘酷的真實記憶被班克斯無意識地阻滯。除此之外,班克斯的異常還表現為他對別人評價的過度敏感,姑姑的這句評價被班克斯偷聽到,自此之后,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是正常的,他總是刻意地改掉或模仿一些行為。父母的失蹤使班克斯失去依靠,讓他處于一種不被認同的不安之中,他十分在意作為唯一親人的姑姑的評價,自此之后,班克斯就盡量避免再次流露出“自我反省”的跡象,壓抑自己,“只在想象中盡情上演和哲玩過的種種偵探劇目”[2],他努力裝出正常的樣子,而這種行為恰恰是異常的。
三、延宕——創傷敘事的效果
《上海孤兒》中的創傷敘事與傳統敘事不同。作者有意打亂時間的順序,破壞故事的邏輯,以人物的幻想記憶填補線索的空缺,使敘事呈現出碎片化和不可靠的特點,從而阻礙案件的進展,達成延宕的效果。
敘事的碎片化“徹底打破了傳統小說線性的敘述鏈,而進入了一個任意組合、拼接的疆域”[6]。《上海孤兒》敘事的碎片化首先表現為時間的無序性。以第二部的記憶敘事為例,班克斯的回憶順序具有隨意性,第二部開篇敘述班克斯對好友哲的回憶,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固執的哲對母親表現出奇特的畏懼感,但是在他看來母親對哲向來溫柔友善,由此他追憶起和哲共同目睹母親斥責衛生檢察官的往事。但是作為旁觀者的班克斯在審視這段記憶時卻產生懷疑,然后由母親的話語想起一段父母爭吵的事。班克斯的回憶不以時間順序延續,而是由一段記憶中的某一點觸發聯想,引起下一段記憶。班克斯對父親失蹤前的回憶也是無序的,在哲離開的那個秋天,有關父親幾件小事的記憶較為清晰,不過這些記憶不以時間關聯,它們都是班克斯對父親異常表現的零碎印象。
傳統的小說敘事依靠邏輯的支撐,要求故事情節環環相扣,碎片化敘述則故意弱化故事的邏輯關系,這也符合人物受創后邏輯混亂的特點。在《上海孤兒》中,作者故意留下邏輯空白,以省去某些關鍵信息,使讀者陷入迷惘。《上海孤兒》分為六部,每部都設置了準確的時間。第二部結尾班克斯追憶到母親失蹤,在這段回憶中,他想起一些頗有嫌疑的細節——菲利普叔叔古怪的行為以及讓母親失態的軍閥顧汪。班克斯也表示他計劃不久就去上海全面調查父母的失蹤案。但是他真正到上海卻是在1937年,拖延了整整六年,如果不是第三部中一些事情的推動,他可能還要推遲上海之行,不過作者并沒有詳細地敘述主人公這六年的經歷。另外,關于那封讓班克斯決定出發的信,作者也只是一筆帶過。第四部和第五部中,班克斯一直要求面見“黃蛇”并且不懈追查“武昌樓槍殺案”,但是已經結案的事件怎么會與多年前兩名英國人的失蹤有關,該情節邏輯鏈是斷裂的,故事的結尾,作者則安排菲利普作為“黃蛇”,直接將所有的真相揭開,用偶然性繼續打破敘事的邏輯鏈條。從延遲的六年到班克斯調查無關事件的拖延,作者的碎片化敘述達成了情節上的延宕,其中破碎的邏輯給讀者留下許多謎團,或許邏輯的破碎正是暗示創傷給班克斯帶來的心理異常。
與傳統小說不同,石黑一雄在《上海孤兒》中摻入了不少虛假的內容。在錯誤線索的指引下,主人公沿著錯誤的道路前進,與真相漸行漸遠。小說中,班克斯不止一次直接表明自己是一個不可靠敘事者,也不止一次以客觀的姿態表示這些回憶“不乏事后想象的成分”。由于年代久遠和兒童記憶能力的限制,敘述者的記憶總是模糊不清。此外,敘述者的一些回憶出現了自相矛盾的情況,不可靠的記憶表現為同學印象和班克斯記憶的矛盾。在同學奧斯本的印象中,學生時代的班克斯是一個大怪人,而班克斯卻對這句評價感到迷惑和惱怒,在他自己的記憶中,他完美地融入了校園生活。在上海,老同學摩根回憶起學生時代時說:“我想我們早應該攜起手來。兩個可憐的孤獨孩子。”[2]班克斯聽到這句話非常驚訝,他認為孤獨陰沉的是畢格沃斯,但是摩根否定了他。
敘事的不可靠性還體現在敘述者通過添加主觀的想象重構出的完整記憶。在治愈創傷或者試圖直面創傷時,為了避免過度的痛苦,受創者只能斷斷續續地回憶創傷發生時的情況,有時還在回憶中夾雜著自我欺騙的幻想和假設以求取心靈上的安慰。班克斯早已在無數的偵探游戲中設想過父母失蹤的諸多可能性,最后在無意識中,他把父母因反對鴉片而被囚禁于一所房子的幻想當作事實,融入記憶,由于虛構的不合常理和與現實的矛盾,讀者很容易就能看出班克斯為了逃避現實,改寫了記憶。后來班克斯依據錯誤的記憶追查線索,他甚至冒著生命危險找尋那所不存在的房子。石黑一雄通過不可靠敘述阻礙主人公的破案進程,完成了敘事上的延宕,這一延宕同時也與人物的創傷癥狀相符合。
四、延宕——創傷敘事的特點
石黑一雄曾說過:“我所寫的是關于個體如何面對痛苦的記憶。”[7]書寫創傷是石黑一雄創作欲望的源頭之一,他在采訪中曾不止一次地表達自己作為文化邊緣人的失落:對于日本文化,他始終無法有心靈深處的共振;而在英國,由于其日裔的身份,他總是懷有一種疏離感和遠離故土的漂泊感。除卻文化上被邊緣化的失落,還有幼年時被迫與爺爺分離的痛苦。分離使親情淡漠,漂泊使心靈空缺。對石黑一雄來說,創作是撫慰內心憂愁和傷痛的有效辦法。《上海孤兒》的主人公班克斯就是一個文化邊緣人,他短暫又快樂的童年時光屬于上海的公共租界,雖然他努力地英國化,但他還是和哲一樣心底里更留戀上海。可惜租界終歸是強國欺凌弱國的產物,不能長久地存在,這注定班克斯要為無根的飄零感所憂愁。小說人物身上處處有作者本人的身影,石黑一雄把寫作視為抒發憂愁或者遺憾并以此療愈心靈創傷的手段,那么班克斯遠赴遠東,找尋創傷源頭,調查父母失蹤事件的過程也是展現和療愈創傷的過程。
如何書寫人物的創傷呢?創傷必然會引發人特殊的心理反應,并對人的記憶、意識等有著特別的影響,因此作者對于人物心理和記憶的描寫需要與創傷的相關理論相符合,或者說作者對創傷有著深刻的理解,其筆下塑造的人物會“自動”地開啟心理防御機制,書寫的記憶亦自然呈現出創傷的影響。為什么《上海孤兒》的書寫有著明顯的延宕特征?這是因為創傷與延宕是不可割裂的兩個概念,延宕不僅是創傷之后的一個環節,也是創傷發生及其影響的標志和體現。創傷與延宕的密切關系不僅體現在文學書寫上,還有著心理學研究基礎。弗洛伊德曾提出創傷壓倒性的即時性導致其延遲的不確定性,卡魯斯在前者研究的基礎上發展了創傷具有延宕性和潛伏期的觀點。她認為創傷事件有時會超出人的認知和理解能力,在記憶痕跡中呈現為一個空洞,同時這也是人的最大防御形式,即通過絕對麻木防御創傷,所以創傷具有延宕性[8]。她還指出弗洛伊德對創傷的核心見解應是:“創傷事件的影響恰在于它的延宕性,在于它拒絕被簡單地定位。”[8]創傷的經歷和延宕的真相不在于對某一現實事件的遺忘,而在于經歷本身內在的延遲。創傷的力量不僅在于遺忘經驗的重復,還在于由遺忘導致的如同初次體驗的壓倒性感受。另外,正是內在的潛伏期矛盾地解釋了創傷特殊的暫時性結構和延宕性:由于對創傷的不可理解,創傷性事件在發生時沒有進入人的意識,它只有在與另一個地點和另一個時間相聯系時才顯現,即以延宕的形式回歸,這造成了事件的重復和閃回。創傷的延宕性和潛伏期在有意識記憶層面表現為一種空白,它們都屬于無意識的范疇[8]。在弗洛伊德和卡魯斯那里,延宕性成為創傷發生及其影響的標志和體現,這從后者給創傷下的定義中亦可得見:“創傷描述的是一種突發或災難性事件的壓倒性經歷,在這種經歷中,對事件的反應常常是延遲的、無法控制的幻覺和其他侵入性現象的重復出現。”[9]Andrew Barnaby認為卡魯斯的延宕強調一種時間上的“錯過”,創傷以壓倒性的姿態出現,而受害者并沒有做好理解和接受的準備,也就是說,在創傷正在發生時,受害者從未清醒過,不過雖然“錯過”了,創傷事件卻不是一個能簡單拋在身后的東西,它潛伏著,在某些情況下以強迫回歸的形式進入記憶。Andrew Barnaby發展了前人關于延宕性的觀點,提出延宕不僅指創傷記憶的延遲出現和延遲影響,還是創傷記憶的形成條件[10]。
《上海孤兒》書寫的是主人公班克斯在童年時失去父母及獨在異國飄零的創傷經歷以及與痛苦記憶和解的心路歷程。作者壓縮了小說推理、尋找線索等內容,這同時也是一種延宕,比如真相的揭示直接以“機械降神”的方式完成,這就為展現人物的心理和記憶留下充足的空間,或者說正是創傷心理和記憶的書寫導致了延宕,所以其他與偵探相關的內容被壓縮。另外由于創傷具有延宕性,所以《上海孤兒》中人物的創傷心理反應和創傷記憶會不可避免地表現出延宕的特征。心理反應的延宕主要體現在人物麻木的狀態上,這與心理防御機制中的壓抑相照應。弗洛伊德在研究創傷性神經癥時提出創傷具有壓抑的特征,且存在一個潛伏期。在《超越唯樂原則》中,弗洛伊德認為“記憶痕跡與它們曾否是有意識的東西無關”[11],從未進入意識狀態的記憶痕跡通常最強烈、最持久。在清醒的狀態下,無意識的東西被壓抑。小說中的創傷人物不只有班克斯,這種壓抑在他的養女身上也體現出來。珍妮弗突然提起父母:“在學校的時候,有時會忘記。只是有時候。我會像其他女孩一樣掰著手指頭算日子,看離放假還有多久。然后就想又可以見到爸爸媽媽了。”[2]在經歷過父母的死亡后,詹妮弗似乎喪失了對痛苦、失落等情緒的感知,面對消極的事,她總是給出不同尋常的反應。行李箱遺失后,詹妮弗沒有表現出絲毫的傷心,甚至還因為可以獲得賠償而很快樂。在學校里,雖然床單都是冰碴,一些同學排擠她,她還是表現出學校生活很愉快的樣子,這些表現是創傷延宕的體現,她在麻木自己對痛苦的感覺,用積極情緒沖淡消極情緒,但是創傷并沒有消失,它被壓抑到意識底層。
創傷敘事與傳統的敘事方式不同。由于創傷的不可理解、重復等特性,小說中的創傷敘事不可避免地帶有延宕性的特點。卡魯斯認為:“創傷攜帶著一種使它抵抗敘事結構和線性時間的精確力量。”[12]由于創傷的即時性和不可理解性,作者一般以書寫創傷記憶來展現受創者的內心。創傷記憶具有碎片化、非理性、不可靠性等特點,所以完整詳細的敘事不會出現。書寫創傷時,作者還需要模仿創傷癥狀以及患者回憶過去的狀態和敘述記憶的方式,這些在敘事中具體表現為前后矛盾、邏輯不通、言辭閃爍和詞不達意。石黑一雄在《上海孤兒》通過書寫人物面對創傷事件的心理狀態和記憶,以形式的復雜搭建起一座充滿誤導和不確定的迷宮,成功將創傷的真相隱匿,同時也達到延宕的效果。
五、結語
小說開篇,疑案、偵探、異國等元素讓讀者期待主人公如何運用縝密的推理和巧思破解這樁謎案,不過《上海孤兒》不是傳統的偵探小說,而是一部創傷小說,并且有著明顯的延宕特征。小說所展現的被創傷陰影籠罩的人的心理和記憶狀況具有明顯的延宕性:創傷發生后,在心理防御作用下,受創者處在麻木的非正常的狀態中,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回避、壓抑或扭曲有關創傷的記憶,而當他們決定面對和療愈創傷時,為了減輕痛苦而虛構的記憶又導致新的迷惘和混亂。在敘事方面,作者以延宕手法配合創傷敘事,達成延宕情節的效果:受創者總是有意或無意地在心理上乃至行動上阻滯對創傷事件的追尋,小說中主人公對過去創傷的躲避直接導致真相揭示的延緩。除了《上海孤兒》,石黑一雄書寫的其他創傷小說《浮世畫家》《群山淡影》等也有延宕的特點。
參考文獻
[1] 鄒濤.敘事記憶與自我[M].西安: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2017.
[2] 石黑一雄.上海孤兒[M].陳小慰,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11).
[3] 趙冬梅.弗洛伊德和榮格對心理創傷的理解[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6).
[4] 周穎.創傷視角下的石黑一雄小說研究[D].上海外國語大學,2014.
[5] Langer L.Holocaust testimonies:The ruins of memory[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
[6] 張學軍.中國當代小說中的現代主義[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
[7] Hunnewell S.Kazuo Ishiguro:The Art of Fiction No.196[J].Paris Review,2008.
[8] Caruth C.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
[9] Caruth C.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10] Barnaby A.Coming Too Late:Freud,Belatedness,and Existential Trauma[J].SubStance,2012,41(2).
[11] 弗洛伊德.超越唯樂原則[M]//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12] 懷特海德.創傷小說[M].李敏,譯.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11.
(責任編輯 夏? 波)
作者簡介:馬晶晶,蘭州大學文學院,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
基金項目: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當代諾獎小說的敘事藝術對甘肅小說‘走出去的啟示”(編號:20YB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