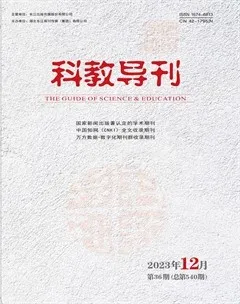基于“整本書閱讀與研討”任務群探討語文整本書閱讀
王詩倩
(浙江大學 浙江 杭州 310058)
1 一主調:提升核心素養
“整本書閱讀”是針對當前浮躁化、淺表化閱讀而提出的有力口號。我們在探討“整本書閱讀”前,首先應厘清“整本書閱讀”的概念。“整本書閱讀”應致力于提升學生核心素養,非一般意義地把書“完整地”讀下來。所以,“整本書”的“整”非數量上的,而是“整合后的學習材料”,是以書為載體的核心問題的學習。“閱讀”也不僅指“通讀”,應包括多種向度的“讀”,如精讀原作、泛讀作品背景及作者生平、研讀他人評論、聯讀相關作品、創意解讀和個性化解讀等。
“整本書閱讀”實際上是教師為引導者、平臺搭建者,學生作為主角的項目性學習、探究性學習過程。“整本書閱讀”后,學生所得非一本書“閱讀任務打卡”或試題的“參考答案”,而是收獲了讀厚、讀深、讀精、讀新一本書的方法,將人類精神文化現狀和自身精神文化體驗進行對話的一種情懷,尋找、探究、克服和總結一個問題的能力。正如褚樹榮老師所說,“閱讀整本書,是學生的生命體驗與人類那些最深刻的經驗建立聯系,從而在語言、思維、審美、文化諸方面提升素養,最終指向終極關懷”[1]。“整本書閱讀”是多向度“讀”的過程,更是深刻“思”的過程,豐富“情”的過程。
2 二重奏:“整本書閱讀”的兩大主體協作
在當前的閱讀環境下,教師理論建設多,落實教學常態少;宏觀指導的多,放緩做細的少;短暫嘗試的多,堅忍執著堅持的少。教師要展開“常、緩、韌”的“整本書閱讀”,面臨著來自學校、學生、家長、社會多方面的壓力。師生作為閱讀的兩大主體,如何有效率地開展整本書閱讀,需進一步梳理。北京市朝陽外國語學校張媛老師,提出了如下書冊閱讀實施流程(表1)[2]:

表1
從中可知,師、生這兩條主線應是互相促進的。整本書閱讀前期,教師的作用較大,體現在引導閱讀方向、搭建討論平臺等,后期學生在交流、拓展的過程中有更大的比重。學生的閱讀興趣和閱讀疑問,應是教師開發閱讀課程的導向而教師對作品的價值取向和主題梳理則是引導學生閱讀走向深入的關鍵。
教師應展開的工作有:確定教學價值(收集學生閱讀興趣、提煉核心問題、導讀預期);開發閱讀學程(收集教學材料,包括原作、背景介紹、鑒賞解讀、互文比讀、學生習作等,規劃閱讀階段,包括閱讀課時、閱讀階段等);設計整套活動(包括教師活動、學生活動);整理閱讀成果(注意呈現學生成果要體現個性化、多樣化)。其中,教師的最重要任務是找到值得討論的“問題”。而學生則需完成:分享閱讀興趣和體驗、收集閱讀資料、初步閱讀筆記、分享閱讀心得、繼續閱讀探討、形成閱讀成果等。教師和學生是演唱好整本書閱讀的兩個聲部,是雙線并行的。分析學生閱讀興趣,切實指導學生閱讀,創新閱讀檢驗方式,建立良性反饋機制,勢在必行,這也是推進“整本書閱讀”的必由之路。
3 三部曲:“整本書閱讀”的導讀、推進、延伸
“整本書閱讀”的教學大致分為三類課型,即導讀課、推進課、延伸課。
3.1 導讀:激發閱讀期待
導讀課是避免“簡單粗暴”地推薦書目,化解學生的畏難情緒,引起閱讀興趣的重要手段,但它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易被忽略。在準備導讀課時,教師要明確:這本書的價值何在?學生為什么要讀這本書?讀了這本書能了解到什么內容?[3]明確了上述三個問題,教師就基本上歸納出書本的核心問題,了解學生的學情和導讀課的預期效果,然后便是調動學生的閱讀興趣。書名設疑、封面解讀、指導讀法、設置情境都是提升閱讀期待的有效方法。
南銀妮老師在設計《鄉土中國》閱讀課時設置了如下情境:生活中常見“北漂”和“南漂”的現象,如今留在深圳過春節的人越來越多,你如何看待該現象?這與費孝通先生在《鄉土本色》一章中提及的“定居是常態,遷移是變態”有怎樣的關聯呢?為何現在的年輕人又普遍想要逃離“北上廣”返回家鄉?此情境的創設能給深圳地區的學生帶來興趣,因為建立書本和學生生活、經驗的聯結,勾起學生的生活生命體驗感,將是促進學生閱讀和探索的最大動力。在此過程中,學生會不經意地將目光投向生活和社會。
3.2 推進:指向性的共讀討論
愛因斯坦說:“提出一個問題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如果說導入課要完成的是“初讀”和“初思”的過程,那么推進課就需要完成“深思”和“熟議”的過程。“共讀討論”旨在讓學生通過共同閱讀,共同討論和共同對話。教師設計問題,讓學生帶著問題閱讀,如吳建英老師在引導學生閱讀《藍鯨的眼睛》時,讓學生品味“藍鯨獻出眼睛”這一段文字,一同琢磨語言的魅力。當然,學生也可在課堂上提出自己的見解,教師梳理,將問題打包和分類,再反饋給學生共同解決。更高效的解決辦法是,將學生分成幾個討論小組,每個小組致力于一個問題的解決,促進學生交流,加強學生合作。
3.3 延伸:整合資源,深化閱讀
延伸課是積淀和拓展學生閱讀成果的重要過程,學生的閱讀成果可通過多種活動呈現,實現閱讀效果可視化、具體化。
學生通過思維導圖呈現人物關系、命運線索,也可互相交流自己的閱讀批注,閱讀感受。課上,對書的外圍研究做深入探討,如作者的生平、創作風格、創作經歷、訪談錄、他傳或自傳,作者評價,作品評論,作品研究,作品改編及跨界的演繹,當代發展等。當然,學生最感興趣的還是“演繹”,將書中故事進行改編或者再創作,往往能讓學生樂在其中。如《林黛玉進賈府》中個性鮮明的王熙鳳,可讓學生串演,再對比電視劇的演繹,讓學生對這個人物理解更加透徹。
4 四重奏:“整本書閱讀”的四種策略
4.1 文體知識策略:課內與課外
整本書閱讀的教學如何通過讀“一本書”,上升到讀“一類書”,培養學生良好的閱讀習慣,文體知識的有效滲透是重要途徑[4]。教師從文本特征出發,從文學鑒賞方法切入,提煉重要的文體知識,這個過程中,打通課內外作品是有力辦法。
如《孫悟空三打白骨精》故事篇,就有可拓展的文體知識。“三”在此篇中經常出現,白骨精的“三變”,孫悟空的“三打”,唐僧的“三責”,豬八戒的“三唆”。這個“三”是文學作品中經常出現的敘事模式,該模式在中外小說中也很常見,僅四大名著就有“劉備三顧茅廬”“劉姥姥三進大觀園”“三打祝家莊”等章節。教師在課堂上講述這種敘事模式的文化淵源和發展演變,講述這種模式在增強敘述張力,豐富人物形象上的作用,這樣我們實現了課內知識的遷移,也在潛移默化中提升了學生的鑒賞能力。
4.2 跨界閱讀策略:深度與廣度
跨界閱讀有很多含義,跨學科、跨身份、跨媒介的閱讀方式,拓寬了學生的閱讀視域,讓學生找到更為深刻和廣闊的美好世界。
如跨時空閱讀,學生需要閱讀什么?當下,加繆的《鼠疫》再度掀起閱讀熱潮。周國平先生在《重讀〈鼠疫〉》中提到,“當這類禍害降臨的時候,我們怎么辦?加繆通過他筆下主人公們的行為向我們說明,唯一的選擇是站在受害者一邊與禍害作斗爭”。也許我們需要在閱讀經典之后思考:我們如何面對災難?災難之后,我們如何生活?這是學生思維走向縱深的過程。
再如跨界閱讀,風靡網絡的美劇《切爾諾貝利》,講述的是蘇聯發生的最嚴重核電事故,其背后很多真實故事記錄在阿列克謝維奇的《切爾諾貝利的祭禱》中。書和影視作品中,那些對真相的追求,對歷史的反思,也會延伸到我們當下的生活中——我們如何面對謠言?我們如何克服災難?我們如何理性思考?我們如何心懷悲憫?學生建立了書籍和影視的聯系,思維也就更寬闊。
4.3 思辨讀寫策略:整體性與生發性
寫作是閱讀能力的重要外化,閱讀最終是接軌寫作訓練的。“思辨讀寫”就是將感性體驗上升到理性思考的方式,也是閱讀教學課程化的主要策略。余黨緒老師在《魯濱孫漂流記》的專題閱讀指導中提倡的“假設性論證法”值得借鑒,即提出值得探討和生發的幾個問題,通過假設性的反向提問,引導學生思維走向深入。如“魯濱孫靠什么征服星期五?這個大問題又包含幾個子問題,如果沒有火槍,他能否征服星期五?如果濫用火槍,他能否征服星期五?”[5]由此,余老師又引導學生對殺戮做了深刻思考,對現代文明的價值觀進行深入理解。
如何進行思辨讀寫的設計?教師首先需要考慮學生的成長階段和特征,提出幾個重要的母題。如《魯濱孫漂流記》中魯濱孫在孤島中獨自生存的成長,《西游記》中師徒四人克服九九八十一難取得真經的成長,還有愛情、成功、尊嚴等都是可入手的方向。然后再結合作品,具體確定有“具體性”和“生發性”的命題。這些問題就是思辨讀寫的支架和抓手,學生的思維也在復雜的關系判斷和價值判斷中升華了。
4.4 多重評價策略:多樣與明確
當前的整本書閱讀評價,傾向于知識點考察,那么學生的閱讀成果的檢驗變成了應試和記憶。整本書閱讀的評價,應基于整本書的視野,指導和促進閱讀。如王娜老師設計的《林教頭風雪山神廟》的考查題:
(1)請用簡潔的語言說說故事的梗概。(2 分)——是否讀了
(2)在這個故事中,林沖的心理發生了怎樣的變化?(2 分)——是否讀懂了
(3)在這個故事中,你覺得風重要,還是雪重要?(2分)——是否讀透了
“讀了”“讀懂了”“讀透了”,是整本書閱讀評價的三個層次。此外,整本書閱讀也要注重過程性評價和綜合性評價。將文本改編成課本劇,寫人物小傳記,開展辯論會、小小研討會,繪制思維導圖等,這些多樣的閱讀活動,都是評價的重要內容。張小兵老師設計的評價非常值得借鑒,讓學生思考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是否適合學生閱讀,如果適合,請寫一封勸說信給反對的家長,如果不適合,請寫一封勸說信給教師。學生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涉及對這個作品內容和人物形象的分析,對作品意義的評價。教師創設了真實的情境,讓學生在明確的任務中進行了評價。總之,評價不應將閱讀窄化為“知識點”的考查,應傾向于對學生閱讀體驗、閱讀能力的考查。
整本書閱讀評價理應關注學生的閱讀產品和閱讀效果,重視閱讀作品后的感悟和收獲。“有效的評價需要結合整本書的內容,精心設計讀書任務,在真實的任務中,激發學生創生出閱讀‘產品’,即可視化的閱讀成果。”[6]這在呈現學生閱讀成果的同時,也提升了學生的閱讀積極性和閱讀能力。正如王棟生老師所說,整本書閱讀的推進,不是靠“熱”,而是靠理性的“韌”。本文提出“常、緩、韌”的原則,希望整本書閱讀能常態化、緩節奏、有韌性地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