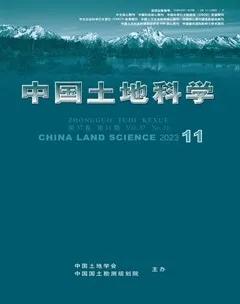基于Shapley值法的“消薄飛地”收益分配方案研究
李學文,石戰強,郜釧貝
(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浙江 杭州 310058)
飛地(Enclave)是指某一行政區位于其他行政區的土地,根據其功能和目的,可以分為移民飛地、資源飛地、文化飛地等多種類型。在我國,飛地更多地服務于區域產業經濟的發展,是一種以加強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協同合作、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為目的的地區合作形式。浙江省作為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是典型的飛地經濟發展先發區。早在1995年,浙江省磐安縣就在金華市區建立了異地開發區(金磐開發區)。2002年,浙江省發布《關于實施“山海協作工程”,幫助省內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的意見》,部分地區嘗試使用飛地合作園區模式開展協作幫扶。2012年8月,浙江省委、省政府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山海協作產業園建設的意見》,明確將飛地產業園作為對口協作模式。山海協作政策的推出和不斷升級,進一步加強了對飛地經濟合作的創新和運用,產生了“反向飛地”“消薄飛地”“創新飛地”等富有創新性的飛地經濟實踐,為打破行政區經濟,促進區域的協同發展探索了一條可能的道路。其中,“消薄飛地”是一種以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為目的的反向飛地合作。相比于一般的飛地經濟模式,“消薄飛地”合作不僅包括飛入地和飛出地政府,還吸收了收入較低的村集體或個體戶參與投資和分紅,在拓寬了發達地區發展空間的同時,也能使收益直接惠及需要扶持的貧困戶或村集體,加強飛出地飛入地的經濟聯系。但利益相關方的增加也使“消薄飛地”的收益分配更復雜。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以“消薄飛地”為分析對象,以平湖—青田“消薄飛地”為案例,運用Shapley值法,對“消薄飛地”合作的收益分配方案進行分析和優化,并提出相應的優化對策。
1 理論回顧與文獻綜述
1.1 飛地經濟合作
美國著名區位和空間經濟學家ISARD最早分析了飛地經濟的雛形[1],到20世紀80—90年代,WEISSKOFF等[2-5]學者提出并分析了飛地經濟的概念。此后,國外學者聚焦于飛地特定空間范圍內的經濟現象進行解讀,并分析了族裔飛地經濟、資源型飛地經濟和FDI型飛地經濟三種飛地經濟類型[6-10]。
國內的飛地經濟在發展實踐中產生了許多獨特模式。一般來說,傳統的飛地經濟合作模式是發達地區(飛出地)在欠發達地區(飛入地)設立經濟園區,雙方進行跨空間的行政管理和經濟開發合作,借助于合理的合作機制,實現兩地資源互補、經濟協同發展的一種區域經濟合作模式[11-13]。反向飛地則是欠發達地區作為飛出地,借助土地指標轉移,主動在發達地區設立飛地經濟園區,利用發達地區的優勢資源和要素,發展或孵化發展前景好、利潤率較高的先進產業,為欠發達地區創造經濟收益或帶動本土產業升級與經濟發展,主要有反向扶貧飛地和反向創新飛地兩種類型[14]。
現有關于飛地的研究可分為對飛地合作的一般性分析和對特殊飛地模式的針對性研究兩個方面。一般性的分析包括對飛地合作的治理邏輯和模式的分析,如李魯奇等從國家空間重構的視角對飛地經濟的空間生產和治理結構進行深入的研究[15],華子巖從府際合作治理的角度,闡述了飛地府際合作治理模式的確立及其邏輯[16];還有的學者關注了飛地經濟合作中不同主體之間的關系,對飛地經濟合作中政府之間的合作競爭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17]。對特殊飛地模式的研究以“反向飛地”和“創新飛地”兩種模式為主,如丁偉偉以金磐扶貧開發區和衢州海創園為例,深入分析了反向飛地模式的優勢與獨特性[14];胡航軍等以區域經濟發展梯度轉移理論為指引,分析了“創新型反向飛地”這一新的飛地經濟模式產生的原因及其創新性[18]。
1.2 地方政府合作與利益分配
地方政府合作中共同利益和地方利益博弈的困境是地方政府合作困境的一個重要方面[19]。利益是形成合作的根本原因,利益的公平分配是地方政府合作的內在激勵,完善的利益分配機制是地方政府合作的原動力[20]。地方政府在合作中有不同的利益和價值偏好,如何合理分配合作剩余以滿足合作主體的不同需求,是地方政府合作面臨的重要問題。現有的關于區域和地方政府合作收益分配機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區域環境合作方面[21],通過運用Shapley值法等合作博弈理論構建合作主體間的收益分配方案,提高地方政府參與合作的有效性和積極性。如陳忠全等基于Shapely值法設計了排污權交易聯盟的收益分配方法[22]。此外,Shapley值也被運用于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流轉入市[23]以及農村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的研究[24]。Shapley值是將成本或者收益按照邊際貢獻進行分攤,合作者所獲得的收益等于其對所有合作聯盟的邊際貢獻的期望值,體現了合作參與者對合作聯盟收益的貢獻程度,避免了分配上的平均主義,也體現了合作者相互博弈的過程[25]。
通過上述文獻回顧可以發現,現有關于飛地經濟合作尤其是特殊飛地合作模式的研究缺乏對合作收益分配的分析,而飛地經濟作為一種區域經濟合作模式,公平有效的合作收益分配方式是激發合作積極性,促進合作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分析和優化現行飛地經濟合作的收益分配方案不僅能夠彌補現有研究的不足,而且對于推進飛地經濟合作深化發展,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在現有的多種飛地經濟模式中,“消薄飛地”作為一種以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為目的的新型反向飛地合作模式,通過飛出地(欠發達地區)向飛入地(發達地區)轉移土地指標,同時協調整合集體經濟薄弱村出資在飛入地建設產業園,借助飛入地的優勢區位和要素吸納高端產業,為村集體創收。這種新型飛地經濟合作在消薄扶貧以及推進共同富裕方面發揮了顯著的作用,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推廣。因此,本文選取“消薄飛地”為分析對象,采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同時引入合作博弈理論與Shapley值收益分配方法,在明確現有“消薄飛地”合作收益分配方式和問題的基礎上,探索建構更加公平有效的分配方案,使“消薄飛地”合作更具發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續性。
2 案例選擇與分析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研究方式,綜合考慮案例的典型性以及數據可得性等因素,選取平湖—青田“消薄飛地”為分析案例,深入分析現行“消薄飛地”收益分配方案及其優化方式。一方面,青田—平湖“消薄飛地”是較早運用反向飛地模式的山海協作結對幫扶項目之一,也是浙江省首個跨縣市“消薄飛地”項目,擁有較為豐富的合作經驗。自2006年起,平湖市就率先在市域內探索村集體經濟“飛地抱團”發展模式,并取得顯著成果。2017年,平湖市在市域內“消薄飛地”實踐經驗的基礎上,與青田在全省率先開啟跨地市“飛地抱團”精準“消薄”新模式,由青田將自己的建設用地指標轉移到平湖,在平湖建設飛地產業園區,同時吸納青田縣村集體籌集資金投入園區建設,為村集體創造收益。另一方面,青田—平湖“消薄飛地”在消薄扶貧方面成效顯著。2018年,青田—平湖“消薄飛地”被浙江省省委省政府聯合發文進行經驗推廣,2020年入選浙江省精準扶貧十大案例,是浙江省“消薄飛地”合作的樣板案例①平湖·青田山海協作“飛地”產業園消薄項目入選省精準扶貧十大案例.浙江政務服務網,2020年10月16日.http://www.pinghu.gov.cn/art/2020/10/ 16/art_1229395937_59019217.html。。自2017年以來,青田先后組織256個經濟薄弱村共1.6萬戶低收入家庭廣泛籌資,到平湖建設“飛地產業園”。目前該產業園已累計投資一二期項目4.65億元,建成后參與投資的經濟薄弱村年均增收12.5萬元,低收入家庭每戶增加1 000~2 000元,為精準消薄、精準脫貧探索了一條可能的模式①青田縣創新實施跨縣域“飛地消薄”項目,探索消薄工作長效機制.浙江政務服務網,2020年5月26日.http://zld.zjzwfw.gov.cn/art/2020/5/26/art_1659790_43458437.html。。
2.1 合作機制
平湖—青田“消薄飛地”實行雙方共同謀劃、共同保障、共同獲益的開發機制。雙方通過采取跨區域“飛地”模式在平湖建設產業園,產業園建設由青田縣國資公司負責,吸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建立青田縣農村集體經濟聯合發展公司,由村集體共同出資在平湖落地建設,產業園產權歸青田農村集體經濟聯合發展公司所有。平湖市在飛地產業園一期工程建成驗收之日起,前5年采用包租固定回報的方法,平均每年給予青田縣農村集體經濟聯合發展公司實際投資總額的10%作為投資固定收益;后5年,采用租金收益加稅收分成的方法,廠房租金收益由青田縣農村集體經濟聯合發展公司收取,園區企業稅收地方所得部分的50%獎補給青田縣農村集體經濟聯合發展公司。在土地指標的供給方面,平湖和青田建立了耕地占補平衡指標調劑長期有償交易合作機制。青田縣大力實施高等別墾造耕地項目,每年有限調劑給平湖市使用,全力為平湖市項目建設提供耕地占補平衡保障,飛地產業園區所占用的建設用地指標由青田縣的土地指標進行補償(圖1)。

圖1 平湖—青田“消薄飛地”合作機制Fig.1 The cooperative mechanism of the “povertyreducing enclave” between Pinghu and Qingtian
2.2 合作成本與收益分配
平湖—青田“消薄飛地”的合作主體包括飛入地政府(平湖市)、飛出地政府(青田縣)和參與投資的村集體三方(表1)。從對合作的貢獻來看,平湖市作為飛入地不僅貢獻了自身的資源要素與區位優勢,也承擔了園區的公共服務、招商引資等管理業務以及一半的投資建設成本;青田縣作為飛出地貢獻了土地指標,同時承擔了合作的協調溝通工作;村集體在合作中的貢獻是承擔了飛地產業園投資建設的一半成本。此外,飛出地和飛入地政府間的合作過程中還會產生交易成本,包括訂立協議、談判以及保障協議執行所產生的成本。交易中的有限理性、投機主義和資產專用性是交易成本的主要來源[26]。從案例來看,合作中的交易成本主要來自合作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一方面,平湖和青田結對合作的時間較長且合作范圍廣泛,彼此間的了解度和信任度較高,且雙方在合作中的需求偏好較為明確,因此信息不對稱以及投機主義對交易成本的影響較小。另一方面,飛地合作的關鍵要素如土地指標以及建設資金都是可以流轉的,因此資產專用性不會顯著增加合作的交易成本。由于雙方合作協議的有效性時間較長,合作中的有限理性、合作收益的不確定性以及后續管理上的復雜性等潛在風險造成雙方合作契約的不完全性,會增加訂立協議時的議價成本以及后續合作維護與協議變更的成本。

表1 “消薄飛地”合作主體的成本與收益構成Tab.1 The cost-benefit composition of different cooperative subjects in the “poverty-reducing enclave”
從合作主體獲得的收益來看,產業園產生的稅收和租金這些直接性的經濟收益由飛入地政府和村集體享有,飛出地政府并沒有得到直接經濟收益的分成。除了直接性的經濟收益,飛入地政府還能夠通過合作項目拓展自身的發展空間,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資源和要素的價值,帶動地方GDP的增長。同時園區的建設和發展還會對周邊地區的發展產生一定的溢出效應,如園區周邊工業用地的升值等。村集體除了稅收和租金的分成,還享有飛地產業園區的所有權,因此長期來看村集體還會獲得園區固定資產升值帶來的收益。飛出地政府能夠獲得收益極為有限,其收益主要來自產業園區可能帶來的高端產業回流。
3 基于合作博弈Shapley值的收益分配
3.1 平湖—青田“消薄飛地”合作聯盟及其收益函數構建
合作博弈 Shapley 值是一種多方合作博弈的收益分配比例的測算方法,是以各主體對合作聯盟的邊際貢獻為依據的關于合作博弈收益分配的解,能夠有效解決合作聯盟收益的公平分配問題[27]。從 Shapley 值模型的定義出發,設定平湖—青田“消薄飛地”合作收益的分配主體分別為飛入地政府(i=G)、飛出地政府(i=J)、參與投資的村集體(i=N),三個利益主體將組成 7 種聯盟,分別是獨自參與情況下的G,J和N,兩方合作參與的(G,J)、(G,N)和(J,N),三方合作的(G,J,N),則各個子集所能獲取的純收益分別為V(G)、V(J)、V(N)、V(G,J)、V(G,N)、V(J,N)和V(G,J,N)。Shapley的計算需要獲得各個子集的純收益,因此需要分別分析7種聯盟的收益情況。
(1)當s=(G)時,即飛入地政府在本地獨自進行投資生產。在沒有外來土地指標調劑的情況下,飛入地進行產業園區的開發必須通過土地復墾等方式獲取建設用地的土地指標。假設飛入地通過土地復墾獲取產業園區的建設用地指標,則其收入為飛入地工業園區10年內的畝均稅收收益V(t)(地方所得部分)乘以土地指標數量V(k),加上園區廠房租金總收益V(r),記為V(a),再扣除飛入地工業園區建設投資成本V(c4)和土地復墾成本V(c6)。收益特征函數為:V(G)=V(a)-V(c4)-V(c6)。
(2)當s=(J)時,即飛出地政府獨自建設產業園創收,其收入為10年內飛出地工業園區畝均稅收收益V(c1)乘以土地指標數量V(k),加上園區廠房租金總收益V(r),記為V(b),再扣除建設投資成本V(c2)和飛出地土地復墾成本V(c5)。收益特征函數為:V(J)=V(b)-V(c2)-V(c5)。
(3)當s=(N)時,是由集體經濟薄弱村獨自籌集資金進行相關的投資營利活動,其獲取的收益為固定資本投資和部分經營性收益,記為V(y),收益特征函數為:V(N)=V(y)。
(4)當s=(G,J)時,是指飛入地政府與飛出地政府進行合作投資,即飛出地政府轉移土地指標在飛入地建設相關產業園,兩地進行租金或稅收的分成。此時園區建設資金由飛入地和飛出地政府承擔,同時,由于飛地園區建設所轉移的土地指標主要來自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指標,需要承擔土地復墾的成本。因此其收入為V(a),再減去投資開發成本V(c3)和飛出地土地復墾成本V(c5)。收益特征函數為:V(G,J)=V(a)-V(c3)-V(c5)。
(5)當s=(G,N)時,飛入地政府與村集體進行合作,由于飛入地政府的需求偏好為建設用地指標,而村集體在合作中所貢獻的生產資料為投資資金,無法貢獻土地指標,且在沒有飛出地政府協調整合與支持的情況下,兩者單獨尋求合作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其收益特征函數值設定為0。
(6)當s=(J,N)時,由飛出地政府和當地集體經濟薄弱村在本地進行合作生產。此時可以由飛出地政府自身通過土地整合和復墾的方式獲取土地指標,村集體可提供建設投資資金,在本地經濟工業區或經濟開發區建設產業園為村集體創收。此時合作收入為V(b),再減去投資開發成本V(c2)和飛出地土地復墾成本V(c5)。收益特征函數為:V(J,N)=V(b)-V(c2)-V(c5)。
(7)當s=(G,J,N)時,飛入地政府、飛出地政府和村集體三方共同進行“消薄飛地”合作,其收益應當為10年內飛地產業園區的畝均稅收收益V(d)乘以園區占地面積V(k),加上園區廠房租金總收益V(r),記為V(c),再減去投資開發成本V(c3)和飛出地土地復墾成本V(c5)。收益特征函數為:V(G,J,N)=V(c)-V(c3)-V(c5)。
3.2 變量取值
本文的研究案例為平湖—青田“消薄飛地”一期合作項目,由于其現有的合作協議對收益分配的規定適用期為一期工業園建成運營后10年。因此,本文在數據的計算中將各收益變量的取值為一年值的10倍(表2)。

表2 各變量取值Tab.2 The value of each variable
V(c1):飛出地工業園區畝均稅收收益。指青田縣工業園區畝均稅收收益的10年累計值,這里采用青田縣人民政府2022年發布的《青田縣開發區(園區)整合提升方案》公布的數據①《青田縣人民政府關于印發青田縣開發區(園區) 整合提升方案的通知》。,其中規上工業企業畝均稅收收益為35萬元/年。10年累計每畝350萬元,50畝土地指標10年共計可創造1.75億元稅收收益。
V(c2):飛出地工業園區投資開發成本。指飛出地即青田縣將土地指標用于本地工業園區的開發建設,在進行建設開發中(包括土地平整,水電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所耗費的成本。這里參考青田縣三溪口街道東岱工業園區開發工程的投資水平①《青田縣人民政府關于下達青田縣2019年政府性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計劃的通知》(2019年)。,平均每畝投資190萬元,50畝面積預計投資9 494萬元。
V(c3):飛地工業園區投資開發成本。指平湖—青田“消薄飛地”一期項目投資成本。由合作協議內容可知,共計1.95億元。
V(c4):飛入地工業園區投資開發成本。指平湖市在經濟技術開發區進行建設投資所消耗的資金成本。參考嘉興市2018年政府性投資項目中相關工業園區的建設投資成本,選定畝均建設投資成本為193萬元②《關于編報2018年嘉興市市級政府投資項目計劃及財政資金計劃的通知》(2017年)。,50畝土地共計需要9 650萬元。
V(c5):飛出地土地復墾成本。參考青田縣2020年政府性固定資產投資項目中的建設用地復墾項目投資,建設用地復墾75畝共計投資488萬元③《青田縣人民政府關于下達青田縣2020年政府性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計劃的通知》(2020年)。,平均每畝約6.5萬元,50畝土地預計需要投資325萬元。
V(c6):飛入地土地復墾成本。參考2022年《平湖市全面推進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政策意見》中的旱地復墾補助費用,設定為8萬元/畝④《平湖市人民政府關于印發平湖市全面推進全域土地綜合整治的政策意見》(2022年)。,50畝土地共計400萬元。
V(d):消薄飛地產業園畝均稅收收益。2021年青田—平湖“消薄飛地”產業園區畝均稅收107萬元,10年累計每畝1 070萬元,50畝土地指標10年共計創造5.35億元稅收收益。
V(r):廠房租金總收益。參考平湖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標準廠房租金為每平方米25元/月,“消薄飛地”一期合作項目50畝土地共建設4.18萬m2標準廠房,10年租金收益為1.25億元。
V(y):村集體自行投資收益。自中共十九大以來,“消薄”就成為浙江省地方政府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⑤《中共浙江省委辦公廳、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實施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三年行動計劃的意見》(2017年)。。在基層治理中,政治任務伴隨著較大的政治壓力,往往被地方政府作為中心工作,通過政治壓力和權威動員下級政府,調配各種資源以滿足任務要求甚至超額完成任務[27]。如青田縣參與“消薄工作”的村集體和鄉鎮干部承擔著每年創收15萬~20萬元的任務指標。即使沒有飛地合作,地方政府依然會通過其它途徑滿足村集體創收的要求。因此可以認為村集體在自行投資創收的情況下依然能夠獲得與飛地合作大致相當的收益⑥青田縣創新實施跨縣域“飛地消薄”項目,探索消薄工作長效機制.浙江政務服務網,2020年5月26日.http://zld.zjzwfw.gov.cn/art/2020/5/26/art_1659790_43458437.html。,即每年每村7萬元,共256個村集體參與合作,10年收益大約為1.79億元。
V(t):飛入地產業園區畝均稅收收益。在此應當取為平湖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畝均稅收的10年累計值。從相關報道中可知,平湖市經濟技術開發區2020年畝均稅收為57萬元⑦十三五紀事 歷史性發展:闖出高質量發展新路子.新華社客戶端,2020年9月30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9216918149698983&wfr=spider&for=pc。,10年累計每畝570萬元,50畝土地10年共計創造2.85億元稅收收益。
V(k):流轉的土地指標面積。由于飛地合作產業園建設所需建設用地全部由青田縣負責補償調劑,因此一期流轉的土地指標應當與飛地產業園區建設用地規模相同,為50畝。
3.3 合作聯盟中各主體收益分配額度
依據Shapley值的定義,合作聯盟中成員i從合作收益V中應當分得的收益為[28]:
式(1)中:|S|表示聯盟S包含的成員個數;(|S|-1)!表示成員i參與聯盟S時的排序個數,其余(n-|S|)個成員有(n-|S|)!種排序,S{i}表示集合S中除去{i}后的集合,(|S|-1)!(n-|S|)!/n!表示成員i在合作中應得收益的權重,設定為ω(|S|);V(S)-V(S{i})對應為主體i在集合S中做出的邊際貢獻[22]。
由表3可知飛入地政府、飛出地政府和村集體在合作種所獲得的收益分別為:

表3 合作主體收益分配Tab.3 Revenue distribution among cooperative subjects
計算可得:φG(V)≈17 815萬元;φJ(V)≈22 543萬元;φN(V)≈5 858萬元。
4 分配方案的比較分析與優化對策
4.1 Shapley值方案與現行分配方案比較分析
經過對合作主體的Shapley值的計算可知:在實際直接收益為4.62億元時,飛入地應當獲得的收益約為1.78億元,約占總收入比重為38.5%;飛出地政府應當獲得約2.25億元,約占總收入比重為48.8%;村集體應當獲得約0.59億元,約占總收入比重的12.7%。這與不同主體對合作的邊際貢獻是大致相符的。飛入地政府貢獻了自身的優勢區位條件和要素資源,在提升飛地產業園的發展效益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飛出地政府在整個飛地合作的達成和推進過程中發揮了主體性的作用,不僅是土地指標轉移調劑的主體,也是兩地溝通協調的主體,對“消薄飛地”合作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其中土地指標作為兩地政府達成合作的核心要素,是兩地合作建設產業園的基礎;而村集體在整個合作的過程中僅僅承擔了產業園投資建設的成本,且這一合作貢獻具有較強的可替代性,其在合作聯盟以及不同子聯盟中的邊際貢獻是較低的。
但這一計算結果與現行收益分配結構有很大的差異。就直接性經濟收益來看,合作產生的直接性經濟收益包括園區廠房租金和稅收,園區固定資產以及投資固定收益返還等。根據合作協議,飛入地政府能夠獲得園區前5年租金稅收收入的全部以及后五年稅收收入的一半;村集體不僅擁有園區固定資產所有權,同時享有50%的投資固定收益返還以及后5年租金與50%稅收收益。因此,在不考慮成本的情況下,合作產生的直接性經濟收益主要在飛入地政府和村集體之間分配,飛入地政府獲取收益約為4.640億元,占比約48.7%;村集體獲取收益約為4.890億元,占比約51.3%。
相比之下,現實中的收益分配方案凸顯了“消薄飛地”的扶貧消薄功能,收益的分配明顯偏重于村集體這一弱勢者。但從合作博弈的角度看,這種分配方案顯然是不公平且無效率的,合作主體所獲得的收益分配比重與其邊際貢獻嚴重不匹配:村集體的邊際貢獻最低卻獲得了最多的合作收益,而飛出地政府作為重要的貢獻者并未享有直接性經濟收益分成。這種扭曲的分配方案不利于合作主體積極性的提高以及合作產出的增長,而高效且可持續的合作是實現“消薄飛地”消薄扶貧功能的重要基礎,因此有必要對現行“消薄飛地”的收益分配方案進行調整。
當然,上述計算結果和分析只考慮了顯性的經濟成本和收益,對于合作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產業園區的溢出效應、飛入地提供的公共服務成本等隱性的成本和收益,由于難以準確測算,并沒有納入計算。在研究中,有必要分析這些隱形成本和收益對最終的收益分配結果的影響。
首先,飛地合作中的交易成本主要來自合作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但這并未對合作產生顯著的影響。雖然雙方的合作契約是不完全的,合作的潛在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但雙方在訂立協議時并未對此制定針對性的合作變更條款,目前青田—平湖“消薄飛地”的合作一直遵循2019年簽訂的協議內容,合作規則一直沒有改變。其次,“消薄飛地”不同于“創新飛地”,主要以創收為目的,產業孵化并不是園區的主要功能,通過產業回流帶動青田產業發展的可能性較小。對于飛入地提供公共服務的成本,由于飛地園區落地于平湖高新技術開發區內,相關服務設施較為成熟完備,需要額外增加的公共服務或基礎設施投入較少,且公共服務成本也能夠從園區的溢出效應中得到彌補,因此其對分配結果的影響并不顯著。
而產業園區產生的溢出效應,雖難以準確測量,但卻是“消薄飛地”合作中飛入地收益的重要部分。飛入地正是通過“消薄飛地”產業園的建設拓展發展空間,園區的建設和發展不僅會帶動周邊土地價格的上升,還能進一步推動產業集聚,提升平湖高新技術開發區的發展效益。因此,產業園的建設為平湖市所帶來的潛在效益是顯著的。
總的來說,現實中“消薄飛地”的收益分配與各合作主體的邊際貢獻不匹配。村集體享受了遠超邊際貢獻的收益;而飛入地政府不僅能夠獲得園區直接性經濟收益的分成,同時還是間接性收益的主要獲益者,因此在收益分配中處于優勢地位;但飛出地政府作為合作的重要參與者和貢獻者,難以從飛地合作產生的直接或間接收益中獲益。因此,現行的“消薄飛地”的收益分配方案并不滿足公平和效率的要求。促進“消薄飛地”合作的可持續發展,需要對現行收益分配方式進行優化。
4.2 收益分配理念與優化對策
“消薄飛地”是以消薄扶貧,推進共同富裕為目的的反向飛地合作,合作的目的和功能決定了其收益分配應當兼顧發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續性[29]。發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續性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要素,也是“消薄飛地”實現其目的和功能的重要條件。發展性要求收益分配有利于合作總體效率的提高和產出的增加,這也是維持合作穩定發展的基礎;共享性要求收益分配要滿足平等、公平等正義價值,既要保障合作主體的自我所有權,又要保障弱勢群體的最大利益與可行能力,縮小收益分配差距;可持續性要求收益分配能夠保障發展和共享的可持續,能夠激發合作主體的積極性,實現合作產出的穩定增加與合理共享。因此,“消薄飛地”的收益分配方案應當是在各主體邊際貢獻基礎上的共享性調整,既要通過以邊際貢獻為基礎的差異化分配激發合作主體的積極性,增加合作的產出和各主體的福利水平;又要加強對村集體這一弱勢者收入的補充和保障,應當在不損害合作整體效益的情況下,遵循平等性和共享性的理念,將合作收益適當向村集體進行傾斜。
對“消薄飛地”合作收益分配的優化可以從直接性經濟收益和間接性經濟收益兩個方面入手。在直接性經濟收益方面,應當適當給予飛出地政府一定的稅收租金收益分成,降低飛出地政府和村集體的分成比例。同時也可以通過調整園區固定資產的歸屬和轉移地土地指標數量等方式,平衡飛出地政府與飛入地政府的合作成本與收益,或在飛入地政府和飛出地政府的其他合作項目中對飛出地予以利益補償,從而保持合作主體的合作積極性。在間接性經濟收益方面,可以借鑒創新型反向飛地的合作模式,在保證“消薄飛地”產業園區一定的創收功能的同時,在后期合作中加強園區的產業孵化和培育的功能。在引進高端產業創收的同時,建設相應的科創中心或產業孵化平臺,加強兩地在公共服務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銜接,利用飛入地高端生產要素集聚的優勢,為飛出地培育優勢產業,促進當地產業升級和跨越式發展,完善當地產業鏈條,使“消薄飛地”在為村集體創收的同時也能夠滿足飛出地政府和飛入地政府的需要,從而促進“消薄飛地”合作模式的推廣和發展。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消薄飛地”這一新的反向飛地模式的收益分配為分析對象,借助合作博弈的收益分配理論,分析了“消薄飛地”合作在收益分配上存在的問題,并運用合作博弈Shapley值法對相應的收益分配方案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指出,現有的“消薄飛地”合作中合作主體的收益與邊際貢獻不匹配,不利于合作效率的提升,本文還考慮了交易成本、溢出效應、公共服務成本等隱性因素對收益分配結果的影響,發現產業園區的溢出效應能夠顯著增加飛入地從合作中獲取的隱性收益。隨著“消薄飛地”實踐的不斷拓展,未來的研究可以對合作中的各項收益和成本進行更加精確的衡量,并對研究對象進行拓展,從而增強結論的穩健性和可靠性。“消薄飛地”作為一種利用飛地合作的形式推動農村經濟發展的創新實踐,可以為縮小區域和城鄉差距,推進區域和城鄉經濟一體化提供一種可行的路徑。但飛地經濟合作本身具有較高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消薄飛地”的推廣和應用,不僅需要各地結合實際,構建合理有效的合作方式,也需要加強相應的政策引導和支持。據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加強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消薄飛地”合作涉及多個行政區域和多個利益主體,需要有相應的政策法規來規范和引導合作行為。比如,暢通飛出地和飛入地的建設用地指標的流轉,加強對村集體的資金扶持,建立健全飛地經濟監管機制等。
二是促進合作主體間的信任和協調。“消薄飛地”合作需要各方共同承擔風險和責任,實現互利共贏。因此,需要加強合作主體間的溝通和交流,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平臺,解決可能出現的利益沖突和價值分歧等。
三是注重產業轉移和升級。“消薄飛地”合作有利于實現產業優化配置和區域協同發展。需要根據各地區的資源稟賦和發展水平,選擇適合自身特點的產業類型,避免產業同質化競爭,推動產業創新和轉型升級等。
四是完善收益分配機制。“消薄飛地”合作中存在著直接性經濟收益和間接性經濟收益兩種類型,目前只有直接性經濟收益有明確的分配規則,而間接性經濟收益則沒有納入考慮。因此,需要建立一個綜合考慮兩種收益的分配機制,使各合作主體能夠根據自身的邊際貢獻和成本獲得合理的收益,同時也要考慮到村集體的扶貧消薄需求,適當給予其一定的收益傾斜,實現收益分配的公平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