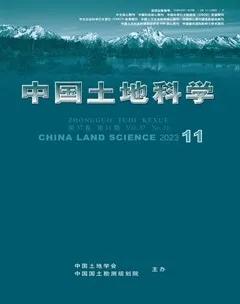土地產權三維界定的技術路線及其評論
杜莖深
(1.中共廣東省委黨校管理學教研部,廣東 廣州 510053;2.中共廣東省委黨校城鎮化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053)
隨著中國城市發展進入存量時代,以軌道交通、地鐵上蓋物業、空中連廊、地下商業街等代表的地上地下開發活動大規模涌現,高密度、垂直式的土地空間立體開發逐漸成為新常態。《民法典》第345條沿襲《物權法》之規定,推動建設用地使用權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地下分別設立,形成土地垂直方向利用方式與權屬多元化之格局,改變傳統以地表為中心的產權認知與界定方式。在平面開發模式下,土地即“地皮”。土地所有權支配范圍“上窮天宇,下及地心”,以平面切塊為產權單元劃分,以面積為度量,以二維地籍為技術支撐的二維產權界定,足以起到定分止爭之作用,由此形成民法上旨在規范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的二維產權范式。實踐中,盡管土地出讓合同也約定了容積率、建筑密度、限高(深)等三維參數,究其本質仍屬于對產權使用內容的限制。但在立體開發模式下,為確保空間占有的唯一性,客觀上要求無論是地表,還是地下、地上產權,其水平面和垂直面均需存在明確的法定產權邊界,即產權客體是一個上下有高度、前后有深度、左右有寬度的“三度空間”[1]。換言之,此時土地產權是以三維化的產權客體為外在表征的三維產權形態。既往以二維方式界定土地產權已無法適應立體開發之需要,亟待引入空間維度的三維界定。
2015年,深圳市前海自貿區在國內率先探索實踐以三維地籍技術為核心的土地立體化管理模式。合作區占地面積為14.92 km2,地下空間開發規模達600萬m2①數據來源于《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綜合規劃》(2013年)。,約占地上開發規模的四分之一,通過鼓勵土地空間多元功能混合使用,提倡建筑空間高度復合,旨在建設高密度立體城市。針對立體開發帶來權屬空間管理難題,前海管理局在技術創新上應用三維地籍讓權屬空間“看得見”,在制度配套上完善供應政策讓權屬空間“摸得著”,在管理流程上建立彈性機制讓權屬空間“動起來”。以聽海大道地下空間為例,該項目上方為市政道路,下方為地鐵1、5、11號線區間及車站、綜合管廊,兩側連接前海綜合交通樞紐、騰訊、交易廣場、華潤、卓越等8個地塊,空間權屬極為復雜,通過采取基于三維地籍的全過程立體化報建系統,動態生產三維權屬空間,有效解決了不同權屬主體的立體空間分層關系。
2020年,國務院印發《關于做好自由貿易試驗區第六批改革試點經驗復制推廣工作的通知》,提出復制推廣前海自貿區“以三維地籍為核心的土地立體化管理模式”改革經驗。隨著先行先試地區示范帶動,越來越多地區開始探索以三維方式設立建設用地使用權。研究土地產權三維界定及其背后的學理邏輯,加快構建支撐立體開發的三維土地產權范式,已成為當前中國土地管理的重大實踐、政策和科學問題之一。本文旨在對已有土地產權三維界定研究文獻涉及的技術路線進行結構性的總體把握。縱觀國內外相關研究文獻,根據其理論基礎、界定起點和界定方案劃分,總體上存在三條技術路線,即基于空間分離原理的技術路線、基于空間區分原理的技術路線和基于三維地籍原理的技術路線。
1 基于空間分離原理的技術路線及其理論邏輯
1.1 技術方案與實踐表達
基于空間分離原理的技術路線認為,隨著人類利用空間技術與能力的不斷提升,土地利用不再囿于地表及其上下極為有限的空間,加之空間資源的稀缺性,使脫離地表之上空或地下的特定空間亦產生了顯著的利用價值和經濟利益,得以具備獨立的財產屬性。考慮到空間具有異于地表土地之開放性和虛擬性等固有特征,主張將空間從既往依附于土地的狀態中分離出來,作為單獨的財產權單元為人類所排他性支配,進而在立法上生成“空間權”這種新型財產權利[2]。盡管空間不再依附于土地,但土地之范圍卻不能僅以地表為限,否則土地所有權人既不能建屋掘井,亦不能挺身于地面,失去應有的效用和獨立使用價值[3]。在物理上,空間與土地對垂直方向空間占有連綿不絕,具有連續性和繼起性。事實上,兩者乃人為之界分,表現在不動產登記簿上登記為不同財產權單元而已。可見,基于空間分離原理的土地產權三維界定,本質上是空間與土地、空間權與土地權之間相分離的法技術運作過程[4]。
這一技術路線主要體現在英美法系土地空間權立法實踐之中。在英美法系,空間與土地分離之法理最早以判例形式確立。早在1857年,美國愛荷華州判決(Rodes V.Mccormick,4 Iowa,386)就肯定“空中權可以分離所有”。1898年,伊利諾伊州判決(Westside Elewared Railway Company V.Spinger,171 1.170)明確可將地表“剔除”而僅以空間為所有權的客體。1973年,著名的“俄克拉荷馬州空間法”總結此前判例和學說,再次確認空間是一種不動產,其與一般不動產一樣,得成為所有、讓與、租賃、擔保、繼承的客體,并在課稅及公用征收上亦與一般不動產適用相同規則。可見,英美法系是依據占用空間的垂直高度差異,通過法技術在觀念層面以水平性分割,并明確其上下范圍,分別以此為客體設立不同的財產權。既然空間是法律上獨立的物,在邏輯上就自然存在空間所有權、空間利用權等完整的權利構造[5]。此外,英美法系還以時間尺度為產權分離。英國1947年頒布《城鄉規劃法》,明確私有土地之未來發展權歸于國家所有。20世紀60年代,發展權作為一項規劃手段引入美國,創設發展權轉移制度。地方政府為緩解分區規劃對私人財產權的價值減損,允許土地所有權人將未利用之發展權轉移至相鄰土地之上,與后者原有之發展權合并與疊加使用。該制度設計意味著將土地“未來發展利益”與“當前使用利益”視為不同標的物,進行分割處分[6]。
1.2 理論基礎
空間分離原理的理論基礎是產權理論。科斯等人所開創的產權理論根植于英美法系財產權社會土壤之中,存在三個顯著特征:一是產權是一束受保護的權利(a bundle of rights),或者說權利集合體。至于這個集合體中包含哪些權利類型,可按照不同標準給出差異化回答,但任何人均無法列舉窮盡。這是由于資產屬性多樣性、信息不完備性和主體行為能力有限性,使得充分界定產權的成本高昂,從而決定了產權界定的相對性、漸進性和公共領域存在的絕對性[7],進而反映在法律上權利人完全可根據實踐需要通過合同自由創設[8]。二是產權具有可分割性。產權束中的各子項權利相互之間不存在從屬或依附關系,具有潛在的獨立性,存在“拆解”開來獨立使用與讓渡的可能性。三是產權強調的是權利人的經濟利益實現,不突出相對人或特定物。如巴澤爾[7]所言,產權在從財產獲益的能力的意思上來說,很大程度上是一個經濟價值問題。凡是能產生潛在經濟價值的利益、收益和權利,在英美法系均可被定義為財產。基于這一邏輯,空間與土地的分離本質上不過是技術進步和稀缺性變化,催動土地空間資源屬性及其經濟價值發現,并從土地中分割出來獨立為產權界定的動態過程。
1.3 研究進展
我國臺灣地區學者溫豐文[4]認為基于空間分離原理的技術路線是將傳統由以地表上下垂直所有與利用為中心之法理,轉換為以地表上面或下面橫切一空間而為水平所有與利用為中心的法理,空間權之構造包括空間所有權與空間利用權,后者又分為“物權的空間利用權”和“債權的空間利用權”。這一認識深刻影響了大陸學者關于土地產權三維界定的立法路徑認知。以王利明[2]為代表的學者認為空間權可以與建設用地使用權相分離,通過登記公示方法加以確定,成為一項新型的獨立物權。于瑋瑋等[9]認為土地與空間之物理形態截然不同,兩者分別是由土壤、砂石組成的混合物和由空氣組成的混合物,決定了空間利用權區別于建設用地使用權。王萬茂等[10]認為,順應城市土地立體空間利用之趨勢,必須確立三維土地觀,將空間視為與土地相分離且具有獨立價值的“物”。王者潔[11]進一步指出我國《物權法》將空間權納入建設用地使用權,事實上否認了其獨立物權的資格,已經不能適應當下及未來空間權制度生成的走向。沿著這一思路,一些學者[12-13]主張在立法上創設獨立的地下空間權制度,明確界定地下空間所有權和使用權,方能加快地下空間合理開發利用。
2 基于空間區分原理的技術路線及其理論邏輯
2.1 技術方案與實踐表達
基于空間區分原理的技術路線認為,在空間資源價值凸顯情境下,土地不應該被視為具有“上窮天宇,下及地心”垂直支配力的“單一物”,而是由地表、地上和地下空間等諸要素構成的“集合物”。在法理上,兩者區別在于,前者是以一個整體作為產權客體,后者則可分別將其構成部分作為客體設定數個產權。地上與地下空間作為土地所有權支配范圍的一部分,已然具備獨立物格。但空間權利獨立不等同于空間權獨立,除客體為地上或地下之一定范圍內的空間之外,空間權與土地上的用益物權在權利的設立、效力、內容及限制等諸方面均無質之差異[14]。亦即,空間權本質是對一定空間上所設定各種權利種類的抽象概括[15],進而主張將空間權利有機嵌入既有土地權利體系,明確區分地表、地上和地下,以使用的空間不重疊、不交叉為前提,分別以之為客體,在一宗土地之上設置數個地上權。由于這種區分是在土地所有權支配的空間范圍內運行,空間所有權事實上已為土地所有權涵括。
這一技術路線主要體現在大陸法系空間地上權的立法實踐。在大陸法系,地上權人享受的對他人土地之使用收益范圍與土地所有權人并無差別。由此導致,土地所有權人在設立地上權于他人后,于同一土地之上下,已無剩余空間再為第三人設定空間地上權[5]。對此,德國1919年的《地上權條例》建立了次地上權制度,允許地上權人在自己支配的土地空間范圍之內,以地表或上下的特定范圍空間為客體,為第三人設置“次地上權”。而《日本民法典》(1966年)和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2010年)則采取了區分地上權模式,允許土地所有權人在普通地上權人享有的空間范圍之內,于土地上下劃定一定空間范圍,為第三人設立“區分地上權”。由于區分地上權的空間本質上屬于地上權人,故而要求土地所有權人或征得地上權人同意(《日本民法典》第269條之二第2句),或按照契約法理(臺灣地區“民法典”第841條之三)和“無妨礙原則”(臺灣地區“民法典”第841條之五),調整區分地上權與普通地上權之間的復雜空間利用關系。
2.2 理論基礎
空間區分原理的理論基礎是物權理論。物權理論始于羅馬法,經過德國羅馬派法學家匯纂,形成以潘德克頓法學為集大成的財產權范式,存在三個顯著特征:一是強調概念嚴謹和體系周密。作為理性主義產物,潘德克頓法學通過“提取公因式”的方法抽象出一般概念,然后由總分概念的層層演繹使得法典成為一個具有高度思想性、科學性和實用性的整體,再藉由三段論式的法律適用達到“只聽從抽象概念那種臆想的邏輯必然性的計算過程”[8]。物權理論就是由物、物權、物權行為、物權變動等環環相扣的法律概念構建的精致理論體系。二是強調對特定物的全面支配權。物權以所有權為中心,以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為重要組成部分。其中,所有權以全面的物之支配權為內容,具有單一性,對標的物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等權能形式[16]。用益物權和擔保物權則是所有權人為他人所設定,盡管所有權的實質內容幾成一個空虛權利,但待他物權消滅之時,所有權仍可恢復其原來之完全圓滿之狀態,謂之彈力性或歸一性[17]。三是強調對特定物的直接排他性支配。物權排他的絕對性,意味著一物之上只能存在特定效力的一個物權。譬如,一物上只能存在一個所有權,當存在兩個以上限制物權時,兩者之間必然存在先后順位差異,其物權效力是有差別的[18]。可見,空間區分原理完美內嵌于大陸法系物權理論體系,本質上在土地所有權支配的空間范圍內,按時間順序先后設立“普通地上權”和“空間地上權”兩個限制物權,并依據一定規則構建物上權利支配秩序,使之各歸其位、各得其所。若按照英美法系做法,冒然將空間與土地、空間權與土地權相分離,勢必造成法律體系的內在邏輯沖突與物權理論大廈的轟然坍塌。
2.3 研究進展
我國物權立法繼受了潘德克頓法學的物權理論。以梁慧星[19]為代表的學者旗幟鮮明否定空間權獨立性,主張將空間權分解為空間基地使用權、空間農地使用權和空間鄰地利用權,分別歸入基地使用權、農地使用權和鄰地利用權之中各別規定。2007年《物權法》第136條引入分層設立建設用地使用權,一些學者[20]認為該規定確立了中國特色的空間權法律制度,尤其是通過對大陸與臺灣地區空間權利設計思路之比較,發現“區分地上權”與“空間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權利體系構建具有明顯的一致性[21]。但是,由于地表、地上與地下空間的邊界不清晰[22],空間權利體系[23]與沖突協調規則不健全[24],尤其是實務中在形成出讓方案和簽訂出讓合同環節,預先確定“建筑物、構筑物及其附屬設施占用的空間”(《民法典》第348條)存在實踐操作困難,導致分層設立建設用地使用權制度事實上處于休眠狀態。為此,一些學者主張在立法上增設分層建設用地使用權制度,以統攝建設用地地上地下分層利用[25]。同時,明確空間權利類型與運行秩序[26-27],優化空間沖突與空間相鄰關系的處理規則[28]、引入三維登記[29]和借助“用地復核驗收”制度[5]等方式,才能激活制度設計。
3 基于三維地籍原理的技術路線及其理論邏輯
3.1 技術方案與實踐表達
基于三維地籍原理的技術路線認為,地籍是關于土地權利、限制和責任等內容的完整而現勢證明,是土地的“戶口”。長期以來,在土地即“地皮”的平面思維認識下,以地表為中心建構二維地籍,將平面界址點形成的閉合多邊形(即“二維宗地”)作為地籍管理的基本單元。土地立體利用導致垂直方向利用方式分異和權利主體多元,顛覆了二維地籍關于土地垂直方向利用方式同質性和權利主體唯一性的邏輯基礎,主張將空間維度引入地籍管理,藉由界址點和界址面圍合的三維空間域界定土地權利,精準表達土地空間利用信息與空間拓撲關系。這種作為權利單元的三維空間域被稱為“三維產權體”,是一個地理空間位置固定、形體唯一,權屬界線(面)封閉、權利獨立的不動產單元,是物質實體和權利的合成體[30]。可見,三維地籍的技術基礎是用數學模型精細化描述和界定空間實體抽象后的幾何形態,由此定義土地產權空間域,導致空間物理形態與產權形態的高度同一性。因此,基于三維地籍的技術路線本質上是沿著工程技術手段實現權利客體特定化的方向,對作為產權客體的“空間域”進行精細化描述、界定與管理,而權利本身則是一個由法律所定義的外生變量。
這一技術路線主要體現在近二十余年來各國探索建立三維地籍的研究實踐。早在2001年,國際測量師聯合會(FIG)就在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成立了三維地籍工作組,將研究領域劃分為法律、技術和組織等三個方面并沿用至今。截至2022年,FIG組織召開了7次國際研討會,推動國際社會在三維地籍數據模型、三維可視化和三維登記等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31-33]。但是,三維地籍的癥結是法律而非技術。如果法律上沒有確立三維產權,三維地籍就不可能存在。近10年,國際學術界逐漸加大了對三維產權研究力度,瑞典、德國、以色列、澳大利亞、馬來西亞等嘗試引入土地產權三維界定與管理[32-36]。如瑞典2004年實施的土地法典第一章第1條規定“不動產是土地,可以被分割為財產單元(Property Units)。一個財產單元是以水平界分,或同時以水平和垂直界分(both horizontally and vertically)”。馬來西亞2008年修訂的土地法典重新定義了地表地塊的最小深度,以便進行分層產權界定與登記。以色列2018年12月頒布的土地法第33條修正案也授權當局以不動產體積作為財產登記單元。按照PAULSSON[37]的定義,同時以水平和垂直界分的財產權即為三維產權(3D Property Rights),并據此將各國法律中業已存在的三維產權歸納為4種類型:(1)獨立的三維產權,包括空中宗地和三維建筑產權;(2)公寓產權(Condominium),包括公寓所有權、公寓使用權和公寓租賃權;(3)間接所有權,包括租戶所有權(Tenant-ownership)、有限公司和住房合作社;(4)授予的權利(Granted rights),包括租賃權、役權和其他權利等。但迄今為止,世界范圍內仍未建立起真正的三維地籍管理體系[33]。這是因為建立三維地籍不僅要升級現有的信息獲取、表達和評價等方法[38],還需構建一套完整定義立體空間權利的法律原則與驗證規則[39],創新登記的內容、方法與技術[32]。
3.2 理論基礎
三維地籍原理的理論基礎是土地空間資源認知論。這一理論認為,土地具有原生的三維空間特質。我國著名學者于光遠[40]指出,土地通常是指地球表面上垂直投影的那個部分,常以面積衡量大小,但是土地本身還是立體的。從土地利用史看,無論是農業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土地利用都不是純粹的二維地面活動,其本質是對一定三維空間的占用。不過在農業社會,由于土地垂直方向利用方式同質性和權利主體唯一性,二維產權界定足以實現定分止爭,導致第三維被忽略了。隨著土地利用不再囿于地表,在滿足日益增長的空間需求過程中,地下、地上空間逐漸成為可資利用的稀缺資源,為完全、獨立和排他性之法律支配,第三維在產權界定中的作用才得以凸顯。因此,土地空間資源是以土地表層為基底或脫離土地表層的可利用的三維空間存在,是從人類可利用與支撐人類生產生活角度所界定的包括土地表層、地上、地下范圍內的自然經濟綜合體,具有自然客觀存在性、容量增長與相對稀缺性、三維形態和綜合屬性等顯著特征[41]。基于這一認識,作為土地概念本源的“空間”,無論是在物理上,還是法律上,都不可能與土地相分離,否則“土地”將不能稱之為土地。“空間”或土地利用的第三維應內嵌于土地產權界定與管理的全生命周期,需要在理念、制度和技術等層面進行三維思維化的創新重構[41]。由此不難理解,《國務院關于做好自由貿易試驗區第六批改革試點經驗復制推廣工作的通知》強調“將三維地籍管理理念和技術方法納入土地管理、開發建設和運營管理全過程”。
3.3 研究進展
當前,國內學者主要聚焦于三維地籍管理的技術問題,在三維地籍產權體拓撲關系自動構建和檢驗算法,三維拓撲關系自動維護算法,三維產權體分析計算和可視化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42-44]。隨著自然資源產權制度改革深入,學者們逐漸意識到傳統土地管理模式不能精細化描述、界定和管理三維產權空間,存在潛在產權糾紛和社會穩定風險,進而提出完善法律界定、優化行政程序變革、完善空間登記和技術支撐等三維產權管理路徑[1]。在此基礎上,杜莖深[45]提出了三維產權空間客體特定化的兩大路徑:一是在觀念建構上,通過三維地籍、三維測繪等現代技術手段精準界定空間范圍,再藉由公示登記等法律技術方法,實現產權客體法律區分;二是在物理實體上,通過立體空間一級開發,對未供應的地下空間實施土建預留工程,框定地下空間三維產權范圍。這些研究有力推動了深圳、上海、廣州等發達地區土地立體利用的實踐探索,形成了以“二維地籍常規化管理為主,三維地籍特殊化管理為輔”的管理格局[46]。在國家層面的土地產權三維界定立法尚付闕如情境下,各地在地下空間利用實踐中主要形成了兩個具體的技術思路:一是以地下建筑物、構筑物外圍所及的范圍確定三維產權,如《上海市地下空間規劃建設條例》(2013年)第28條、《深圳市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管理辦法》(2021年)第37條;二是以水平投影坐標、豎向高程和水平投影最大面積確定三維產權范圍,如《廣州市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管理辦法》(2012年)第32條、《成都市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管理條例》(2022年)第31條。對于建(構)筑物形態規則且上下部外圍所及范圍一致的情形,基于上述技術思路的產權界定結果并無差別。但是,對于建(構)筑物形態不規則或者上下部外圍所及范圍不一致的情形,以水平投影坐標、豎向高程和水平投影最大面積確定產權空間范圍將明顯大于前者的實際產權空間范圍。
4 評論與展望
本文旨在對已有文獻涉及土地產權三維界定研究的技術路線進行一個結構性的總體把握,以整體展示該項研究的脈絡及趨勢,以期為土地產權三維界定在方法和范式上改進提供思路。但這種總體結構性的把握,難免會掛一漏萬,使得一些有價值的文獻囿于研究目標而無法進入視野。尤其是,一些學者不追求理論邏輯的純粹性,在論述過程中往往將不同層面的技術路線交織于一體。如胡蘭玲[47]認為“土地空間權是一種可以與土地所有權相分離的獨立財產權”,同時又認為“就性質而言,空間基地使用權為普通基地使用權之一種”。馬栩生[48]將“以水平投影坐標、豎向高程和水平投影最大面積確定三維產權范圍”和“以地下建筑物、構筑物外圍所及范圍確定三維產權范圍”結合在一起探索地下空間三維登記法。
總體看,既有研究在土地產權三維界定的法律表達與技術方案方面取得了積極進展,相關成果也已在國家政策層面引起反響。但在以下三個方面存在明顯分歧:(1)關于土地產權三維界定的邏輯起點,即將空間作為一種可以實現的利益或特殊的商品,還是物權客體?這是英美法系產權范式與大陸法系物權范式的根本區別。在英美法系,空間是土地產權束中的一項具有潛在經濟價值的特殊利益,一旦其價值被實踐需求所激活,隨時可作為獨立財產讓渡于人,不強調對特定物的支配性。筆者認為,討論中國土地產權的三維界定問題,必須立足于我國《民法典》以大陸法系物權范式為藍本的土地產權制度建構,這是減少制度變遷成本的必然選擇。(2)關于土地與空間的關系,是空間異于土地,進而空間權異于土地權,還是空間內生于土地、空間權內生于土地權?這是基于空間分離原理的技術路線與后兩條技術路線的重大區別。英美法系基于合同法上的利益分割要求,將空間與土地視為不同財產單元分別處置,高度契合產權范式的內在邏輯。大陸法系在法技術上則將兩者視為“整體”與“部分”的關系,若簡單地照搬英美法系邏輯,勢必混淆土地、地表與地面之概念區分,將土地等同于地表乃至地面[49]。其實,在《民法典》分層設立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制度背景下,無論是地表,還是地下、地上建設用地使用權,其客體均是一定范圍的空間,都必須以三維方式進行界定,這種爭論已然失去了其理論和實踐價值。(3)關于三維產權界定的技術路線,是基于意思自治,還是行政確認?事實上,無論是空間分離原理,還是空間區分原理,均是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權人通過民事合同方式讓渡其地上地下部分空間供他人使用,屬私法領域當事人意思自治的范疇。三維地籍將空間維度引入地籍管理,本質上是不動產權登記機關在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背景下,對土地產權支配范圍為精準化的行政確認之結果,屬于對既有物權的公示公信方式,在法理上沒有生成新的土地產權形態。即便如此,基于三維地籍的三維產權客體精準界定無疑為三維產權形態的可能演替提供了技術支撐。
總之,上述三條技術路線分別反映了法學和地籍學對土地產權形態與產權客體進行三維界定的不同技術方案。但就其內在機制而言,均脫離了我國公有制背景下土地上權利與權力群之構建邏輯與運行秩序,本質上都是沿著構建平等主體之間財產關系范式方向,將國家公權力之于土地產權三維界定的重要作用完全外部化、前提化,導致三維界定的內在邏輯與實施機制不清。“沒有一個國家理論的產權理論,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完整產權理論”[50]。在我國以“所有權——使用權”相分離為基本特征的城市國有土地產權結構體系下,以建設用地使用權為內容指向的三維土地產權形成,首先必須在公法框架下,通過規劃配置、容量生成到空間供應等三大機制層層遞進、環環相扣,將土地開發的三維要素轉換為產權邊界,框定三維產權空間的具體范圍或者產權客體,進而生成“開發容量”這個擬制的商品,實現國家公權力向民事權利轉化。爾后,“開發容量”這個商品才能在私法框架下,以民事權利的形態進入市場,并在產權實施的漸進性、不確定性、不可逆性、不可視性等復雜動蕩環境中,伴隨建設項目規劃設計方案由粗到細的動態調整,分階段逐步校準三維產權的空間范圍[49]。在此過程,國家公權力對三維土地產權具有明顯的催生、準生和確認作用,是決定三維產權內容、生成平面與豎向界址的關鍵因子,成為三維產權不可或缺的有機構成部分。亦即,三維產權不再是單純民事權利,而是通過將產權形態與產權客體界定統一起來,形成公私法交錯領域的一種新型的復合性權利形態,在法理上可視為一項兼具規劃權和物權特征的特別物權。沿著這一方向,未來學術界需要從我國土地管理的實然出發,改變當前土地立體利用研究與實踐“重技術、輕產權”的思維慣性,進一步厘清土地產權三維界定的內在邏輯與實施路徑,尤其是解析三維土地產權客體特定化實現機制、國家公權力植入三維土地產權的實現機制和三維土地產權的排他性支配機制,以及由此可能帶來的從二維產權向三維產權的土地產權范式變遷,才能打通理論與實踐的巨大鴻溝,激活分層設立建設用地使用權制度設計。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對三維土地產權的討論是在《民法典》規定的國有土地所有權支配的空間范圍內,以完善土地用益物權制度設計為價值取向展開的。隨著社會和技術進步,未來土地立體利用勢必要突破集體土地所有權人行使土地所有權的利益限度及其支配范圍。如日本2001年施行的《大深度地下公共使用特別措施法》明確規定大深度地下空間排除地表土地所有權人支配而歸國家所有。這意味著在《民法典》既有的土地所有權之外產生了新的物權形態,即三維地下空間所有權。深化土地產權三維界定研究,不斷豐富和夯實我國土地立體開發的產權理論體系,才能促進空間合理開發,切實提高土地節約集約利用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