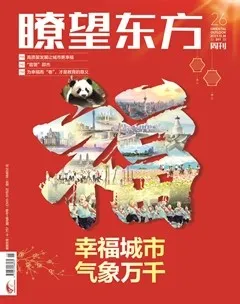海漄:在科幻中延展歷史精彩
馬宜超

海漄在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某次活動
2023年10月21日晚,33歲的海漄步入了被他描述為“理想照進現實”的時刻——在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雨果獎的頒獎禮現場,他憑借科幻小說《時空畫師》獲得最佳短中篇小說獎,成為繼劉慈欣、郝景芳之后,第三位獲得雨果獎殊榮的中國作家。
海漄并沒有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專業科幻作者,現供職于深圳某金融單位的他,從2016年起利用每天的業余時間穩定、持續地創作科幻小說,為自己搭建起繁忙現實生活之外的一方精神世界。“很多同事表達了對我這種狀態的羨慕。”海漄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他的經歷,一時間讓很多同在大城市打拼的青年人心生向往。
如果說科幻讓海漄獲得了高于現實的“翅膀”,對于“歷史科幻”門類的鐘情,則讓他打破了時空限制,在想象中遨游歷史。《時空畫師》的創作契機,始于海漄對北宋名畫《千里江山圖》的題跋產生興趣:“短短的幾十個字,信息量非常大。”海漄禁不住去想象這位被譽為天才的畫師希孟,為何在“出道即巔峰”后即隱匿于歷史的長河,并最終在自己創作的故事中讓這位畫師“復活”于紙面。
在科幻中向中國傳統文化靠近,對于海漄來說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同時熱愛閱讀科幻與歷史書籍的他,希望用科幻的筆觸填滿歷史的留白,“非常自信和大膽”地展示出那些動人心魄的“青綠山水”、五千年文化中的璀璨明珠,甚至是那些從古綿延至今的民族精神特質。
“歷史有強烈可讀性”
“歷史本身就有強烈的可讀性。”在海漄的童年時期,歷史首先是以故事的面貌出現的。童年時期的他就曾沉迷于白話版《資治通鑒》,津津有味地游走于其中的精彩人物和歷史故事。“相比于日常生活,歷史是高度濃縮、高度凝煉的,本身已經足夠精彩。”海漄在談到他如何為歷史科幻創作揀選素材時,總會有面對浩渺寶庫的感慨,而其中最吸引他的,莫過于歷史中那些“留白”的部分:在他看來,那些未詳盡的記述、待解答的謎團,正為科幻作家留下充足的可發揮空間。
在海漄看來,相較于其它類型的歷史敘述,科幻作品提供了另一種觀看歷史的角度、釋放了思考維度;在表達人物內心情感時,客觀的描述不一定能夠達意,科幻則可以通過具象的方式傳遞。
在《時空畫師》中,海漄試圖去解釋畫師希孟未遍歷華夏卻心有山川的歷史之謎,彌補天才少年如流星般轉瞬即逝的遺憾;在“離魂”冥思之際,希孟以高維生物的身份神游天下的設定,讓畫師掙脫時空束縛、遍覽名山大川和洞悉歷史成為可能,浪漫的想象填補了歷史的拼圖,為讀者展開歷史的另一層瑰麗空間。
“ 只要科學在發展,科幻的生命力就不會枯竭。科幻反之又會繼續引領人們的好奇心,讓人們對科學有一種更全面、更熱情的看法。”海漄說。
“我們生于斯,長于斯,思維方式其實就體現了我們的文化特質。”海漄眼中的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延續性,它“從來沒有中斷過”,因此對于當下的人們來說不會有太多陌生感,容易激起情感共鳴。在海漄看來,歷史題材創作者甚至無需刻意尋找歷史與當下的連接點,只需要準確并“足夠自信”地將它們展現出來。
中國神話中的“龍”是海漄多篇作品的主題;曾在2021年獲得第四屆冷湖獎中篇二等獎的作品《走蛟》,首發于《銀河邊緣006:X生物》一書的小說《龍骸》,都將“龍”置于真實的歷史與科技發展脈絡中,催生了引人入勝的科幻故事。比如《龍骸》的故事以現代硬式飛艇發明者齊柏林爵士、中國飛艇之父謝纘泰在膠州灣與巨龍的邂逅為起點,不僅用科學的方式對龍的存在提供了一種有趣的解釋,也引入了特定時代背景下對國家與民族命運的思考,既有歷史的厚重感,也有文學作品的可讀性和趣味性。
回顧自己的創作經歷,海漄認為自己對歷史與傳統文化題材的探討,隨著閱歷增加而逐步深入和發展。他坦言,在創作較為早期的一篇作品《血災》時,會更追求講一個好看的故事,于是為“血滴子”這樣的民間傳說創造了幻想中的可能;在創作《龍骸》時,科幻作為故事核心推動力的作用被進一步加強,讀者可以在科學推理中獲得更為酣暢淋漓的閱讀快感;而到了《時空畫師》的創作階段,海漄更在意透過對人物個體命運的洞察,塑造更立體的人物形象,“在歷史中去體現人類個體的渺小”。
海漄認為,中國科幻作家在創作以本國文化為背景的作品時,能夠無地域限制地進行溝通的是就與人性相關的部分:“在我們的歷史和傳統文化中,有很多體現人性本質的元素,我覺得這些東西可以打動所有人。”他總會被歷史書寫中那些不太知名卻有著不凡經歷的人物所吸引,比如在他最近閱讀的歷史學者李碩所著的《樓船鐵馬劉寄奴》一書中,劉宋開國皇帝劉裕跌宕一生的故事就讓他興味盎然。

海漄雨果獎獲獎小說《時空畫師》;最新短篇《極北之地》;小說《龍骸》的插圖(插畫/阿茶) ( 從上到下)
在三座城市培育好奇心
在海漄與科幻結緣的人生經歷中,湘潭、深圳、成都這三座城市分別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從播下科幻的種子,到見證他畢業后的初始奮斗,再到助力科幻創作理想照進現實。
“在我小時候的記憶中,工業城市會有一種非常粗糲、非常原始的東西存在。”對于成長于“雙職工家庭”的海漄來說,故鄉湖南湘潭總有撲面而來的工業氣息。他覺得,這樣的環境可能在潛移默化中,塑造了他作為科幻迷最初的“科幻審美”。
故鄉的書店是童年海漄打發時光的地方,他在這里接觸到了《海底兩萬里》《珊瑚島上的死光》《美洲來的哥倫布》等科幻作品。而真正讓海漄開始著迷于科幻閱讀,是在2001年左右:他從同學那里借來《科幻世界》,在上面讀到了劉慈欣的《吞食者》、潘海天的《餓塔》,震撼之余,從此隔段時間就會去老家公園里的一個二手書攤上購買一元錢一本的《科幻世界》過刊,沉浸在科幻文學所構筑的宏大、奇妙的想象世界中。
22歲時,海漄來到深圳工作,他在這座城市感受到,科技創新正在將科幻帶進現實:這里集合了眾多高新技術企業,正在建設一座將新能源應用變為日常的“超充之城”。
在11年快節奏的深圳生活中,海漄養成了現在的性格與做事風格:“深圳培養了我的價值觀和職業精神。”海漄已經習慣于將工作和業余時間安排得井井有條、互不干擾,“在每個不同的區間內,我會非常投入,非常專注去做一件事情,我會有目標感、會很自律。”每天晚上,海漄都會抽出固定時間來寫作,遇到卡殼的時候,就看看書來放松;在深圳上下班的地鐵上,他也總能發現和自己一樣捧著書閱讀的人,“這里很有文化氛圍”。
與中國眾多的科幻迷一樣,海漄也將成都視作“精神故鄉”,這座最早開始孕育中國科幻文學的城市也是他“想象空間中私密的小花園”,代表著他“對于另一種生活的向往”。近些年,借參加科幻相關活動的機會,海漄得以走進了這座心目中特別的城市:“成都非常現代,又是厚重的,有著悠遠的歷史,但它的歷史從來不是沉悶的,而是有浪漫感。”
就在本屆雨果獎頒獎的同一天,高校科幻平臺青年科幻實驗室聯合深圳科學與幻想成長基金,在世界科幻大會上發布了《中國科幻城市指數報告》的階段性成果,公布了中國十大科幻城市——其中就包括海漄所熟悉的成都和深圳。
海漄與眾多科幻迷一起,見證了成都從一座僅有科幻圖書出版產業的城市,逐步發展成為亞洲第二個舉辦世界科幻大會的城市。本次世界科幻大會的主場館——“星云”中的“科幻之眼”,給海漄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從三星堆文化中獲得設計靈感,讓傳統與現代穿越千年“對話”,人們還可以通過“時空隧道”進入內部錯落有致的空間。
“場館非常‘好耍,也帶動了科幻迷的消費需求,產生了經濟效益。”這次科幻大會,讓海漄又一次窺見了中國科幻產業的進步,他期待自己的作品未來能加入科幻影視、衍生品等科幻產品的開發,“科幻是一個非常通俗的門類,需要跟市場、讀者、商業走得非常近。當然,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有持續的產出,盡量把作品寫得更好一些。”

《時空畫師》的創作契機,始于海漄對北宋名畫《千里江山圖》的題跋產生興趣。圖為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將《千里江山圖》布置到展柜中(沈伯韓/ 攝)
“科幻讓我更樂觀”
在海漄這一代科幻迷的經歷中,中國科幻文學的出圈是從劉慈欣的系列科幻作品“橫空出世”開始的。“他是一顆超新星。”海漄認為,“大劉”為中國科幻搭起了一個搖籃,幫助孕育和滋養了影視、圖書出版等科幻產業鏈,為科幻在中國釋放更大的能量場提供了動力;而中國眾多的科幻作家、科幻產業從業者們,也在各自的軌道上專注于自己的使命。“新興的科幻產業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整個產業鏈上的每個人做好自己的事情。”
至今,海漄仍對劉慈欣的小說《球狀閃電》中的一句話記憶猶新:“幸福的人生,在于迷上了某樣東西。”在2016年重拾科幻寫作的時候,海漄確信愿意持續為之付出時間與精力:“我覺得自己非常幸福和幸運,因為我有屬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愛好可以幫助我克服現實中的壓力和沮喪,我會更堅強、更樂觀。”
“異常事件局(AIB)”是海漄在他的系列作品中虛構的一個調查組織,主要成員包括歷史專家胡炎、文物修復師陳雯和警察周寧——這個穿梭于科幻故事中的組織還會不斷壯大,在歷史的時空中串聯起奇思妙想。“我覺得周寧是我比較理想主義的一個化身。”海漄說,“我在現實生活中也會有很多彷徨和無助的時候,而他似乎是可以‘無所不能的。”
科幻讓人們對賴以生存的地球、神秘的宇宙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我會去做很多事情——腳踏實地工作,同時仰望星空。”海漄說。
談到對自己未來作品的要求,海漄提到,自己是一名紀錄片愛好者,希望在科幻作品中也能保持紀錄片式的客觀、冷靜。“當你把細節都做足的時候,才能把讀者帶入作品中。”海漄希望在作品中搭建出一個又一個既充滿幻想、又真實可觸的迷人世界。
在尊重已知歷史基本事實、不改變原有歷史脈絡的基礎上,海漄享受于用科幻的眼光去觸碰歷史:“科幻賦予了歷史更多可能,它根植于想象力,是自由、靈動的。當我的創作足夠成熟的時候,我會希望將過去作品的這些側重點都統一起來,在一篇作品中給大家呈現一個最好的樣貌。”
如今已過而立之年,海漄對未知的好奇、對科學與知識的敬畏并未改變。無論是充滿了科學哲思的“硬科幻”,或是更多融入了人物塑造與人文情感的“軟科幻”,只要作品中有可以滿足好奇心、打動人心的地方,他就會細細品味。
“只要科學在發展,科幻的生命力就不會枯竭。科幻反之又會繼續引領人們的好奇心,讓人們對科學有一種更全面、更熱情的看法。”海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