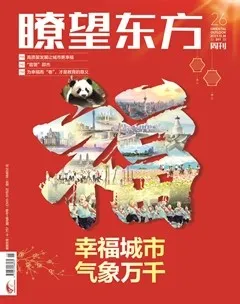共同守護“數字原住民”
劉佳璇

6月24日,小朋友在位于河南省鄭州市高新區的網絡安全科技館參觀體驗( 張浩然/ 攝)
日前,我國出臺首部專門性的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綜合立法《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條例》將于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截至2023年6月底,中國未成年網民規模突破1.91億。這1.91億未成年人,正是“數字原住民”一代——他們自出生起就生活在網絡高度普及的世界,使用各類數字工具是一種日常生活方式。
在成長過程中,“數字原住民”面臨著上一代人不曾遇見過的挑戰,例如網絡沉迷、網絡有害信息、網絡霸凌、網絡犯罪等問題。
針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提出實行“社會共治模式”。
“未成年人網絡保護不能完全強調父母責任或者完全強調平臺責任,家長、學校、政府、社會、平臺,缺了哪一個環節都不行。”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執行副主任苑寧寧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未成年人網絡權益保護及安全感滿意度調查報告》顯示,公眾對互聯網平臺應承擔的保護責任有較高期待,超過半數希望互聯網平臺能成為引導和管理未成年人上網的責任主體。
面對“雙刃劍”
2023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期間,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論壇在浙江烏鎮舉辦,這是世界互聯網大會創設10年來首次設立該主題的論壇。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未成年人的網絡權益保護已經不止是社會所關注的熱點,也是事關當代網絡治理與未來網絡發展的重要議題。
在此次論壇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華副代表畢曼達表示:“我們不能忽視孩子們上網的好處與其面臨的潛在風險之間的矛盾。”
對未成年人來說,網絡的“雙刃劍”屬性尤其明顯。
一方面,網絡使大千世界的信息觸手可及,更強的數字連接能為其成長帶來巨大的機遇;另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發展尚不成熟,自控力、判斷力較弱,使用網絡時的風險也更多。
13歲女孩被不法分子以追星期間泄露藝人隱私為由詐騙35萬余元;15歲少年遭遇網絡暴力自殺……此類未成年人涉網侵權事件,近年來不時出現在媒體報道中。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廳長缐杰介紹,2020年1月至2023年9月,檢察機關起訴成年人涉嫌利用電信網絡侵害未成年人犯罪1.16萬人。針對通過網絡聊天脅迫女童自拍裸照等問題,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確立了無身體接觸猥褻行為等同于線下犯罪的追訴原則,目前已累計追訴犯罪3000余人。
基于全國135家網絡社會組織共同發起的“2022網民網絡安全感滿意度調查”結果而形成的《未成年人網絡權益保護及安全感滿意度調查報告》顯示,近半數未成年人遭遇過網絡暴力,三成多參與過網絡罵戰,兩成多曾遇到網絡違法有害信息,一成多遇到過網絡詐騙、流量綁架等。
這項調查也顯示,有八成的成年人擔心未成年人發生網絡沉迷。
“近年來,借治療網絡沉迷之名,行傷害未成年人之實的行為也屢見不鮮。網絡不是洪水猛獸,操控和保護也不構成一體兩面。”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陳碧說。
面對高速發展的數字技術,將未成年人與網絡隔離開來不僅不現實,也不符合數字化轉型對未來人才的需求。在苑寧寧看來,在當今的數字時代、網絡空間中,實現未成年人發展權和受保護權的平衡,需要更多的法律法規和頂層設計來支撐。
發展權即未成年人獲得網絡素養和數字技能的權利,受保護權即為未成年人化解面對網絡時的風險,使其免受侵害。
“《條例》對這兩個核心議題做了非常好的回應,一方面注重發展權益,一方面注重未成人的網絡安全,在二者之間做出了一個平衡。”苑寧寧說。
壓實平臺責任
《未成年人網絡權益保護及安全感滿意度調查報告》顯示,公眾對互聯網平臺應承擔的保護責任有較高期待,超過半數希望互聯網平臺能成為引導和管理未成年人上網的責任主體。
“‘壓實平臺責任在我國行政司法機關治理網暴違法犯罪行為的文件中屢屢出現,主要是基于‘誰提供,誰治理的原則。在保護未成年人網絡權益的語境之下,這種平臺責任的壓實又多了一層‘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期待,這對于建設未成年人友好型的網絡空間至關重要。”陳碧說。
以防止網絡游戲沉迷為例,2021年8月30日,國家新聞出版署下發《關于進一步嚴格管理切實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網絡游戲的通知》,對未成年人的游戲時長、實名認證等做出更嚴格的限制,要求所有網絡游戲企業除規定時間外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網絡游戲服務。
中國音數協游戲工委、中國游戲產業研究院聯合伽馬數據發布的《2022中國游戲產業未成年人保護進展報告》顯示,經過政策推行與企業落實,未成年人游戲沉迷問題得到相當程度緩解,75%以上的未成年人每周游戲時長在3小時以內,未成年游戲用戶群體整體消費水平處于低位。
“從企業的具體實踐來看,只有企業主動承擔才能推動保護水平的提高。”北京理工大學智能科技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員王磊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在社會共治的共同體中,作為監護人的家長是第一責任人。”苑寧寧說。
此次出臺的《條例》,明確了對未成年人用戶數量巨大或者對未成年人群體有顯著影響的網絡平臺企業的有關義務。同時,《條例》還要求,智能終端產品制造者應當在產品出廠前安裝未成年人網絡保護軟件,或者采用顯著方式告知用戶安裝渠道和方法,來強化智能終端產品的未成年人保護功能。
“這都是此次立法在未成年人保護法基礎上做的一些突破,但這些條款不是憑空而來的,是一些頭部企業做了很多探索,也提供了思路。”苑寧寧說。
“但與此同時,很多平臺企業對怎樣做好未成年人網絡保護工作仍了解不夠、重視不夠,也不清楚如何更好地做工作。”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麗華說,從國家立法的層面來看,《條例》與其說給平臺企業提出了各種要求,不如說指明了方向、確立了方法,企業只有積極落實規定才能實現健康持續發展。
社會共治
針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提出實行社會共治模式,體現為家庭保護、學校保護、社會保護、政府保護的多方聯動,明確了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學校、家庭、行業組織、新聞媒體等的責任義務。
在此之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責任更多落在了提供互聯網服務和產品的企業頭上。“但這種保護是不全面的。”長沙市芙蓉區檢察院第一檢察部副主任徐艷俠說。
從諸多實際案例來看,未成年遭遇網絡侵權、發生網絡沉迷的背后,往往牽涉家庭教育矛盾升級、網絡素養鴻溝凸顯、青少年心理健康等復雜問題,僅僅調動平臺很難化解未成年人面對網絡時的風險。
徐艷俠認為,只有各方主體在各方面承擔義務和履行職責,才能將未成年人的全面保護貫徹落實在網絡環境中的每個環節,而“社會共治模式”對于不同的主體責任義務劃分也存在差異,更有針對性,更易于履行。
“在社會共治的共同體中,作為監護人的家長是第一責任人。”苑寧寧說。
綜觀《條例》內容,監護人對未成年人網絡保護的責任義務包括:保護未成年人個人信息安全;預防未成年人沉迷網絡及接觸有害信息;提高自身的網絡素養,以教育、示范、引導和監督未成年人。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發布的《青少年藍皮書: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運用報告(2023)》,在近10年中,僅有四成左右的家長對未成年人上網有規定和指導,例如家長會規定未成年人上網的時間、地點,對瀏覽的網站和內容進行甄別。
“只有家長、監護人提高自身網絡素養,才能對孩子進行教育。”王磊說。
在現實生活中,很多家長常常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什么工具對孩子使用網絡進行管理更有效。
苑寧寧表示,《條例》要求平臺在研發軟件和智能終端的過程中提供“家長工具”,為父母在數字空間中履行好自己的監護責任提供相應幫助,可視為一種賦能方式。
“社區和學校等可以為家長提供相應支持。”北京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黨委書記方增泉說。
實際上,《條例》也要求,學校應當將提高學生網絡素養等內容納入教育教學活動。不過,目前部分學校和教師對網絡素養的認知和重視程度還有待加強。同時,在網絡使用方面現有師資本身也與“數字原住民”一代存在一定鴻溝。
細看《條例》的每一則條款,認真執行落地仍需全社會共同努力。如何營造一個未成年人友好型的網絡世界,仍然是一項需要全世界共同面對的社會治理難題。
“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切身利益時,應當盡可能做到予以充分的尊重、理解和鼓勵,站在未成年人的立場,為其創造充分的發展空間。”陳碧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