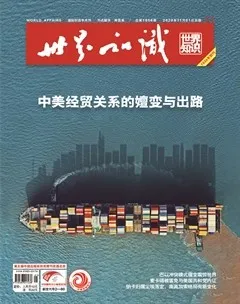影響中美經貿關系的因素空前復雜,預期在改變
周密:在觀察和談論中美經貿關系時,不能忽視的一個現象是,人們對它的預期在改變。過去,人們覺得中美經貿摩擦更多是源于兩國經濟和市場方面的競爭與矛盾,沒有什么不能通過協商談判加以解決的,因而多為短期現象,特朗普挑起的“貿易戰”也是其作為“非主流總統”采取的“非主流措施”。然而,拜登政府上臺后,繼承了特朗普時期的衣缽,以更大聲勢和力度推進對華戰略競爭,并且在科技、軍事領域采取更加精準、嚴厲的對華封堵打壓措施,把人工智能、視覺識別、通訊電子等高科技領域的更多中國企業納入“實體清單”,進行更嚴密的監控和限制。這使得大家意識到,中美經貿關系的逐漸疏離只不過是兩國戰略目標對立、戰略矛盾激化在具體領域的具體表現罷了,有可能形成長期化的趨勢。與此同時,中美經貿關系也日益受到意識形態、人權、地緣政治等非經濟因素沖擊,甚至受到不與中國相鄰地區的重大地緣政治事件(比如烏克蘭危機)影響,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
市場預期的改變必然帶來市場主體行為的改變,企業不再僅根據成本高低來估算比較優勢、確定發展戰略,而是不得不考慮即使達到合規要求,正常經營的項目是否也仍存在因政治、安全等領域不可測事件而發生中斷的風險。越來越多的兩國和其他國家企業主動調整供應鏈布局,以規避中美關系不斷惡化帶來的風險。放到更廣視域里看,中美乃至全球貿易的邏輯也發生了改變,從原來只注重分工和效率,變成現在既強調分工和效率,又重視安全和防風險,對安全的注重甚至超過對分工和效率的強調。這樣的結構性變化越來越嚴重地擠壓著中美、中外經貿關系中的利益協調和妥協空間。
繼今年7月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訪華后,9月商務部長雷蒙多也對中國進行了訪問。中美省州經貿合作研討會9月在廈門召開。雙方最近也已商定,成立經濟領域工作組,包括“經濟工作組”和“金融工作組”。接下來會有一些平時重點關注經濟問題的美國國會議員訪華。包括總統拜登在內的美方政要都在不斷重申,美國“不尋求與中國脫鉤”。應當承認,雙方在經貿問題上還有合作的空間。但是,企業對中美關系信心的流失也是顯而易見的,不認為中美關系在短期內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的可能。中方對美方不僅“聽其言”,更在“觀其行”。美方一邊口頭強調“無意脫鉤”,一邊不斷出臺行政令、國會立法或部門清單嚴限雙邊貿易投資活動,無助于重建有利于兩國合作的底層邏輯。
圖表2:白宮發布的兩版關鍵與新興技術清單(CET)

制表:楊水清。數據來源:美國白宮官網,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
董汀(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結構性的變化背后,是結構性的矛盾。中美兩國當前的首要任務不應是與對方進行戰略競爭并重構世界格局,而是謀劃好、維護住自己的安全與發展,彼此經貿關系的核心矛盾可能已經變成各自日益增長的安全和發展需求與地緣政治、技術迭代等帶來的不確定性之間的矛盾。所以我們看到,中美在經貿領域的相互重要性在下跌,存在一系列強行脫鉤的舉動,但各自又在不斷出臺刺激經濟、創造就業、扶持創新、保護發展的產業政策,實際上形成一種“倒掛”。
中美之間強行脫鉤的舉動最集中體現于科技領域,背后的驅動力是新一代顛覆性技術發展的不確定性。現在的網絡技術門檻比較低,后發優勢明顯,而新一代通用人工智能技術的增長是指數級的,可能是“去后發優勢”的,也就是說,一旦一國掌握了先機,就有可能是“一騎絕塵”式地一直領先下去,不給別國留下趕超的可能。美方要發展自己的經濟,就要確保占據新技術的上風,為此挖空心思打壓最主要的競爭對手中國,甚至采取產業政策、政治打壓以及非常規手段,不惜犧牲自己的企業和經濟利益,純粹的經濟理論和市場邏輯不再起絕對主導作用。但與此同時,新技術帶來的風險也高度不確定。“脫鉤”也好,“去風險”也罷,都是美方應對技術不確定性的手段。風險不確定,所以手段也不固定,不斷變化,動態調整。
美方對我們進行科技打壓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要削弱中國的數字技術競爭力。新一代數字技術,集成電路是“根基”,人工智能是“本源”。過去十幾年,美方對中國的科技打壓主要集中在“根基”部分,也就是限制與芯片相關的對華硬件出口。接下來,限制措施會逐漸向人工智能的算法等領域聚攏。美國對中國人工智能發展潛力的基本評估大概是:中國雖然在全球人工智能發展格局中已經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但基礎研究能力尚不足以引領“范式性的”技術突破;中國的人工智能產品發展和創新深度得益于國際合作,憑借驚人的學習能力和龐大的人口基數,在算法測試與改進方面比美國更有優勢,但美國仍能憑借自己的基礎研發和社會創新能力在商業模式創新方面占據先機。這一判斷恰恰構成了美國把“大刀”砍向中國加強基礎科研所需產品和技術的底層邏輯,而“大刀”一旦落下,受損的不僅是基礎研究本身,商業創新、研發投資都會受到影響,因為科研作為科技產業價值鏈的支柱,既是創新的根基,也是可持續研發投入的重要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