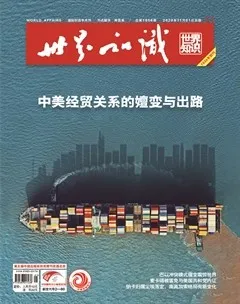麥卡錫被罷免與美國共和黨內訌
陳佳駿

美國國會眾議院眾議長坐席。
10月3日,在一小群共和黨“叛亂分子”的策動下,凱文·麥卡錫被從美國國會眾議長的位子上趕了下來。此后半個月,共和黨努力尋找麥卡錫繼任者的過程混亂不堪。無論是眾議院多數黨領袖史蒂夫·斯卡利斯,還是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吉姆·喬丹,都或多或少面臨黨內個別派系的堅定反對而難以取得多數支持——前者面臨來自屬于喬丹派系的極右翼保守派抵制,后者盡管擁有特朗普和麥卡錫的背書,但還是遭到斯卡利斯的盟友以及溫和派阻擊。回顧既往,2015年10月約翰·博納宣布辭去眾議長一職后,眾院共和黨人花了一個月時間選擇他的繼任者,不排除這次還需要那么久。
兩種議長“生涯模式”
共和黨的內部混亂為何會走到這一步?表面原因是,“大歸類”(Big Sort,指美國社會越來越由政見所隔離,人們選擇與志趣相投的人交往)造成的離心式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一方面,“大歸類”為兩黨現任議員創造了極其“安全”的選區,他們任內面臨的唯一挑戰是黨內初選。在初選中,競爭的焦點不是候選人說服搖擺選民的能力,而是他們的黨派意識形態“純潔性”。另一方面,在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媒體煽動下,許多初選選民更渴望聽到候選人堅持與另一黨相對抗的不妥協言論,這又迎合了政客們的表演欲。不過,除去這些表面原因,引發共和黨內訌背后的制度和政治文化上的深層誘因更值得關注。
麥卡錫遭罷免在美國國會眾議院歷史上幾乎沒有先例。唯一一次類似的努力是在1910年,被稱為“眾議院沙皇”的議長約瑟夫·坎農將“罷免動議”作為打擊黨內“叛亂分子”的政治威懾手段。當時,身兼眾議院規則委員會主席一職的坎農可謂“獨攬大權”,不僅決定著立法規則,還能根據個人喜好來決定各委員會主席與委員會成員人選。這引發了不少黨內成員的反抗,一些“叛亂分子”與民主黨聯手剝奪了坎農的規則委員會主席特權,甚至對其議長職位造成威脅。坎農隨即給自己提出了“罷免動議”。由于大部分共和黨同僚支持他繼續擔任議長,動議最終未獲通過,但坎農通過此舉將“叛亂分子”記錄在案,震懾住了他們。坎農最終成為“傳奇議長”,至今國會山南側的三座眾院辦公樓之一仍以他的名字命名。
麥卡錫作為一名弱勢議長,面對的是黨內成員對他提出“罷免動議”,而非像坎農那樣自己提出,因而兩者幾乎沒有可比性。但如果從議長“生涯模式”的角度來看,坎農和麥卡錫的遭遇又屬同一類,即都遭到黨內一小撮“叛亂分子”的反抗。事實上,縱觀近100年美國眾議院的發展態勢,議長的“生涯模式”大致可分為兩類:“終身”模式和“反抗與拒絕”模式。
1933至1987年這段時期的議長“生涯模式”可被視為“終身”模式。從亨利·雷尼開始,到提普·奧尼爾為止,其間的八位議長除共和黨人小約瑟夫·馬丁因政黨失去多數席位而不再擔任議長外,其余七人的議長生涯均終結于正常退休或任上過世。這一時期的議長職位之所以穩定,主要歸功于民主黨統治國會的核心方式,即委員會主席終身制。眾議院在起草立法時很大程度上服從委員會主席的意見,議長所起的作用是“主持”(preside),并以自己的方式發揮影響力。
1987年至今,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內部愈發呈現出分裂和派系斗爭的趨勢,尤其是在1994年“共和黨革命”使共和黨時隔40年重新奪回眾議院多數席位之后。究其原因,是紐特·金里奇擔任議長后,基本顛覆了委員會主席終身制,議長權力進一步擴大(值得一提的是,后來的民主黨眾議長佩洛西又進一步增強了這種影響力),共和黨內部的派系斗爭由此展開,并在2010年“茶黨浪潮”之后加劇,三位共和黨眾議長均遭到來自黨內右翼的“反抗與拒絕”。
這又回到與坎農的類比,似乎眾議長權力越大,就越有可能失去權力,麥卡錫也未能逃脫這一“宿命”。而要擺脫“宿命”,或許就要回到20世紀大部分時間的“常規秩序”中,即重建眾議院委員會程序。但在當下,無論是黨內還是兩黨的極化斗爭背景下,這種重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目前也看不到共和黨任何一位眾議長候選人會配合這種重建。
“93號航班選舉”邏輯
當前共和黨極右翼“反抗與拒絕”的本質,是其對政治抱有“末日般的看法”。他們將民主黨、深層政府、拜登政府乃至共和黨“建制派”都視為“左翼敵人”,認為他們既腐敗又邪惡,以至于任何同他們進行的合作都是“下賤的妥協”。麥卡錫今年6月與民主黨達成債務上限協議、9月同民主黨達成避免政府關門的“續期決議”后,立刻被共和黨極右翼指責為“進行了事關共和黨生死存亡的背叛”。在共和黨極右翼看來,妥協措施在“末日世界”里等同于自殺,他們寧可為沒有明天而“戰死”,也不愿為更美好明天而“建設”。
美國輿論近年來經常用一個詞匯來概括這種邏輯,那就是“93號航班選舉”(The Flight 93 Election)邏輯。該名詞最早是2016年9月《克萊門特書評》里一篇文章的標題。作者使用化名,后來被發現是曾任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戰略溝通事務副助理的邁克爾·安東。2001年9.11事件當天,美國聯合航空公司的93號航班被恐怖分子劫持,機上乘客奮勇反抗,結果飛機在賓夕法尼亞州尚克斯維爾附近鄉村墜毀,以機上所有人的性命為代價避免了恐怖分子利用該機攻擊華盛頓重要目標的企圖。邁克爾·安東借用這件事來鼓動共和黨以同樣的殉難方式反抗“民主黨的統治”。他寫道:“2016年的總統選舉是‘93號航班選舉:控制好駕駛艙,否則你死定了”;“無論如何,你都可能會死……但如果你不嘗試,就一定會死”。
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中的失利以及2021年1月“國會山騷亂事件”的爆發,使“93號航班選舉”概念得到更多關注。可以說,“國會山騷亂事件”遵循的就是“93號航班選舉”邏輯:他們希望像那架飛機的乘客一樣,控制駕駛艙,幫助特朗普從拜登手中接管飛機。對他們而言,特朗普固然有很多缺陷,但這些缺陷與他毫不留情、無所顧忌地消滅左翼力量的“美德”相比顯得微不足道。
“國會山騷亂事件”后,安東又在《克萊門特書評》上發表題為《持續危機》的文章。他一面否認自己是“國會山騷亂事件”的罪魁禍首,一面鼓動共和黨右翼“制定新戰略”,繼續沖擊飛機駕駛艙,讓93號航班的“緊急狀態”或多或少成為永久情況。事態正在沿著他的設計發展:特朗普幫助一批極右翼共和黨人進入國會,這些人如今將“93號航班選舉”邏輯完整貫徹于債務上限、政府關門、議長罷免等議程中。安東曾在其2020年出版的《賭注:不歸路上的美國》一書中警告:“‘紅色美國可能會悄悄開始讓聯邦在其地盤上的行動變得更加困難——一開始是自發的,后來可能會通過更明確的合作。”

2023年10月3日,美國眾議院表決通過罷免共和黨籍眾議長麥卡錫的動議后,麥卡錫(圖中)在眾人簇擁下離開表決現場。
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
“93號航班上的乘客們”對美國對外政策也在產生影響,他們是從對抗國內左翼的立場出發思考美國對外政策的。
例如,他們將反對繼續援助烏克蘭作為制約聯邦政府開支的重要砝碼。許多評論將他們稱為“保守的孤立主義者”,這種說法并不完全準確。他們當中有一些人雖然要求削減對烏援助,但卻強烈支持在巴以沖突升級背景下增加對以色列援助。他們反對援烏的更深層次邏輯是,他們將俄羅斯總統普京視為同美國國內乃至整個西方世界“覺醒左翼”進行對抗的“盟友”。
同樣的,他們也持有一套“病態”的對華邏輯:相信美國左翼“全球主義者”正密謀剝奪美國工人的財富并將之轉移給中國。盡管如此,他們并不像共和黨建制派中的對華鷹派那樣歇斯底里反華,而是將國內議程置于更高位置。以極右翼的“自由黨團”為例,為了阻止提高債務上限,今年3月他們提出了520個限制政府開支的法案,其中就包括限制對美國在臺協會、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等涉華機構撥款的動議。由此可見,盡管“93號航班上的乘客們”會說一些對華強硬的言論,但在他們眼中,“意識形態純潔性”始終要比建制派口中所謂國家安全戰略利益更為重要。不過,美國國會的反華議程主要還是由共和黨建制派中的對華鷹派把持,“93號航班上的乘客們”在對華政策上究竟有多大影響力仍有待繼續觀察。
(本文截稿于2023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