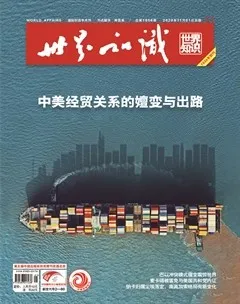德國經濟陷蕭條泥潭:短期現象還是長期趨勢
寇蔻

2023年9月5日,2023慕尼黑車展開幕,德國總理朔爾茨出席。汽車業是德國經濟的支柱產業。
近期,德國經濟形勢引發多方關注。10月10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最新預測,今年德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同比下降0.5%。IMF稱,曾是歐洲經濟引擎的德國將是今年唯一沒有增長的發達經濟體。
從“歐洲病夫”到“經濟引擎”
19世紀以來,德國形成了以多樣化、高質量生產為特征的工業和制造業體系,逐步建立了汽車制造、機械制造、化工醫藥和電子技術四大支柱產業。德國制造業價值鏈體系高度垂直一體化,涵蓋了上游原材料加工、中間產品生產、最終產品生產,建構了以大型跨國企業為核心、中小企業集聚于產業鏈上的強大工業網絡。
2022年下半年以來,德國經濟呈現低迷態勢,2022年第四季度GDP環比下降0.4%,2023年第一季度GDP環比下降0.1%,2023年第二季度環比增長0%。今年8月《經濟學人》的報道甚至發問,德國是否將再次成為“歐洲病夫”?此文在德國社會引起熱烈討論。“歐洲病夫”這一稱呼喚醒了德國人歷史上一段不愿提及的回憶。
1990年兩德統一之后,聯邦德國面臨“統一后遺癥”,兩德在經濟和社會上的巨大差距使得聯邦政府必須投入大量資源進行整合。1993年聯邦德國GDP萎縮1%,失業率上升至9.8%,東部失業率更是高達15.4%。經過一段時期的平穩增長后,2002年和2003年德國又連續兩年陷入衰退,GDP分別下降0.2%和0.7%,失業率更是超過10%。2005年底默克爾上任,采取整固財政、改革社會體制以及增加投資預算等方式穩定經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經濟企穩回升。但好景不長,德國很快又遭遇全球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沖擊。不過相比于歐洲其他國家,德國憑借其強大的工業體系在兩次危機之后迅速恢復。默克爾在任的16年間,德國GDP從2005年的2.29萬億歐元提高到2021年的3.62萬億,增長58%,從“歐洲病夫”一躍成為歐洲經濟的發動機。
除了強大的制造業,歐洲一體化也為德國經濟的增長提供助力。1993年歐洲共同體正式轉變為歐盟,隨后成員國數量持續增加,特別是2004年中東歐十個國家加入歐盟,歐洲統一市場大幅擴張。歐盟為德國提供了低廉的上游產品供應和巨大的下游市場,而歐元區的擴大也進一步降低了德國與成員國的交易成本。德國約60%的進出口在歐盟成員國之間發生,歐盟也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對象。

2023年4月15日,德國最后三座核電站——伊薩爾2號、內卡韋斯特海姆和埃姆斯蘭停止運行,這意味著德國正式告別“核電時代”。圖為內卡韋斯特海姆核電站外景。
德國經濟模式面臨的挑戰
烏克蘭危機、能源危機是引發2022年以來德國經濟低迷的導火索,但其背后則凸顯出德國經濟模式面臨的挑戰。
第一,對外依賴程度高是德國經濟的特征,這使得其易受全球政治經濟局勢動蕩的影響。德國經濟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特別是廉價的能源供應和廣闊的國際市場。在全球化時代,企業將不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環節轉移到海外,同時從國際市場以低成本獲取資源。憑借在高端制造業市場的強大競爭力,德國產品在全球市場獲得高額利潤,德國也成為全球化浪潮中重要的受益國之一。
不過早在2003年,德國經濟學家漢斯-維爾納·辛恩就對此種模式提出質疑,他將德國的經濟模式稱為“大市集經濟”(Bazaar Economy)。他指出這種模式存在的風險是,供應鏈附加值會逐步轉移到靠近消費者的下游生產。對德國而言,這些環節大多在國外,致使德國形成國外高附加值、國內低附加值的“大市集經濟”。
第二,能源危機波及宏觀經濟。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前,德國主要依賴俄羅斯的能源供應,尤其是天然氣供應。德國超過55%的天然氣進口來自俄羅斯。2022年2月,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后,歐洲國家追隨美國對俄實施包括能源制裁在內的多輪制裁,德國切斷俄羅斯能源供應,導致其國內能源價格暴漲。2022年9月至11月,德國能源價格同比上漲超過40%。此次能源危機影響范圍不僅僅在能源領域內部,更重要的是對整個經濟社會帶來巨大沖擊。2022年,德國通脹率達到7.9%。能源價格上漲對制造業的影響包括:一是成本激增,抑制私人消費,致使企業經營困難,部分企業倒閉;二是成本上升導致德國在吸引投資時區位優勢下降,德國一些本土企業甚至考慮將生產線轉移至能源成本更低的地區。
第三,德國貿易出口面臨諸多挑戰。德國是出口大國,但通脹引發德國企業出口成本上漲,德國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國際市場需求端依舊萎靡。新冠疫情后,全球經濟恢復緩慢,德國最大的單一貿易市場——中國和美國均受不同程度的影響。歐盟受通貨膨脹拖累,預計2023年GDP僅同比微升0.8%。德國ifo經濟研究所的出口預期指數顯示,從2023年6月起德國出口持續萎縮,9月該指數甚至下降11.3(8月下降6.6)。該機構認為,當前德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出口情況都不樂觀,并且波及所有主要的制造業產品。
更為值得關注的是,新冠疫情以來全球產業鏈發生深刻變化,在成本之外,供給安全成為新的約束條件,以往過長、分工精細的產業鏈開始向短平化、區域化轉變,下游企業尋求增加供應商數量以提高上游供給安全。德國以及歐盟反復強調的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增加貿易多樣性,這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產業鏈變化趨勢,進一步提升企業的國際貿易成本。
第四,德國經濟長期以來的產業轉型問題。盡管在傳統制造業領域依然保持全球競爭力,但是多年來德國在數字經濟等新興領域發展緩慢。默克爾任內曾推出多輪“數字化”戰略,并于2019年公布首份聯邦政府人工智能戰略,但仍收效有限。德國傳統優勢制造業中,化工屬于能源密集型行業,受能源危機和通貨膨脹影響較大。而汽車行業則面臨電動化、智能化變革,戴姆勒、寶馬、大眾等德國傳統汽車廠商在新能源市場上不再擁有其在燃油車領域的優勢。
經濟是否會陷入長期衰退
制造業競爭力下降,通脹率居高不下,企業撤離,德國是否會出現“去工業化”的風險?德國經濟是否將就此陷入長期衰退?盡管當前困難較多,但此次經濟下滑不會從根本上削弱德國制造業競爭力。原因在于:
首先,能源危機沖擊最大的是高耗能行業,如化工業、金屬制造加工、建筑材料、造紙業等。近年來德國能源轉型已大幅降低化石燃料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能源成本占德國大多數經濟部門總成本的比重只有2%~5%。產業轉移時刻都在發生,能源密集型產業也并非德國的比較優勢所在。短期的產業轉移并不意味著長期的“去工業化”。
其次,德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從來不是來源于成本優勢。德國制造業的競爭力來源于其高效的創新體系,包括了強大的工業企業、高校、科研機構以及重視框架條件設定的政府。德國制造業企業的基礎依然雄厚,高校和科研機構仍保持旺盛的科研產出和產學研協作,而聯邦政府近年來則不斷加大對創新領域的投入。這些因素都未因能源危機而受到削弱,能夠支撐德國經濟在經歷短暫低迷后逐步走出困境。
不過,德國經濟也面臨一些問題。2022年德國總理朔爾茨提出“時代轉折”的概念,指出德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地緣政治關系、國家安全環境均已發生巨大變化。事實上,德國對內和對外經濟導向也正在轉向。新冠疫情期間,德國政府一方面采取堅決有力的措施穩定國內經濟基本盤,另一方面強化經濟安全、經濟主權、貿易多樣化。2021年朔爾茨政府執政以來,對內強力推動能源轉型和綠色經濟,對外實施價值觀導向的貿易政策。整體而言,國家在德國經濟體系中的作用提高,政治對經濟的干預更加頻繁。
烏克蘭危機對歐洲的影響是深遠的,它打破了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地緣政治平衡,摧毀了俄歐能源供應體系,同時暴露了德國經濟的一大短板,即能源供應高度依賴歐盟之外的地區和國家。而能源短缺只是表象,德國經濟體系中長期存在的頑疾則是產業轉型問題。目前,能源方面,德國聯邦政府通過能源供應分散化、修訂《可再生能源法》、大力推動風能、氫能、太陽能建設,加速能源轉型。技術投資方面,德國政府積極吸引優質外資,2023年宣布投入99億歐元和50億歐元,補貼英特爾和臺積電在德國設廠,發展芯片技術。技術創新方面,2023年德國政府公布新的創新政策——“研究和創新未來戰略”草案,用以強化前沿尖端科技創新,加強跨部門協調。當前是德國經濟發展和變革的關鍵時期,傳統產業能否實現向數字化、綠色化轉型,新興產業能否盡快成長,都是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此外,當前朔爾茨政府內部齟齬不斷,很多政策推行緩慢。未來,在全球產業加速變革、產業競爭愈發激烈的背景下,聯邦政府的產業促進政策和創新政策能否有效推動德國產業轉型,加速新興產業發展,值得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