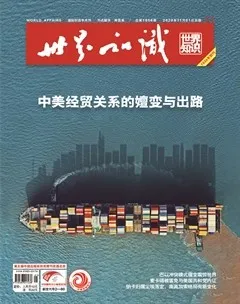尼泊爾與印度的文化起源之爭
張樹彬

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杜巴廣場上的印度教寺廟。
尼泊爾地處喜馬拉雅山南麓,北鄰中國,其余三面與印度接壤。受地理等因素影響,尼泊爾與印度有著深厚的歷史文化聯系,但也存在深刻的民族主義認知矛盾。6月18日,改編自印度教史詩《羅摩衍那》的印度寶萊塢電影《阿迪普魯什》因有“悉多(羅摩之妻)是印度的女兒”這句臺詞,招致尼泊爾多個城市禁映印地語電影。而在此前5月28日,印度新議會大廈揭幕,內設的“大婆羅多”(Akhand Bharat,意為“不可分割的印度”)地圖壁畫,也引起包括尼泊爾在內的印度鄰國的強烈不滿。那么,尼印兩國的民族主義認知矛盾有何典型表現?
不被視為外國?
印度教和佛教在尼泊爾和印度影響廣泛。在2006年5月尼泊爾議會歷史性地宣布本國為世俗國家前,尼泊爾是世界上唯一以印度教為國教的國家。如今尼泊爾86.2%的人口信仰印度教,而印度則有80.5%的人口信仰該教。也因此,印度領導人訪問尼泊爾時經常會參拜當地的印度教寺廟。此外,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佛陀)出生在尼泊爾的藍毗尼,而印度北部的菩提伽耶、鹿野苑、拘尸那羅三地分別是佛陀悟道、初轉法輪、涅槃的圣地。2022年5月,印度總理莫迪曾專程赴藍毗尼,參加佛陀誕辰2566周年慶祝活動。此外,兩國還開展了宗教文化跨境旅游合作。例如,印度開設了跨國旅游專列,將《羅摩衍那》主人公羅摩的出生地印度的阿約提亞與其妻悉多的出生地尼泊爾的賈納克普爾等印度教圣地相連。
1950年7月,尼印兩國簽署《和平與友好條約》互開邊境,此后兩國民眾可在彼此國家自由工作生活。當前,近800萬尼泊爾公民(約占尼總人口1/4)定居印度,約60萬印度人定居尼泊爾。兩國公民在彼此境內幾乎享有與本國公民同等的經濟與受教育機會。由于尼泊爾語與印地語同屬印度—雅利安語分支,皆使用天城體梵文字母,因此尼泊爾人大多能聽懂印地語。印度開國總理尼赫魯曾稱,“盡管尼泊爾是一個獨立國家,但它在文化與傳統上與印度聯系非常密切,我們沒有把它視為外國。”
兩國在軍事安全方面亦聯系緊密。例如,尼泊爾廓爾喀雇傭兵是印度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大約有3.2萬廓爾喀人在印軍服役。自1950年以來,尼軍參謀長和印度陸軍參謀長都曾獲對方軍隊授予的榮譽上將軍銜。
文化起源之爭
雖有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但尼印經常陷入文化起源紛爭,“悉多的國籍之爭”是其中一個較為典型的案例。
據《羅摩衍那》記載,悉多是“大地的女兒”,其養父即彌提羅國國王遮那竭王(Janaka)在田地的犁溝里發現并收養了她。她的名字悉多(Sita)意為“犁溝”。羅摩是拘薩羅國王子,他在比武招婿中拉開了遮那竭王的濕婆神弓,成功迎娶悉多為妻。尼泊爾的印度教信徒認為,位于尼泊爾的賈納克普爾(Janakpur,意為“遮那竭王之城”)是悉多的出生地,因此悉多是“尼泊爾的女兒”。印度的印度教信徒則認為,位于印度西北部比哈爾邦的西塔馬爾希縣的“悉多池”(Sita Kund)朝圣地是悉多的誕生地。因此,寶萊塢電影《阿迪普拉什》在尼泊爾上映后,引發觀眾的強烈不滿,加德滿都市長巴倫德拉·沙阿宣布禁映所有印地語電影,并引發尼泊爾十幾個城市效仿。不過,即使遭到禁映,該電影在尼泊爾的票房收入仍高達1990萬盧比,兩國之間的文化聯系之深由此可見一斑。
此外,尼印兩國還對佛教發源地存在爭議。尼泊爾認為佛陀誕生于藍毗尼,因此佛教起源于尼泊爾;印度則認為釋迦牟尼在菩提伽耶頓悟成佛,佛教理應起源于印度。
“大尼泊爾”與“大婆羅多”
除不時浮現的文化起源之爭外,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喧囂與擴張主義行徑經常激發尼泊爾民間的反印情緒。例如,印度曾在1975年利用錫金內亂將其吞并;在1975年、1989年與2015年,印度曾對尼泊爾進行三次貿易封鎖;尼泊爾主張主權的卡拉帕尼、里普列克與林比亞杜拉等地也被印度占據。
因此,在尼泊爾看來,印度新議會大廈內設置的被印方宣稱顯示了“古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時期疆域”的“大婆羅多”地圖壁畫散發著印度霸權主義迷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大婆羅多”便存在于一些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的臆想中,他們認為從羅摩衍那時代起就存在真正統一的印度,從今天的阿富汗到緬甸,從中國西藏到斯里蘭卡,包括尼泊爾在內,都屬于當時的“大婆羅多”版圖。幾十年來,印度執政黨印度人民黨(印人黨)的意識形態母體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RSS)一直在推動“大婆羅多”構想。2022年4月,RSS最高領袖莫漢·帕格瓦特在一次公開集會上表示,印度將在10~15年內實現“大婆羅多”理想。此次關于“大婆羅多”的爭議出現后,印人黨政客甚至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新議會大廈的‘大婆羅多地圖代表我們強大和自力更生的印度”。這引起巴基斯坦、尼泊爾和孟加拉國等印度鄰國的強烈不滿,但印度外交部辯稱該地圖“是文化和歷史地圖”,不具有政治性。隨后,加德滿都市長巴倫德拉·沙阿在辦公室懸掛涵蓋部分印度領土的“大尼泊爾”地圖進行反擊,更有尼泊爾眾議院議員提議在本國議會建筑內也放置該地圖。
“大尼泊爾”是一個政治地理概念,其范圍超越了尼泊爾目前的邊界,包括了1816年12月尼泊爾王國在英尼戰爭中戰敗后簽署《蘇高利條約》割讓給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大片領土,這些土地如今已成為印度北部旁遮普、喜馬偕爾、北阿坎德等邦的一部分。一些尼泊爾民族主義團體渴望恢復“大尼泊爾”版圖。例如,激進的尼泊爾非政府組織“大尼泊爾民族主義陣線”長期以來積極推動“大尼泊爾運動”,該組織認為“(如今印度)從西姆拉到大吉嶺的大片區域,甚至包括印度教七圣城之一的瓦拉納西都應歸還尼泊爾”。一些尼泊爾學者和前政府官員也經常撰文表示:“我們割讓給東印度公司的土地不應屬于印度。”
總之,尼泊爾雖與印度同為印度教信徒占主導的國家,但尼自豪于本國“從未被殖民”,不斷強調自己同印度的差別,并通過文化起源之爭與對印度教右翼“大婆羅多”構想的回擊等行為彰顯其獨立的民族主義認同,而尼印之間的這種民族主義認知矛盾很難在短時間內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