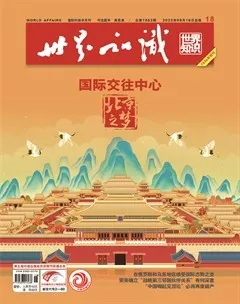印臺經貿關系:看似發展迅速,實則阻礙多重
劉宗義
近些年,印度與我國臺灣省經貿關系的快速發展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例如,6月28日,臺灣當局表示,有極大意愿同印度簽署“自由貿易協定”;2022年9月,臺灣地區代工企業巨頭富士康、印度礦業巨頭瓦丹塔與印度古吉拉特邦政府簽署諒解備忘錄在印度設立半導體與顯示器制造廠,預計投資約200億美元,雖然富士康于2023年7月宣布退出該項目,但這在當時是印度自1947年獨立以來最大的一筆公司投資;自2017年起,隨著美國蘋果公司加快挺進印度市場的步伐,其在印三大供應商,即臺企富士康、緯創資通與和碩,也在不斷追加對印投資、擴建工廠,甚至對印轉移生產線。
實際上,自上世紀90年代臺灣地區與印度建立正式的民間交流機制以來,包括經貿關系在內的印臺關系就一直保持上升勢頭。那么,應如何理解如今印臺經貿關系的迅速加強?
經濟邏輯非主要驅動力
上世紀90年代,臺灣地區與印度正式建立民間交流機制,彼時臺灣當局推行所謂“銀彈外交”和“南向政策”,鼓勵臺商在東南亞與南亞地區投資。同一時期,印度政府在實行經濟自由化改革后也提出“東望”政策,要與東南亞、東亞國家和地區發展經貿與政治關系。1995年,印臺在臺灣地區設立“印度—臺北協會”,并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設立“臺北經濟文化中心”。此后,印臺經貿互動持續增溫。但該時期臺商受大陸經濟騰飛吸引,對印度市場興趣不大。
進入21世紀后,由于馬英九當局推行所謂“活路外交”,提出“優質平價新興市場推動方案”,并將印度作為主要目標,印臺關系發展較為迅速,特別是雙方貿易額增長較快,從2006年的20億美元增長到2011年的75.69億美元。2011年7月,印臺還簽署了關于避免雙重征稅和海關互助的協議。
2014年莫迪政府上臺后,將印度外交的“東望”政策調整為“東向行動”,針對中國加強與東亞、東南亞國家和地區的安全與戰略合作,并與美國開展戰略對接。2016年,臺灣蔡英文當局上臺后,為配合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推出所謂“新南向政策”,將印度作為“重中之重”,謀求將“新南向政策”與“東向行動”對接。但彼時“新南向政策”對促進印臺關系發展并沒有迅速產生作用,直到2018年美國發動對華貿易戰后,臺灣地區對印度的投資額才出現明顯躍升。當前,約有160多家臺灣企業在印度有活躍的業務。2019~2020財年,臺灣地區對印度的直接投資額為4400萬美元,但截至2022年4月,這一數據已升至15億美元,不過僅占臺灣地區對外投資總額的近1%。印臺貿易額也有較大幅度增長,2022~ 2023財年,貿易額達到109億美元,但仍不到大陸與臺灣地區雙邊貿易額的1/30。
從印臺關系的發展軌跡可以看出,其主要受政治因素驅動,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印臺關系也在不斷增強。臺灣當局希望減少對大陸的經濟依賴,擴展其所謂“國際空間”;而印度不僅想得到臺灣地區的投資和經貿發展利益,還想利用涉臺問題對中國施壓。此外,印臺關系的逐步加強也受到中美戰略競爭的影響。
印度欲借勢發展芯片制造業
2018年后,印臺經貿關系獲得較大幅度發展,雖然美國發起對華貿易戰及其隨之而來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調整是重要原因,但實際上,臺灣當局與臺企希望降低對大陸經濟依賴的動因非常復雜。對臺灣當局來說,“臺獨”勢力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希望推動經濟“去大陸化”,其最終目的是孤立大陸,并追求所謂“獨立”;而對臺企而言,大陸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上地位的不斷攀升對其大陸市場份額的壓縮,外加大陸生產成本上升、美對華在高科技領域的選擇性脫鉤,及新冠疫情導致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暫時性中斷,都使其希望開拓新市場,多樣化發展其產供鏈。事實上,這一過程在中美貿易戰前便已開始,但中美貿易戰使這一過程加速。“新南向政策”在推動臺企將印度視為一個潛在的、有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印度已成為臺灣當局所謂“對外戰略”中的重要一環,是其在亞洲制衡大陸的長期力量。

2023年4月18日,美國蘋果公司位于印度的第一家旗艦店在孟買開業。
對印度而言,莫迪政府早在2018年便關注到美國商會報告中關于中美戰略競爭將引發全球產供鏈連鎖反應的分析,并注意到一些跨國公司為規避風險,正在考慮將業務自中國大陸轉移到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莫迪政府自2014年提出的“印度制造”計劃發展成效一直不佳,印方認為這是發展該計劃、“替代中國”的重要機遇。因此,印度開始積極與蘋果公司、富士康、大眾汽車、現代汽車等大型跨國企業協商,通過提供稅收優惠和免稅期等措施,鼓勵它們將整個或部分業務從中國大陸轉移到印度。其中,臺資企業是印度著力爭取的對象。對印度來說,與臺企合作可在很大程度上幫助印度成為一個替代性的供應鏈中心。2018年,印臺更新“雙邊投資協議”后,臺灣地區對印投資大幅增長,蘋果公司的主要供應商富士康引領了這一波潮流。在過去五年里,蘋果公司在印度的發展戰略也已發生變化,從在印度生產面向本地市場的產品,轉變為在印度建立戰略性生產基地,生產用于向歐洲等第三方市場出口的產品。
臺灣地區的產業優勢在于機械和電子制造行業,當前其對印投資也主要集中在橡膠制品、電子制造、化學品、計算機軟件和冶金工程等領域,印度希望利用其產業優勢,實現促進本國半導體制造業發展的目標。目前,印度國內所使用芯片皆為進口,其智能手機行業使用的芯片75%以上來自臺灣地區。芯片是現代電子產品的“大腦”,美國認為“芯片戰”關乎國家的“生死存亡”。2022年10月,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發布公告,對向中國出口的先進計算和半導體制造物項實施新的出口管制,這是自2018年以來,美國再次升級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制裁。印度不希望未來像中國一樣在芯片方面受美國限制,希望盡早擁有獨立的先進芯片生產能力,成為繼美國之后臺灣地區半導體制造商的第二個生產中心。印政府預測,到2026年,該國半導體市場價值將從2020年的不到200億美元增至630億美元。當然,大力發展芯片制造業也是印度成為“全球大國”野心的重要體現。
臺企在印度的發展遠非一帆風順
印臺經貿關系是當前印臺關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因其部分產業合作發展趨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際產供鏈的重新調整。
然而,對臺企來說,商業可行性和運營成本比臺灣當局所謂的“對外戰略”更具決定性,其在印度的發展遠非一帆風順。例如,2020年12月,緯創資通在印度的裝配工廠發生工人暴動,損失高達712萬美元;2021年底,富士康在南印泰米爾納杜邦首府金奈的工廠遭遇工人因勞資糾紛而舉行的大規模罷工。2023年5月,在長期經歷一系列工人鬧事、醫療事故與印度政府的行政處罰后,緯創資通宣布整體退出經營了15年的印度市場。臺企上述遭遇的更深層次原因在于印度投資環境對外企的“不友好”。當前,莫迪政府是印度自上世紀90年代實行經濟自由化改革以來在對外經濟政策上最保守的政府,其雖希望借助外國資本和技術來推動“印度制造”發展,但對外企在印度市場盈利又充滿“恐擠壓本土產業發展空間”的“不安”,因此當某一產業在外國資本扶植下有了一定發展時,外企往往會遭遇莫須有罪名的處罰。事實上,幾乎所有在印外企都“難逃一劫”,谷歌、亞馬遜、諾基亞、三星均曾遭遇數十億的“天價罰單”,因此外界甚至將印度稱為“外企墳場”。大陸企業小米在印度的遭遇也是臺企的前車之鑒。2022年5月,小米印度公司被印執法部門指控以支付版權費為名義“非法”匯款給外國實體,印方從小米集團在印度當地的銀行賬戶中扣押了約555億盧比(約合48億元人民幣)。對此,小米公司表示一直在全球范圍內堅持合法合規經營,但這部分資金或將被正式沒收。此外,印度基礎設施尚不完善等硬件問題也仍較突出。例如,半導體產業生產需要無污染的環境、不間斷的電力供應和大量的清潔用水,而當前在印度找到完全滿足這些條件的地點仍有較大難度。

2023年7月28日,印度總理莫迪出席該國在古吉拉特邦首府甘地納格爾舉行的第二屆半導體產業大會。
當前,印臺正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臺灣當局希望通過該協定使其半導體制造商可以較低成本進口生產所需組件,而印度卻認為這項協定沒有多大價值,因其一貫希望外企在印生產任何產品的所需部件也都在印生產,目的在于讓外國投資者為印度建立全產業鏈。此外,當前印臺貿易逆差已擴大到57億美元,這對印度來說難以接受,因為其所簽訂的雙邊自貿協定在實踐中幾乎都是印方享受貿易順差。
綜合來看,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印度政府和臺灣當局有意鼓勵經貿關系發展的情況下,雙方貿易額與投資額增長與總量仍十分有限。雙方企業在開展產業合作的過程中面臨多重障礙,因此印臺經貿關系發展難以一帆風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