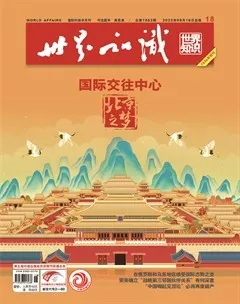在俄羅斯和烏東地區感受國際態勢之變
安剛
清華大學俄羅斯研究院的吳大輝教授是國內著名的俄羅斯和歐亞問題專家。他曾長期在軍內從事研究工作,有著豐富的理論和實踐經驗,也對中國的對俄和歐亞政策以及彼此人文交流有著重要影響力。2023年8月12日至22日,吳大輝教授赴俄進行學術訪問,出席了第11屆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參觀了“軍隊-2023”國際軍事技術論壇。他還利用此行實地探訪了烏克蘭東部的俄控地區。吳教授回國后,本刊對他進行了獨家專訪,話題圍繞此次俄羅斯、烏東之行的三項主要活動展開。以下是8月31日在清華大學明齋進行的訪談實錄。
莫安會上的大國思維
《世界知識》:在8月15日舉行的第11屆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上,俄領導層密集發聲,縱論國際秩序。您從中感受到了俄羅斯的思維方式和戰略導向正在發生哪些新變化?
吳大輝:這是我連續第四年參加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過去三屆因疫情線上出席,這是首次赴俄現場參會,又是在烏克蘭危機背景下,所以非常珍惜這個機會。除俄方人士外,許多非西方國家的官方代表團——包括中國、眾多非洲國家以及緬甸、柬埔寨等東盟國家——出現在會場上。本次莫安會沒有任何西方國家的官方代表參加,但有法國等歐洲國家的民間人士到會。同往屆相比,此次莫安會的最大變化是,俄羅斯及其盟國白俄羅斯同“集體西方”徹底決裂了。
會上,從總統普京到防長紹伊古、外長拉夫羅夫、對外情報局局長納雷什金,再到白俄羅斯防長赫列寧,所有講話均圍繞同一敘事進行:美國領導的“集體西方”為了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進行圍剿,不斷制造沖突,然后從解決沖突的過程中獲益。他們嚴厲譴責“集體西方”自以為他們的十億人是有權生活在陽光下的“黃金人口”,不屬于西方陣營的人就無權生活在陽光下。各場小組討論也圍繞這套敘事進行。自然而然,美歐國家輿論認為這屆莫安會是一次“反美反歐反西方的大合唱”。
俄領導人和專家學者也在會上闡述了一個值得注意的觀點:“集體西方”一邊在歐洲制造烏克蘭危機,一邊在“印太”挑動臺海危機,這兩場危機構成一西一東兩個“戰略支軸”,被“集體西方”當作謀霸維霸的工具。所以“集體西方”口口聲聲地說“如果烏克蘭倒下了,臺灣將成為烏克蘭第二”。對此,中國代表團在大會發言中強調,共同發展就是世界最大的安全,而有些國家只要自己發展,不要別國發展,這是世界的亂源和禍源;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中國統一是歷史大勢,在臺灣問題上玩火、妄圖“以臺制華”必將以失敗告終。在小組會上,中方代表和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中國學者也亮明了臺灣問題與烏克蘭問題沒有可比性的觀點。
《世界知識》:根據您的現場觀察,俄方在目前國際形勢劇烈變動期對中俄戰略協作有著怎樣的期待?
吳大輝:烏克蘭危機發生后,中國始終秉持客觀、平衡的立場,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自主地作出判斷、表達觀點。然而,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美國及其一些盟友國家在烏克蘭問題上把中國劃入非西方陣營,借機推行針對中俄兩國的“雙遏制”,中俄戰略協作向何處去也就更引人關注。從普京總統等俄領導人的講話可以看出,俄方堅信多極化正在加速形成,只要俄中站在一起,世界就不會重返冷戰結束后美國“一超獨霸”的局面。

吳大輝教授在俄羅斯“軍隊-2023”國際軍事論壇上進入一架米格-28H3“浩劫”武裝直升機參觀。
紹伊古防長在此次莫安會上高度評價中俄戰略協作。他說,西方對臺灣正在使用對付烏克蘭的方法,美國已將莫斯科和北京宣布為“戰略對手”,力圖確保自己在軍事對抗中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俄中關系在各個方面均已超越戰略關系的水平,也超越了盟友關系。雖然紹伊古并未羅列“超越”的實際依據,但仍表明俄方特別希望同中方進一步加強戰略協作的意志。我方代表在發言時強調,中俄應共同抵制對他國不擇手段的打壓,兩國軍事關系是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典范。紹伊古還公開談到,俄軍在烏克蘭繳獲的美西方武器,以及從烏軍戰俘那里了解到的北約訓練方法,可以同盟友伙伴分享。
《世界知識》:俄領導層一再宣稱,他們面臨終結美國霸權、重組國際秩序的歷史性機會,您剛才對會議情況的介紹反映了這種思潮。就目前俄國際處境而言,特別是在深受美西方制裁的情況下,您認為俄離這一目標是越來越近還是越來越遠了?
吳大輝:俄領導層的確認為世界格局多極化前景日趨明朗,現在需要有強大力量加以引導。俄相信,美西方霸權的衰落趨勢不可阻擋,新興力量崛起為世界格局主要力量中心的趨勢同樣不可阻擋,中國是引領世界形成新的力量中心的主要因素。在此過程中,中國、俄羅斯、印度、東盟等國家如能攜起手來,將有力推動多極化加速形成。
與此同時,一個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構成也在變化,這個世界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靠軍事硬實力定天下,除人口、領土、經濟、軍力以及戰略意圖、國家意志等因素外,還要考慮到國家治理水平和決策能力。目前俄國力同中國、美國相比差距越來越大,尚未出現重新縮小的趨勢,其科技創新力、全球影響力等都在萎縮。但是,俄仍有硬實力無可替代,一個是能源供給力,另一個是糧食產能。以石油、天然氣、煤炭等綜合產能來衡量,俄仍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出口國。俄也已恢復一度因烏克蘭危機受到削弱的糧食出口大國地位,今年上半年糧食出口量達7000多萬噸,非洲、中東眾多國家無法擺脫對俄糧食依賴。
依托全球最大核武庫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俄將是多極化世界重要一極,在大國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它的發展路徑不可復制。從歷史的角度看,俄歷次崛起和復興都不是以經濟發展見長。從18世紀初葉彼得大帝時期開始,到1812年鮑羅金諾戰役擊敗拿破侖、1815年參與甚至主導創建維也納體系,再到1854年克里木戰爭,俄都是歐洲乃至世界的第一軍事強國,習慣憑軍事實力說話。現在俄仍在沿著歷史慣性向前發展,也就難以融入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尤其是全球經濟和科創體系。在未來的國際競爭和戰略博弈中,俄無法憑借一己之力單獨實現重組國際秩序的目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通過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來塑造對己有利的國際環境。
《世界知識》:西方把中俄定義為“現行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國家”。然而從俄領導層的一貫話語看,其對現行秩序更多是想推倒重來,與中國從現行秩序內部對其進行改革完善的思路似乎有所不同。您認為這種差異的存在是否會影響中俄戰略協作效果?
吳大輝:在現行國際秩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中國始終是參與者、受益者和貢獻者。俄認為現行國際秩序是由西方主導,越來越基于美國制定的規則,已進入一種“疲憊”甚至“混亂”狀態,難以支撐世界的正常合理運轉,必須從根子上動手術。這些與我們的看法和主張有所不同。但是,兩國在反對國際霸權霸道霸凌、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方面有基本共識,構成戰略協作的基礎。
中俄有4300多公里長的共同邊界線,正所謂“鄰居不能選擇”,兩國只能交好不能交惡。美國的全球戰略已經走向對中俄進行“雙遏制”,同時以各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劃線,企圖將世界分成西方和非西方陣營,中俄已被劃入非西方陣營。這樣的形勢使得中俄除了不斷加強戰略協作別無選擇。當然,我們所處的時代并非靠玩弄大國平衡、利用一國制衡另一國就可實現絕對安全,國力發展和大國競爭的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于國內治理和發展水平的高低。
軍事技術論壇上的戰斗邏輯??
《世界知識》:從您在個人社交賬號上發布的信息和圖片看,您對俄羅斯“軍隊-2023”國際軍事技術論壇的觀摩可謂細之又細。能否與我們的讀者分享一下觀感?
吳大輝:此次俄官方為了方便來賓、擴大影響,特意把莫安會推遲幾個月,與國際軍事技術論壇這個實際上的防務展背靠背舉辦。我花了很多時間參觀防務展,過程相當過癮。整個展覽分為四大展區,同往屆相比不僅規模更大、武器種類更全,而且重裝備更多,也為中國等參展國提供了更多展示空間。
此次防務展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展示方式由過去的品種化改成系列化,不僅坦克、裝甲車、自行榴彈炮、直升機、無人機、反導系統琳瑯滿目,而且從第二代展示到第五代,可以說亮家底了。人機一體化空降作為俄軍長項,基于冷戰時期大量訓練積累起來的經驗,是獨步全球的,這次把已經列裝的20多種戰車全部展示出來,僅傘兵戰車就有23種。在對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初期,俄軍在無人機對抗方面一度處于下風,但此次俄方“知恥后勇”,一次性展示了50多種自研無人機,其中已列裝的有十幾種。往屆防務展,參觀者是在警戒線以外看展品的,這次卻可以觸摸,甚至上到裝備里面去看,蘇霍伊戰機、S-400導彈系統等都不例外,開放駕駛艙、指揮艙,以便讓參觀者進一步了解性能。
整體來看,俄羅斯的傳統軍事裝備依然很強,而且具有耐用、維修快、彈藥通用等優勢,不過數字化水平還難以同美國、中國及其他軍事強國相媲美。俄方迫切希望通過此次防務展告訴其國民和世人,它的武器裝備是擁有持久力量和成體系化發展的,現在扛得住,將來會更好,完全可以贏得“特別軍事行動”。應該說,展覽達到了提振士氣的效果,現場設有留言墻,很多俄民眾在上面寫下豪言壯語,還有人向政府提出了發展軍備的具體建議。
《世界知識》:有報道說這次防務展上特意展示了從烏克蘭繳獲的裝備,您能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嗎?
吳大輝:繳獲武器區面積相當大,西方列裝的所有主戰裝備都能看到,包括迫擊炮、自行火炮、坦克、裝甲車、步兵戰車、直升機、無人機、單兵制式武器,以及反坦克導彈、便攜式防空導彈,等等,甚至還有北約制式的單兵干糧和彈藥。不過,這些武器普遍破損嚴重。芯片也被拆除,沒有得到展示。
對繳獲武器的展示附有詳細說明,告訴參觀者俄軍是用什么手段將它們擊毀、擊落的,言外之意就像俄軍領導人在莫安會上說的,西方武器沒什么好怕的,靠蘇制武器足以應對,那些最新研發的俄制武器甚至還沒有大量出場,敵人的裝備就已在燃燒了。俄方此次大量展示繳獲武器,也是對烏方和北約一段時間以來在基輔、華沙、柏林等地頻繁展示所繳獲蘇俄制武器的一種對抗和回應。
烏東俄控區的瘡痍與重建
《世界知識》:您這次從莫斯科出發,用了幾天時間,來回驅車2500公里,探訪了烏東俄控區。您具體到了哪里,看到了什么情景?
吳大輝:經與俄方協調,在他們核準下,我與俄方安保人員進入頓巴斯戰區。與我過去幾年兩次乘飛機抵達頓河畔羅斯托夫、再驅車進入頓巴斯不同,這次行程曲折。因靠近烏東部地區的俄五個邊境州在烏軍遠程火力打擊威脅下關閉了全部機場,我與俄方安保人員只能改成從莫斯科出發,驅車16小時前往目的地,去克里米亞的想法則因沒有辦法安排回程而放棄。我們途徑莫斯科州、圖拉州、利佩茨克州,前往頓河畔羅斯托夫。行至半路,由于普京總統突然視察頓河畔羅斯托夫,整個羅州戒嚴,我們又臨時改變路線,從利佩茨克州直奔沃羅涅日州,然后從沃羅涅日州進入盧甘斯克地區,最后到達頓涅茨克市。
我們走的這條路線屬于烏克蘭南部赫爾松—扎波羅熱—頓巴斯—俄本土三條供給線的中間一條,相對比較安全,但距交火線也只有80~120公里,中途路過多處剛剛遭到炮擊的檢查站。一路穿行了17座城市,它們曾是烏克蘭鋼鐵、煤炭、冶金和機械制造中心,共同構成烏東核心工業城市群。這一路基本看到了烏克蘭東部前線俄方一側的全貌,最近到達離前線2.8公里的俄軍“第三道防線”區域。相較于第一、第二道防線部署的主戰部隊,第三道防線的兵力多為無人機、炮兵和警戒部隊。2800至3000米是狙擊手的極限射距,俄方出于安全考慮不允許我們再靠前。

俄羅斯“軍隊-2023”國際軍事技術論壇上展示的俄軍9A316M3防空系統。

吳大輝在“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政府大樓內觀看“海馬斯”火箭彈殘片。

2023年8月19日,遭“海馬斯”火箭彈襲擊后的頓涅茨克理工大學教學樓。

“軍隊-2023”國際軍事技術論壇上展示的俄羅斯量產無人機。

2023年8月21日,烏東地區的馬里烏波爾鋼鐵廠廢墟。
我在頓巴斯戰區停留期間,一直住在頓涅茨克市的市中心酒店,雖然每天有八九十枚導彈、炮彈落到這一地區,但市中心還算安全。自2014年烏克蘭危機形成以來,烏東地區大量居民遷入俄境,現在盧甘斯克地區還有140萬人口,整個頓涅茨克共和國也只剩下220萬人。街上看不見老人、孩子、婦女,都是些青壯年男子在活動,秩序井然。在烏東地區的多數城市,目前水電煤氣公交全免費,馬里烏波爾更是如此,每個街區都設有食堂,但自來水和蔬菜供應緊張。
馬里烏波爾距前線較遠,烏方的常規火箭炮夠不著,所以比較平靜,但仍有烏方滲透小組在活動。那天我們的車剛駛過一座區政府辦公樓,那里就遭到爆炸破壞。俄方正積極推進馬里烏波爾的重建工作,到處是工地。我們路過馬里烏波爾第50中學時,看到有學生在活動,便提出進去看看,陪同聯系后,校方欣然應允。我在操場上叫住幾個學生,問他們對戰火的感受,一個女孩兒當場哭了起來,說起在家門口看到野狗撕咬尸體的經歷,顫抖不止。顯而易見,這場沖突帶給孩子們的心理創傷是何等嚴重。我在頓涅茨克等地與當地居民交談,他們說并不怨恨烏克蘭,也不認同非要把居民分成“烏族”“俄族”——經過多年交融,家家既有在俄羅斯的人,也有在烏克蘭的人,“都是一家人”,為什么非要按族群劃分并作選擇?他們說他們憤恨的是“當年亞速營的濫殺”。
我也接觸到一些俄軍人員,從他們口中聽到的都是“俄羅斯必勝”,并沒有失敗主義的情緒。我問他們是否擔心烏軍即將獲得F-16戰斗機?他們回答,“有什么好怕的”,“無非就是遠火炮彈被飛機投彈取代罷了”。他們同意最終還是要通過和談解決問題,但認為必須是在“俄奪回整個頓巴斯之后”,“就和烏方堅持待奪回克里米亞、頓巴斯之后才能和談一樣”,所以目前“和談的條件還不具備”。
《世界知識》:是不是也想去火線烏克蘭一側看看?
吳大輝:當然,正在找機會。
《世界知識》:您對局勢未來發展有何判斷?對中國的作用有何期許?
吳大輝:今夏以來烏軍發動了“大反攻”,但進展并不順利。實際上烏東目前的態勢是互有攻守的:東北方向庫皮揚斯克、盧甘斯克、頓涅茨克一線俄軍在堅守中有進攻,特別是在庫皮揚斯克一帶,正極力清除烏方控制的幾個“陽臺”(注:指距離俄方第一道防線過近的陣地),并且繞過庫皮揚斯克突入哈爾科夫州,未來有可能進一步向波爾塔瓦州推進;在南邊赫爾松州和扎波羅熱的奧列霍夫一線是俄軍在防守,烏軍8月底對“第一道防線”有所突破,在羅布蒂諾方向形成一個突出部。總體來看,俄軍在東北戰線上的主動處境正在擴大,大于烏軍在南部獲得的主動性。
俄畢竟是大國,國防工業已全面開動起來,產能擴大到正常時期的八倍;雖未進行全國動員,但大量合同兵與志愿兵投入戰場,15萬動員力量等著上前線;“彈藥告罄”說也已在事實面前破產,俄軍目前每天平均打出4萬到6萬發大口徑炮彈,今夏一度出現的前線彈藥供應跟不上現象主要是因為后勤運輸而非產能問題,現已找到分散存放、分散運輸的辦法……
總體看,膠著狀態還在持續,雙方都暫無法擊穿對方防線,各自在戰術上取得的成果也尚難轉化成戰略性的成功,和平曙光仍未出現。俄烏各自提出的談判條件均無法被對方所接受:俄方對立即恢復談判持開放態度,目前主要要價是烏承認9月“公投入俄”的烏東四州屬于俄領土,但絕大多數烏民眾對此是反對的,哪個烏領導人接受這樣的條件就會立即失去執政合法性;烏方的原則是恢復1991年蘇聯解體時的俄烏邊界,不與普京治下的俄羅斯談判(且已以立法形式確認),在俄境內100公里范圍內建立緩沖帶,以及審判“責任人”等,這是俄方豈能接受的?
現在啟動和談的主動權在基輔而非莫斯科。各方有一些私下溝通,俄美最近在瑞士私下談了三輪,還要在迪拜談一輪。將來即便往最好處想也不大可能簽署和平協定,或許會簽一個臨時停火協議,然后談談停停、打打停停。非要讓我估算一個時間點的話,明春雙方誰也打不動了,真正的談判意愿有可能形成,和平的機會或許到來,中國屆時將發揮更大作用。
此次考察,所到之處暢通無阻,處處感受到俄方人員的友好和對中國勸和促談作用的期待。我們也在出席莫斯科國際安全會議過程中感受到,國際社會、特別是“全球南方”國家,對中國政府今年2月提出的《關于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的認可和支持在擴大。美國、德國、英國、荷蘭等西方國家的官員和學者在與我們的溝通中也承認,中方主張的大方向是合理的,正在得到烏克蘭危機發展形勢的事實檢驗。
(本文圖片均由吳大輝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