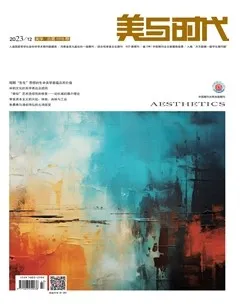媒介與受眾共塑下的“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研究

摘? 要:當代視覺轉向趨勢下層出不窮的視覺形象重塑著大眾的視覺體驗。作為上海迪士尼新推出的角色,“玲娜貝兒”的視覺形象建構遵循著視覺文化的內在邏輯,從形象、視覺表征到視覺性再到視覺建構,由淺入深的形象建構過程體現著視覺文化所蘊含的社會意義。而在“玲娜貝兒”的視覺形象建構的過程中,媒介與受眾是兩個不可或缺的主體。一方面,“玲娜貝兒”在媒介的生產性編碼中淪為制造物欲的符號和抹殺真實的擬像;另一方面,受眾的想象性延伸和視覺文本的再創造為“玲娜貝兒”的視覺形象增添了意義。在媒介與受眾的共塑下,“玲娜貝兒”的視覺形象最終得以完成建構。
關鍵詞:視覺形象;玲娜貝兒;大眾傳媒;受眾
進入后現代社會以來,社會形態的變遷裹挾著文化形態的更迭,視覺文化以其強大的視覺性和表意能力影響著人類對世界的理解和呈現方式,視覺元素逐漸成為主導日常生活信息表達與傳播的重要媒介形式。日新月異的視覺技術將現實生活包裝成可視化的生存圖景,視覺形象成為當代社會最為普遍的文化奇觀。
面對著由視覺形象堆砌而成的當代社會,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在《景觀社會》的開篇斷言:“在現代生產條件無所不在的社會,生活本身展現為景觀的龐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轉化為一個表象。”[1]
在當代視覺文化浪潮的席卷之下,視覺形象成為社會公共空間中最“吸睛”的存在。而在當下諸多視覺形象中,迪士尼角色“玲娜貝兒”以其可愛又極具個性特征的形象征服了受眾的視覺感官,迅速在IP市場中俘獲龐大的消費者群體。自2021年9月29日“玲娜貝兒”在上海迪士尼樂園首次亮相以來,與角色相關的圖像、視頻、表情包等視覺文本在社交平臺上被瘋狂地瀏覽、轉發和再創造,帶有角色視覺圖標的衍生產品供不應求,甚至被炒至天價。種種現象都足以證明“玲娜貝兒”這一視覺形象所具有的文化和經濟潛力。
實際上,“玲娜貝兒”這一迪士尼角色的爆火與其視覺形象的建構密不可分,而其視覺形象的建構實則依賴于多層次的視覺邏輯結構。在“玲娜貝兒”的萌態的視覺表象之下,體現著視覺文化與當代社會的種種勾連。與此同時,在“玲娜貝兒”視覺形象建構的過程中,大眾傳媒與其受眾也是不可或缺的主體。一方面,大眾傳媒作為視覺文本的生產與傳播的媒介參與著“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生產性編碼;另一方面,大眾作為視覺文本的接受者和消費者而對視覺形象進行消費性解碼與再生產,二者共同完成了對“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建構。基于此,本研究在視覺文化的視域下分析迪士尼角色“玲娜貝兒”視覺形象是如何被生產和建構,并探究作為視覺形象建構主體的大眾傳媒和受眾在視覺形象建構過程中如何發揮其功能和角色。
一、“玲娜貝兒”的視覺形象建構分析
視覺形象的建構并非單純是形象外表的設計與造型,而是涉及到更深層次的文化內涵與意義象征。周憲教授曾在其主編的《當代中國的視覺文化研究》中提出了視覺文化研究的四個基礎概念:“形象”“視覺表征”“視覺性”“視覺建構”。這四個概念構成了視覺文化的內在邏輯,并進一步展現為紛繁復雜的視覺文化現象結構[2]17。通過對這四個基礎概念的分析,由當代大眾傳媒和受眾共同生成的“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建構過程得以由淺入深地展現。
(一)形象
形象是視覺文化的基本單元,特指經由感官所感知的視覺形象[2]18。視覺文化的實質在于將不可見的事物轉化為可見的形象。作為視覺文化的重要載體,形象直接地呈現為被精心設計后的物質外觀,并憑借其強大的直觀性和具象性而搶占著大眾的注意力。而作為迪士尼樂園最熱門的角色之一,“玲娜貝兒”的外形設定完美地符合普羅大眾對“可愛”一詞的想象:毛茸茸的粉色狐貍、圓圓的大眼如藍色玻璃般透亮、大且蓬松的狐貍尾巴、手持放大鏡、頭別紫色蘭花。這一系列的視覺元素共同塑造了“玲娜貝兒”俏皮討喜的視覺形象,契合著當代大眾追求“萌態”和“美感”的視覺偏好,角色形象的每一次亮相都是對大眾視覺感官的強烈刺激,不斷刷新著大眾的視覺體驗感。
媒介技術的升級催生出視覺形象的多重樣態。就“玲娜貝兒”這一視覺形象而言,其形象呈現形態是豐富多樣的,既有二維平面式的圖像形態和影像形態,也有由真人扮演的三維立體形態,不同類型的形象之間相輔相成,共同塑造著大眾視覺感官之下的“玲娜貝兒”形象。圖像式的“玲娜貝兒”形象憑借可大規模生產的印刷媒介而成為日常生活最為常見的主要形態,從文化工業生產的形象衍生品到機械復制技術下的形象印刷物,“玲娜貝兒”的圖像可謂是無所不包,并以無限增長的龐大數量“圍剿”著人類的日常生活。影像式“玲娜貝兒”形象的生成依賴于電子媒介,更具視覺效果的動態影像建構和補充了“玲娜貝兒”的角色設定與性格特征,通過配樂以及畫面中角色身體語言等視聽元素的雙重疊加來構筑鮮活的形象。而三維立體式“玲娜貝兒”的則將視覺形象具體落實到了物質的肌理質感上,以物質實體呈現其“毛茸茸”的外觀特質。在此,“玲娜貝兒”以“吸睛”的形象外觀構筑了其視覺形象建構的根基。
(二)視覺表征
當形象被創造出來并進入當代視覺文化場域時,形象的意義在一次又一次的被觀看和感知之中誕生,而視覺表征則是對這一意義獲取過程的概括與總結。英國文化研究學者斯圖爾特·霍爾曾對“表征”概念進行詳細論述:“各種‘事物、‘概念和‘符號間的關系是語言中意義生產的實質之所在,而將這三個要素聯結起來的過程就是我們稱為‘表征的東西。”[3]具體到視覺文化中,視覺表征就是形象從生產到傳播再到消費的全過程,形象在這一過程當中獲得了符號的意義與象征。
對“玲娜貝兒”的視覺表征分析實際上就是對其意義生產與接受過程的分析。一方面,在視覺文化生產場域中,以大眾傳媒為代表的“玲娜貝兒”形象生產者將其編碼為象征著某種消費觀念、旨趣情調、生活理想、審美氛圍等內涵的意象;另一方面,接受場域當中的受眾通過對形象的感知、理解和消費而進行意義解碼,在對意義的接受認同或排斥中進行想象性投射。而在這一表征過程的背后,實際上暗含著市場經濟和消費主義的邏輯,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當代消費社會對大眾視覺感官的強制性操控。從視覺文化生產場到接受場,從客觀世界中的“玲娜貝兒”再到符號化的“玲娜貝兒”,象征意義由此被深深地銘刻于與“玲娜貝兒”有關的一切事物當中。
(三)視覺性
“從形象到表征,也就是從視覺文化的基本單元,向表意實踐的意義生產的延伸,這就必然會涉及視覺經驗,涉及人們如何看以及看什么”[2]28,而這就與“視覺性”的概念相聯系。視覺是人類感受和認知世界的首要媒介,而主體的視覺經驗記憶以及特定時代的社會文化語境則影響著人類觀看世界的視覺焦點。不同的時代文化語境生成著不同的主體視覺經驗與偏好,而視覺性則是揭示了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如何建構人類的視覺觀看方式和觀看內容。
“玲娜貝兒”視覺形象建構的背后實則是社會大眾文化對受眾視覺觀看方式的收編與馴服。弗雷德里克·詹姆遜以“無深度的平面化”形容后現代以來的文化特征,大眾文化的形象生產在工業化和消費邏輯的潮流推動之下走向了通俗化、娛樂化,由此也形成了追求視覺刺激和快感的視覺性。作為大眾文化的一部分,“玲娜貝兒”的視覺形象被賦予了娛樂與快感滿足的特質,以感性符號的形態契合著“快感優先”的價值取向,將欲望、刺激和快感轉換為純粹的感性愉悅。每一次觀看“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背后,都是一次訴諸于主體視覺感官的滿足感和快感的獲取。
在當代大眾文化和視覺文化的“聯姻”之下,以“玲娜貝兒”為代表的感性形象建構著大眾的觀看方式,視覺快感引導著大眾對文化商品的選擇。然而,對視覺快感無止境的追求和濫用實則是對主體能動性與創造性的剝奪,過度的娛樂與快感成為掩蓋無意義之實質的障眼法。
(四)視覺建構
從形象到視覺表征再到視覺性,“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建構不再局限于視覺文本本身,而是深入到其符號象征意義和觀看之感性原則,逐步突顯出視覺文化現象的社會屬性。如果說此前三個維度更加強調社會文化經驗在視覺領域的呈現,那么視覺建構則旨在進一步地探索視覺文化現象對主體、對社會的建構作用。“視覺文化通過各種可見性符號和形象來構建主體,通過視覺實踐來塑造人們對社會、文化乃至自我的認知。”與語言文字相比,視覺文化具有更強的主體建構能力,視覺形象以更加直觀的表意功能強有力地塑造著主體的認知和觀念。
“玲娜貝兒”的視覺形象既包含著當代消費社會的消費邏輯話語,也映射著某種消費社會時代的新審美氛圍和生活理想。在這些話語的支撐下,“玲娜貝兒”視覺形象建構著廣大受眾的消費觀念和自我認知。一方面,在大眾傳媒和文化工業的“審美氛圍”加持下,“玲娜貝兒”視覺形象被賦以童真與夢幻的特質,經過市場經濟邏輯的浸潤而成為景觀消費品,在一次次的被觀看和消費之中重塑著主體的欲望;另一方面,“玲娜貝兒”視覺形象親和可愛的樣態誘發著主體的審美愉悅感,以視覺形象替換了美好生活的概念,受眾的消費形象過程既是對“玲娜貝兒”所代表的生活理想的認同,也在這一過程中完成對形象的想象性投射。
在大眾傳媒和視覺技術等視覺形象生產傳播手段高度發達的當代社會,視覺在建構主體認知方面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誠然,盡管“玲娜貝兒”的視覺形象以其萌態外貌契合著大眾的審美傾向,為受眾營造了視覺上的感性愉悅,但其實質上是迪士尼美國夢的視覺象征,其中摻雜著西方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在資本跨國界流通的當下,我們仍需警惕外來價值觀念與視覺文化和消費主義的“合謀”。
二、“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媒介生產性編碼
“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建構離不開當代大眾傳媒的生產性編碼。在視覺文化生產場中,大眾傳媒以形象生產者的姿態將當代市場經濟的消費話語和大眾文化邏輯置入“玲娜貝兒”的形象建構中。在此過程中,“玲娜貝兒”的視覺形象被編碼為操縱物欲的符號與“童話世界”的擬像,以消費社會的意識形態塑造著大眾對社會和自我的認知。
(一)視覺化的物欲符號
當社會形態從生產主導向消費主導轉變之時,視覺形象不可避免地在市場資本的帶動之下而成為商品,并按照消費社會的秩序被重新編排分類。而媒介參與著視覺形象的生產與編碼,依照編碼規則的媒介承擔起“造欲”的責任,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將視覺形象向符號轉化的過程合法化。在此,大眾傳媒的生產性編碼改寫了視覺形象的屬性,視覺形象因此擁有了用于彰顯和區分的符號象征意義。
“玲娜貝兒”視覺形象是媒介編碼規則之下的符號性產物,以廣告為首的大眾傳媒將審美內涵附著于視覺形象中,不斷地強化“玲娜貝兒”視覺形象與童真夢幻的美好生活之間的聯系,并以此來操控受眾的視覺消費行為。在“玲娜貝兒”的視覺形象編碼中,大眾傳媒將不可見的物質欲望轉化為可見的視覺形象,在視覺形象和童話世界之間建立起想象性聯結:只有觀看和占有“玲娜貝兒”視覺形象之時,才能享受童話般的生活。在媒介的生產性編碼之下,“玲娜貝兒”視覺形象以視覺化的童話符號建構著大眾的欲望和認知。
實際上,媒介的生產性編碼是景觀社會下的符號操控,觀看“玲娜貝兒”視覺形象所帶來的感性愉悅被編碼為一種符號意義,其實質是消費社會之下媒介對大眾馴化。因此,編碼規則下生產的“玲娜貝兒”視覺形象淪為一種同質化、無深度的符號堆疊。
(二)超真實的擬像
波德里亞曾在《消費社會》中論述了大眾傳媒是如何通過編碼手段來達到解構真實的目的。通過媒介技術的任意編輯和加工,現實景觀被呈現為“根據這種既具技術性又具‘傳奇性的編碼規則切分、過濾、重新詮釋了的世界實體。”[4]
產自大眾傳媒編碼規則的“玲娜貝兒”視覺形象是經過符號化后“超真實”的現實替代品。一方面,由大眾傳媒生產的“玲娜貝兒”視覺形象并無現實本源,其視覺形象本身成為了比現實還要真實的存在,而大眾傳媒上被瘋狂瀏覽轉發的“玲娜貝兒”影像更加強化了視覺形象的真實感;另一方面,“玲娜貝兒”視覺形象在大眾傳媒的編碼下被塑造為樂觀主義的幻影,并與其他迪士尼形象一同構筑起童趣、美好與夢幻的仿真世界。在迪士尼仿真世界中,理想與現實的鴻溝被消解,經過編碼的“玲娜貝兒”以其形象符號而成為“現實”。
大眾傳媒的“編碼游戲”將現實營造為充滿符號和擬像的“超真實”世界,現實生活在仿真世界的映襯下反而顯得不那么“美好”。然而,看似美好的“超現實”世界背后實則是由大眾傳媒與消費邏輯共謀之下的符號操縱,“玲娜貝兒”化身為視覺形象符號而制造著無限擴張的消費欲望。與此同時,經由媒介編碼的“玲娜貝兒”實則是一種“偽形象”,它以童話般的幻象剝奪了現實生活中真實形象的魅力,讓人沉浸其中,無法自拔。在對幻象無限向往的背后,是個體想象力和批判性思考能力的退化。
三、“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受眾消費性解碼
當視覺形象從生產場域進入接受場域時,意味著視覺形象完成了媒介編碼而進入受眾解碼的環節。斯圖亞特?霍爾所提出的“編碼/解碼”模式揭示了媒介的符號編碼與受眾的意義解碼之間的差異性,受眾憑借自身的前理解對文本進行闡釋和重構。在的當下,受眾對“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解讀既有基于認同的想象式解碼,也有視覺文本的再創造式解碼。在受眾的消費性解碼下,“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建構朝多元化發展。
(一)想象的延伸
新媒介的誕生強化了受眾在視覺文本解讀中的主體能動地位,“媒介文本的解讀過程不再是機械性的,而形成一種動態的張力,居于受眾期待與文本的符號式指令之間”[5],這就意味著“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建構并非僅是大眾傳媒的單向式編碼,而只有經過受眾的意義解讀和想象延伸,“玲娜貝兒”的形象建構才算完成。受眾對“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一次觀看就是一次形象的消費和形象意義的解碼,受眾在視覺形象的消費性解碼中產生對“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無窮遐想。
基于對“玲娜貝兒”的價值認同,受眾從自身的生活經歷和情感需求出發,將想象和情感寄托于形象之上,豐富了“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最終呈現。“她聰慧、敏銳、見多識廣,擁有豐富的自然知識,像偵探一樣熱衷于解密”是“玲娜貝兒”的官方設定。在“玲娜貝兒”官方視覺形象和性格設定之外,受眾以想象性延伸或將其想象為“呆萌”“乖巧”,或將其與“調皮莽撞”相聯系,以想象力建構了新的“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由此改造和扭轉了“玲娜貝兒”原有的意義內涵。
(二)再創造的視覺文本
新媒體時代下社交網絡平臺的興起打破了視覺文本生產一元化的局面,視覺文本生產主體更加多元,受眾對視覺文本的接受從單向的凝視轉向雙向的參與式互動,受眾參與下的視覺文本再創造極大地豐富了景觀社會中的視覺形象。
受眾對“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再創造是一種積極能動的解碼行為。去中心化的社交媒體賦予了受眾對“玲娜貝兒”視覺形象再創造的權利,受眾基于自身審美旨趣而自發地編輯和改寫視覺形象。在眾多再生成的“玲娜貝兒”視覺文本中,既有以圖文拼接而成的繪畫和表情包,也有視聽元素疊加而成的動態影像。在此,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再創造成為“一種爆炸式、娛樂式的符號狂歡行為,任何主體都有可能對其進行符號創作和篡改,即‘人人皆生產主體”[6]。受眾的復制、拼貼、改編等二次創作行為是“玲娜貝兒”視覺形象的再建構,也是視覺形象意義和影響力的再生產。在受眾的再創造式解碼下,“玲娜貝兒”的視覺形象得以逐漸飽滿和鮮活。
四、結語
“玲娜貝兒”視覺形象本質上是景觀社會下遵循市場經濟邏輯的視覺化商品,它以娛樂快感式的視覺體驗搶奪著大眾的視覺注意力。在消費邏輯無處不在的當下,“玲娜貝兒”難逃“物化”的命運。一方面,媒介的編碼在符碼的操控中抹殺了現實的真諦,悄無聲息地制造著欲望;另一方面,受眾若沉溺于解碼所帶來的感官愉悅中,也難免麻木感官與心智。在觀看形象之時,仍要警惕埋藏形象背后的符號操縱和意識麻痹。
與此同時,以“玲娜貝兒”為首的迪士尼視覺形象正以無可阻擋之勢占據著當代視覺文化場域的高地,這既是外來文化傳入中國文化市場的結果,也是我國積極地順應文化全球化趨勢的表現。不可否認的是,“玲娜貝兒”等迪士尼視覺形象在經濟價值方面有著極大的開發潛能。然而,這些視覺形象實質上是西方價值觀念與意識形態的視覺化呈現,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國人的視覺經驗建構。視覺形象已成為國際間文化交流的“無聲語言”,構建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視覺形象是構建國家認同感、構建民族共同視覺經驗的重要之舉。依筆者之見,北京冬奧會的“冰墩墩”乃是可與“玲娜貝兒”相匹敵的中國本土視覺形象。
參考文獻:
[1]德波.景觀社會[M].王昭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2]周憲.當代中國的視覺文化研究[M].南京:譯林出版社,2017.
[3]霍爾.表征:文化表征與意指實踐[M].徐亮,陸興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25.
[4]波德里亞.消費社會[M].劉成富,全志鋼,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133.
[5]劉國強,粟暉欽.解構之欲:從后現代主義看媒介文本解碼的多元性[J].新聞界,2020(8):31-39,94.
[6]姚文苑.“萌”的審美與文化表達:青年對動物表情包的使用及其視覺文化實踐[J].新聞與寫作,2023(2):96-105.
作者簡介:吳思雅,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藝術學理論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藝術生產與文化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