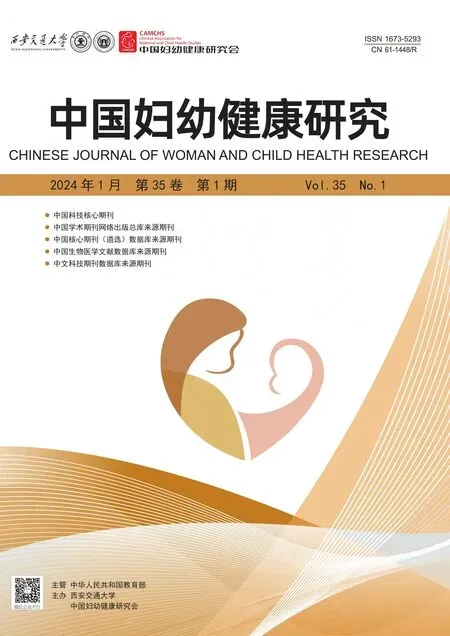嬰兒體脂指數的影響因素分析
張 婷,張 莉,劉慧娟,邢德強,趙亞楠,張一兵,李 燕
(1.青島大學附屬山東省婦幼保健院,山東 濟南 250014;2.聊城市東昌府區婦幼保健院,山東 聊城 252000;3.滕州市婦幼保健院,山東 滕州 277500;4.東營市人民醫院,山東 東營 257091)
嬰兒期是兒童生長發育的第一個高峰期,也是預防后期肥胖與代謝性疾病的關鍵期。已有研究表明,幼兒肥胖率增長速度比其他年齡段更快[1]。近1/2的肥胖兒童達到超重狀態是在2歲之前,嬰幼兒時期體重的過快增長與后期肥胖的發生密切相關[2],提示肥胖可能在生命早期就已開始。體成分即身體組織細胞的重要組成部分,廣義上將其分為體脂重(fat mass,FM)和瘦體重(又稱去脂體重,fat-free mass,FFM)。Van-Itallile[3]提出體脂指數(fat mass index,FMI)和瘦體重指數(fat-free mass index,FFMI),將體脂重和瘦體重像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一樣除以身高的平方,這兩個指數能有效地建立體成分與身高的關系,并允許將不同大小的個體進行比較,給營養障礙性疾病的診斷提供更多依據。鑒于不同性別嬰兒生長發育存在差異,本研究通過男女嬰體脂指數探究其影響因素,為有針對性地干預和控制嬰兒超重肥胖提供依據。
1 研究對象和方法
1.1 研究對象
于2021年10月至2022年12月以山東省濟南市、聊城市、滕州市、東營市4家省市級綜合醫院及婦幼保健院兒童保健科為研究中心,招募單胎,無遺傳代謝病,健康查體正常的9 533名嬰兒開展多中心橫斷面研究,進行嬰兒體成分及影響因素研究。納入標準:①1~12月齡新生兒;②嬰兒健康查體正常。排除標準:①診斷患有遺傳代謝病;②非單胎妊娠。研究最終納入9 291名研究對象。本研究通過山東省第一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YXLL-KY-2022(017)],所有參加本研究的嬰兒監護人均閱讀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方法
本研究應用電子調查問卷收集受試嬰兒的基本信息(性別、民族、出生胎齡、出生體重、輔食添加時間)與父母特征(嬰兒健康查體時父母親的身高、體重、母親孕期增重及孕期合并癥)。利用康宇KF-5000型嬰幼兒營養綜合監測系統獲得健康查體嬰兒的身長、體重、體脂率(fat mass percentage,FMP)、體脂重、瘦體重,并基于FMI=體脂重/身長2(kg/m2)計算體脂指數。
1.3 研究指標與標準
嬰兒體重測量精確至0.01kg,身長精確至0.1cm,體脂指數精確至0.01kg/m2。嬰兒出生情況評估指標:①根據出生胎齡(gestational age,GA)分為早產(GA<37周)、足月(37周≤GA<42周)、過期產兒(GA≥42周);②根據出生體重(birth weight,BW)分為低出生體重兒(BW<2 500g)、正常出生體重(2 500g≤BW≤4 000g)、巨大兒(BW>4 000g);③根據出生體重和出生胎齡的關系分為小于胎齡兒(嬰兒的BW在同胎齡平均出生體重的第10百分位以下)、適于胎齡兒(嬰兒的BW在同胎齡平均出生體重的第10~90百分位之間)、大于胎齡兒(嬰兒的BW在同胎齡平均出生體重的第90百分位以上)。孕期母親增重指標:<10kg為孕期增重不足,10~15kg為孕期增重正常,>15kg為孕期增重過高。父母親體重指標: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行業標準《成人體重判定》(WS/T 428-2013)分為,體重過低(BMI<18.5kg/m2),體重正常(18.5kg/m2≤BMI<24.0kg/m2),超重(24.0 kg/m2≤BMI<28.0kg/m2),肥胖(BMI≥28.0 kg/m2)。
1.4 統計學方法

2 結果
2.1 不同性別研究對象的一般情況
在9 291名嬰兒中,男嬰4 905名(52.8%)。男女嬰平均出生體重分別為(3.34±0.47)kg和(3.22±0.46)kg,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1),其中早產兒234名(4.73%),過期產兒14名(0.31%),小于胎齡兒381名(7.87%),大于胎齡兒722名(14.07%)。男女嬰母親妊娠期糖尿病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47),見表1。

表1 不同性別嬰兒及父母的基本信息特征

特征男嬰(n=4 905)女嬰(n=4 386)χ2/tP 母親BMI0.4940.920體重過低220(4.49)209(4.77)體重正常2 367(48.26)2 111(48.13)超重1 579(32.19)1 399(31.90)肥胖739(15.06)667(15.20) 父親BMI4.5190.211體重過低168(3.43)168(3.83)體重正常1 859(37.90)1 575(35.91)超重1 803(36.76)1 653(37.69)肥胖1 075(21.91)990(22.57)
2.2 不同性別嬰兒FMI影響因素的多因素線性回歸分析
嬰兒的月齡、大于胎齡兒、4~6月齡添加輔食、父母親肥胖對嬰兒FMI均具有顯著正向相關(P<0.001),小于胎齡兒、妊娠期糖尿病、母親體重過低與嬰兒FMI均具有顯著負向相關(P<0.05)。男嬰中,妊娠期高血壓與FMI存在顯著正向影響(P=0.038);女嬰中,純配方奶喂養與FMI存在顯著正向影響(P=0.046),孕期增重不足對FMI呈顯著負向影響(P=0.032),見表2,僅列出為陽性結果。

表2 影響嬰兒FMI的多因素線性回歸分析
3 討論
3.1 兒童肥胖及防控干預
WHO最新數據統計,5歲以下兒童肥胖人數已達4 200萬[4]。兒童早期肥胖是一個嚴重的健康問題,兒童肥胖影響兒童早期的身心發育,同時增加生命后期肥胖及其相關的健康風險。兒童早期作為預防超重肥胖的重要階段,因此這一年齡段人群的相關研究具有更高的價值,應被重點關注。最初控制肥胖的干預措施主要集中在年齡較大的兒童及成年人身上,但其在逆轉疾病的發生率與嚴重程度方面相對不足。已有多篇綜述強調了2歲以下兒童的肥胖干預措施,兒童超重/肥胖的控制關口應前移,在妊娠期及嬰兒期應及時采取干預措施[5-7]。
3.2 FMI的優越性及其影響因素
體成分檢測可用于嬰兒超重肥胖的精準評估,能明確給出身體組織各成分的值,實現脂肪組織與去脂組織的區分,優于傳統監測手段即身長別體重(weight for height,W/H)。體脂指數和瘦體重指數由VanItallie等[3]于1990年首次提出,作為身高調整指數,FMI和FFMI能夠在不同體型的人之間進行比較。FMI提供了單獨說明體脂肪量并考慮其相對于身高的可能性,因此對于超重、肥胖的判定更有說服力。眾多研究證實嬰幼兒的超重肥胖與母親的體重狀態有關,母親肥胖會明顯增加嬰幼兒超重肥胖的風險[8-10]。本研究同樣提示母親肥胖與FMI呈正相關。在Weng等[11]的研究中指出父親BMI高的兒童超重的風險更高,即父親BMI與兒童超重呈正相關。大于胎齡兒、配方奶喂養、妊娠期高血壓的發生增加嬰兒高體重狀態的風險,本研究結果與之一致[12-14]。
3.3 FMI與妊娠期糖尿病
許多研究提示妊娠期糖尿病使兒童患超重肥胖的風險增加,但也有研究示宮內暴露于妊娠期糖尿病的兒童與非暴露組相比,其BMI無統計學差異[15]。本研究結果示妊娠期糖尿病與FMI呈負相關,一方面可能考慮隨訪時間的問題,本研究是在嬰兒期,妊娠期糖尿病對于FMI可能是遠期影響,另一方面近年來產檢越來越重視,醫院產檢越來越規范,能做到及時發現、及時診斷、及時治療和及時控制,并且在胎兒出生后,家長的兒童保健意識也越來越強,同時兒童保健科的相關專案建立且制定針對高危險因素兒童個體化指導方案。基于以上兩方面考慮,妊娠期糖尿病暴露與嬰兒肥胖的關系可能減弱。
3.4 小結
本研究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針對嬰兒FMI的研究相對較少,影響因素的證據多來自于超重肥胖兒童群體的影響因素研究,其次影響因素的數據均來自于父母自填式問卷調查,可能存在一定的回憶偏倚。
綜上所述,胎齡別體重、喂養方式、輔食添加時間、孕期增重、妊娠期糖尿病和高血壓、父母親BMI可能是嬰兒FMI的影響因素。因此,應在生命早期采取有效的干預措施進行預防與控制。妊娠期婦女應合理膳食,控制增重在合理范圍,預防妊娠期合并癥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