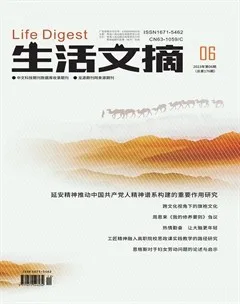論教唆犯預備中教唆者的從犯性質
在《刑法》第29條第2款的性質中屬于“教唆未遂”也可以進行認定為“犯罪預備”的性質,立足于我國《刑法》條文的規定,在堅持共犯從屬性的前提下在被教唆者處于犯罪預備階段時將教唆者的定性將《刑法》第29條與第27條進行結合,從而緩解對于機械的理解“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中,對于法益的侵害更為直接地被教唆者的處罰。
一、問題的提出
我國《刑法》第29條第2款規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對于教唆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刑法客觀主義與共犯從屬性原則相結合的前提下,教唆者與被教唆者皆可以構成犯罪預備①。然而在教唆犯對于被教唆者實施了教唆行為之后,被教唆的人僅進行了預備沒有實施相應行為的情況下,可以將刑法第22條關于預備犯的規定與29條第2款進行結合進行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但是對實施教唆行為者只能適用第29條第2款進行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相對于被教唆者面對法益侵害的直接性而言,教唆者距離法益侵害更加遙遠最多只具有對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險。但是相對于被教唆者而言教唆者的處罰卻更為嚴厲這與我國刑法所要求的罪刑相適應原則并不符合。
現實中過分擴大共犯從屬性法理的 “射程”,在刑法客觀主義并未得到較好貫徹的語境下,會動搖正犯概念和構成要件觀念,從而帶來負面影響②。當然在此種情形下可以將《刑法》第29條第2款與第22條關于預備犯的處罰規定結合進行處理。
教唆犯對于實行犯并不能夠產生實質意義上的支配,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并不能夠與正犯相當,會低于正犯。所以,比較合理的觀點應當與現行做法相反,即教唆犯通常是從犯,在特殊情況下才是主犯。③本文嘗試在立足于我國現行《刑法》條文規定的情況下解釋論證在教唆者對被教唆者實行教唆之后,被教唆者僅進行犯罪預備的情況下,對于教唆者的定罪處刑可以適用《刑法》第27條的規定認定為從犯,進而應當進行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從而緩解在此種情形下所造成罪刑不相均衡的局面。
二、“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中犯罪預備的兩種形式
(一)犯罪預備的兩種具體形式
在我國的刑法界,支持共犯從屬性的學者占據較為多數。筆者同樣認,從貫徹刑法客觀主義的視野下與實施罪刑法定原則的角度出發,應當對共犯從屬性說保持堅守。將刑法29條第2款所規定的情形作為對教唆未遂這種特殊的犯罪預備進行處罰。在我國立法工作人員的解讀中對于“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區分為了兩種不同的情形:一種是教唆犯的教唆沒有對被教唆人起到教唆的,用,被教唆人既沒有實施被教唆的,罪,也沒有實施其他,罪,教唆行為沒有造成直接的犯罪;果;另一種是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罪,但因為被教唆而犯了其他的罪。④在解讀中其中第一種情形教唆犯的教唆沒有產生實質上的作用力,被教唆者沒有實施所教唆之罪也沒有實施其他犯罪,可以分不同的情況認定為在教唆犯罪中教唆者與被教唆之間構成犯罪預備。
筆者認為其中又可以分為兩種具體的情形:第一,教唆者為了使被教唆者產生犯意而實施了教唆行為,被教唆者當時接受了教唆,但是事后并沒有將所接受的教唆付諸行動;第二,被教唆者接受教唆之后著手實施了為犯罪而進行的準備工具、制造條件的預備行為,但是被教唆者的犯罪行為只是停止在預備階段,也即被教唆者的犯罪預備行為。其中第二種情形也是可以認定為被教唆者因為自身的預備行為可以適用刑法第22條的規定進行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而教唆者只能適用刑法29條第2款的規定進行從輕、減輕處罰的規定從而導致處罰不均衡的情形。
(二)教唆犯自身教唆行為的預備可以適用犯罪預備的法理
如前所述,第一種情形中在被教唆者并沒有接受教唆或者當時接受了教唆并沒有實際實行犯罪的情況下,教唆者與被教唆者之間是不能成立共同犯罪的,因為只有教唆者實施單純的教唆行為,所以并不能對被教唆者進行處罰。但是對于教唆者因其主觀上有教唆他人犯罪的故意,客觀上也實施教唆的行為,可以適用犯罪預備的法理對其進行處罰,結合具體的案情中起所教唆的具體犯罪行為與實施的教唆行為的程度等情況綜合進行判斷。
將刑法29條第2款與刑法第22條的規定結合進行考察,看是否需要對其進行從輕、減輕還是進行免除處罰。在教唆犯自身預備的情形下對教唆預備進行處罰的理論依在于對我國刑法第25條所規定的預備犯的承認,并沒有涉及共犯從屬性與共犯獨立性之間的定性與理論爭議。因為根據我國刑法第25條的規定犯罪預備是指為了犯罪,準備工具、制造條件。
對于此種情況的處理張明楷教授提出:“教唆者唆使他人犯罪,他人實施了犯罪預備行為的,如果需要處罰預備犯,則對于教唆犯同時適用刑法29條第1款與第22條,對于教唆犯,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⑤
三、被教唆者處于犯罪預備的階段也可以與教唆者成立共同犯罪
(一)對于共犯從屬性說進行適當的修正
在我國刑法理論的一般認知中,在堅持共犯從屬性的前提下條件下對于共犯的處罰必須是正犯已經著手實施了犯罪行為即發展到犯罪施行階段,便會得出當正犯并沒有著手實施犯罪行為處于預備階段時,因為并不能夠成立共同犯罪所以形成了教唆犯與幫助犯不能對其進行處罰的困局。但是從刑法法理出發進行理解,不必將共犯的從屬性進行絕對化的理解,認為正犯的著手是處罰共犯的前提,而應當從共犯從屬性的本質出發進行理解,即在本質上來說共犯的處罰中對從犯的處理是以正犯可罰為前提。易言之,共犯的成立應當以正犯實行構成要件行為為前提,其中包括了基本構成要件行為以及修正構成要件行為。⑥
我國刑法在總則原則性地規定了對于預備犯的處罰,原則上對于所有罪名的預備犯都有處罰的可能。所以在處罰預備犯的場合可以以預備行為作為不法的起點,著手只承擔不法程度升高的職能⑦。在已經實行了犯罪預備的情況下已然產生了不法對于共犯的成立存在解釋的空間。
(二)被教唆者預備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可以成立共同犯罪
我國《刑法》第25條規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教唆者已經將教唆行為實施完畢,并且被教唆者也已經接受了教唆,將被教唆之罪的不法階段推進到了預備。此時就可以證實教唆者與被教唆者形成了教唆犯罪的共同故意⑧。
既然在此種情況之下教唆者與被教唆者之間已經形成共同故意,便可以根據《刑法》第25條的規定認定成立共同犯罪。在我國《刑法》并沒有明確規定共犯的成立必須從屬于正犯之著手的情況下,為了滿足某一種理論而去特意地縮小刑法的處罰范圍并不是一種明智的做法。當教唆者與被教唆者之間已經形成共同故意去犯罪的時候,作為正犯的被教唆者其行為其實已然違法,不論其符合基本的構成要件還是修正的構成要件,共犯的行為已然達到了值得刑法處罰的不法階段。所以在我國《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之下教唆者與被教唆者之間完全可以成立共犯。
四、對于教唆者可以按從犯進行論處
(一)《刑法》第29條第1款與第2款皆是關于共同犯罪的規定
如前所述,在教唆者已經完成教唆行為,被教唆者處于犯罪預備之時便可以成立共同犯罪。這是因為,被教唆者接受教唆并為了著手施行犯罪而進行預備的行為之后,就表明教唆者與被教唆者在主觀上已經相互連接成犯罪的共同故意,客觀上已有共同的犯罪行為,教唆者與被教唆者之間已經成立共同犯罪⑨。
在成立共同犯罪的情況下,對于教唆者與被教唆者的定罪處罰可以將《刑法》29條第1款與第2款進行結合適用。對于刑法第29條第1第2兩個條款之間的關系,應當立足于刑法體系之中進行整體性的理解。首先,可以將第29條第1款理解為關于共同犯罪中教唆犯具體情形處理的原則性規定,而第2款規定則可以理解為教唆犯的預備形態和從輕處理形態,但必須受到第1款的原則性限制,因為從文義理解的角度出發第2款只是第1款的提示性規定:教唆他人犯罪應當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處罰⑩。在將第29條第2款視為提示性規定而29條第1款視為原則性規定的情況下。適用第29條第1款的規定。
(二)符合從犯的立法規定與精神
在被教唆者僅處于預備階段的情況下可以適用《刑法》第22條從犯的規定“可以”進行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而教唆者也可以作為從犯適用《刑法》第27條的規定“應當”進行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不僅可以實現罪與刑罰之間的妥當性,而且將第29條與第27條進行結合適用不會產生單純適用第29條第2款時需要以未遂犯的處罰條款來對預備犯進行處理,從而在實質上緩解各種輕重失衡的處罰不公平。例如,被教唆人僅實施了預備行為時,被教唆人被處以預備犯,而教唆人卻被處以未遂犯的情形。?
(三)相比于其他教唆犯預備的處罰理由更具有合理性
由于在教唆犯預備這種特殊的情形,機械地適用《刑法》第29條第2款的規定進行處罰將會形成不公平不合理的局面即作為正犯的被教唆者可以適用預備犯的規定從而存在免除處罰的可能性,而危害性程度更輕的教唆犯卻只能進行從輕、減輕處罰。正是據此我國的學者才對于這種現象的處罰提出了不同的解釋路徑與適用方法。
正如筆者之前所論述,我國刑法第29條規定中第1款與第2款皆是關于教唆犯罪中對于共同犯罪的處罰規定。在第29條第2款所規定的“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中,當被教唆者處于犯罪預備之時,可以將我國《刑法》第29條的規定與第27條的規定結合進行適用。
結語
在我國的刑法學界關于第29條第2款的性質定性與具體適用的爭論一直是最激烈討論的問題之一,由此條款所產生的爭議更是關于共犯性質等問題的主戰場。但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卻是,刑法條文解釋理解的模糊會對實務界對于《刑法》條款的適用產生巨大的影響事關許多公民在有教唆行為的情況之下定罪量刑與人身自由。對此劉明祥教授提出:這種處罰上的不均衡,是由于立法不科學造成的⑨,筆者也贊同這個觀點。但是立法的修改周期往往十分漫長,在立法的規定修改完善之前如何立足于我國《刑法》的規定,將處罰上的不均衡在合理的解釋與適用之下形成公平、合理的處罰格局也是一項重要的任務,這也正是我們作為一個刑法的學習者更應該努力做好的一件事。
注釋:
①由于共犯從屬性與刑法客觀主義并不是本文論證的重點,所以筆者在此僅提出觀點,并無完整與仔細的論證.
②周光權.“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之理解——兼與劉明祥教授商榷[J].法學研究,2013.4.
③周光權.刑法總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四版),2021,第377頁.
④參見郎勝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M].法律出版社,2009,第34-35頁.
⑤參見張明楷.論教唆犯的性質.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21卷[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第89頁.
⑥蔡穎.論教唆行為的兩種性質——兼議《刑法》第29條第2款之理解[M].刑事法評論:刑法規范的二重性論.
⑦勞東燕.論實行的著手與不法的成立根據[J].中外法學,2011.6.
⑧李光宇.被教唆者刑事責任新議——我國《刑法》第29條第2款解析[J].法學雜志,2017.11.
⑨劉明祥.“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之解釋[J].法學研究,2011.1.
⑩同②第188頁.
?何慶仁.我國《刑法》第29條第2款的合憲性解釋[J].政治與法律,2021.8.
參考文獻:
[1] 周光權.“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之理解——兼與劉明祥教授商榷[J].法學研究,2013(4).
[2] 周光權.刑法總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
[3] 郎勝.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4] 張明楷. 《論教唆犯的性質》.《刑事法評論》[M].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5] 蔡穎.論教唆行為的兩種性質——兼議《刑法》29條第2款之理解[J].刑事法律評論.
[6] 勞東燕.論實行的著手與不法的成立根據[J].中外法學,2011(6).
[7] 李光宇.被教唆者刑事責任新議——我國刑法第29條第2款解析[J].法學雜志,2017(11).
[8] 劉明祥.“被教唆的人沒有犯被教唆的罪”之解釋[J].法學研究,2011(1).
[9] 何慶仁.我國《刑法》第29條第2款的合憲性解釋[J].政治與法律,2021(8).
[10] 蔡桂生.刑法29條第2款的法理分析[J].法學家,2014(1).
[11] 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
[12] 譚堃.論《刑法》29條第2款的解釋——以共犯罪名從屬性為路徑[J].清華法學,2021(6).
作者簡介:
周覺東(1995—),男,漢族,湖南郴州人,湘潭大學法學院法學碩士,研究方向: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