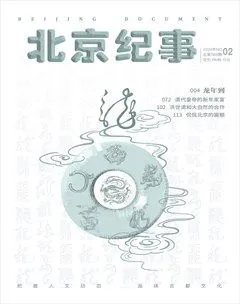還記得春節發的帶魚嗎
曹磊
直到1990年代末,每年節前一進臘月,全國各地大部分單位,特別是國營大單位,都有個一年一度的“保留節目”,就是統一給職工發過年的年貨。老北京有句俗話,肉不能埋在飯里,有粉不能往屁股上抹。類似單位發東西這種露臉的事,真要是說把大門一關,自個兒跟院里悶得兒蜜,那就沒意思了,所以那時候單位過年發東西,都愿意跟大門口找塊不礙事的地方,把成袋、成箱的油、米、帶魚、水果和飲料高高低低碼成一堆,堆得跟小山似的。單位的職工和家屬,男女老少一大幫,頂著西北風,縮著脖子,捂著耳朵,哆哆嗦嗦,原地跺腳,嘴里呼呼冒白氣,按先來后到往“小山”跟前那么一排隊,等著負責發年貨的人拿著花名冊挨個驗明正身,領自己那份東西。
我可趕上這撥了
每個單位的效益不一樣,所在地域的生活習慣不一樣,發的東西也不一樣,可是發來發去,十有八九都離不開大米、帶魚、食用油這“老三樣”。尤其是帶魚,應該算是“老三樣”里的重中之重。就連黃土高原那種壓根兒跟海不沾邊,連海味兒都聞不著的地方,單位過年也愛發帶魚。陜北人年夜飯吃的八大碗里邊,必定少不了一碗先炸后蒸的香酥帶魚。話說到這,海里的魚品種多了去了,單位發年貨干嗎非就認準帶魚了呢?這事真要掰扯起來,根兒還得往60多年以前捯。
1960年代以前,多數中國人其實都不怎么吃帶魚。就拿老北京人來說,真正上得了席面的海魚,也就只有黃花魚這一種。清末民初,北京還保留著每年開春接姑奶奶回門,吃黃花魚的風俗。除了黃花魚,像什么偏口魚、石斑魚、魷魚之類的海魚,倒找錢都沒人吃,壓根兒就沒人認這些玩意兒。
19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老百姓吃不上肉,缺營養。那時候中國沿海的漁場就屬帶魚最富裕,價格便宜,量還特別足,怎么撈都撈不完。為了解決大伙的吃肉問題,好多離海遠的內陸城市這才開始給居民定量供應帶魚。當時的條件有限,冷藏設備少,市面上最常見的帶魚都是半干半濕、又腥又臭的咸帶魚。相聲演員高英培的代表作《釣魚》有句自帶天津味兒經典臺詞:“二兒他媽媽,你給我烙倆糖餅,明兒還有一撥兒呢!明兒那撥兒可好啊!我都打聽過了,這撥兒,全是咸帶魚。”這段相聲最早創作于60年代初,正好也是中國老百姓剛開始普遍接受咸帶魚的那個時間段。
中國人從1960年代開始全民吃帶魚,吃來吃去,天長日久就形成了一種味覺記憶,也可以說一種情結。春節那幾天,蜂窩煤爐子上要是沒有一鍋紅燒帶魚小火慢咕嘟著,不就著干炸帶魚喝兩盅二鍋頭,這個年過得好像就不算特別圓滿。
買魚別忘搪瓷盆
1970年代以后,冷庫越修越多,儲藏條件改善了,市面上的咸帶魚隨行就市也就換成了冷凍的鮮帶魚。那時候買東西都得憑本、憑票。每年春節,北京市民可以拿著家里的副食本,去副食店、糧店、菜市場這些地方買幾樣過年物資。按人頭算,每人大概可以買2兩瓜子、半斤花生、1兩香油、5斤富強粉,剩下的還有芝麻醬、豬肉、帶魚什么的。70年代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市面上的商品統一定價。一樣的東西,甭管去什么地方買,價錢全都一樣。話雖這么說,一樣的帶魚,不一樣的副食店、菜市場的進貨渠道不一樣,再就是貨到了以后的儲存條件不一樣,品質也就有高有低。老百姓兜里的銀子有限,誰都愿意花最少的錢,買最好的東西,追求最高的性價比。所以買帶魚以前,就必須得搞搞調查研究,打聽清楚哪個地方賣的帶魚品質最好。
現在西單路口東北角有個君泰百貨。40多年以前,君泰百貨的位置是個二層的水泥小樓,叫西單菜市場。這地方當年可是整個西半邊北京城的老百姓過年扎堆買帶魚的“風水寶地”。20世紀七八十年代那會兒沒有塑料袋,老百姓出門買菜一般都是提摟著書包,挎著菜籃子,最不濟也得拿個尼龍網兜。帶魚腥了吧唧,還容易流湯,擱在書包、菜籃子里,當時倒也能湊合拿回家,就是容易弄得到處全是腥湯,過后還得費力氣收拾。大伙去西單菜市場排隊買帶魚,都得提前預備專用的“神器”。什么“神器”呢?就是一個小搪瓷盆。買帶魚的小搪瓷盆,樣式跟老式的搪瓷臉盆差不多,只不過口徑稍微小點,差不多也就一二十厘米的意思。老北京管這種小盆叫“淺子”,說得再簡單點,加個兒話音也可以叫“淺兒”。意思就是告訴您說,這種家伙什兒比盤子深,比正常的盆呢,稍微又淺點。100多年以前,老北京賣鍋碗瓢盆的小買賣人走街串巷,專門還有一套吆喝:“哎,賣小盆兒咧,賣小罐兒咧,喂貓的淺兒咧,舀水的罐兒咧,大小夜壺咧。”
家家戶戶過日子,多少都得置辦幾個小搪瓷盆。平常可以洗菜、和面,也可以早上起來端著去早點鋪買油餅,趕上家里吃面條,還可以拿它撈面條,給面條過水。出門買豆腐、豬肉、帶魚這類容易灑湯漏水的東西,直接端個小搪瓷盆去,干凈又方便。每年進了臘月,大伙扎堆買帶魚那幾天,您就看去吧,柜臺前頭排隊的人,人手一個小搪瓷盆。盆的顏色攏共只有兩種,要么是白的,要么是淺黃的,上頭多少還都帶點紅、藍花。趕上家里的小孩淘氣,再不就是老人干活的時候沒留神,保不齊就得把盆掉在地上摔幾下。搪瓷盆不禁摔,一摔就容易掉瓷。排隊這幫人手里端的搪瓷盆多數都是這兒凹下去一塊,那兒癟進去一塊,摔過的地方瓷還磕掉了,露著里頭的黑胎,坑坑洼洼、斑斑點點,很少能看見品相完美的新盆。
男女老少一幫人端著搪瓷盆排隊買帶魚,售貨員穿著藍大褂,戴著白套袖、白帽子,站在木頭柜臺后頭賣帶魚。那時候市面上的帶魚都是按寬窄、薄厚統一分級,魚身子越寬、越厚,等級就越高,價錢當然也就越貴。3毛8一斤的高級帶魚,又寬又厚,性價比最高。2毛5一斤的帶魚呢,多少就差點意思,可是湊合也還吃得過。2毛5再往下,還有1毛5一斤的帶魚,魚身子比手表帶寬點有限,除非是日子特別緊巴的家庭,輕易沒人愿意要。3毛8的帶魚,檔次再往高了走,還有4毛多、5毛多一斤的特級帶魚,那就不是一般人消費得起的了。
2毛5、3毛8一斤的“經濟適用型帶魚”數量有限,先到先得。再者說,排隊排得越靠前,挑挑揀揀的余地也就越大。為了花最少的錢買到最好的帶魚,快過年的那幾天,大伙都得起五更趕著去副食店、菜市場排隊。負責排隊買帶魚的以老年人和婦女居多,脾氣好,也耐得住性子。
帶魚陪我去跨年
甭管幾毛錢一斤的帶魚,買回家第一件事都得麻利收拾出來,要不就容易壞。帶魚最大的好處就是肚子里沒東西,身上也沒鱗。收拾的時候,最多就是拿把腦袋和尾巴一鉸,把腸子掏了,再把身子鉸成一段、一段的,然后拿到自來水管子底下沖干凈。收拾利落的帶魚段,立馬就得下鍋油炸,為的是讓魚肉定型,減少水分,延長保存時間。炸這個帶魚段最多只能炸到八九成熟。魚炸好了以后,擱在干凈的搪瓷盆里,蓋上蓋,跟院里找個陰涼的地方凍起來。真正吃的時候還可以再加工,特別方便。想吃干炸帶魚,那就把魚段再回鍋使勁炸炸,出鍋的時候撒一把花椒鹽;要是想吃紅燒帶魚,那就把魚段放在鍋里,倒一碗蔥、姜、蒜調的糖醋汁,加足了水,小火慢咕嘟,越咕嘟越入味,越咕嘟越香。
為了省煤氣,過年炸帶魚用的一般都是屋里取暖用的蜂窩煤爐子。爐子的風門徹底打開,火燒得旺旺的,架上小鐵鍋,鍋里倒滿了油,不光能炸帶魚,捎帶手還能把過年吃的排叉、饹馇盒、素丸子、豆泡、松肉、藕合什么的全炸出來。各種炸貨漂在滾燙的油鍋里,“刺啦、刺啦”一響,帶著香味的油煙子順著窗戶直往外飄。油煙子的香味跟串門客人抽煙、喝茶、嗑瓜子、剝花生的香味,還有家家戶戶燉雞、燉肉的香味摻和到一塊兒,配上“當、當、當”的剁餡聲,電視機里音量開到最大的歌聲和笑聲,街坊鄰居“你好”“我好”的拜年聲,還有大街上小孩揣著小鞭、舉著香頭瞅冷子“噼啪”來一響的放炮聲……各種亂七八糟的香味和動靜摻和到一塊兒,彌散在胡同里,再那么一發酵,就是記憶深處揮之不去的年味。
臘月二十九那天夜里,好多人都愿意把第二天吃的帶魚提前燉出來。臨上床睡覺,裝滿了帶魚的鐵鍋擱在爐子上咕嘟、咕嘟直冒泡。小孩鉆到被窩里,枕頭旁邊擺著第二天起來穿的新衣服,聞著燉帶魚的香味關燈睡覺。睡到半夜,迷迷糊糊,半夢半醒還能聽見大人從床上起來,給鍋里的帶魚翻身。第二天早上天光大亮,坐在被窩里伸著懶腰,揉著眼睛仔細一看——鍋里的帶魚已經咕嘟得骨酥肉爛,自己盼了整整一年的這個年,也就算是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