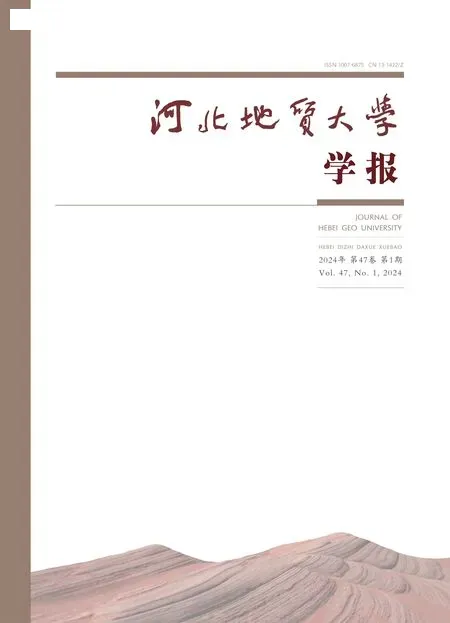典型國家“雙碳”目標實現路徑解析及中國借鑒
張夢楠,曹楠楠,朱雪蓮
1.河北地質大學 a.學術傳播中心,b.經濟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31;2.河北地質大學自然資源資產資本研究中心,河北 石家莊 050031
近年來,氣候變化加劇在全球引發了一系列經濟、社會和環境問題,影響了人類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世界各國高度重視碳減排的合理規劃,其中部分國家已在低碳減排、綠色發展領域取得顯著成效。中國提出要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即“雙碳”目標),為減緩全球氣候變暖、提振全球氣候治理信心釋放了積極信號。“雙碳”目標的提出及推進,不僅彰顯了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責任擔當,也符合中國能源結構、產業結構、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自身發展需要,對中國實現綠色低碳發展、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相對于走在低碳發展前列的國家來說,中國的碳達峰、碳中和進程起步較晚,目前面臨著碳排放總量大與碳達峰碳中和過渡時間短的雙重壓力。在此背景之下,如何探索出適合中國的綠色低碳發展模式,平穩實現向碳達峰、碳中和過渡,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基于此,通過分析低碳發展水平處于前列的典型國家在實現碳達峰時的階段發展特征及碳達峰碳中和路徑,從中汲取有益經驗并結合中國實際情況進行借鑒和參考,以期為“雙碳”工作部署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1 典型國家及地區碳達峰、碳中和目標實現路徑及階段發展特征
1.1 典型國家及地區碳達峰目標實現路徑及階段發展特征
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2017年發布的報告[1],可以發現世界碳減排趨勢整體向好,已經達到碳達峰水平或承諾未來將實現碳達峰的國家數量從1990年的19個逐步增加到2030年的57個,且已經達到或承諾達到排放峰值的國家所覆蓋的全球排放份額從1990年的21%增長到2030年的60%(見表1)。在這些積極推進碳減排及碳達峰的國家中,包含一些世界上碳排放較大的國家,如美國、俄羅斯、中國、日本、巴西、德國和墨西哥等。然而,這份報告也指出達到峰值的國家數量和它們達到峰值的排放水平不足以滿足《巴黎協定》所確定的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目標,即在21世紀末,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不高于工業化前水平2 ℃以內,并努力將氣溫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1.5 ℃以內。要實現全球增溫不超過1.5 ℃~2 ℃的目標,不僅取決于實現碳達峰的國家數量,還取決于這些國家所占據的全球排放份額、達峰時的碳排放水平、實現碳達峰的時間以及實現達峰后的減排速度。由此可見,在碳減排和碳達峰的進程中,世界各國仍任重而道遠。

表1 全球碳達峰實現情況Table 1 Global carbon peak achievement status
幾十年來,世界各國在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推動綠色能源發展等領域不斷付諸努力,其中部分國家成效顯著,率先實現碳排放達峰。下面通過梳理其中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且較早實現碳達峰的歐盟①、美國、日本等典型國家及地區碳達峰目標的實現路徑,并基于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WDI)數據的相關指標發掘其目標實現時點階段發展特征的共性規律,以期為中國碳達峰行動方案的制定提供可借鑒經驗。
1.1.1 典型國家及地區碳達峰目標實現路徑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在生產生活中對化石能源的消耗呈現指數級增長。為解決溫室氣體過剩導致的一系列全球氣候環境問題,各國或主動或被動地開啟碳減排之路。由于資源稟賦、發展階段和經濟體量的不同,世界各國有著不同的碳排放變化曲線和碳達峰時間。相比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較早實現了碳排放達峰,因此,探究其低碳發展方式和碳達峰的主要實現路徑,可為中國實現碳達峰及后期的碳中和提供借鑒。總結典型國家及地區實現碳達峰的經驗,其實現路徑主要涉及國家發展動能轉換、能源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優化、政府政策支持等方面。
從國家發展動能轉換來說,大多數已經實現碳排放達峰的發達國家的主要發展動能都經歷了從第二次工業革命高碳能源規模化應用帶動生產力急速發展到第三次工業革命新興科學技術成為國家發展的主要驅動力的轉變,碳排放在經歷增長平臺期之后出現了下降趨勢,經濟發展和碳排放逐漸脫鉤,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規律開始顯現[2]。
從能源結構調整來說,典型國家多從能源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方向入手形成合力完成能源結構優化。歐盟、美國和日本作為低碳減排的先行者對能源結構的優化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一方面,在能源供應上較早的關注到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潛力,不斷加大對天然氣等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資源的開發,優化能源結構并提出以清潔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作為現代工業戰略的核心。截至目前,這些典型國家在可再生和清潔能源上的投入取得較好的成效,瑞典已基本實現電力生產不依賴石油和煤炭,水電和核電是其主要電力來源[3];歐盟前成員國英國目前可再生能源已成為僅次于天然氣和石油的第三大能源,其天然氣的開采使用逐漸超過煤炭和石油[4];歐盟整體在2022年的風能和太陽能可再生能源生產能力超過400億千瓦,比2020年增長了25%以上②;碳達峰前后美國煤炭和石油開采使用比例下降,而天然氣等清潔能源及水資源和核能等可再生能源比例上升,能源結構不斷優化[5]。另一方面,在能源消費上以多種方式引導幫助企業完成既定減排目標。如歐盟前成員國英國利用稅收優惠、減排援助基金等方式,引導作為能源需求者的企業使用減排技術,并限制高污染、高排放和高能耗的企業發展[6];美國對于涉及高碳消費的行業或企業要求其履行可再生能源利用占比增加、綠色生態投入增加等相關低碳承諾[7];日本則采取將新能源與高度信息技術控制相結合的方式,助力企業提高能源的利用率[8]。
從產業結構來說,實現碳達峰的國家大多都經歷了工業化向后工業化的過渡,即第二產業主導向第三產業主導過渡的產業結構變遷。除波蘭外,1996年以后實現碳達峰的大多數發達國家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達65%以上,生產性服務業和高加工制造業成為主導產業[9]。歐盟、美國和日本一直走在產業結構的優化以及低碳技術研發和創新的前列,較早的對經濟低碳發展進行了先行產業布局。一是逐步降低鋼鐵、建材行業、有色金屬等的行業規模;二是推動生物技術、航空航天、汽車、電子信息等高附加值、低消耗的高端制造業和新興產業發展[10],同時利用自身電子信息技術優勢為其他行業進行升級改造,有力促進了產業結構優化調整;三是推進以企業為導向的生產性服務業迅速發展,以政府影響力保障金融保險業、運輸業、信息通訊業等第三產業穩定成長,有力推動化石能源消費降低以及碳排放量進入峰值平臺期[11]。美國在產業結構轉型的過程中,通過向全球范圍轉移高耗能高排放的工業及制造業以減少自身碳排放,導致長期持續的制造業占比降低。雖然有利于服務業的發展以及整體碳排放的下降,但是從長遠看制造業是經濟發展的根本所在,且一旦流失很難恢復。[12]
從政府政策支持來說,雖然碳排放達峰與一國經濟階段及產業結構有著密切的關系,但在此過程中碳減排政策規制在客觀上對碳達峰起到了不可忽視的協同促進作用。從典型國家和地區已發布的政策來看,政策內容一是聚焦于對低碳社會轉型的總體規劃。如日本自1997年出臺《關于促進新能源利用措施法》之后,陸續于2002年、2008年、2009年頒布了《新能源利用的措施法實施令》《面向低碳社會的十二大行動》《綠色經濟與社會變革》,為各部門進行向低碳社會轉型提供了規則引導。二是側重于鼓勵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助力能源結構優化以及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具體來說,歐盟較早開始嘗試使用各類政策工具來刺激新能源發展。1986年,歐盟(歐共體)在《能源政策》中提出將能源發展的重點從核能轉向可再生能源,為歐盟能源政策的發展方向奠定了基礎。1988年,歐盟(歐共體)發表了《能源內部市場》報告,提出通過對天然氣與電力部門的整合,推動天然氣對煤炭和石油的替代,進一步提高歐盟內部能源利用效率,促使各成員國相互合作以實現歐盟整體能源安全、能源結構調整、能源使用效率提高的目標。除了整體上的規劃,歐盟各成員國也在各國內部進行了一些有益的嘗試,如德國對可再生能源的關注以及制定能源轉型的戰略可以追溯到1985年德國開展的氣候變化大辯論和1987年成立的大氣層預防性保護委員會[13],在1989年又提出了風電計劃③,進一步開發利用新能源。此外,瑞典政府也一直在積極支持非高碳能源的開發利用,自1975年開始每年對生物質燃燒與轉換技術研發進行補貼[14]。美國在1993年提出的《氣候變化行動計劃》中首次明確減碳目標之后,先后出臺了《國家能源綜合戰略》、替代燃料免稅舉措、碳封存項目開發、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系統集成計劃、清潔燃料資助計劃、生物質能研發計劃等一系列計劃[15]以及發起“氣候拯救者”等政企合作項目④,以期提高自身能源利用效率,優化能源結構。同時,美國也注重新能源的開發利用,提出了《能源安全法案》(2005)、《新能源法案》(2005)、《美國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2005)、《低碳經濟法案》(2007)等一系列政策法規,以此推動美國新能源的發展并有力約束了碳排放。
1.1.2 典型國家及地區碳達峰目標實現時點發展特征及與中國情況對比
1)經濟發展水平及產業結構
從經濟發展的絕對值來看,歐盟、美國、日本在實現碳達峰時點均達到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基本都在兩萬美元以上(以2015年不變美元價格),且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達峰時間更晚的國家及地區其人均GDP水平更高,如美日兩國在21世紀實現碳達峰時人均GDP分別達到5.427萬美元和3.424萬美元。作為對比,中國2020年人均GDP為1.037萬美元,與典型碳達峰國家及地區達峰時人均GDP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較高的人均GDP 水平可為后續深度減排以及碳中和的實現提供良好的經濟基礎,因此,中國在未來減排過程中可能面臨較大的成本支付壓力。此外,這些典型國家在實現碳達峰后GDP增長與碳排放基本實現了“脫鉤”,歐盟(1990年達峰)、美國(2007年達峰)、日本(2013年達峰)在實現碳達峰之后4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平均值分別為1.274%、0.360%、1.071%,而對應時期平均碳排放增長率為-2.488%、-3.568%、-3.504%。
從經濟發展速度來看,除較少數國家屬于自然達峰外,大多數國家受政策驅動實現了碳達峰,因此通常在實現碳達峰后該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會明顯下降,歐盟、美國、日本⑤在實現達峰后10年的平均GDP年增長率為2.215%、1.518%、0.076%,相較于達峰前10年平均GDP年增長率2.288%、3.351%、0.696%,均有明顯下降。中國近些年一直保持著6%以上的經濟增速,遠高于上述國家及地區,這為中國在實現碳達峰后可能出現的經濟增速下降提供了足夠的緩沖區間。
20世紀90年代后實現碳達峰的典型國家的三次產業結構均呈現明顯的“后工業化”特征,美日在實現碳達峰時點第三產業占比遠高于第一、二產業,三產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比例約為1∶20∶70。歐盟整體在碳達峰時點的數據缺失,但參考芬蘭、冰島、奧地利、瑞典、丹麥這些歐盟主要國家的數據來看,各國在碳達峰時點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約為55%~62%,產業結構總體上依然呈現第三產業占比較高的特征。而中國2020年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比例約為8∶38∶55,與已實現碳達峰目標的典型國家相比,中國的第三產業占比較低,高碳行業密集的第二產業占比較高,產業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
2)能源結構及利用效率
從能源消耗結構來看,除少數資源稟賦優越且較早進行可再生能源布局的國家在實現碳達峰時化石燃料能源消耗占總量的百分比在60%以下,如瑞典為36.877%、芬蘭為56.885% ,多數國家在實現碳達峰時化石燃料能源消耗占比仍然較高,歐盟在1990年實現碳達峰時,化石燃料能源消耗占比高達80.881%,美國在2007年實現碳達峰時該比例為85.615%,日本在2013年時更高為94.633%。歐盟、美國、日本在碳達峰年份的可再生能源消耗占最終能源消耗總量的百分比較低,都在10%以內。此外,在實現碳達峰后典型國家及地區的化石能源消耗占比呈現下降趨勢,能源消費結構更加低碳化。近些年中國化石燃料能源消耗占總量的百分比呈現下降趨勢,但比例仍然較高處于80%以上,可再生能源消耗占最終能源消耗總量的百分比在2018年為13.124%。就現有數據來看,中國的能源結構與已實現碳達峰的典型國家相似,還是以高碳能源為主,因此在實現碳達峰的過程中應逐步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使能源結構趨于優化。
從能源利用效率來看,歐盟、美國和日本在碳達峰時點每1 000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以2017年不變購買力平價處理)分別為115.672、138.853和90.161千克石油當量,其中,歐盟和日本在實現碳達峰年份的能源利用效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美國則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在實現碳達峰前后典型國家的能源利用效率一直保持逐年提高的狀態。中國在2014年化石燃料能源占比為87.670%、可再生能源消耗占比為12.061%,與大多數已達峰國家相比相差不大,但與走在低碳發展前列的瑞典、芬蘭等北歐國家相比,中國高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仍有較大的進步空間。在能源效率方面,中國2014年每1 000美元GDP的能源消耗(以2017年不變購買力平價處理)為187.687千克石油當量,遠高于當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20.794千克石油當量,說明中國能源利用效率仍有較大增效空間。
3)城鎮化水平
城市是承載人類活動的重要場所,而人類活動又是20世紀中葉以來造成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的原因。歐盟、美國和日本在碳達峰時點的城市化水平即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分別為69.369%、80.269%、91.226%,而中國在2020年該數值為61.428%,與較早實現碳達峰的歐盟水平接近,但與較晚達峰的美日相比城鎮化水平較低,預計未來中國城鎮化水平還會繼續攀升。此外,歐盟、美國、日本在2000—2020年間城鎮化水平增速進展較慢,分別為5.836%、4.563%、16.682%,而中國則在這20年間增長了近一倍,遠高于上述國家,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由2000年的35.877%增長為2020年的61.428%。
1.2 典型國家碳中和目標實現行動方案梳理
目前,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2020年排放差距報告》(2020 Emissions Gap Report),已有超過120個國家做出零碳或碳中和承諾,但在國際范圍內仍缺乏成熟且系統的碳中和經驗。在碳中和目標時間安排上,歐盟、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走在低碳發展前列,這些國家大多將碳中和目標年份設定在2035—2050年之間。回顧上述國家及地區的碳中和行動規劃,不難發現實現不同國家和地區實施的政策及路徑有一些相通之處可為中國低碳轉型及碳中和目標實現提供借鑒經驗。
1.2.1 運用政策工具有力約束碳排放,保障碳中和目標實現
在邁向碳中和的過程中,典型國家大多已根據各自國情頒布了關鍵指導性文件,規劃了碳減排行動的長期政策路徑。為實現社會可持續發展,歐盟較早的明確了綠色發展理念與碳中和目標,并先后推出了《歐洲綠色協議》《歐洲氣候法案》《歐洲綠色新政》等文件,擬通過立法及綱領性文件的形式確保歐盟各機構和成員國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在2021年美國重返《巴黎協定》后,美國就碳中和目標實現路徑頒布的綱領性文件主要有《清潔能源革命與環境正義計劃》《建設現代化的、可持續的基礎設施與公平清潔能源未來計劃》[16]和《關于應對國內外氣候危機的行政命令》,將氣候變化納入國家安全戰略并調整外交政策加強國際合作以繼續推動美國碳中和進程。為支撐日本碳中和目標的實現,日本在立法層面頒布了《低碳城市法》,并于2021年5月修訂了《全球變暖對策推進法》,為政府提供了監督審查國內氣候政策和行動的法律保障。同時日本政府還發布了《2050 年碳中和綠色增長戰略》《革新環境技術創新戰略》等,分別從能源、產業和技術等方面提出了碳中和實現過程中具體的發展目標。
1.2.2 分階段、分部門進行合理分解落實碳中和目標
在實現碳達峰之后,歐盟、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就碳中和目標的實現從時間及部門兩方面進行了行動方案的制定[17],提出階段性碳減排目標并具體細化各個部門的減排措施。首先從時間上來看,歐盟委員會于 2018 年 11 月首次提出 2050 碳中和愿景,之后歐盟委員會2021年通過了一系列關于歐盟氣候、能源、土地使用、運輸和稅收政策的提案,計劃在2030年前將溫室氣體凈排放量相比1990年的水平減少至少55%[18]。美國設定了“3550”碳中和進程,即在2035年美國電力部門實現碳中和,建筑庫存的碳足跡減少50%;2050年確保美國實現100%的清潔能源,達到凈零排放。日本方面截至2023年3月,已有包括東京、京都和橫濱在內的934個地方政府做出了2050年實現凈零碳排放的承諾,約覆蓋日本人口的99.7%[19]。日本碳中和進程顯著推進,這離不開日本政府對碳減排的合理規劃。日本經濟產業省在其發布的《2050 年碳中和綠色增長戰略》中提出要在2018年 10.6億噸碳減排量的基礎上,到2030年碳減排量達到 9.3億噸 ,實現排放下降25%的目標,最終到2050年通過碳減排和碳移除等手段實現凈零排放[20]。其次從不同部門來看,歐盟為推動2050年凈零排放目標的實現在氣候、能源、環境及海洋、農業、交通、產業等領域提出了一系列轉型政策與措施,并推出了諸如REPowerEU計劃、綠色協議產業計劃(The 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等特色項目。此外歐盟還對部分部門設定了更為具體的單獨減排目標,如在能源方面,到2030年歐盟能源結構中可再生能源占總能源比重至少為32%、能源效率至少提高32.5%;在交通方面,到2030年歐盟新乘用車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較 2021 年降低55%、貨車降低50%。美日也對碳減排的關鍵部門進行了減排目標的具體化設定,如美國計劃到 2035 年實現電力系統零碳污染;日本將碳減排涉及的各部門分為能源相關產業、建筑相關產業、交通運輸/制造業相關產業三大類共14個產業,并為這14個碳減排關鍵領域制定更為細致的產業和能源政策方面的行動計劃。
2 典型國家碳排放影響因素定量解析及與中國情況對比
通過對典型國家及地區碳達峰、碳中和發展軌跡的梳理,典型國家均通過頒布關鍵指導性碳減排文件來保證碳減排行動的長期穩定性,并在此基礎上制定階段性碳減排目標,具體細化各個部門的減排措施。除了強有力的碳減排政策支持外,碳達峰、碳中和作為一個多維度的轉型發展問題始終受到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的綜合影響。因此,通過建立STIRPAT 模型,量化分析影響典型國家碳達峰、碳中和進程的因素,并與中國情況進行對比。
2.1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1 STIRPAT模型
20世紀70年代,美國生態學家Ehrlich和Comnoner提出了關于環境影響程度(I)與人口規模(P)、財富水平(A)及技術水平(T)關系的IPAT模型,即:
I=P×A×T
(1)
STIRPAT模型是由 IPAT模型拓展而來,由于IPAT模型存在所有影響因素等比例影響環境因素的缺陷,DIETZ等于1994年在IPAT模型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優化,使其中各影響因素的系數可以作為參數來估計,同時依據研究需要允許對各影響因素進行適當分解或增加其他控制變量,模型等式如式(2)。
I=aPbAcTde
(2)
目前,STIRPAT 模型已成為碳排放預測的經典模型之一。STIRPAT模型是一個多自變量的非線性模型,在實際應用中通常將模型兩邊取對數使其轉化為線性方程,如式(3)。
lnI=lna+blnP+clnA+dlnT+lne
(3)
式(2)、(3)中,a為模型系數;b、c、d分別為人口規模、財富水平和科技水平因素的系數,根據彈性系數概念P、A、T每發生1%變化,將會引起I的b%、c%、d%變;e為隨機誤差項,其余變量含義與式(1)一致。
2.1.2 數據來源
本研究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WDI)數據庫。在綜合考慮相關數據的可得性和準確性的基礎上,選取2000—2020年德國、美國、日本以及中國的相關數據指標進行實證分析。需要說明的是,由于歐盟各成員國自然資源稟賦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有較大差異性,若采用歐盟整體數據會導致結果缺乏代表性且會有部分數據缺失,因此選擇較能代表歐盟發展水平的德國進行實證分析。
2.2 模型構建與變量選取
通過上文對典型國家及地區碳達峰、碳中和路徑的梳理總結,并借鑒余利豐[21]和張哲、任怡萌等[22]的做法,引入經濟水平、能源結構、能源效率、人口規模、產業結構和城鎮化水平等因素將STIRPAT模型拓展為:
lnI=lna+β1lnP+β2lnA+β3lnT+β4lnE+β5lnS+β6lnU+lne
(4)
式(4)中,I為環境影響程度,用單位GDP碳排放表示;P為人口規模,用總人口表征;A為經濟水平,用各國家或地區人均國內生產總值(2015年不變價美元)衡量;T為能源效率,用能源使用效率測度,即GDP與能源使用量之比;E為能源結構,用化石燃料能源消耗量占總量的百分比衡量;S為產業結構,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表示;U為城鎮化水平,用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表征。
2.3 實證結果分析
梳理現有使用STIRPAT 模型進行碳排放影響因素分析的文獻,可以發現,選取的解釋變量之間一般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多重共線性,易造成“偽回歸”現象。目前,解決多重共線性的方法主要有增加樣本容量、偏最小二乘法、差分法、主成分分析和嶺回歸等。其中,嶺回歸分析能夠較好化解共線性數據的有偏估計,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數值的穩定性、提高計算精度。因此,為了提高模型估計結果的有效性,采用嶺回歸分別對德國、美國、日本以及中國進行擬合分析,回歸結果見表2。通過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發現,經濟水平、能源效率和產業結構因素與碳排放呈現出負相關關系,而能源結構和城鎮化水平因素則為正相關關系。具體結論如下:

表2 回歸結果分析Table 2 Analysis of regression results
第一,實現碳達峰后,多數國家實現了經濟發展和碳排放脫鉤。除日本外,其他典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對碳排放的影響顯著為負,這主要是由于這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且較早實現碳達峰的典型國家,大多已經處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的下降階段,且經濟發展與碳排放之間已經實現了脫鉤。而中國雖然影響系數也顯著為負,但其影響力度遠小于表中其他國家,可見目前中國經濟發展與碳排放的關系尚未實現脫鉤或處于弱脫鉤階段。
第二,以化石燃料能源為主的高碳能源的使用仍是影響各國碳減排進程不可忽視的核心源頭因素。由實證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以德國為代表的歐盟、美國、日本這些典型國家,能源結構都是影響碳排放的顯著因素,尤其對中美兩國來說,更是影響碳排放最主要的因素。
第三,在中日兩國數據中能源效率與碳排放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即能源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單位GDP碳排放的減少。相較于日本來說,中國能源效率系數的絕對值更小,其對碳排放的抑制作用還有可提高的空間。
第四,產業結構因素的影響系數在中國和美國數據中都顯著為負,特別是對中國來說,產業結構因素是對碳減排拉動力度最大的因素。這其中既有第三產業本身的碳強度較弱的原因,也有這些國家處于或正在向后工業化時期過渡,高耗能工業產品需求下降,整體產業結構向高端發展的原因。
第五,在城鎮化過程中,城市的高速發展以及人口的過度集聚會導致城市基礎設施需求飛快提升,導致一些城市化水平較高的地區碳排放水平居高不下。這一點也在中國和德國的數據中得到了印證,實證結果中城鎮化因素對碳排放的影響表現為顯著的正向影響。
第六,各國實現碳減排的主要驅動因素都不相同,因此中國在設定碳達峰、碳中和路徑時,既要借鑒典型國家的成熟經驗,也要因地制宜制定合乎自身實際情況的碳減排方案。
3 中國實現雙碳目標的問題與對策
3.1 中國實現雙碳目標面臨的主要問題
第一,從經濟發展速度來看,中國近些年經濟增速遠高于其他國家及地區,但就經濟發展的絕對值來說,中國2020年人均GDP水平與典型碳達峰國家達峰時人均GDP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這使得中國在未來減排過程中,雖然具備一定的經濟增速放緩區間,但也面臨著較大的成本支付壓力。
第二,從階段發展特征梳理及實證分析中均可看出,典型國家及地區GDP增長與碳排放基本實現了“脫鉤”,而中國雖然對應影響系數也顯著為負,但其影響力度遠小于表中其他國家,可見目前中國經濟發展與碳排放的關系尚未實現脫鉤或處于弱脫鉤階段。
第三,產業結構因素即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對中國碳減排的拉動效應最為明顯,但與已實現碳達峰目標的典型國家相比,中國的第三產業占比較低,高碳行業密集的第二產業占比較高,產業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
第四,以化石燃料能源為主的高碳能源的使用仍是影響各國碳減排進程不可忽視的核心源頭因素,由實證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以德國為代表的歐盟、美國、日本這些典型國家,能源結構都是影響碳排放的顯著因素,特別對中國來說高碳能源的使用是碳排放增加最主要的影響因素。總體來看,中國目前的能源結構與大多數已達峰國家相比相差不大,甚至優于部分國家在達峰階段的能源結構,但與走在低碳發展前列的瑞典、芬蘭等北歐國家相比仍有較大的進步空間。
第五,在能源效率方面,中國能源效率與碳排放呈現顯著的負相關關系,但中國能源效率水平與世界平均水平仍有一定差距,能源利用效率需提質增效。
第六,目前中國的城鎮化水平與較晚達峰的美日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且中國城鎮化水平增長速度遠高于上述典型國家,結合實證結果中城鎮化因素對碳排放的正向影響,可以預見未來中國將面臨城鎮化水平持續攀升帶來的更大的碳排放壓力。
3.2 推動雙碳目標實現的對策建議
3.2.1 在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階段,要努力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和經濟發展并行不悖
由典型國家及地區碳達峰經驗來看,較高的人均GDP水平以及經濟增長與碳排放的脫鉤是保障平穩達峰的兩個重要前提條件。因此在著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保持經濟在合理區間運行的同時,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努力推動區域長期綠色低碳發展。
3.2.2 在雙碳目標實現的過程中,應持續關注產業結構的調整
在碳減排的不同階段,產業結構對其的貢獻有一定的差異性。就目前來看,中國處于工業化的中后期,第三產業本身碳強度較弱對碳排放降低有較大的推動作用,因此大力推進服務業等低碳行業發展、增加第三產業比重將有益于低碳發展的實現。但從長遠來看,由于第二產業是經濟發展的根本所在,不宜一味降低其占比,且隨著第三產業比重不斷增長,甚至趨于飽和,單一強調以第三產業發展帶動碳減排變得不再可行,此時更應關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內部產業規模和結構的調整升級對碳減排的貢獻。
3.2.3 從能源供給和消費兩方面入手,實現能源轉型的同時要注重能源效率的提高
能源是影響碳減排進程的核心源頭因素,因此以能源轉型作為重點,構建更為低碳高效的能源系統是實現雙碳目標以及長期低碳發展的必由之路。中國想要轉變以高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就要擺脫對傳統能源的依賴,減少化石能源占比,對水電、核電、風電、太陽能等清潔能源的使用提出合理的定量目標,逐步實現低碳能源對高碳能源的替代;同時要充分利用稅收優惠、減排援助資金等手段引導企業積極使用減排技術和低碳能源;此外,要面向社會倡導低碳生產生活方式,使綠色發展理念不斷深入人心,增強公眾參與綠色低碳發展的意愿。
3.2.4 堅定碳達峰、碳中和信心,對目標進行多維度的分解落實
碳達峰、碳中和的實現離不開堅定的綠色發展信心和科學的計劃制定。在完善碳中和行動方案時應以碳中和目標為終點反過來擬定階段性的碳減排目標并具體細化各個部門的減排路徑;對工業、電力、建筑以及交通等關鍵行業要分別制定有針對性的達峰目標,這些行業是控制碳排放的重點和難點,因此在設定階段性碳減排目標時,既要符合碳中和目標的整體節奏,也要符合行業特點,同時還要為其謀劃專項轉型方案,提供資金、技術以及政策方面的全方位支持;此外中國幅員遼闊,各地的資源稟賦、歷史沿革不同,導致碳排放積累也不同,因此要科學地甄別處于已達峰、未達峰或近達峰的地區,制定差異化的區域碳達峰目標,鼓勵有條件的地區率先實現達峰,并探索出可復制的經驗帶動周邊地區達峰。
注釋:
① 關于歐盟碳達峰時間學界說法尚不統一,但總體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章參考孫傳旺,占妍泓在《碳中和發展軌跡的國際比較與中國碳中和發展力研究》中的觀點即認為歐盟達峰時間為1990年;許多歐盟國家在歐盟正式成立前已實現了碳達峰,因此在梳理實現路徑時多針對各個成員國的情況進行梳理。
② 資料來源:《A 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 for the Net-Zero Age》。
③ 資料來源:IEA. 250 MW Wind Programme. https://www.iea.org/policies/3857-250-mw-wind-programme?country=Germany&page=2&qs=ger&topic=Renewable%20Energy。
④ 資料來源:IEA.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Climate Savers. https://www.iea.org/policies/2176-public-private-partnership-climate-savers?s=1。
⑤ 由于可獲得數據限制,此處日本數據為碳達峰后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