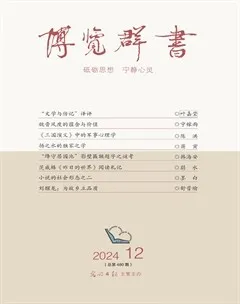魯迅留學事輯
魯迅最初的求學經歷,先是到南京水師學堂學習海軍,又轉入礦路學堂學開礦。1902年3月,魯迅以“南京礦路學堂畢業奏獎五品頂戴”的資格,官派留學日本,進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繼而學醫。從他的求學經歷看,本是個理科生。
留學生頭頂的“富士山”
1902年4月魯迅東渡日本到東京弘文學院學習。他在《藤野先生》寫道: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日本的富士山,曾經是一座蘊藏著豐富能量的火山,是日本一道著名的風景。當時在日本東京的留學生人數超過兩萬以上,大多學習法政、鐵路和速成師范,目的是為了做官發財。魯迅很看不起那些清國留學生,因為他們不求上進、不學無術,頭頂上盤著大辮子,把學生制服中的帽子頂得高高聳起,所以稱他們是“形成了一座富士山”。和魯迅一起的同學聽到魯迅的比喻后笑得噴飯。當時有個同學名叫王立才,送了魯迅一個綽號叫“富士山”,于是“富士山”就成了魯迅的一個諢名在學生中流傳。那是因為魯迅內心有一股火一樣的熱情,時時都想噴發出來。雖然是留學,但各有不同,魯迅曾說:
現在的留學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總疑心他們大部分是在外國租了房子,關起門來燉牛肉吃的,而且在東京實在也看見過。那時我想:燉牛肉吃,在中國就可以,何必路遠迢迢,跑到外國來呢?
中國學生出國留學的目的是吸收國外的先進文化與科技為建設中國而出力,而不是到國外鍍金回國撈金的。中國需要像魯迅一樣的海歸們。
周樹人署名的第一本書
魯迅在1927年在黃埔軍校演講時曾說:“我首先正經學習的是開礦,叫我講掘煤,也許比講文學要好一些。”魯迅很早就對中國的地質地理感興趣,童年時就喜歡讀帶插圖的《山海經》,這是先秦時富于神話傳說的地理書籍,他還買過《徐霞客游記》等地理類書籍,在南京礦路學堂讀書時,主要學習礦物學,目的也是采礦,教學采用德國體制,學的是德語。課程包括礦學、地質學、化學、熔煉學、格致學、測算學、繪圖學等。所做論文題目有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等。學習過的譯本有《地質淺說》《求礦指南》等著作,對中國的地質礦產有了更多的了解,深知這門學科的意義,打下了堅實的地質學基礎。
“凡留學生一到日本,急于尋求的大抵是新知識。除學習日文,準備進專門的學校之外,就赴會館,跑書店,往集會,聽講演。”(魯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剪辮拍照,以表反封建的決心。1903年,浙江同鄉會連續刊載浙江地區列強掠奪浙江礦產事件,魯迅于10月《浙江潮》雜志上發表《中國地質略論》,通過論述中國地質分布、地質發育、地下礦藏,使人們了解“中國在陸里面之情狀”,“以備后日開采之計”,成為中國第一篇系統介紹本國礦產的科學論文。魯迅指出:“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撿;可容外族之贊嘆,不容外族之覬覦”,呼吁國人“奮袂而起”,表現了極大的愛國情懷。
1906年5月,《中國礦產志》由上海普及書局出版發行,封面上印有“國民必讀,江寧顧瑯、會稽周樹人合纂”。此書由馬良作序,書后附有《中國礦產全圖》一幅和《中國各省礦產一覽表》。其中《中國礦產全圖》是將日本政府農商務省地質礦山調查局所繪中國礦產地質的秘圖放大12倍改繪而成。由于年代久遠,現存的舊版本《中國礦產志》并無附圖,《魯迅全集》也未收入,現存的一張是1959年被發現的,原圖作為文物現存上海魯迅紀念館。
《中國礦產志》是辛亥革命前第一部全面記述我國礦產資源的專著。全書分述了全國地質狀況及礦產分布,以科學著述表達了作者的愛國思想。序言中稱此書“羅列全國礦產之所在,注之以圖,陳之以說,我國民深悉國產之所有,以為后日開采之計,不致家藏貨寶為他人所攘奪,用心至深,積慮至切”。此書同年12月修訂再版,1907年1月增訂發行第三版。時年清政府農工商部通飭各省礦務、商務界購閱,學部批準此書為中學堂參考書。此書雖為合著,但體現了魯迅對地質科學有著深入的研究并做出了豐碩的成果。
學醫到棄醫
少年魯迅經歷過父親生病給他帶來的痛,諸如用原配的蟋蟀一對、經霜三年的甘蔗、破鼓皮制成的藥丸等做藥引,現在看來簡直是莫名其妙。中醫的巫術使他痛恨不已,認為“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于西方醫學的事實”。魯迅在南京求學時,就已經接觸到醫學書籍如《全體新論》和《化學衛生論》等,那是他向往讀到的,因為這是魯迅的一個理想。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
1904年9月,魯迅進入地處日本東北部的偏僻小鎮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習醫學。課程有解剖學、組織學、物理學、化學、倫理學等,外語是德語。老師是藤野嚴九郎,教解剖學理論,敷波教授教組織學理論。魯迅在這里學習是很刻苦的,因為沒有教科書,聽課和記筆記必須特別用功。敷波教授講課用的是拉丁文和德語,背記起來難度就更大。魯迅上課從不遲到,藤野先生對他也特別關心,他記的筆記藤野先生從頭到尾地加以批改,連文法的錯誤都一一改正。他跟藤野先生學完了骨學、血管學、神經學。魯迅說:“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第一年的學習成績平均為65.5分,在總共142名學生中名列第68名,屬于中等的排名。第二年的學習又增加了解剖學實習、組織學實習、細菌學、生理學、病理學、診斷學、外科及藥物學等科目。魯迅在學習期間,參與解剖過二十幾具尸體,許壽裳說:“他的學醫,是出于一種尊重生命和愛護生命的宏愿,以便學成之后,能夠博施于眾。”
1906年初,魯迅在仙臺醫專的這一學期沒有學完,在一次微生物學的課上,魯迅看到了播放日俄戰爭的幻燈片:
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件事給了魯迅很大的刺激,他曾寫道:
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這年3月,魯迅棄醫從文,走上文藝救國之路。
藤野嚴九郎
1904年9月,魯迅到日本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習醫學,老師是藤野嚴九郎,課程有解剖學、組織學、生理學等。魯迅的學習是很努力的,從現在保存在魯迅博物館的魯迅的醫學筆記中,可以看到魯迅學習的認真,他手繪的解剖圖簡直就像印刷的線條畫,一絲不茍。但他的學習成績僅在中等,第一學年的考試總成績排在全班140名同學中的第68名。由于學校考試十分嚴格,全班有30人因成績不及格而不能升級。因此魯迅受到了猜忌,學生會干事檢查魯迅的講義,并有匿名信舉報魯迅能有這樣的成績是因為藤野先生在講義上做了記號,因而預先知道了題目。魯迅把這事告訴了藤野,班長鈴木逸太郎也向藤野做了匯報。藤野先生說:“沒有這樣的事!”后來事情被平息了,這事使魯迅受到了很強烈的刺激。后來魯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回憶:“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一個人,只有自強才是真正的強大。妒忌一定是不夠強大的人的心理。
藤野先生是個在教學上很嚴謹的老師,同時他的教學方法也很獨特。魯迅在回憶散文《藤野先生》之外還講過一個故事:有一次測驗骨骼系統,他把四肢的骨頭擺放在講臺上,然后向學生們提問:這是左臂骨還是右臂骨?這當然考驗學生的識別骨骼的能力,會帶來五花八門的回答。實際上,他在臺上擺放的那塊骨頭即不是左臂骨也不是右臂骨,而是一段腳脛骨。藤野先生的目的是訓練學生們獨立思考和觀察的能力。教師的教學方法各有不同,藤野先生的確是一名好的教師。
嗜書·退稿·辦雜志
魯迅在東京讀書時博覽群書,買書是他最大的開銷。神田一帶的舊書鋪、銀座的丸善書店是他常光顧的地方。由于讀書愛好面很廣,常常逛完書店即錢袋空空,說:“又窮落了!”有一次他從東京到仙臺,買完車票后只剩銀幣兩角和銅板兩枚了,因為學費馬上會由公使館寄達學校,他就大膽買了兩角錢的香煙上了車。車到某站后上來一大堆人,座位沒有了,魯迅見一位老婦人上車便起身讓座。婦人很感激,開始聊天,并送給他一大包咸煎餅。他大嚼一通,覺得口渴了,到了下一站,便喚買茶,但忘記囊中已羞澀,只好對賣茶人支吾了一聲不買了。可好心的老婦人以為他沒來得及買,所以到了第二站就急忙為他代為喚茶,魯迅只好推說不要了。于是老婦人買了一壺送他,魯迅口渴,一飲而盡了。
魯迅在日本時開始做文章寫稿子,自己認為寫得不錯,就寄到上海商務印書館投稿,然后等待發表,可等來的卻是原封不動的退稿。魯迅并不灰心,繼續寫文章投給商務印書館,但不久又退了回來,而且附了字條,說這樣的稿子不要再寄去了,這使魯迅感到失望。但他仍不灰心,還是寫文章寄去。后來魯迅翻譯的幾本書陸續出版了,回國以后又到北京工作,商務印書館也要出他的著作了。終于,魯迅成為中國現代史上的偉大作家。堅持不懈是魯迅的性格,也是成功路上的必須要有的一種精神。
1907年夏,魯迅從仙臺回到東京,并決定籌辦《新生》雜志,目的是“轉移性情,改造社會”。雜志的名字《新生》意即“新的生命”。當時在日本還沒有由學生辦文學性刊物的,留學的學生只重法政和理工,文學性刊物不被重視,甚至許多人都以為這名字是剛新入學的學生之意。魯迅的創意是一個創舉。最初參與創辦《新生》的有魯迅、周作人、許壽裳和袁文藪等人。魯迅為辦這個雜志付出了很多心血,專門印了許多稿紙,第一期的插圖也由魯迅選好,是英國19世紀畫家瓦支的油畫《希望》,畫中是一個詩人蒙著眼睛,手里抱著一把豎琴,跪在地球上面。許壽裳曾回憶說:
出版期快到了,但最先就隱去了若干擔任文稿的人,接著又逃走了資本,結果只馀下不名一錢的三個人。這三個人乃是魯迅及周作人和我。這雜志的名稱,最初擬用“赫戲”或“上征”,都采取《離騷》的詞句,但覺得不容易使人懂,才決定用“新生”這二字,取新的生命的意思。然而有人就在背地取笑了,說這會是新進學的秀才呢。我還記得雜志的封面及文中插圖等等,均已經安排好好的,可惜沒有用。
(許壽裳《魯迅印象記》)
這個“逃走了資本”的人就是袁文藪,一開始,魯迅非常看重他,他們在東京談得很好,袁要去英國,說好一定寄來出版的費用和稿子,但他一去就音訊全無了。這個雜志最終沒有辦成,但他們所作的文章或譯文后來多在《河南》雜志或后來結集的《域外小說集》中發表了。
暗殺行動·母親·原配夫人
光復會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團體,又名復古會。1903年冬由王嘉偉、蔣尊簋、陶成章等人在東京醞釀協商。1904年11月,光復會在上海成立,推蔡元培為會長,陶成章為副會長。宗旨為“光復會宗旨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主張除文字宣傳外,更以暗殺和暴動為主要革命手段。魯迅說他曾經加入過光復會,并曾經被命令去進行暗殺活動。但魯迅說,我可以去,也可能會死,死后丟下母親,我問母親怎么處置。他們說擔心死后的事可不行,你不用去了。這故事說明:一,魯迅也很重孝;二,魯迅處理問題很冷靜;三,魯迅考慮問題很全面。如果魯迅那時因行暗殺行動真的死了,就沒有后來的魯迅了。
魯迅在日本讀書,家里傳言說他是新派人物,擔心他可能不拜祖先,反對舊式婚禮,又傳言他在日本娶了老婆,于是急急火火地催促他回國,有時一天來兩次信,魯迅因為生氣和煩躁搞得有點神經衰弱了。后來家里又打來電報,說母親病危了。魯迅沒辦法,只好回國,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結婚的布置都已停當,只等他回來做新郎了。在舊中國,由家長給孩子包辦婚姻是天經地義的事,悔婚是不行的。魯迅的母親急于給他成親,也是出于無奈。魯迅不忍違背母親的意愿,于是犧牲了自己的意志,與朱安結了婚。兩三天后,他又睡到母親床邊的一張床里。婚后第四天,便回日本去了。魯迅后來說:“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無論如何,魯迅還是一個孝順的孩子,在婚姻大事上盡管違心,還是聽了家長的話。可見孝與幸福并不是一回事。
朱安比魯迅大三歲,身材矮小,不識字,小腳,會烹飪,會做針線活,性格溫順。周作人說朱安“極為矮小,頗有發育不全的樣子”。1906年7月6日魯迅與朱安結婚,那年魯迅25歲,在舊中國要算是晚婚了,婚后魯迅對朱安并沒有產生愛情。1936年魯迅在上海去世,朱安又在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用丁香與棗樹點綴的四合院中,陪伴并送走魯迅的母親。1947年,朱安經過了41年的漫長無愛的婚姻生活后離世。
(作者系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員)